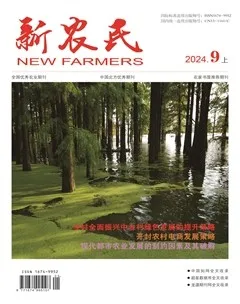积极老龄化视域下农村留守老人媒介素养分析
2024-10-12曾家淇黄可曾杰尹罡
摘要:为了响应国家积极老龄化的号召,探讨了农村留守老人的媒介素养状况及其受影响情况。通过走访调查、深入访谈和文献整理等办法,详细分析了农村留守老人的新媒介使用热情、媒介使用工具、媒介使用能力、信息甄别能力,以及是否科学使用媒介5个方面的现状问题。结果表明,目前农村留守老人的媒介素养普遍较低,对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产生了负面影响;进一步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以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的媒介素养,促进其积极老龄化。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留守老人;媒介素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以及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农村地区的留守老人问题愈发显著。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推进养老产业发展,致力于使每一位老年人都能获得基础的养老服务保障。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媒介技术在老年人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面对媒介环境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要结合媒介时代的发展趋势和政府的支持政策,深入研究农村留守老人的媒介素养问题,为推动农村留守老人的积极老龄化提供有效的路径和策略。
1 文献回顾
1.1 农村留守老人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被留在家中,面对着生活照料、心理健康等多重挑战。本项目根据文献整理,将农村留守老人的概念界定标准确定为:(1)拥有农村户籍,60 周岁以上;(2)子女及子女配偶户籍仍在本地,但长期在外务工,有一定的经济支撑;(3)老人独居或夫妻居住,或与孙辈居住,且具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和行动能力,以足够支撑其进行基本休闲活动。
1.2 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一词最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F·R Leavis和Denys Thompson合作出版的《文化与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中所提到的“文化素养”,用来教育受众抵制传媒文化,汲取经典文化的力量,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重视培养个体对于媒介的批判性辨识能力。Rubin[1]提出一个三维媒介素养框架:能力、知识和理解,旨在强调信息传递的方式、接收者对于信息的认知过程以及他们对信息进行理解和判断的能力。在我国,媒介素养的研究始于1990年末,卜卫教授率先系统地介绍了这一概念,2001年,刘晓红和卜卫明确指出,媒介素养就是人们对于媒介如何进行使用的能力。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介素养不应只停留在对繁多信息的判断能力上,还应该包括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2]。张志安等[3]认为媒介素养应包括个体对各种媒介内容的理解、批判分析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以改善个人生活、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能力。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及其对老年群体的影响逐渐加深,学界对媒介素养的关注点也逐渐转向了老年人群。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媒介,新兴媒介在老年群体中始终占据较小地位。从数字鸿沟的角度来看,老年人提升媒介素养主要有接入沟、使用沟、知识沟这三大鸿沟[4]。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诸如“老年网瘾”“短视频养老”等现象也逐步抬头成为社会的关注点[5]。尽管我国老年群体在数字接入方面已有所进步,但其整体信息意识仍然较为薄弱,网络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因此,加强对中老年人的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势在必行,不仅要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化生活,更要引导其科学理解媒介和正确使用媒介[6]。
尽管全球研究者对于媒介素养的定义仍存在分歧,但其普遍认可的核心内容是相似的。迄今为止,最为广泛引用的定义是来自1992 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所提出的:媒介素养是指个体面对媒介所传达的各种信息时所展现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创造和思辨等一系列反应能力。更狭义地说,媒介素养包括媒介的使用和接触、媒介信息的处理、对媒介的参与态度和媒介知识的掌握程度[7]。综上所述,本文将从媒介使用热情,媒介使用工具,媒介使用能力,信息甄别能力,科学使用媒介5个角度探究媒介素养。
2 农村留守老人媒介素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新媒介环境的融入热情不足
农村留守老人因居住环境相对闭塞,对新媒介缺乏了解,且过去积累的经验均在新媒介环境下遭遇失声困境,使其觉得新技术难以掌握,因而有较强的畏难情绪。此外,由于知识和体能限制,农村留守老人在新事物的接收上有较大的无力感,加之社会普遍存在“年龄歧视”和“技术至上”的观念,导致他们不仅没有直观感受到新媒介带来的好处,反而逐步感到被边缘化,进一步打击了他们的媒介融入热情。
2.2 新媒介工具的接触率不高
信息基础设施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留守老年人对互联网的接触率和使用率。受基础设施匮乏等条件限制,农村留守老人使用的媒介工具大多仍停留在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上,能够使用手机、互联网等新兴媒介工具的农村留守老人总体较少。尽管有老人想接触新媒介,但常常受限于当地信息基础设施条件和自身经济能力,难以承担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费用,导致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率较低。
2.3 新媒介使用的能力鸿沟难以跨越
互联网技术属于信息时代涌现的新兴媒介,需要学习和接收的新事物很多,由于老年群体身体机能和认知能力的衰退,复杂的网络页面和繁琐的操作过程对于农村留守老人来说都是莫大的挑战。此外,社会各界在新兴媒介上对农村留守老人这一弱势群体的需求关注一直较少,缺乏适老化技术和内容,因而农村留守老人的媒介使用能力也难以提高,与新媒介环境之间的“数字鸿沟”也就愈发明显。
2.4 新媒介信息的自主甄别素养较低
在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虚假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而农村留守老人属于互联网下的弱势群体,无法对信息进行主动检索和验证,对各类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只能被动接受。加之其缺乏自主甄别信息真假的能力,极易成为网络诈骗的受害者,甚至成为各种谣言和虚假信息的传播者,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巨大的财产和精神损失,极大削弱农村留守老年群体互联网媒介使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5 新媒介工具的精神作用被异化
互联网等新兴媒介本应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但研究显示,媒介工具的使用已经在少部分农村留守老年群体中出现异化趋势,老年人在上网时可能会因追求心理慰藉和消磨时间而过度依赖虚拟网络空间,有沉迷网络世界虚幻美好之中而无法自拔的风险[8],过度依赖电视和手机等媒介,缺乏适时的休息和自控能力,使得其身心健康受损,甚至也因为过分关注媒介使用而减少了和身边亲友的交往,偏离了利用媒介工具改善晚年生活的初衷。
3 农村留守老人媒介素养提升对策
3.1 破除农村留守老人的畏难心理屏障
针对农村留守老人对新媒介环境存在的畏难情绪,政府应广泛动员社会各界践行“积极老龄化”理念,并消除社会对老年人的年龄偏见和技术偏见。媒体应展示农村留守老人更多积极、活泼的媒介形象,增强社会对其接纳度,进一步激发他们对融入互联网的信心和热情。此外,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应定期举办相关宣传讲座,以更接地气的方式向老年人普及互联网的益处。同时,在村委会内开设心理咨询服务,解决村内老人在使用新媒介时的心理障碍。
3.2 营造浓厚农村数字学习氛围
为实现农村现代化发展,必须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化程度。当前,我国农村数字化水平落后,应尽快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使更多农民接触互联网。为此,政府、村委会应为其提供设备和技术支持,如为老人提供免费电脑、手机或技术培训,建立“数字角” “数字课堂”等,促进老人交流和学习新兴媒介;同时,要鼓励在外的年轻一代通过网络与家中老人保持联系,从而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
3.3 推动新媒介与农村留守老人的双向适应
农村留守老年群体媒介素养的提升不仅需要老年人“适新”,也需要新媒介“适老”[9],通过双重合力帮助他们跨越“数字鸿沟”。在家庭层面,子女应积极鼓励老人使用新兴媒介,通过“家庭反哺”帮助其学习新媒介,增强代际沟通的同时也能提升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技能。在社会层面,各基层组织应设立老年数字教育活动中心等可供村内留守老人学习新媒介的平台。同时,技术的供给端也应主动“适老”,在开发各类媒介软件时,同步提供“老年模式”,简化操作页面,提高各类新媒介产品及技术的适老性。
3.4 稳固老年群体媒介信息安全防线
政府应出台相关法律严惩网络诈骗者,肃清网络环境,以提升农村留守老人媒介使用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各类软件的管理平台和监管部门也有义务通过建立信息筛选机制,最大限度抑制各类虚假信息的传播。此外,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也可以通过定期在村内举办防诈骗安全讲座等方式,唤醒农村留守老人信息安全防范意识,传授虚假信息识别方法,帮助他们自主提高信息甄别能力,稳固信息安全防线。
3.5 减少老年群体新媒介过度依赖
随着新媒介深入农村,媒介作用的异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针对此问题,首先可以在网络平台建立防沉迷系统,利用技术手段限制老年群体媒介使用时间。其次,建立老年电子监督系统,记录并监控老年人媒介使用情况,号召乡村干部和志愿者定期与其交流,以确保他们得到适时的监督和引导。最后,提倡制定家庭内部媒介使用规则,通过家庭监督,合力帮助老年人自主控制媒介使用时间。
3.6 稳固扶持媒介素养新发展
政府需强化对媒介素养教育相关部门及民间机构的法律支撑,以推进老年人媒介素养教育。地方政府可带头成立专门机构,建立全国性教育网络,并将媒介素养纳入终身教育体系,通过立法确保学习权利,激励各类社会资本投入老年教育[10]。同时,政府要考虑设立“农村留守老人媒介教育基金”,对表现优异者给予奖励;为鼓励生产“适老型”手机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对购买者实施财政补贴,降低其经济负担,助力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
4 结语
本文基于老龄化视角通过实地调研的方法分析了当前农村留守老人这一特殊群体在媒介素养方面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提高留守老人媒介素养的相关对策,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是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拓展和改进。首先,在研究方法上,由于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研究样本主要集中在益阳地区,范围狭小,未能全面代表全国农村留守老人的媒介素养状况。同时,研究主要依赖于访谈法和问卷调查,缺乏定量分析和实验验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主观偏差和解释偏差。其次,在研究内容上,本文虽揭示了农村留守老人媒介素养现存的问题,但在如何结合个体和地方差异提供个性化、针对性教育方面仍缺乏普适性。另外,学界内对媒介素养的定义尚不统一,且由于本文作者知识有限,可能存在对该概念的误解或混淆。最后,在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上,本文虽然针对农村留守老人媒介素养的现状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和策略,但这些建议的可行性和实用性,还需要进一步地实地试验和长期观察加以验证。此外,对于媒介素养提升后的效果研究,本研究也暂未涉及。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农村留守老人的媒介素养问题日益凸显。为改善这一状况,要从多个方面着手,通过科学探究、构建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和提供全面的媒介素养培训,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同时,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的媒介素养水平,也是现代社会“积极老龄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社会各界应继续关注留守老人群体的媒介素养问题,深入探讨农村留守老人媒介素养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并注重研究结果的实际应用和推广价值,让更多身处农村的老年人也能够掌握新科技,丰富其生活,并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为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 Rubin,A.M..Media literacy[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8,48(1):3-4.
[2] 张冠文,于健.浅论媒介素养教育[J].中国远程教育,2003(13):69-71.
[3] 张志安,沈国麟.媒介素养: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J].新闻记者,2004(5):11-13.
[4] 李明菲.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数字融入困境与支持对策研究——以四川省三所养老机构为例[D].昆明:云南财经大学,2023.
[5] 罗程琳,李玥冉.数字失声: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与媒介素养[J].新媒体研究,2022,8(17):78-82+114.
[6] 周葆华,陆晔.中国公众媒介知识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对媒介素养一个重要维度的实证分析[J].新闻记者,2009(5):34-37.
[7] 张建芳.城市老年人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与提升策略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8.
[8] 武文颖,朱金德.弥合数字鸿沟:老年群体数字化生存的困境与突围[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3,44(1):162-169+213.
[9] 许蓓蓓,邹宝元.新媒体与老龄人口双向适应路径探究[J].新闻世界,2021(12):85-88.
[10] 胡文静,李梦涵,王晓珊.“银色浪潮”下的老年人新媒介素养分析[J].东南传播,2019(2):11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