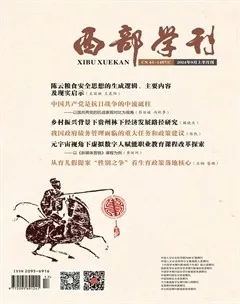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双重境界
2024-10-10朱贺炜
摘要: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主张幸福是人所追求的至善,是合德性的灵魂的实现活动,沉思是最大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对德性进行二元划分,认为“理智德性”,特别是其中的明智和智慧是实现幸福的关键因素,就此明确幸福的双重境界:一种是通过明智引导的,灵魂实践德性的活动;另一种是源于智慧,体现为纯粹理性的沉思。这两者虽在具体表现上不同,实则具有内在的同一性。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的双重境界进行深度分析,揭示个体德性修炼与公共领域道德行为实践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强调了知识探求与智力活动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帮助现代人在道德德性和智性追求之间找到平衡,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幸福。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幸福;德性;思辨
中图分类号:B502.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4)17-0152-04
The Dual Realm of Aristotle’s Conception of Happiness
— A Textual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Nicomachean Ethics
Zhu Hewei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136000)
Abstract: In the Nicomachean Ethics, Aristotle asserts that happiness is the supreme good that man seeks, the activity of the soul’s realization of conformity to virtue, and contemplation is the greatest happiness. Aristotle makes a dualistic division of virtue, considering “rational virtue”, especially wisdom and intelligence, to be the key factor in the realization of happiness, and in this regard makes clear the dual realm of happiness: one is the activity of the soul in practicing virtue, guided by wisdom; the other is contemplation, which originates from intelligence and is embodied in pure reason. Although these two are different in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they are intrinsically identical.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Aristotle’s dual realm of happiness, we reveal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 virtue cultiva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ethical behavior in the public sphere, and at the same time emphasize the supreme value of intellectual inquiry and activity, helping modern people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ethical virtue and intellectual pursuits, and to promote the overall well-being of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Keywords: Aristotle; happiness; virtue; critical thinking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作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受到密集研究和讨论的伦理学著作之一,这部著作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其作为历史经典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它成为现代德性理论讨论的核心。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以幸福是人生最高的目的为出发点,形成了其独特的伦理学体系,其第一卷和第十卷对于“幸福”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然而学界出现了亚里士多德对幸福概念的论述存在某种前后断裂的声音,主要的分歧集中在:幸福是由道德明智作用的一种“合德性的灵魂的实现活动”,还是由智慧作用的纯粹思辨的一种沉思活动。对此,亚里士多德到底持怎样的态度?二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从中能够得到哪些启示?想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是要追溯文本。
一、《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体现
在古希腊哲学的语境中,“幸福”一词所传达的含义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愉悦或是短暂的喜悦感。要深入理解这一概念,需从语源学角度了解“eudaimonia”这个词。“eudaimonia”的前缀“eu”翻译为“好”或“良好”,daimo是神灵的意思。当古希腊人在谈论“eudaimonia”时,他们实际上是指一个人的一生或生活状态处于一种最理想的、有益的状态,得到神灵的青睐和指引,体现了完美的人性品质。这一点反映出当时哲学家认为的“幸福”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感受,而是一种与伦理德性相结合、可追求的客观境遇。这种哲学思考在中国文化中也有所体现,人们通常会用“吉星高照”或“鸿运当头”来表示人生处于一种顺利和成功的状态,好运和吉祥的象征同样融入了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说:“就其(幸福)名称来说,大多数人有一致的意见。无论是一般大众,还是那些出众的人,都会说这就是幸福,并且会把它理解为生活得好或做得好”[1]6。因此,在eudaimonia这个古希腊词语的理解上,对译成happiness也许不如well-being或prosperity来得更加准确[2]35-37。
既然古希腊人常以“幸福”作为人生的目的,那么亚里士多德究竟认为何为幸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初始章节,他提出了对善的探究,这可能为理解其关于幸福的见解提供了方向:“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善为目的。所以有人就说,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1]1这里明显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与他的导师柏拉图关于“善的理念”所持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善”的概念:一是具体的善,即那些作为明确目标的善;二是最终的善,即作为所有其他较低级目标的包容体的善[3]。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善的理念”显得过于抽象且无法触及,而真正的幸福是体现于现实生活之中的,故而他在伦理学中特别强调“实现活动”,认为活动本质上涉及肉体及灵魂力量的运用。因此,他称“人类的善”即“幸福”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1]20
这里剖析两个概念,首先是德性。德性(aretee)一词是从战神Arees派生出来的,形容体格健壮、孔武有力[2]58。在古希腊,aretee的原初意思并不专指人,而是可以用于一切有功能的东西,只要这个东西将自身的功能发挥得好,就可以说这是有德性的。譬如在《荷马史诗》中,该词对应着“好”,指任何事物的美善和卓越。同样,古希腊的德性除了有功能发挥得好之外,也指使得功能发挥得好的素质与能力。其次,在古希腊哲学中,灵魂(psuchē)是指生命的原则,凡有生命者皆有灵魂,而不只为人所特有。根据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的观点,灵魂是生物的形式,指包括消化生长、欲求、感知、运动以及理性在内的能力。其中,理性能力才是人的灵魂所独有的。“自然馈赠我们的所有能力都是以潜能形式为我们所获得,然后才表现在我们的活动中。”[1]37就此而言,德性自然就包含了由习惯、风化养成的非理性部分,是人的非理性灵魂接受理性的指导和约束,与理性相融合而成的可以遵从理性指导的部分,即“道德德性”,以及作为“潜能”的理性部分,是人的理性思维的能力,是纯粹理性灵魂自身活动的产物,即“理智德性”。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理智德性”,其中重点区分了两种理智德性,即实践的理智和沉思的理智及其对象。简单来说,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心灵哲学框架中,实践理智是在考虑目标和欲望的情境下构建的知识,其域内的真理符合实践目的的要求,并在对事物应如何行动上给出指导。这种真理,尽管仍符合真实性的要求,然而其性质并非静态且绝对的,而是包含着行动的变量和实践的评估,是一种动态的、目的相关的、情境依赖的真实。与之相对,沉思理智的运作超越了欲求的界限,其关注点在于揭示事物固有的、不依赖任何外在目的的真实本质,即事物本质所具有的不变真理,这是一种不涉及行为目的的认知活动。据此,可以洞察到,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拥有双重境界,是由理智德性作用的“合德性的灵魂的实现活动”以及纯粹思辨的沉思活动。
二、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双重境界之内在同一性
在细致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时,可以揭示一种看似存在的逻辑矛盾,在作品的早期章节中,亚里士多德明确强调实践活动作为实现幸福生活的核心途径,并且致力于展开深入的剖析以阐明实践活动与幸福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是,到了著作的第十卷,他似乎转变了立场,提倡人应通过理性的反思和沉思来达成幸福的境界。这两个不同的论点可能反映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本质的多维理解,或者表明其哲学体系中存在着需要进一步阐释的概念张力。在结合上文对于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相关内容的阐述后,我们可以洞悉这看似矛盾的两种观点在实质上并不矛盾,且具有内在同一性。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以亚里士多德对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实践与沉思的关系的理解为出发点进行解答。上文说到,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体系中对德性的分类提出了一个二元结构,将德性区分为伦理德性和理性德性。伦理德性与个体的欲望和情感相对应,而理性德性与人的理性思维能力相联系。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对理性德性进行细分,强调了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这两个方面。实践理性的完善表现为“明智”(有时被译为“实践智慧”),强调的是在行动和决策中展现出的精辟与适宜性;理论理性的德性则体现为“智慧”(有时被译为“哲学智慧”),这涉及对知识的纯粹追求和理性的自我实现。
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德性和明智是不可分割的,道德德性必须有明智的指导,因为道德德性听从的理性是明智:“明智似乎离不开道德德性,道德德性也似乎离不开明智。因为,道德德性是明智的始点,明智则使得道德德性正确。”[1]337
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将“智慧”作为所有理性智慧的总体把握,位于最高层次,与“明智”相比较,文本中有明确的结果:“德性使我们确定目的,明智是我们的选择实现目的的正确的手段。然而,明智并不优越于智慧或理智的那个较高的部分。”[1]208由此可见,“智慧”优于“明智”,且这个位于最高层次的“智慧”服务于沉思的理性。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体系中对沉思活动进行了最优美地推崇,将其定位为一种超越实践活动的更高层次的行为。
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具有由明智作用的一种“合德性的灵魂的实现活动”以及由智慧作用的纯粹思辨的一种沉思活动这种双重境界,从亚里士多德的视角窥探可知后者比前者更为高级。然而亚里士多德又向我们明确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事实上产生一种结果,即幸福。”[1]204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实践活动可以称之为“不完全完善的”幸福,而沉思活动则是“最完善的”幸福。沉思优于实践,但并不与实践相矛盾,二者只是在作用方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先是着重于活动和实践的方面,并指出这些活动在塑造德性和实现幸福中的重要性。而在后面章节中,他似乎将重点转移到了沉思和理论层面,提出沉思乃是获取幸福的至高路径。这种方法论的转变可能表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中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两个方面的综合与互补,并展现了如何在实践与理论之间找到幸福生活的平衡。
三、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双重境界之思想启示
应对当今复杂的问题尤其是价值观的挑战,现代德性伦理学尤为重要,它虽然以多种形式发展,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伦理学模式被看作是理解和解释人类道德行为和幸福的重要框架,并被广泛认为是迄今为止德性理论的最好代表。亚里士多德通过对实践、道德美德和幸福的全面探讨,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道德哲学体系,深入探究了人类伦理行为的本质和价值观。德性伦理学讨论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可以直接基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著作,或者是从亚里士多德的思路出发来考察,从而更好地解决当前的伦理问题。因此,《尼各马可伦理学》在现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为伦理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深刻和持久的思考,同时也为理解幸福、道德行为和个人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指导。
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双重境界影射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即实践生活和沉思生活(或称之为理论生活),这两种生活方式体现了该幸福观的“双重”特性,实践生活侧重在个人和公共领域的道德德性实践,而沉思生活则强调知识追求和智性活动的至高价值。
第一,亚里士多德通过“明智”作用的实践生活主要强调个人的幸福不仅仅是内心的一种感受,而是通过积极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行为来实现的,他认为,这种德性的修养并非一蹴而就的,需要个人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次行动中不断实践,通过反复练习和自我反省而逐步培养和巩固。
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生活让我们认识到,幸福不仅仅是个人的心理状态,也与个体在社会中的参与程度和行为质量有关。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即幸福是通过个体在社会角色中的积极行为和社会实践中所积累的德性而成就的。当代学者可能会将实践生活的概念链接到公民参与、社会责任乃至社会资本的构建上。幸福被视作是与他人互动、共同面对挑战和努力改善社会状况时所产生的共鸣和成果。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可以进一步指导我们理解:个体不应仅仅关注物质上的满足,还应该追求通过贡献社会和提升公共利益的道路实现自我完善和满意。因此,实践生活的概念对现代社会有着深刻影响,它鼓励人们在个人层面上进行德性修养,同时在公共生活中积极参与,既追求个人的内在发展,也关心和促进社会整体的福祉。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既实现了与他人的和谐共处,也实现了自身的最高幸福——即在有限的生活条件下的最佳状态。
第二,经“智慧”作用的沉思生活则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另一种观点,即沉思生活是与人类的理性本性最为契合的生活方式,因为它致力于认知上的纯粹追求,与完善和提升人类理性相关联。哲学思考、科学研究、数学推理等都是沉思生活的表现形式,因为这些活动不为任何实践目的所限制,而是出于本身的价值和对知识的爱好。这突破了日常生活的实际操作和社会事务,转向理智与思辨本身作为生活的中心。沉思生活的核心是对知识的渴望,尤其是对最高形式知识的探求,即对真理和原理的理解,这种知识与实用和技术知识形成对比。
在当代语境中,沉思生活显得尤为重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理性思考与创新的重要性愈发突显。持续地学习、批判性思维、对科学真理的探索以及哲学和艺术上的深入研究,都是现代人实现个人潜能和内在生活丰富的途径。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生活给予现代人深远的启示,那就是:虽然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可能带来某种程度的满足感,但真正持久的幸福和内心的宁静来自于理性的培养和智慧的追求。在知识和理性的激励下,个体能够实现对自我的超越,摆脱物质欲望的羁绊,触及精神性生活的深层可能。学术界继续探讨亚里士多德的沉思生活概念,将其与现代人类行为、决策理论以及心理幸福感研究相联系。其中,特别关注如何在今天这个物质迅速发展和信息爆炸的时代维持和发展理性思维的清晰度和深度。研究者们探索这种理论活动如何影响人们对生活意义的体验,以及它如何为人类社会带来长期和持久的益处。在个人层面上,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论鼓舞了无数寻求真知与智慧的人,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日常生活中,理论探索都成为实现个体卓越的关键路径。
四、结语
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中说:“现阶段最要紧的,是构建文明、理智与道德生活能够在其中历经已经降临的新的黑暗时代而继续维持下去的各种地方性的共同体形式。”[4]在构建这一“共同体形式”的过程中必定会发生规则与规则的矛盾与冲突,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依然要诉诸于人的德性。亚里士多德对于在实践活动中人们欲求绝对和同一的反对,强调必须具有实践智慧,与具体的境况相结合才能达至幸福[5]。因此,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充盈着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的时代,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作为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依然要与当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实现其更具现实意义的价值。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余纪元.亚里士多德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刘素民.在分别幸福境界中由“善”达及“存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之幸福论及其思想启示[J].学术交流,2021(11):5-17,191.
[4]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M].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35.
[5]丁万华.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6.
作者简介:朱贺炜(1997—),女,汉族,山东费县人,单位为吉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伦理学。
(责任编辑:冯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