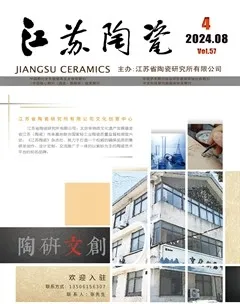当代陶艺中技与艺的关系
2024-10-06张蕴文
摘要当代陶艺创作是展现自我观念和技术的媒介,是艺术家和工艺的对话渠道,当代陶艺创作也是对技术和艺术有着双重要求的艺术门类,厘清艺术和技术的关系则显得至关重要。本文以英国艺术家克莱尔·托梅为例,分析其陶艺作品对于技艺关系的探讨,借此观察个体审美在技艺中的呈现。
关键词技术与艺术;当代陶艺;克莱尔·托梅
1当代陶艺的发展概述
当代陶艺立足于传统陶艺之上,与之最大的区别在于对陶艺概念的界定,其不仅仅局限于材料这一概念,而是随着艺术家个体性的增强,范围逐渐扩大,并与其他材料相互融合,亦将陶当作一种媒介,传达其个人的观念、思考和认知。艺术家通过火让泥土的柔软、空间等形式在手中变成永恒,以此来抵御时间的侵蚀。陶艺是一种媒介,以人类参与讨论世界的一种物质存在于我们周围,带给人们有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思考。
20世纪初期的奥蒂斯革命,国外的部分著名陶瓷艺术家在创作中加入新的尝试,赋予了陶瓷新的视觉形式,转变了陶瓷的工艺品概念,从此陶瓷进入了个性化创作的时代,创作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对传统形式的反叛,有的是综合材料的嫁接运用,有的受到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冲破了长期以来陶瓷艺术远离纯艺术的状况,陶瓷材料成为新的承载艺术家情感、观念的载体。中国的陶艺启蒙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最初的发展与西方的陶瓷革命并没有太大的关联,之后的相关概念则是脱胎于陶瓷革命中某些词语的解释,多元化的面貌开始出现,涉及的题材也多种多样,有自我反思、文化叙事、社会批判、基于日常经验的实验性突破等。传统陶艺多是以实用为目的,具有严格的技术分工和技术规范,且具有极强的工艺性,在当代陶艺的语境下,这种以实用为目的的制作和审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作者主体性的发挥。当代陶艺不仅在外观上改变了以实用为目的而进行设计的造型形态,且利用传统陶艺的技巧来达到某一技术的极限延伸和审美形式的展现,不仅改变了其审美特征,还改变了其实用目的,使其逐渐变为一种纯粹的艺术创作,是实现个体精神价值的媒介。总的来说,传统陶艺是历代陶艺工匠们集体智慧的瑰宝,当代陶艺则是个体创作者精神世界的结晶。
2对技与艺两者关系的思考
“技”是指解决问题的方法及原理,形成新事物或是改变旧事物功能、性能的方法;“艺”是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发挥其独有的方式认识世界。在传统工艺中,“技术”是指手工艺制作的流程,包括材料选择、工具运用等,“艺术”则指器物外观的视觉体验。
技术与艺术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哲学家冯友兰在其《新理学》中说:“旧说论艺术之高者谓其技进乎道,技可进于道”,意思是技术达到高超境界之时就可以与道同在,先贤已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案,但是在当前时代语境下,创作者们不断利用新的技术、新的材料打破传统的工艺带来的桎梏,创作的思维方法也在不断地更新前进,当下部分制作工艺的制作手段已经被机器、人工智能所替代。技术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加速进程以及达到理想的效果;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是创作者表达情感、观念的载体。技术和艺术分别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发挥作用,在基本的生存问题得到解决后,人们对于艺术品的不断追求,收藏家收藏艺术品是对于相同精神世界的追求,艺术家创作艺术品是对于个体精神世界的输出,画廊贩卖艺术品是精神世界的构建。人们对艺术品的要求不断升级,创作者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方法来进行创作,由此产生对技术的依赖,被总结、参与到新的艺术创作中。中国古代对火的运用使得陶变成了瓷,最开始的烧成技术是平地堆烧,烧成完全是随机的,将晾干的陶坯堆在平地上,覆盖柴草点火燃烧,燃尽熄灭即可,这是全人类古老也是延续时间较长的陶器烧成工艺。新石器时期先后出现了横穴窑和竖穴窑,竖穴窑比横穴窑更为完善。到了商代,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北方以馒头窑、南方以龙窑发展为主。随着技术的进步,窑炉的烧制技术越来越成熟,发展到清代出现了古代窑炉技术集大成的镇窑,到了现代社会出现了以电、天然气为烧制材料的电窑、气窑,技术进一步成熟,极大地拓展了陶瓷创作的表现手法和表现空间。
19世纪中期,达盖尔摄影法问世,该方法在一个平面上以微妙的细节永久地固定具有精确色调的外在世界形象,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的画家们在创作新的绘画形象时都考虑到由摄影媒介所带来的真实印象。摄影对绘画的冲击较为直接、明显,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人们所创作出来的新的绘画形式摆脱了摄影的冲击,并且摄影技术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具有审美性的艺术,一直到今天传统的技术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变得更加丰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更加多样化,潜移默化地介入到了艺术的系统之中,艺术不再局限于架上绘画,也不再是只能在美术馆中才能看到,艺术作品与观众也能够更进一步地交流,学科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技术与艺术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当然,艺术与技术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场景的需要、目的的不同、使用人群的要求来变化的。艺术是表达情感的载体,技术的进步可以作为一种催化剂,但当技术凌驾于艺术之上,一件工艺品没有手工的参与,制作过程全部由机器所替代,这样的一件工艺品还能称为艺术品吗?
3以克莱尔·托梅为例
克莱尔·托梅1968年生于英国,工作和生活都在英国伦敦,她是英国的独立艺术家,也是威斯敏特大学的研究员,1991年至1994年在爱丁堡艺术学院学习陶瓷,之后进入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攻读陶瓷与玻璃硕士学位。经过15年的实践,她提倡将工艺与广泛的视觉艺术并立,保持着对于工艺、材料以及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关注,她的实践和黏土紧密相连,黏土是她使用的媒介,她的作品精彩之处在于对陶瓷媒介独特的理解和运用,对工艺与视觉关系的把握使得作品往往呈现出敏感、细腻的观感。
2015年她在约克美术馆创作的作品《Manifest:10 000Hours》体量很大,一系列的平台上放着一堆堆苍白的、整洁的碗,一直延伸到白色拱形木屋顶,这些摇摇欲坠的碗让人感受到一种独立空间的形成,联想到工厂里面10 000小时日夜不停地工作,这些碗是由志愿者、画廊的工作人员、学生和当地团体成员制作出来的,每一个碗代表的是1小时,这个作品探讨了工艺技术与手艺的关系,因为作品的视觉呈现不同,让10 000小时得到量化,进一步让观众思考人和技艺之间的关系、工艺与视觉的关系。在作品《Piece By Piece》中,利用翻模技术探索了收藏对象和观众之间的关系,进而思考到收集如此精美而丰富的陶瓷物品所需要的完整性的深度思考,这些收藏品清晰地展现了几代制造商之间的技能和技术的传播交流,利用翻模技术对这些藏品进行翻模具有其特殊的意义,这些收藏品作为翻模的母模,然后对形态进行复刻,不禁让人思考通过工业化技术制作出来的作品是否具备收藏价值?工业化作品欣赏的点又在何处?对于工业化制作技术的提升在艺术作品中更多的侧重点又是什么?
经过两周左右的时间尝试,作品《Factory:the seen the unseen》进一步探索了工厂生产概念与人类创作过程之间的关系:第一周,一条30米长的生产线、40名工厂员工、8吨黏土、一面墙的干燥架和2 000多件烧制的黏土制品将占据泰特交易所的地板,你可以打卡、加入生产线,学习用黏土工作的技能,你可以用自己制作的东西交换工厂里的茶壶、水壶或鲜花;第二周,生产线停止,工人离开,你将进入一个工厂的背景,现在的工厂成为了一个充满疑问的地方,在现在这个工厂里面代替工业生产的是行业专家的演讲,探求工业生产过程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未来我们对于工厂的需求又是什么?里面有摆放在各处的卡片让你来思考原材料、知识是如何获得和共享的,这些事物的变革又发生在哪里,通过这些事物应用在物质文化和人际关系之间的不同价值体系。艺术家为泰特交易所建造的工厂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工厂,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作场所,它是一个模拟的地方,目的是去对话一个关于我们如何与日常的劳动、价值和交换思想联系起来的。当工厂有生命的时候,它会把我们吸引到它的劳动任务的节奏中,让我们感受到处理材料的魅力,劳动的语言、技能,工艺的重复和知识的发展。在那个多余的工厂里,工人们已经走了,但他们的声音和呼吸还在,机器、材料、长凳都变成了小小的纪念碑,这个空间充满了人的证据,但工厂的整体性却断裂了,一个人类被渴望的空间存在了,工厂的目的成为了一个既失落又潜在的命题。探索围绕生产概念与人之间的关系,克莱尔的作品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通过克莱尔的作品可以窥见她艺术精神世界的一角,了解她对于创作的态度和对于现实世界的反应,从而进一步探讨处理个人表达和对创作手法的巧妙运用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感,艺术与技术谁更占据主导地位可以从她的作品中找寻答案。
4结语
从陶艺创作的角度来说,工艺制作过程的熟练程度固然重要,但技术只是创作中的一部分,如何用技术将所想要表达的观念传递出来,用非日常的方式展示出来。当代陶艺的创作将技术融合进艺术表达,在满足个人艺术创作需求的同时思考如何构建自身创作作品与技艺的关系,对技艺的使用达到何种程度,展现出什么样的视觉感受?由此通过创作进行作者之间、物与人之间、现实与个体生命意义之间的表达。
参考文献
[1]赫伯特·里德.艺术的真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朱乐耕.当代陶艺问道集[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
[3]柳宗悦.工艺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杭间.语焉不详的中国“现代陶艺”——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陶艺的现实和问题[J].文艺研究,2003(1):111-123.
[5]黄岱.技术与艺术关系之辨析[J].艺术市场,2023(1):66-68.
[6]周武.后工业社会语境下的陶瓷手艺[J].中国陶艺家,2007(4):10-15.
[7]方李莉.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新艺术史观——以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为例[J].民族艺术,2013(3):5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