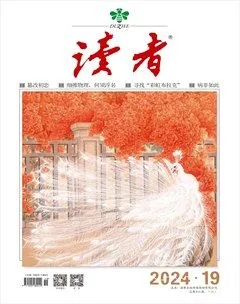病非如此
2024-09-30刘绍华

1
就像一次命运的交会,疾病几乎是同时落在了我和母亲身上。2018年7月,我被诊断为淋巴癌一期,母亲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初期。
在我24岁那年,父亲就是因为胃癌淋巴结转移过世的。从此,我对“淋巴癌”的印象就是它会把人快速带走。当时我还不知道,父亲所患的实质固态瘤转移淋巴和我的恶性血液淋巴瘤不是同一回事,前者一确诊通常就已经很严重了,而后者的治愈率还算高。
那几年,母亲的状况越来越差:煮饭时经常重复加盐;生米刚下锅又四处找米;倒水吃药,走到饮水机前就忘了自己要干吗;经常找东西,咒骂谁谁谁又偷偷进她的房间拿走了什么……但这些变化就像梅雨天,水汽缓缓渗透进来。大家一开始没有警觉,以为这些只是衰老的表现,直到医生的诊断结果出来,那些令人不安的言行才终于有了一个医学解释。
在我治疗的半年时间里,为了预防感染,医生让我回避亲友探视,我和母亲几乎都是通过电话交流。这也成为我心中的一个遗憾,我错过了在母亲失智症初期陪伴她的机会。很多次,我发现她已经忘了我生病的事。
有一次化疗结束,我的白细胞数量明显回升,哥哥带着母亲来住处看我。那时我的新头发长得快,我托朋友买了癌症病人也能用的植物染发剂,染完后,满头的橙红短发让我看起来就像《灌篮高手》里的樱木花道。母亲见到我,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笑嘻嘻地说:“你这么时髦啊,把头发剪得这么短!”
说来也奇妙,母亲和我同时生病后,无论是我和母亲的互动方式,还是讲话的语气,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生病后,只要我跟她见面,我不是抱着她,就是牵着她的手。在我成长的时代,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肢体关系跟现在的很不一样。我的哥哥姐姐不会像我这样理所当然地去抱母亲,但是自从我生病后,我会理所当然地去抱抱她。
随着病情的恶化,母亲逐渐失去了一部分社会性能力。她会忘记洗澡,或者以为自己已经洗过澡。当她失去了洗澡这个能力,我们帮她洗澡时,她会抗拒,要经过一个被哄骗的过程。而我常常是主动扮演哄骗她洗澡的那个人。
2
疾病改变了我和母亲的关系。生病之后,我从自己的生命经验里,开始理解母亲究竟在经历什么。
生病以前,我是一个不怕脏的人,上山下海。我跑过空难新闻,上过“保钓号”渔船采访“保钓人士”,在柬埔寨等国家做过国际发展项目,在尼泊尔陷入过武装暴动的烽火,也曾深入毒品与艾滋病重灾区进行采访报道。
但在化疗期间,我的免疫力受到药物的抑制,身体变得虚弱,我对卫生环境的要求变得严苛,不仅我自己会很重视清洁,来看我的人,我也需要他们重视清洁,不然我会不安心。对不了解病人身体需求的人来讲,他们会觉得我变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在意卫生。
我想起一个画面,是32年前母亲患癌化疗回来的某一天。我当时对这些知识没有了解,也不晓得应该如何应对生病的母亲。母亲进门后,往里看了一眼,她没有直接休息,而是坚持要拖地,我说我来拖,她却不肯。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理解她为什么执意自己擦地板,也不理解她当时脸上生气的神情。等到我住院,朋友带着一大束花前来探望,医生看见花,立刻叮嘱朋友将花移走,还要我在床前贴上“禁止探病”的告示时,我才终于理解了母亲当年回家看见脏乱状况时的恐惧。
化疗药物发挥药效之时,也是副作用让病人的免疫力降到谷底之际。哪怕寻常的细菌、病毒都可能让病人发烧,从而影响治疗进度,甚至引起复杂的并发症。病人不仅要承受化疗的副作用,身心还都可能处于不同于平常的位移中。有一次我牵着母亲散步,她突然问我:“你有没有觉得我走路摇摇晃晃的?”其实母亲走路并没有摇晃,那只是她身体内在的感受。治疗后期,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外人完全看不出来,甚至可能以为是病人的幻觉,但那是病人的真实感受,也说明病人正在辨识体内的信息,并努力稳住自己。
因此,我生病之后,不管母亲跟我讲什么,即便有些时候她可能口齿不清,我都会认真地听她讲,然后猜测她可能想要讲的内容,帮她补充完整。如果不是我自己生过病,我就不一定能那么深刻地理解病人的处境,也不一定有耐心听她说话。那次我做完开刀检验后回家,母亲的病情还算和缓,她还记得我生病的事,大老远地去买鸡,要给我补一补身体。我看着她沉默地忙进忙出,心里真的很愧疚。后来她从厨房里出来,对我说:“妈妈可以,你也可以的。”那一瞬间,我的眼泪立马掉了下来。生病后每当我感到身心下坠时,我都会想起母亲的这句话。
3
我和母亲的病程很不一样,我的病程主要分为两个时期:6个月的治疗期间,身心脆弱;治疗一旦完成,进入康复期后我宛若“新”人。母亲的病程则是可预期地逐渐走下坡路。
和母亲共同生病的这段日子,我既是被照护者,也是照护者。如果说这段旅程教会了我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示弱的美德。
我们常常会以为,示弱是一种投降或依赖,但是我想讲的示弱,是不因循习惯或偏好,而是愿意将自己交托给他人,追求对生命的顺服。在治疗和康复期间,我接受了非常多的协助。对任何愿意向我提供协助的人,我几乎来者不拒。
我也学会了向身体示弱。生病以前,尽管我也定期运动,好好照护身体,但回头看,那些都只是在应付,是用一种外在的知识或概念来告诫自己,要运动、要睡觉、要吃饭。生病之后,我意识到,身体不是工具,我们不仅要喂饱它、清洁它、检查它、修复它,更要学会保养它、安抚它、欣赏它、平等待它。现在即使事情再多,我也不会硬撑,因为我知道这样下去身体绝对会出状况。
很多生过重病的人,无论是对自己生命的认识,还是对自己身体的认识,都会经历重生。
如果生命是一个方程式,那你遭遇了什么,体会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决定了什么,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那个生命品质。只是生过病的人警觉性会更强,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仿佛见过了棺材,被惊吓过,吃过这个苦。
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大家都想追求成功,或者满足各方的期待。在不断应付这些外在的压力时,对身心的照护就很容易失衡。所以,最重要的是怎么跟自己的身心好好相处。
在看待失智症和癌症时,我们常常在第一时间把它们想成很可怕的病症。就它们可能带来的伤害,或者造成生命终止的后果而言,的确是这样,但反过来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的进步——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集体性地活到如此高龄,而长寿不正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追求的吗?
我们在追求长寿,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去接纳这些病症,不要歧视它们,不要对它们那么深恶痛绝,觉得它们不该存在于生命当中。如今它们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种常态。
在治疗的过程中,我经历过很多“闻癌色变”之人的安慰。有一次,两位朋友来探望我,表情凝重地坐在我对面,为了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也为了让自己摆脱沉闷,我只好全程靠着自说自话度过被探望的时间。朋友离开后,我感到疲惫至极。
我们缺乏认识生老病死的生命伦理与合宜应对的方法,整体社会多以为这属于医疗或宗教的范畴。在长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也发现,很少有年轻人会主动关注医疗健康议题,如果有,也多是因为自身或家人的疾病之苦。
我写了一本书,书名是《病非如此》。在真正和疾病打过交道后,我反而觉得,病了,并非一定会怎样。
母亲和我各自独行又并行的这段生病历程,虽然母亲很辛苦,家人照顾她也很辛苦,但是我确实看到了她那些超越刻板印象的变化,也看到了彼此的生命、关系都变得更为圆熟。
人的生命一定是从被照护开始的,人也需要进入照护的角色,才能形成完整的生命照护经验与感受,正如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凯博文在《照护的灵魂》里所说:“人需要照护他人,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我康复之后,走向人生下半场时的体悟。
(大浪淘沙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沈 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