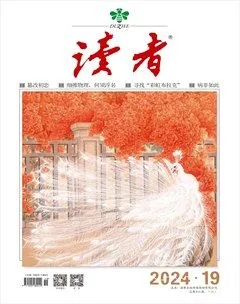《读者》树
2024-09-30钟志红

家乡的大渡河畔,有一片“读者林”。21世纪初,在由读者杂志社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保护母亲河绿色工程”公益事业活动中,四川乐山成为“保护母亲河,共建读者林”的3个项目区之一。
十年树木,岁月如8wounjqm8m8iR+pCVfZo/M5LugfZV5Fdi/pdiHxnQnM=歌。不久前,我再次来到久违的“读者林”,触景生情。昔日那片荒芜的山坡,如今万木吐翠、生机盎然,我却在光阴的催促下,告别风华正茂的年华,走向双鬓染霜的花甲。回首往昔,曾在戈壁植树的场景历历在目,其中也有难以割舍的《读者》情结。
20多年前,下岗潮迭起,我亦不能幸免。因无一技之长,又跨过了35岁的门槛,再就业的机遇始终没有垂青于我。蜗居在家的日子,拮据的生活不停地拷问着我,特别是父母孱弱的背影、妻儿暗淡的眼神,将一个男人的自尊心撕得支离破碎。
那年春节,从新疆返乡的堂弟对我说,国家投入巨资治理西北环境,大力推进治沙造林工程。他劝我节后跟他一起去新疆植树。我别无选择。行前,妻为我收拾行李,将往年订阅的几本《读者》塞入其中,说是为了让我打发旅程中难熬的时光,我却分明感受到她细致的关爱,还有一份期许和勉励。
3月,一场沙尘暴将我们困在屋内3天3夜,本该到来的供给车迟迟没有出现。此时,填补空寂时光的烟酒早已告罄,扑克牌也难以拯救饱受无聊煎熬的我们,唯有狼嗥般的风声,长久地为孤烟大漠伴奏。
烛光下,我无聊地翻阅起已破旧不堪的《读者》,整夜辗转反侧。与我共居一室的甘肃同事,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烟蒂,递给我,说:“还是你会打发时间,可否借书给我一看?”《读者》为我换来了意外的福利,我当然应允。
“这是咱家乡的杂志,全国发行量最大,全国人民都知道的!”甘肃同事惊喜的声音招来了大家的围观和重视。虽然我不知道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文字究竟能给人们带来多少慰藉,但至少在怂恿声中,我没理由不取出所有的《读者》,和同事们分享。
新疆同事舔指翻书,但不影响他全神贯注的姿态;大字不识几个的甘肃同事,目光停留在漫画版面,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从小爱看小说的堂弟低吟“千字文”的卷首语,激发了我的倡议:“大点儿声——要不,每个人都读上一段!”
屋外,“群狼”长啸,大有不吞噬整个世界誓不罢休的态势;屋内,我们或坐在床上,或索性站上桌凳,尽情释放着一板一眼的南腔北调——我可以忽视花前月下的浪漫,但无法忽视捧读《读者》的真实,特别是这些带着朴实本色的“装腔作势”。
我们诵读名人名言,分享幽默笑话。我至今都不曾怀疑,根植在三毛心底的那棵“橄榄树”以及“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诗句,自那时起从字里行间走来,再也没有走出我人生的边境。
虽然,我不知道一本杂志能为我们带来多少乐趣,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为荒烟蔓草的戈壁生活平添了一抹亮丽色彩,给孤寂的人们递上了一份温暖的守望、一缕踏实的期许。
(本文系“我与《读者》的故事”征稿二等奖获奖作品,〔美〕迈尔斯·海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