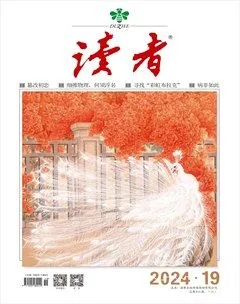从拔尖的陷阱到掌控的反噬
2024-09-30刘云杉

在今天,我们对“精英的傲慢”和“精致的利己主义”有许多检讨。与其用这些词来批评年轻人,不如去看看背后造就这一现象的制度逻辑。
与此同时,教育的“成功学”现象或者被热情追捧,或者被激烈批判,但我更愿意探寻这些成功学如何在教育场域里被制造出来,又如何侵蚀、改写、异化着教育的实践。
抢跑的代价
我们都愿意相信天赋异禀者存在,也乐意塑造神童。第一位出场的同学杨抢跑,就被视作神童。
3岁时,杨抢跑的妈妈就给她买了第一本字典,并教会她怎么查字典。4岁前,她学会了10以内的加减法,误打误撞做对了奥数题。小学二年级她开始系统学习奥数,三年级学习初中英语,五年级学习初中数学,六年级学习初二物理,在小升初的暑假背完了中考必背的古诗词。
抢跑让她能获得很强的正向反馈,她尝到了抢跑的甜头。因为成绩好,她深得老师的信任,获得各种荣誉,甚至有批改同学作业的特权。
但是,领先的优势是因为超常的学习能力,还是因为超前的学习节奏?
抢跑有甜头,也有代价。初中毕业后,杨抢跑进入一所重点高中的实验班。她发现,在高中,“抢一步、赢一路”不再是她个人的制胜秘诀。实验班里的多数同学按下了超前学习的快进键。老师将学生已经学过一遍默认为基础水平,会直接在课堂进行拔高与拓展训练。校外培训成了“生存”的必需——不提前学,很难跟上常规的学校课程进度。
杨抢跑们为什么普遍地超前学习?因为中小学正在经历中国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
新世纪开始的第八次课程改革,出发点是学业减负,改变过去课程中繁难的知识传授,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用学生自主学习替代老师的教授。老师从讲台上的知识的讲解者,变成激发者、辅导者、各种能力和积极个性的培养者,把主要精力放在检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上。
这一改革背后是一套新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是一套解放的逻辑,它建构了一个自主的学习者的意象——好像只要学校松绑,学生就会自主地学习。
学生看起来是在自主地学习,但是,校内减负与学业外包,自主学习与校外培训,多元选择与项目超市、成长赛道,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教育生态——学生在校外系统地学习知识,在校内输出能力,体验碾压别人的快感。
这种复杂的教育生态背后是名校垄断。一个学生的成就取决于学校所拥有的资源:赛道是否多元?学生有无在竞赛中获奖?对考试规则是否熟悉?其中,教育中最优质的资源其实是那些拔尖的学生。
有拔尖就有掐尖,学生考试的名次与学校的排名直接对应,学校究竟是在对人进行增值培养,还是仅仅完成了对学生的精准筛选与简单分层?
此外,课程改革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以前老师是依据教学大纲教知识,而现在老师教学的效果要用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可表现的能力来衡量。因此,评价体系变得非常重要。
从学业评鉴到指标记录、发展诊断,再到自我诊断、自我表现鉴定,评价体系不断迭代优化。“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本来是很开放的,却被套上了严格的行为指标的铁格,形成一个控制细密的指标迷宫,学生在指标迷宫里不断打卡通关。
学校成了优绩主义的实验场。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学生会有怎样的心理感受?他们今天的脆弱或者孤独,是否与此有关?
套路的秘籍与代价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题词是:“不要考第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原生态的孩子一般考试就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到100分,需要付出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争这100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要给土地施10遍化肥,最后孩子的创造性都被磨灭了。
为什么学生提不出好问题?因为他们在不断地练习某种套路。
最早进入套路的是老师。套路的实质就是老师把一些思考型的工作拆解成操作型的知识,将复杂的工作不断地标准化和程序化,再编成相关的学案和套路,让学生大量刷题。其背后是泰勒教学模式的盛行。
泰勒模式不要求劳动者具备基本的智力,但是需要其有忍受单调工作的意志。泰勒教学模式源于泰勒模式,也是通过细致的分工,把复杂的知识分解成最小和最简单的部分,再娴熟地连接起来,保证摄入知识的速度与准确性。
一个学生告诉我:“寻找标准答案是我在高考以前的人生阶段的主要矛盾,为此我可以从早上7点端坐到晚上11点,在做题总结和反思的流程中无限循环。”
他相信一切都有标准答案,都有一个最优解。因为考试总有标准答案,所以没必要去质疑老师讲的结论。他也变得害怕不确定的结果,因为不确定的结果就意味着考试的分数可能会更低,这让他条件反射地心理恐惧。
可是,不确定、瑕疵正意味着新知识和新经验生长的可能性。
因此,这一群中国基础教育生产出的最优秀的学生,其中很多人逐渐丧失了对复杂世界的认识能力——世界对他们而言,只有对和错、是与非。因此,他们也失去了直面真实世界的能力。
一场自我监控的学习
这群最优秀的学生进入大学后,有些人就陷入了一个“忙、茫、盲”的囚徒困境,彼此之间展开了逐底竞争。
他们被困于“茫”——外部目标缺失,内在价值虚无。于是,他们用群体性的“盲”来回避内在的茫然,又用竞争性的“忙”来提升标准,不愿也不敢正视自己独有的使命。
在经典的大学理论里,大学是一个人的自我教育时代的开始。从高中到大学,一个人需要茫然又自主地探究,通过知识和学科打开一个“小我”,走向一个更大的世界。同时,他们要和身边不同的人打交道,阅读不同的心灵,建立一些可信任的稳定的关系。通过自身的理性和力量驾驭动荡的人生,不断地塑造内在生活,形成自己的准则和风格,在一个更大的世界让自己的内在精神变得更充盈。
可是我们今天的自主教育,更像一种自我调控、自我监控的学习。自我监控的学习意味着学生要知道评价标准是什么,针对这个目标制订计划,去看自己和目标之间的差距是什么,要实施什么样的策略缩小差距,检查与评价实施结果是否符合计划,改进不符合计划的部分,再针对特定情况提出一个新的计划和新的目标……如此周期性地循环。他们不断地评价自己的能力,走向一个看似高效能的状态。
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眼睛始终没有看向外在的世界。真实的世界中常有斑驳的光影、模糊的色调,他们自幼被训练习惯于去追求明晰、可达成的目标,来提升自我效能感。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习惯于目标明确、规则清晰的生活。今天,他们离开了一切都清晰、确定的目标铁格,来到了奔涌的水流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猎手的抉择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学生如此在意评价和考试。在他们看来,评价构成了目标本身。因为他们从小熟悉的就是学业评价、综合素质的测评,要清楚地知道赛道,不断地对标别人,一路打卡通关。评价制度不仅影响着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还塑造了他们基本的习惯和性情。
一个很聪明的学生说,在大学里,非常重要的是学会学习,策略比知识更重要。做题家总是揣摩出题人的心思,我们要从做题家变成命题者。
稳妥的策略是,成为一个全能型人才,每个部分都要做得最好。那如何做到呢?
这需要一种高阶能力,需要的是一种“超注意力”,在多重任务、多个信息来源和多个工作程序之间不断地转换焦点,而不是进入一件具体的事情中去。
这种高阶能力非常强调灵活性,也就意味着人要机动,要随时离开,随时重组。它与专注无缘,具备这样能力的人不会为一件事情着迷,对任何事情都是没有差别的投入。
因此,今天更多的学生变成了“猎手”。猎手既要追踪猎物,也要警惕四周,还要监控自己,更要出手果断迅速。因此,他们讲适应性,适应性让他们变得非常灵敏和机警。
他们不能深度投入,在人和事之间都要强调边界,辗转于得失之间。他们对猎物的热情有限,选定的猎物是精心算计过的,是可置换的对象。猎物可以是绩点,也可以是学分,还可以是赛事与证书。因此,他们要把自己训练成一个灵巧的元素,以便随时自由地嵌入,又能轻易地脱嵌、移动。于是,他们采用一种“选而不择”的策略,这也让他们陷入选择的悖论。
而人的真正成长需要一种否定性的力量。选择意味着选择完成后的承诺、付出和责任、契约。选择作为一种生命实践,正需要“有所不为”的内在坚定性,“有所不为”恰是“终有所为”的前提。你只有有所舍弃,才可能真正获得一些东西。
这也影响了他们与人的关系。这一代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搭子——饭搭子、酒搭子、运动搭子……他们只在某件具体的事情上共事,不是朋友,彼此之间不再是深刻的、持久的、信任的关系。
一位教育学教授这样描述他们的状态:“所有的人都是桥,可以帮助他们过河的桥。老话说‘过河拆桥’,而现在都不存在拆桥。他人的桥都可以是浮桥,一只脚踏上去,另一只脚又离开。”
“高效掌控”的反噬
另外一个同学,我把他称为达,因为他总是能达到目标。达是高效掌控管道中的高手,掌控塑造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习惯,让他活成了一台高效且封闭的机器。一旦离开这个管道,他的生活也将随之崩塌。
达说:“其实在成长过程中我一直在升级打怪,升级打怪本身就非常刺激。你一定要问我意义,这个意义会让我困惑,它会逼迫我去想,我到底要做什么,这让我很惶恐。”
达相信生活中的一切都有最优解。他没有谈过恋爱,因为他没时间,他说:“爱情常常是不受控制的事情,但我要做的是控制我自己。”
他将日常生活理性化的能力超强,内心很少起波澜,很少受到触动,甚至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感觉。没有人可以进入他的内心,他将自己完全封闭了起来。
自我负责的陷阱
像达一样的猎手成长于一个真实的制度空间,在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下,他们被要求对自己的学习结果高度负责,这一能力关系到他们未来的职业素养、工作能力,乃至在一个快速变动的世界中的可迁移能力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置身奔涌的潮汐中,如何掌控自己,成为不败的“弄潮儿”。
非常有意思的是,整个世界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很多年前,X一代(出生于1964—1975年的人)从科层制的机构里走出来,享受着流动的好处,他们不愿意也不想追求终身制的工作,但渴望终身学习。但是,到了千禧一代(出生于20世纪,在21世纪初成年的一代人),我们看到,他们的独立变成了漂移,对稳定重复的工作的感受从无聊变成不断的焦虑。而且他们非常强调弹性。弹性背后是能伸能缩,能够不断地适应不同的机构、不同的文化。这种适应要求你像变色龙一样。更为关键的是,你不需要有内在的原则、内在的坚持。
我们还会看到“斜杠青年”的流行,在多重经验背后,他们不断地进行自我塑造、自我定义,面目模糊。在自律与自我塑造中,这些和潮汐一起奔流的弄潮儿,常常通往深深的倦怠。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猎手,他们的眼睛被训练得既灵敏又盲,他们永远把目光盯着目标,对其他东西视而不见。他们看不到更大的世界。他们辗转于得失之间,奔波于动荡和风险之间,直到他们的猎手生涯终结,或者自己成为一个猎物。
他们在一个孤零零的自我头脑里面,构建了一个高度形式化且体系化的全球定位系统,砍断了一切联系。这个定位系统把他们拉向远方,把他们和身边具体的他人、近处的世界完全割裂。
那么他们到底是离世界更近,还是更远?
(哈哈镜摘自微信公众号“一席”,本刊节选,勾 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