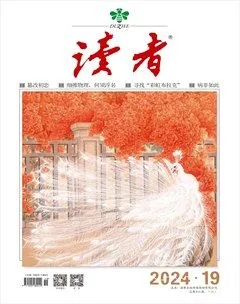还剩半瓶
2024-09-30戴建业
读者 2024年1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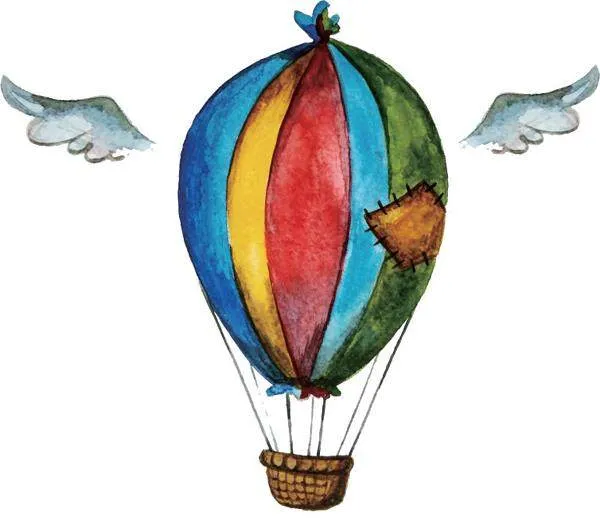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能按照理性原则来生活,因此,“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
这可能是他身而为人的自恋。试问,有多少人能真正按照理性原则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理性在为情感辩护,而不是情感为理性服务。譬如,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是因为先爱上他这个人,再去寻找爱他的理由,而不是先找到了爱他的理由,再去疯狂地爱他。没有爱的冲动,就没有爱的理由。事业也和恋爱一样,人先有追求某一远大目标的生命激情,然后才会去思考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行路径。
遇上同一件事情,面对同一种风景,不同的人常有不同的情绪反应。且看林黛玉与薛宝钗如何面对暮春的柳絮。看到“一团团逐对成球”的柳絮,林妹妹发出“飘泊亦如人命薄”的哀叹——柳絮轻才会飘零,人命薄才会漂泊。可是,“东风卷得均匀”的柳絮,反而激起了薛姑娘的雄心:“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柳絮“无根”便无羁,缺点反成优点,坏事变为机会,否则怎么能“上青云”呢?
对人、对事、对景的第一印象,是以后做出决定的“首因效应”,甚至是有没有“以后”的关键因素。难怪马尔库塞不仅把建立新感性视为审美命题,而且还把它作为政治任务。同样,李泽厚不仅把它作为美学课题,还把它提升到心理本体的哲学高度。
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德鲁·吉尔平·福斯特说:“教育的目的不是要积累一堆知识,而是要学会一种思维。”我倒是觉得,教育的“第一义”是让人建立新感性,一种新感性的建立之日,便是一代新人的诞生之时。有了新感性,我们的后代才会有敏锐的直觉、积极的心态、向上的活力、乐观的精神。当看到半瓶酒时,他们都会快乐地说:“太好了,还剩半瓶!”
(令狐冲摘自《读书》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