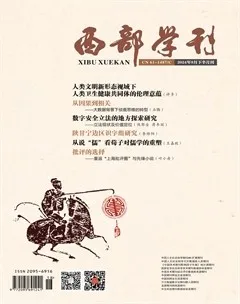科技与伦理交叉视域下李觏思想研究
2024-09-26霍君吕变庭
摘要:基于科技与伦理交叉视域观照李觏的思想就会发现:其以物质第一性为基础构筑自己的世界观,坚持彻底的经验论;在创造性地构建自己的“礼论”体系下有条件地肯定了利和欲,并强调了情的作用;在“礼”与“学”的加持下李觏认为,人“性”的境界可以提升、与“命”得以相宜;以唯物的科学思维和中正观为基础,李觏阐述了“人事”需要遵守的道德准则,强调了在中正之上的“权宜”性。宋代造就了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峰,李觏等人的天和人相和谐的本质和精髓仍值得现代社会借鉴和传承。
关键词:科技与伦理;宋学;李觏
中图分类号:G40-09;B24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4)18-0144-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河北大学社科培育项目“北宋科技伦理思想史研究”(编号:2022HPY025)阶段性研究成果
On Li Gou’s Thou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section of Technology and Ethics
Huo Jun1Lyu Bianting2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2. Song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section of technology and ethics,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Li Gou constructed his worldview on the basis of material primacy and insisted on thorough empiricism: With the creative construction of his own “ritual theory” system, he conditionally affirmed the benefits and desires, and emphasized the role of emotions. With the blessing of “ritual” and “learning”, Li Gou believed that the state of human “nature” can be improved and compatible with “fate”. Based on materialistic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the thoughts of neutralization, Li Gou elaborated on the moral principles that need to be observed in “human affairs” and emphasized the “expediency” over neutralization. The Song Dynasty created the peak of ancient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essence of the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is worth learning and maintaining in modern society.
Keywords: technology and ethics; Neo-Confucianist Study of the Song Dynasty; Li Gou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背景下科技处于附属地位,伦理虽未直接作用于科技活动,但也规范着人的生产生活等实践活动,其中优良的道德规范传统和伦理原则仍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赵宋一代成就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这背后自然是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在宋代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下,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宋学的出现一扫汉唐的章句之风,除有义理派之外,还有事功派,与义理之学的重义轻利相比,更注重实际的功用和效果。李觏被认作是事功派开山的代表性学者,同时亦是开启宋学的领军性人物。对李觏思想的研究集中在功利和礼思想方面,主要围绕礼的特质和经世致用展开分析,散见有对物、技的论述。本文主要从李觏对“利欲情”的辩证认识和对“性命之学”的阐发这两方面展开论述。
一、“利欲情”在李觏思想中的辩证关系
有研究认为,宋代的经济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不仅很多人脱离了土地,成为被雇佣之人,士阶层与工商之间的流动性也不断增强[1],以致南宋事功派代表人物叶适曾言道:“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2]利欲的驱动在客观上增进了技术进步,但过度的追求会带来负面影响。对此,李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有关李觏对利的认识,诸多研究多引“人非利不生”一句,以示他对利的首肯。不过,虽然李觏是在强调利,但还是增设了一定的限制条件。在“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一句后,李觏继续说道:“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3]342这里也就点明了礼对利欲的制约关系以及生与情在李觏思想中的关系地位。笔者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重点强调利与生和情的辩证关系。
要理解李觏对利的认识,笔者认为可以着眼一“生”字,它既可以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可以是指人类生命的起源。首先,从生命起源来看,李觏在创造性地解释元亨利贞中涉及对利的阐发。
或曰:敢问元亨利贞何谓也?曰:大哉乎乾之四德也,而先儒解诂未能显阐,是使天道不大明,君子无所法。若夫元以始物,亨以通物,利以宜物,贞以干物,读易者能言之矣。然所以始之,通之,宜之,干之,必有其状。窃尝论之曰:始者,其气也。通者,其形也。宜者,其命也。干者,其性也。[3]67
元亨利贞中的利,按照儒家一般的解释,是宜物,即有利于事物,亦从事物中获取利益。而李觏却以气形命性对应元亨利贞,从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利、宜、命的关系。阴阳二气相交,合而成形,形成胎、卵、勾萌等“万物生存于各不相同的生命样态之下,各得其所。”[4]利和命都与宜相关,与客观物质环境相宜,也就是宜命,因时因地而宜,便是利之德。这就给利附加上了道德价值的标准。宜而利,就是根据现实客观要求合情合理地满足自身需求,从而适应客观环境。
其次,从物质生产资料的角度看生,利即是“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3]6一句中的“人之性欲”。这又与器物财物等物质资料紧密相连。宋代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人们对物质的要求也随之高涨。对李觏来说,“人所以为人,足食也;国所以为国,足用也。”[3]79李觏重视农具的开发和手工业的发展,这表明他对物质利益获取的肯定。但这些并不是站在商品经济的立场上,而是处于农业社会的大背景下考量的。《国富策第一》中有“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3]138,因财用才可以“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3]138。同时李觏也强调“所谓富国者,非曰巧筹筭,析毫末,厚取于民以媒怨也,在乎强本节用,下无不足而上则有余也”[3]138,在此之上才能实现“故知礼者,生民之大也,乐得之而以成,政得之而以行,刑得之而以清……无一物而不以礼也”[3]20。
对于利益,李觏认为要贯彻中正节用思想,不能心存私念。利和欲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并且由着利欲恣意妄为,导致危机的到来。“进取之时易见,退避之时难知。盖利者,人之所欲,欲则存诸心,存诸心则计之熟矣。害者,人之所恶,恶则幸其无之,而不知为谋矣”[3]39,李觏对于利欲的态度,从对元亨利贞的解释和“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3]6一句可知,利欲是人生存必要所必需,是人“为”的动力,但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时需要礼进行节制。
李觏在强调中正观的同时,也不会生硬地套用各种模型,将自己封闭起来。在讨论利欲时,李觏用情作润滑剂,调节两者之间的平衡。对情,具有典型性的阐述是在《复说》当中。所谓“复”是“择乎中庸”“直而温,宽而栗,柔而立”[3]347,即不能过度偏执一端,失其平衡。《复说》当中出现了“圣人之情”。《复说》中有言:“人之患不在乎不及,而在乎过之。不及则下于人,下于人则愤,愤则知进矣。过之则出乎类,出乎类则矜,矜则不知其反矣。”[3]347李觏列举了伯夷、于陵仲子、鲁隐公等贤人看似守礼的行为,但矫枉过正。因此,李觏才强调:“应时迁徙,各得其所。礼所以制乎中,义所以谓之宜也。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圣人之情也。”[3]347肯定了“子见南子似不正”“昭公知礼似不直”等看似有违常礼的行为。礼不是死板的条条框框,遇事需要“权宜”之计和通变。李觏所谓的“情”已不是简单的情感问题。关于“情”,《中国哲学大辞典》相关条目中有如下阐述。
“情”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儒家、墨家、道家,以及佛家对其都有阐释。“孔子重视情感之正当的流露”,孟子“所谓恻隐、羞恶、辞让等,皆以情当合道德原则”。而韩愈认为“情同性一样分为三等,‘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原性》)。”[5]169
结合《复说》中的“圣人之情”,李觏的情接近韩愈的“动而处中”的上品之情。李觏对于“动”也表示过“动而处中”的意思,“或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请问动而无悔则奚由?曰:时乎时,智者弗能违矣。先时而动者,妄也;后时而不进者,怠也。妄者过之媒,怠者功之贼也。”[3]39除“圣人之情”外,有“洪惟圣神,扫五代之弊,跨唐据汉,拱揖三王,教化之情靡不存乎中矣”[3]175的“教化之情”,“圣人者,非其智造而巧为之也。天之常道,地之常理,万物之常情也”[3]265中“万物之常情”也是与“常道”“常理”相比肩。由此也可推知,在礼的节制下,为满足必要所需的利欲,发挥了情的能动性作用。
二、“性命之学”在李觏思想中的辩证关系
有关性命之学与科技的关系牵涉到了天人关系与科技之间的互动。在对天的认识中,除了自然天之外,还有命运天,表现为一种客观世界的限制作用。天人合一倾向于听天由命,天人相分则侧重于我命由我不由天。而科技发展更多的是与天人相分联系在一起。在近代科学兴起初期,不仅表现在将物质世界、宇宙生成视为研究的客体,而且还相信“人是破坏自然秩序而不是遵守自然秩序的,是有绝对力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的,并且是完全自决而不受外物决定的”[6]。面对西欧彻底的二元对立,中国古代思想表现出的则是一种辩证性的天人相分。
关于李觏对性的阐发,学界目前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李觏持有性三品说[7],第二种表示李觏是主张性善论[8],第三种则比较综合,指出李觏早期坚持性三品说,之后发展为情善和性善。通读李觏的文集,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前后的变化。针对这样的变化,李存山认为这是李觏早期人性论中存在的“前后矛盾”“不确定性”[9],章林也表示这是一种“混乱”的“不彻底之处”[10]。李觏24岁作《礼论》,并且他还自诩“好尚与众异”[3]404,因此,早年在其自身思想的体系完备性上有欠缺,亦是可理解之事。不过,引起笔者思考的是李觏在人性论前后的变化中,是否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是否存在一种将前后变化连接起来解释的可能性。
关于人性,大多数研究都指出李觏受到韩愈的影响,认为人性有上、中、下三品。李觏在《礼论第四》中写道:
上智,不学而自能者也,圣人也。下愚,虽学而不能者也,具人之体而已矣。中人者,又可以为三焉:学而得其本者,为贤人,与上智同。学而失其本者,为迷惑,守于中人而已矣。兀然而不学者,为固陋,与下愚同。是则性之品三,而人之类五也。[3]12
从以上引文可知,“性三品”主要指的是生而有之的自然之性。其逻辑前提是将人分为了三个层级:上智、中人和下愚,中人再分三层,共五类。三个层级上的人所具备的性不同。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性三品”中同时包含了经验之性和先验之性。在李觏看来,圣人包括孔子以及尧舜禹等先王,是“不学而自能”,先验地具备了圣人之性,并且圣人同中人和下愚是生活在同一个经验世界当中。在同一时空下,首先,圣人自然拥有经验性的圣人之情,可以在形而上的仁义智信中留出随机应变的余地;其次,为作为中人的贤人成圣打开了通道,通过自身的努力开辟出上升的空间。作为同时具有经验性和先验性的圣人,其身上的圣人之情和圣人之性就有了相互游离于经验世界和先验世界的小幅空间。圣人之性作为道德伦理规范,具有了形而上的色彩。李觏在“性三品”的基础上着重强调的是作为人行为、修养、精神境界的标准的圣人之性。一方面,这样的圣人之性很自然地与孟子所主张的“性善论”有了交集。孟子之性是道德之性、形而上之性,具备了先验性。李觏的圣人之性也具有规范性和先验性。另一方面,身为士阶层的李觏始终坚持“性不能自贤,必有习也”[3]34,道“人斯有之也。……圣人因其有而品节之,使之坚守而弗去”[3]230,肯定了成圣的可能性。由这两方面共同可推知,李觏之后所推崇的“性善论”并不是和孟子所提倡的完全一致。在李觏阐述“受命于天,性善是也”[3]231“民之欲善,盖其天性”[3]338,这些具有形而上色彩的内容的同时,它的底色是作为士人的李觏所坚持的贤人可成为圣人、民亦可成为贤人的信念。
在此基础上再看“养天性,灭人欲”一句的内涵,过度消费欲望当然是要被消灭的,而在养天性中,比起生而有之的自然之性,天性更可以被理解为是作为道德标准的圣人之性,这与下文所分析的李觏的天命有异曲同工之处。另外,“养”也彰显了人寻求改变的能动性。这又与李觏的“民生在我不在天”[3]420的天命观有联系。
在李觏看来,命除了有生命、命令等基础的意义外,还有表示非人力所及的客观限定之意,和表示自然之至理这两种含义。然而,李觏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在这两种含义之上再有所发挥。
李觏说:“患自已招,斯可患也;患非已招,斯不足患也,其必免矣。如其不免,是有命焉,非智之过也。”[3]47这一阐述表明李觏承认在物质客观世界中存在着对人和事物限定的条件,非人力所可及。这是身处被动环境的状况,而当自身处于能动的情况下,如他在《命箴》中所说:“宜失而失,斯谓之正。宜得而失,斯谓之命。身之不修,责命可乎?”[3]348这就表明李觏并不是将所有结果都归结为命运的安排,他区分了“宜失而失”和“宜得而失”,强调因自身原因造成不当的后果,不应该将其视为人力不可及的命运,而应该反省自己。李觏认为命虽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部客观存在,然而存在着有利于事物发展且与之相宜的外部条件。这样的宜并非完全依靠人力去改造,而是包含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思维,即注重“思维对象的差异性或具体规定性,并依据这些差异性或具体规定性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方法”[5]349。
可以说李觏思想中的性是与情一样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并且也同样主张“上品的性情”是“动处于中”。李觏秉承的“天人合一”,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对李觏来说,命是人力所不及影响的,作为客观被动的条件,人可以去适应外部环境,而遇到由于人自身原因造成的后果时则需要进行自身的反省。同样作为客观规律存在的命也是需要人遵守并通过自身努力而实践这一准则,“观其善则见人之性,见其性则知天之命”[3]68。虽然命是客观的难以更改的条件和结果,但也伴随着人的能动性可与之相适宜,特别是对于人自身可以控制的结果来说就更具有选择性。
三、结束语
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用“科学的精神气质”一词来形容近代科学在英国之诞生与社会诸层面之间的关系,在本书的中文版序言《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预示》中重申了“规则——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论——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11]。李觏的精神世界在物质第一性的基础上也展现出同样的气质。李觏注重实效、经世致用的思想体现出他的功利主义和对世俗的兴趣,对“礼”创新性的解释表明他自由的研究学风,他“重民”的思想也与默顿所说的无私公有性相通。
然而,默顿没有提及的便是李觏始终贯彻的中正和权宜的思想。“中正”保证了实践活动的不偏不倚,而“权宜”实现了行为主体在中正的前提下随机应变、灵活变通。而这也是西方近代科学在一开始的时候便欠缺的精神气质。赵宋一代处于10—13世纪,这一时期的技术高峰在亚洲,宋代的农业、纺织等技术领先于世界,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在北宋前期有一批倡导经世致用的士人的存在,李觏、范仲淹,以及之后的王安石等人的思想在中国科技思想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傅筑夫.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M]//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81:669-708.
[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M].北京:中华书局,1977:324.
[3]李觏.李觏集[M].王国轩,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4]陈彦杰.李觏易学的图书之辨及天人内涵[J].周易研究,2019(6):30-37.
[5]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修订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6]斯宾诺莎.伦理学[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95.
[7]姜国柱.李觏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2.
[8]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445.
[9]李存山.李觏的性情论及其与郭店楚简性情论的比较[J].抚州师专学报,2002(4):13-21.
[10]章林.李觏与儒家经济人性论的形成[J].广西社会科学,2021(12):95-101.
[11]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
作者简介:霍君(1983—),男,汉族,山西阳泉人,博士,单位为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
吕变庭(1962—),男,汉族,河北石家庄人,博士,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
(责任编辑:张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