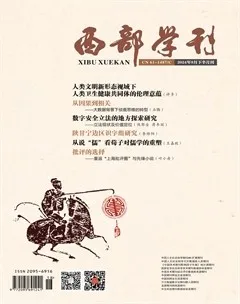陕甘宁边区识字组研究
2024-09-26李维阳
摘要: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工作面临着外部环境和现实需求的双重压力。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边区积极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教育活动。鉴于农村人口分散、无法设立学校的情况,识字组成为社会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识字组将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人员组合在一起,指定小组长,赋予他们监督和推进识字的重要职责,通过专门辅导培训,普遍采用“小先生制”的教学方式,从家庭邻里扩展至街道巷口,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利用任何空闲时间,随时随地进行教学活动,推动了教学互动,为实现教育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提高群众文化素养、政治意识、促进生产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社会教育;识字组
中图分类号:D696;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4)18-0136-04
A Study of Literacy Groups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Li Weiyang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71)
Abstract: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ocial education faced the double pressure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need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is situation, the border region actively carried out extensive and in-depth social education activities. Given the dispersing rural population which made it impossible to establish schools, literacy group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ocial education. The literacy groups brought together individuals closely related to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designated group leaders, and assigned them with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of supervising and promoting literacy. The literacy groups, through special training and with a widely adopted teaching method of “little teacher system”, expanded from neighborhoods to streets, utilizing any available time and space to conduct teaching activities anytime and anywhere, free from time and space restrictions. Moreover, the groups promoted teaching interaction, provided powerful support for achieving educational goal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the cultural literacy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of the populace, and facilitating produc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ocial education; literacy group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直接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把社会教育当作政府工作的重要一环,发布了一系列决议和通知,对社会教育的对象、任务、内容、形式、经费等问题做出了具体指示和规定。通过努力,提高了边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为边区的建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边区的社会教育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崛起,并在其发展历程中肩负着明确的使命,展现了独有的特色。
一、社会教育的背景
(一)社会教育的紧迫性
教育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两种。学校教育是要学生脱离生产来受教育。如小学、高小的学生,他们放弃了白天的生产劳动而到学校里来学习。社会教育则是一面参加劳动生产,一面受教育,受教育不妨碍生产的一种教育方式。如夜校的学生,白天工作,夜间空闲了才来学习;识字组的组员是生产完毕后来参加识字。
二者的方式虽然不同,但它们的目的却是一样的——完成国防教育的任务,而且社会教育需要学校教育的帮助和推动。因为边区限于教育人才及经费的紧张,不能多建立社教机关,多聘专职教师,学校教育理所当然应当负担起社会教育的任务。如领导识字小组,附设半日班,开办夜校,帮助俱乐部,训练小学生作小先生,教群众识字等,把社会教育工作当成学校教育经常性的重要工作。
边区是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林伯渠曾在关于边区文化状况的报告指出:“共产党在此地建立政府之前,这里可以说是文化教育的一片荒漠。就小学教育而言,在边区政府管辖的范围内,据说仅有120所小学。至于社会教育,如识字组或民众学校等,几乎是没有建立起来的。”[1]18在一段时间里,文盲占据了全人口的绝大部分。尽管土地分配和苛捐杂税废除后,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但要让这些文盲大众脱离生产去学习仍然是困难的。受限于自然环境和落后的农业、工业技术,群众缺乏学习的时间和机会,只有少数人能够长期进入学校学习。为了弥补这个问题,需要大规模推行深入广泛的社会教育,利用群众的空闲时间给予补习教育。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教育作为团结群众的最有力工具,需要迫切地被使用起来。边区政府需要迅速普及国防教育,消灭文盲,提高民众的政治水平和抗战所需的知识技能。然而,巨大的经费和人才短缺在短时间内难以满足。短期内培训足够的人才也不现实,长期下去又不符合抗战的紧迫环境。因此,社会教育工作成为战时重要工作之一。对于教育的轻视,应该克服。教育机关,教育工作者,以及所有工作人员都应该重视社会教育,推动社会教育。
(二)社会教育的可能性
1933年冬季,以刘志丹为首的共产党员们在陕甘边界成立了革命根据地,其中心位于南梁。他们在该地区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延续了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并进一步深化。通过分配土地给农民,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这增强了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这一措施为在该地区展开社会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0年,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刊物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总结“五四”以来的文化教育经验,提出新民主主义教育应具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2]。此前,中国共产党结合“五四”运动以来文化教育的经验和民众的教育实践,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成为边区社会教育实践的理论基石。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获得胜利的重要策略之一,在文化教育领域,中国共产党同样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在1934年,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无论其政治倾向、职业或性别如何,都应联合起来,共同在反帝统一战线下,团结起来与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作斗争。”[3]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社会教育事业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共同支持。
“当前党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全国范围内的一致抗日战线和全面民主政治,首先在我们自己直接领导的陕甘宁特区创建抗日的楷模。”[1]1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致力于将陕甘宁边区打造成全国抗日的典范,以赢得各界赞誉并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根本目标在社会教育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文化普及、政治动员和封建迷信根除。其中,封建迷信的根除主要通过群众参与的文艺娱乐活动来实现,而正规的教育则着重于文化普及和政治动员两个方面。
二、识字组概述
识字组是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社会扫盲工作中使TKFv4pTYIBSEoR80M8KqsQ==用的一种最简单、经济、灵活的教学组织形式,也是边区社会教育中重要的教学方法之一。在边区人口稀少、难以设立学校的情况下,通过组织生产繁忙的民众成立小组进行识字教学,是最有效的教学组织形式。
(一)小组成员构成
识字组的特点最明显地体现在其小组成员的构成上。鉴于农村人口分散、无法设立学校的情况,识字组结合了群众的生产与生活需求,将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人员组合成识字小组。在乡村中,识字小组可能是几个相邻的农户或家庭组成;在机关和部队中,识字小组则由经常共同工作和生活的人员组成。每个识字小组由三至七人组成,成员们选举一位组长负责监督和推动小组的识字工作。
(二)小组长推选
虽然识字组的人员数量有限且结构简单,但每个识字组都会指定一个小组长,并赋予他们重要的职责。小组长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和管理整个识字组,监督组员的学习进度,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情况,并将自己所学传授给组员。此外,小组长需要制订识字进度计划,并保持与附近学校的紧密联系。当小组长离开本地时,需要任命代理人来履行其职责。因此,选举组长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首先要有责任心;其次要乐于学习和帮助他人;第三,最好能识字一些(尽管不识字也不是问题,只要有积极学习的态度)。总之,组长要领导组员,并督促他们学习识字。
通过采用“小而精”和由组长负责的方式,识字组在教学过程中展现出高效的特点,便捷的组织形式使得识字组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蔓延开来。
(三)识字组的组织教学方式
识字组的教学通常并无固定的学习场所和时间要求,教学方式不拘一格,灵活运用各种时间和地点进行教学,主要内容包括识字和阅读报纸。由于识字组的广泛设立,并且普遍融入群众的生产生活中,为了弥补师资短缺等问题,识字组普遍采用“小先生制”教学方式。
边区教育厅强调:“小先生是普及教育最为有效的方法,各地应积极鼓励小学生担任小先生。他们在学习的同时,抽出时间进行普及教育,教导民众识字,传达信息,宣传知识,是普及教育的有力手段。小先生的工作重点包括四方面:首先,初始教学时应逐渐增加学生数量,最好先教父母、兄弟姐妹以及邻居的小伙伴,不宜拥挤;第二,教学材料应具备趣味性和实用性,最好能紧扣当下事件,例如标语、传单、宣言、信函和纸币等都是极佳的教材选择;第三,教学过程需要耐心和友善,不应失去信心;最后,各小先生应联合起来,学生们也需组成团体,定期互访学习。”[1]74
由于小先生并非专职教员,在识字组教学工作中难免出现误差,因此对小先生进行培训显得至关重要。“在实践‘小先生制’时,必须对小先生进行培训,不仅要教会他们所需传授的知识,还需要指导他们如何进行教学。”[4]在学校中,培训小先生成为一项重要任务:首先,明确学校负责辅导小先生;其次,每天安排一节“小先生训练”课程,内容涵盖小先生教授知识,强调在教学中遇到的困难和心得,教师对于表现优异的学生应给予表扬和奖励,以及相互批评和讨论困难问题,另外,要进行下次教学任务的预习;第三,在小先生实际进行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定期分组巡回辅导,帮助小先生解决困难,并评估他们的教学表现,同时向社会解释小先生制度的价值;最后,对表现差的小先生,需要进行更多个别辅导,以防止他们掉队;对于表现特别优异的学生,也需要提供额外指导,以激发其专长的发展[1]73。
通过接受专门的辅导培训,小先生在识字组教学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常情况下,小先生在识字组教学中采用“就近进行教学”的方式,从家庭邻里扩展至街道巷口,融入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他们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利用任何空闲时间,如劳动间隙或休息时,随时随地进行教学活动,帮助人们学习文化知识和识字技能。
三、识字组的典型案例
各级政府通过竞赛、检阅等方式,经常对识字情况进行评比和检查,以督促识字工作的进展。边区识字组的经验说明,读报与识字结合的形式是最有效的形式,因为识字开眼界,读报开脑筋,两者又互相推动。所以,这种形式在边区文教大会上得到了肯定和提倡,并对模范识字组进行了表扬。
(一)王家桥识字组
绥德四十里铺王家桥识字组,是由乡文书贺汉德领导的一揽子的农村识字组,是农村识字组的典型。王家桥村有129户居民,除50岁以上的、7岁以下的外,共计373人。男劳力141人,参加变工队的76人,都参加读报识字。成、青年妇女138人,参加识字组的有42人。男女儿童94人,上学的25人,参加识字组的23人,共计参加识字的166人[1]240-242。
该村的识字组,是从群众的需要和自觉的要求而组成的,如儿童识字组,是因该村于古三月初动员儿童,到离1里多路远的石佛堂去上学,群众虽愿识字,但因上学耽误生产,所以要求在本村成立识字组。全组23人,就有11人是学校转来的。如妇女识字组的成立,因该村赶脚夫很多,常常写信回来,婆姨们不识字,感到不方便;加之有劳动英雄的媳妇马润兰是完小学生,能写能算,一般妇女感到非常羡慕,男人也受到影响。特别是当变工队在读报的时候,读到“锄奸英雄冯光祺组织妇女识字”的消息后,男人们很想让自己的婆姨也能识字。至于变工队的识字组,是在生产组织的基础上,进行读报。在读报中,又增加了生产常识,如除害虫、造肥等,大部分不识字的队员,感到听报不如看报,因而产生了识字的要求,推动了识字活动的展开。同时,由于有干部担任教员,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如儿童识字组由贺汉德直接来教,妇女识字组由冯润兰、徐志丹二人来教(徐志丹是由她丈夫教她念过二十几本书的)。变工队76人6个小组,有14个人识字,每个组都有一、二个识字的人来教。
在农村环境中,不可能有一致的时间标准,所以在教字的方法上,采取不拘形式,随来随教,个别教学为主。儿童识字组,每天早晨学习,早饭后即上山拦羊,妇女识字组,每隔六七天教一次,均在早饭后,每次教六七个字。变工队识字组,多利用每天在地里休息的时间教,不睡午觉。在教的分量上,根据接受的程度不同来决定,识字多的多教,识字少的少教,每人有一个沙盘,自由复习。为了检查效果,在每次教字以前,进行一次考验。
由于采用以上这些办法,王家桥识字组的效果是比较好的。首先,从识字方面来看,如儿童识字组,据两个月的统计,识字最多者百余字,最少者70余字;妇女识字组最多者195字;变工队识字组,多者200余字,少者30字。不过运用还比较差,这是教字方法上的一个缺点。在生产方面,通过了识字教育推动了生产,如儿童识字组的7个女儿童,通过识字组织,进行集体纺线,组长王金姐,一天能纺5两中等线。
(二)深井村的识字组
在盐池城区二乡的深井村,每个青年人,都会问你“你念冬书没有”“书本本哩”,同时,他们也会这样回答你“念了”“在这达,你看”[1]243-245。他们并且会从贴身衣服的口袋里,取出装钱的皮夹子,或是一个小圆洋铁盒,或是老婆给他缝的荷包上,而用五色丝线绣着美丽的四季花草,这里边装满了一寸大小的白纸片,用楷书写着:“马”“牛”“驴”“羊”“草”等单字。这就是他给你看的课本,他们叫“字拖拖”。
识字组一共34人。古历十月初三,在合庄会上成立的。按住房的远近,分编了4个组,选举了朱拴着、张子善、杨文秉、朱彦祯4人当组长,请朱彦政当教员。每天分早、午、晚三个时间去学。当天上午才商量好,晚上,朱彦政家里就挤满了人,这个喊着要写“骡马成群”,那个叫着要“牛羊满圈”。谁愿意学哪些字,教员就给谁写在“字拖拖”上。
识字组开头都是青年人,后来,学热火了,年纪大些的人也参加了进来。45岁的张志强,已念会了200多“百家姓”,还教给他的10岁的女儿学。杨文会和他的14岁的儿子杨住丁父子俩共用一个识字本,他们每认够50个“字拖拖”时,教员就给誊写在本子上,再教新的。
这个识字组,在不到40天里,识字最快的朱秃娃,已认了430个字。大部分都认会150多个字,最笨的朱彦信、张从仁也识了40多个字。这些字,都做到了会写、会认、会讲,如你问他“深”字,他会说:“这是我们的深井的深,深浅的深也是它。”
四、结束语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实际,依靠群众需求和自愿参与,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不仅推动了教学互动,还为实现教育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提高群众文化素养、政治意识、促进生产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边区社会教育工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造了一系列教学方法。这些方法灵活多样,确保了识字组教学的顺利进行。例如,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生活经验以及传统文化元素等,制定出适合边区特点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使得教育活动能够真正地贴近民众的生活和需求。
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工作在艰难的环境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它不仅提升了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还为边区的发展和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边区社会教育的成功经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教育和当前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都有启示。虽然时代变了,但社会教育仍有重要意义。因此,汲取边区社会教育的经验教训,既是传承历史,也是展望未来。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借鉴历史经验也可以为教育进步和完善提供指导。
参考文献:
[1]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6.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11.
[4]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档案[A].全宗号10,卷宗号332.
作者简介:李维阳(1998—),女,汉族,山西大同人,单位为长安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赵良)2024年9月下半月刊(总第219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