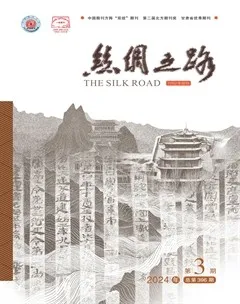米兰戍堡古突厥文文书语史新探
2024-09-25洪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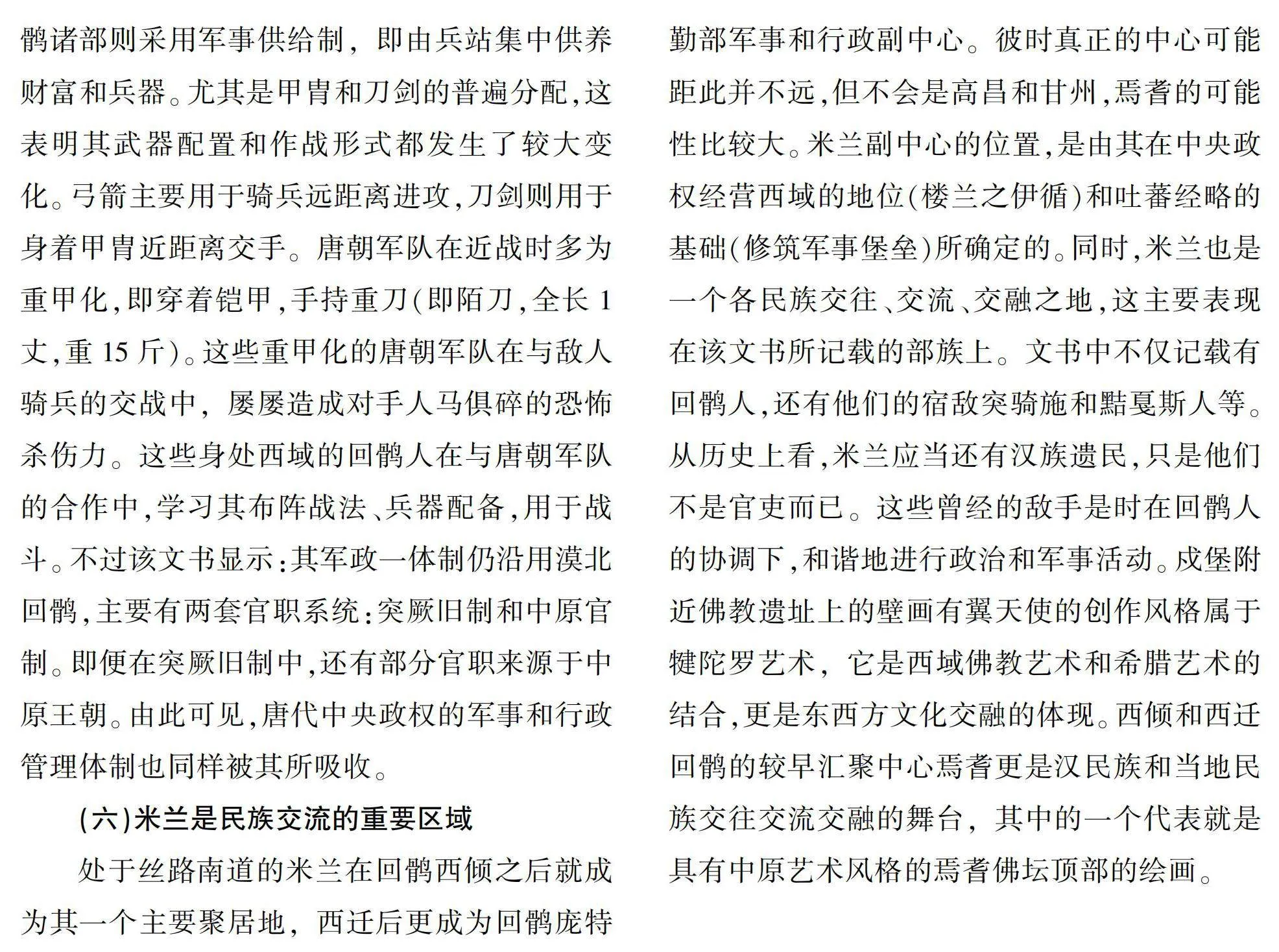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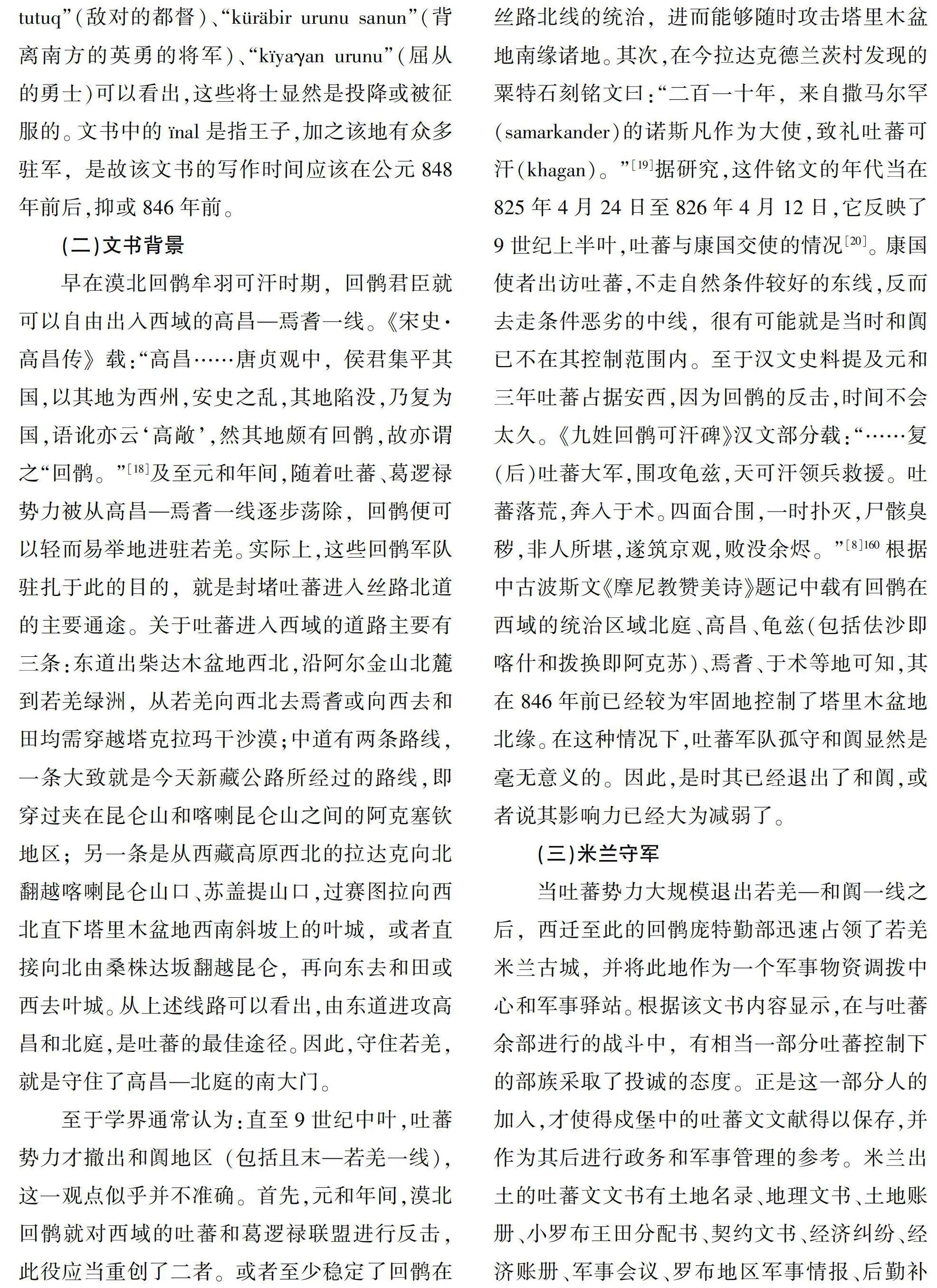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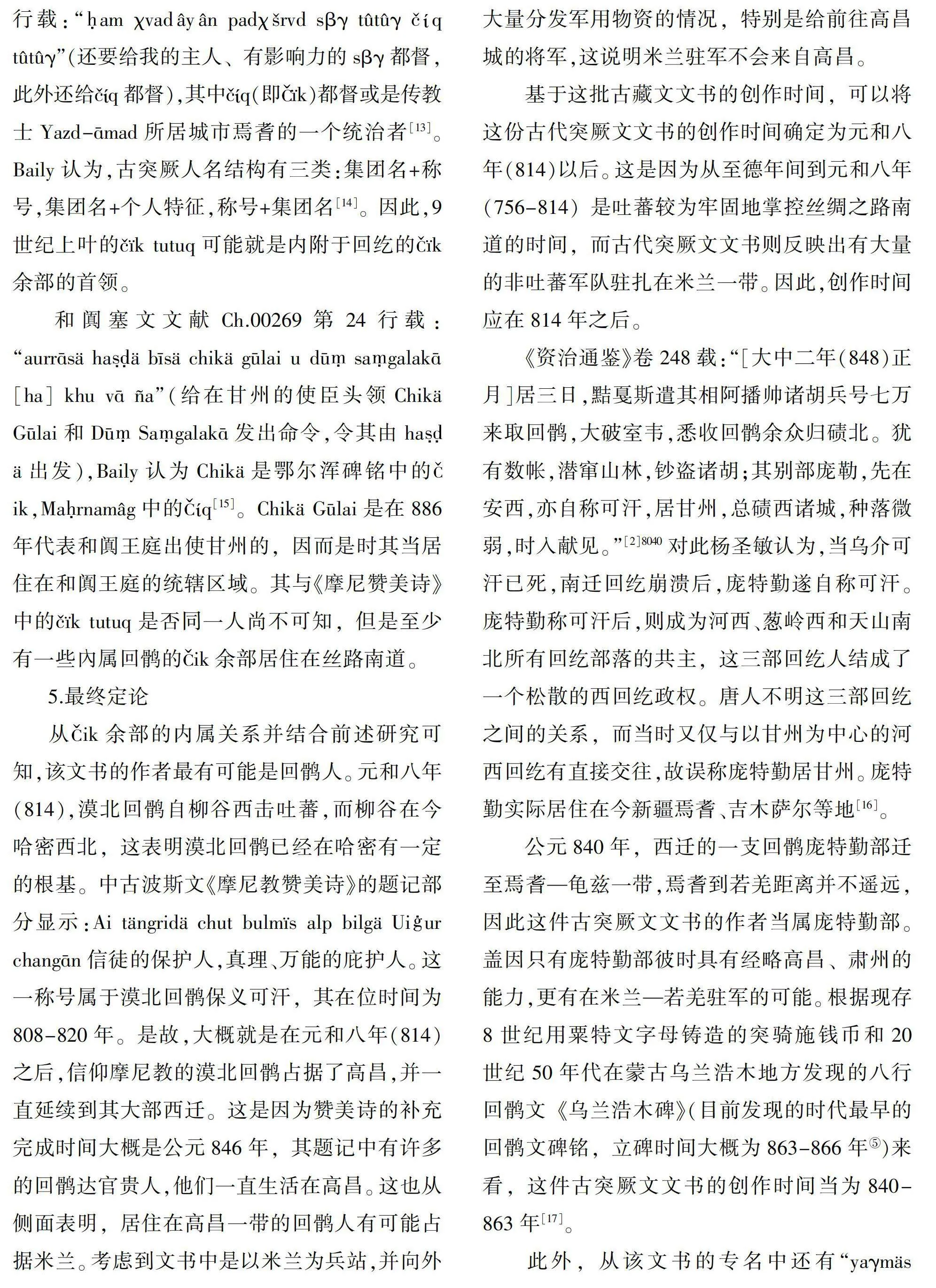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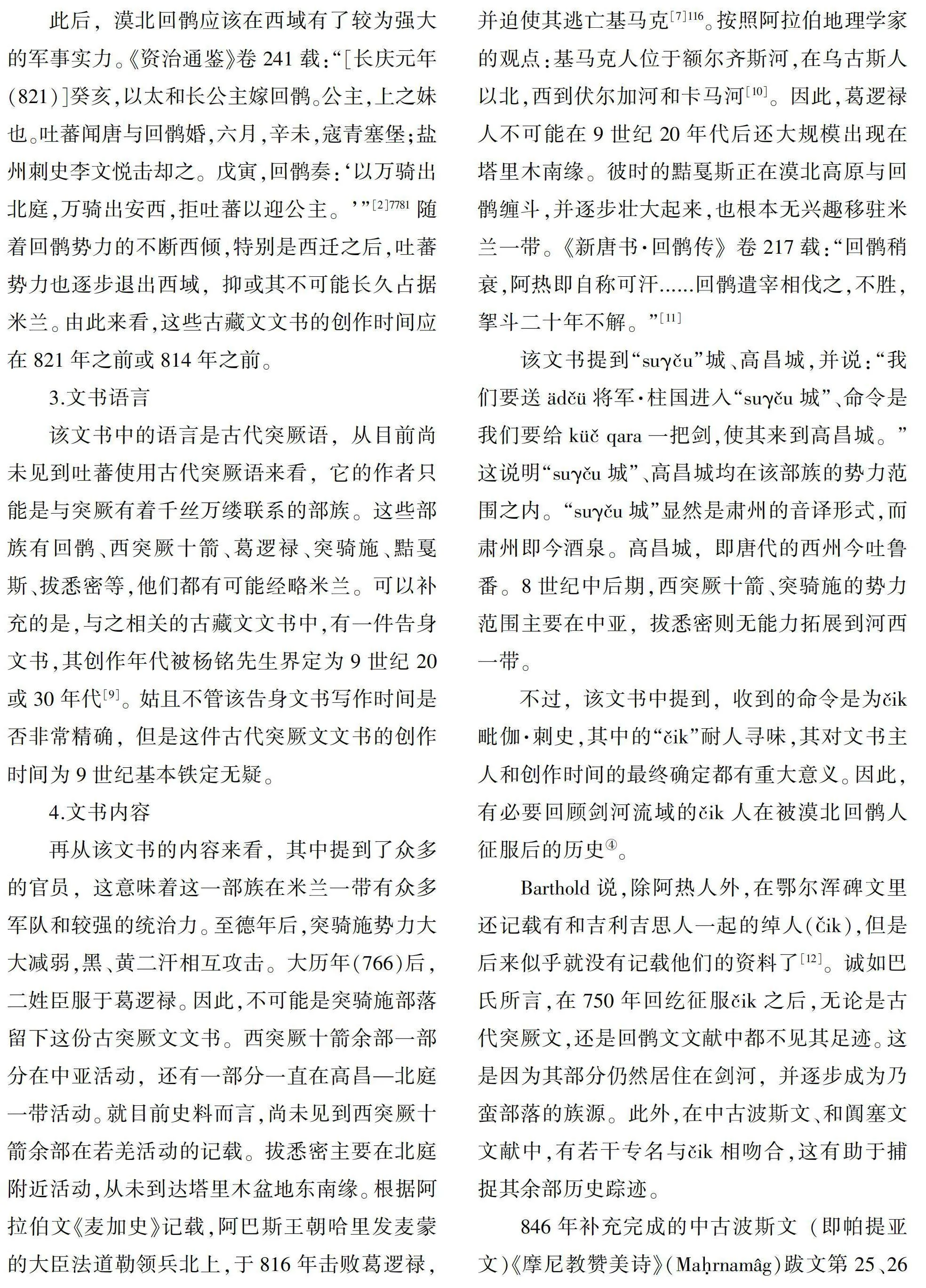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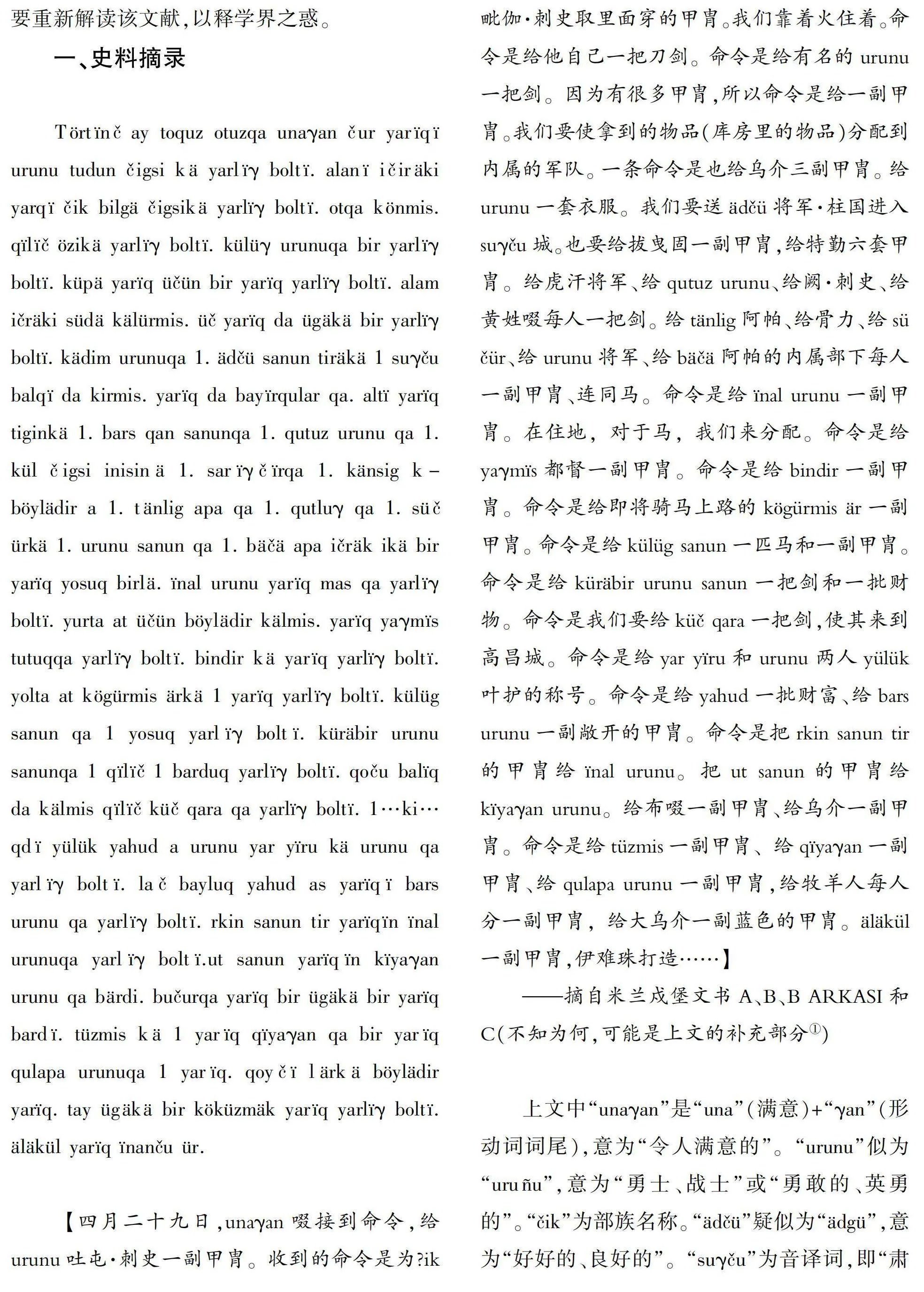

[摘要] 米兰是古丝绸之路南道的商贸中心和进出中亚的重要商道,米兰戍堡古突厥文文书由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所获,其内容主要为军事物资的分配。通过解读文献,可得出有关漠北回鹘西倾、西迁回鹘占据焉耆、回鹘在西域大规模使用回鹘文、西州回鹘与高昌回鹘区别、回鹘改游牧为农业和定居生活、米兰城市属性等结论。研究表明,居住在且末—若羌一线的回鹘人也是来自漠北蒙古高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唐朝西北边境,防御吐蕃人对此地的攻击。同时,米兰不仅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地区,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展示。
[关键词] 米兰; 古突厥文文书; 民族交流; 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K877.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3115(2024)03-0066-11
[作者简介] 洪勇明(1971-),新疆石河子人,汉族,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古代突厥—回鹘和西域—中亚语文学。
[基金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新疆语言安全问题研究”(2023AZD002);新疆大学社科基金培育项目“新疆中华民族共享文化符号研究”(2022)。
古代米兰(miran)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面的绿洲城市,在罗布泊和阿尔金山脉的交汇处。历史上,米兰曾是丝绸之路南道的商贸中心和进出中亚的重要商道。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为了避免横渡死亡之海以及塔里木盆地,往往从米兰南北两边绕行。米兰遗址位于若羌县东80余公里的米兰农场团部东3公里处,是由8座佛塔、3座佛寺、汉屯田水利设施和唐代吐蕃古戊堡遗址组成的一处面积广大的遗址群落。唐古戍堡遗址南临米兰河道,呈不规则正方形,南北宽56米,东西长70米,四角有望楼,西有城门。戍堡中间低凹,北部是阶梯形大坡,从坡底至坡顶依次盖屋,屋皆平顶,下半截挖在土中,上半截土坯砌成。古戍堡曾发掘出大量吐蕃文木简、吐蕃文书和唐代陶片。
米兰戍堡古突厥文文书于1906年年底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所获,地点是唐古戍堡东墙内侧,其内容主要是军事物资的分配。创作时间通常被认为是8世纪末期或9世纪初期。由于在塔里木盆地尤其是丝绸之路南道极少发现古突厥文文献,特别是纸质文书,因此它于史、于文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长期以来,学界有关这一文书的定性都是以斯坦因的观点为依据,鉴于相关研究尚存诸多疑义,本文认为有必要重新解读该文献,以释学界之惑。
一、史料摘录
二、史料分析
(一)文书主人
关于文书主人,斯坦因认为是西突厥,并且说:突厥文文书的出现,显而易见地说明,当时在塔里木盆地遥远的一隅仍然有一些强悍坚毅的西突厥人活动。西突厥人如果不是吐蕃人的同盟,便一定是他们的仇敌[1]。但是从西突厥的活动区域来看,似乎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因为要确定文书主人,首先要确定文书的创作时代。而文书的创作时间,取决于考古发现、西域混战、文书语言和文书内容。
1.考古发现
根据斯坦因的记录,这件古突厥文文书出自米兰古城东南角。在其中两间大屋子里塞满了垃圾和大量的古代文书(大都是吐蕃文/古藏文文书),主要是佛经和军事方面的内容,其他是一些琐碎的公文文书。由于军事方面的内容大都是边陲屯戍需要粮草、求援和军队调动的情况,因此可以推测此时吐蕃在米兰一带驻扎着大量军队。此外,由于这批文书多达1000多件,说明吐蕃至少在此连续经营生活多年,才可能产生如此庞大的文书。由于该文书是夹杂在大量的吐蕃文书里面的,所以其创作时间可能与后者相去不远。同时,因这批文书中没有一件汉文文书,说明此时唐朝的统治影响已经在此大为削弱。唐朝势力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大量减弱,应当是在751年“怛罗斯之战”以后。由此可以推定这件出土于唐古戍堡的古突厥文文书应写于751年之后,甚至是数十年之后。
2.西域混战
吐蕃从7世纪初叶建立地方政权之后,就与西域发生关系。《资治通鉴》卷201载:“[咸亨元年(670)]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2]6360长寿元年,吐蕃在西域的势力基本被清除。《资治通鉴》卷205载:“[长寿元年(692年)]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2]6481焉耆、于阗的收复,意味着吐蕃暂无可能在若羌—米兰一线大量驻军。开元初,吐蕃借道小勃律进攻安西四镇,遭到严重挫折。随着唐朝在葱岭地区外交和军事活动的胜利,吐蕃不得不谋求从图伦碛东进入西域。在这一道路上,若羌具有举足轻重的军事地位。吐蕃若想从此进入西域,势必首先要占领若羌。吐蕃文《大事记年》载:“及至猴年(720年)东突厥之使者前来致礼……冬……攻陷唐之Sog song城。”[3]白桂思指出:“Sog是古藏文对名词Sog dag(粟特人)的简写形式。”[4]而“Sog song城”即石城镇(今若羌),乃粟特康国大首领康艳典所建立②。很显然,在720年之后,吐蕃人就可能进驻米兰了。不久之后,由于在小勃律失利,吐蕃退出西域。《资治通鉴》卷212载:“[开元十年(722年)八月],癸未,吐蕃围小勃律王没谨忙,谨忙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蒿曰:‘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蒿乃遣疏勒副使张思礼将蕃、汉步骑四千救之,昼夜倍道,与谨忙合击吐蕃,大破之,斩获数万。自是累岁,吐蕃不敢犯边。”[2]6764
“安史之乱”后,西域政治情形发生巨变。唐朝戍边部队的离开,为吐蕃再次进入西域提供了契机。王尧认为: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后,河陇以西之地尽失,只有若干孤城在吐蕃包围之下苦战苦撑。建中二年(781)以后,河陇、西域一带都是吐蕃的势力范围[5]。王小甫推测:石城、屯城复入吐蕃乃至德、乾元年间[6]。自此以后,石城一带就被牢牢地控制在吐蕃手中。从阿拉伯史料来看,9世纪初吐蕃似乎仍掌控着北庭—高昌以西、以南的地区。阿拉伯文《历代先王与帝王史》记载,公元808-809年左右,位于锡尔河(中国称为药杀水)和阿姆河流域的康国动乱达到了高潮。起义军首领拉菲厄的手下,存在大量来自中亚的人员,其中赫然包括“吐蕃的军队”[7]113。这些吐蕃军队前往康国,从塔里木盆地南缘或北缘显然比翻越昆仑山脉要方便得多③。
元和年间,漠北回鹘对西域的吐蕃和葛逻禄联盟展开攻击。《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部分第20行载:“□□□□□攻伐葛禄、吐蕃,搴旗斩 ,追奔逐北,西至拔贺那国,俘获人民及其畜产。”[8]在这次征伐中,吐蕃的势力基本被逐出西域,漠北回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此地。同时,这次征伐也是漠北回鹘国势西倾的主要体现。根据该碑的粟特文部分有“马年”的记载,可以推测出立碑时间是公元814年,此次征伐的时间则可能就在吐蕃援助拉菲厄起义之后。阿巴斯王朝第五任哈里发哈伦·赖世德的次子麦蒙为第二王储,驻守呼罗珊首府木鲁。他在与其兄长艾敏的争斗中落于下风,因此,准备逃离呼罗珊。阿拉伯文《历代先知与帝王史》中记载,公元810年麦蒙对他的大臣说:“事已至此,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我想我还是放弃王位投奔吐蕃国王吧!至少他能保护我的生命安全,免受这些人的攻击。”[7]114这说明公元810年吐蕃在中亚和西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漠北回鹘征讨吐蕃的时间应在公元810年以后、814年之前。
此后,漠北回鹘应该在西域有了较为强大的军事实力。《资治通鉴》卷241载:“[长庆元年(821)]癸亥,以太和长公主嫁回鹘。公主,上之妹也。吐蕃闻唐与回鹘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盐州刺史李文悦击却之。戊寅,回鹘奏:‘以万骑出北庭,万骑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2]7781随着回鹘势力的不断西倾,特别是西迁之后,吐蕃势力也逐步退出西域,抑或其不可能长久占据米兰。由此来看,这些古藏文文书的创作时间应在821年之前或814年之前。
3.文书语言
该文书中的语言是古代突厥语,从目前尚未见到吐蕃使用古代突厥语来看,它的作者只能是与突厥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部族。这些部族有回鹘、西突厥十箭、葛逻禄、突骑施、黠戛斯、拔悉密等,他们都有可能经略米兰。可以补充的是,与之相关的古藏文文书中,有一件告身文书,其创作年代被杨铭先生界定为9世纪20或30年代[9]。姑且不管该告身文书写作时间是否非常精确,但是这件古代突厥文文书的创作时间为9世纪基本铁定无疑。
4.文书内容
再从该文书的内容来看,其中提到了众多的官员,这意味着这一部族在米兰一带有众多军队和较强的统治力。至德年后,突骑施势力大大减弱,黑、黄二汗相互攻击。大历年(766)后,二姓臣服于葛逻禄。因此,不可能是突骑施部落留下这份古突厥文文书。西突厥十箭余部一部分在中亚活动,还有一部分一直在高昌—北庭一带活动。就目前史料而言,尚未见到西突厥十箭余部在若羌活动的记载。拔悉密主要在北庭附近活动,从未到达塔里木盆地东南缘。根据阿拉伯文《麦加史》记载,阿巴斯王朝哈里发麦蒙的大臣法道勒领兵北上,于816年击败葛逻禄,并迫使其逃亡基马克[7]116。按照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观点:基马克人位于额尔齐斯河,在乌古斯人以北,西到伏尔加河和卡马河[10]。因此,葛逻禄人不可能在9世纪20年代后还大规模出现在塔里木南缘。彼时的黠戛斯正在漠北高原与回鹘缠斗,并逐步壮大起来,也根本无兴趣移驻米兰一带。《新唐书·回鹘传》卷217载:“回鹘稍衰,阿热即自称可汗......回鹘遣宰相伐之,不胜,挐斗二十年不解。”[11]
5.最终定论
基于这批古藏文文书的创作时间,可以将这份古代突厥文文书的创作时间确定为元和八年(814)以后。这是因为从至德年间到元和八年(756-814)是吐蕃较为牢固地掌控丝绸之路南道的时间,而古代突厥文文书则反映出有大量的非吐蕃军队驻扎在米兰一带。因此,创作时间应在814年之后。
《资治通鉴》卷248载:“[大中二年(848)正月]居三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帅诸胡兵号七万来取回鹘,大破室韦,悉收回鹘余众归碛北。犹有数帐,潜窜山林,钞盗诸胡;其别部庞勒,先在安西,亦自称可汗,居甘州,总碛西诸城,种落微弱,时入献见。”[2]8040对此杨圣敏认为,当乌介可汗已死,南迁回纥崩溃后,庞特勤遂自称可汗。庞特勤称可汗后,则成为河西、葱岭西和天山南北所有回纥部落的共主,这三部回纥人结成了一个松散的西回纥政权。唐人不明这三部回纥之间的关系,而当时又仅与以甘州为中心的河西回纥有直接交往,故误称庞特勤居甘州。庞特勤实际居住在今新疆焉耆、吉木萨尔等地[16]。
公元840年,西迁的一支回鹘庞特勤部迁至焉耆—龟兹一带,焉耆到若羌距离并不遥远,因此这件古突厥文文书的作者当属庞特勤部。盖因只有庞特勤部彼时具有经略高昌、肃州的能力,更有在米兰—若羌驻军的可能。根据现存8世纪用粟特文字母铸造的突骑施钱币和20世纪50年代在蒙古乌兰浩木地方发现的八行回鹘文《乌兰浩木碑》(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回鹘文碑铭,立碑时间大概为863-866年⑤)来看,这件古突厥文文书的创作时间当为840-863年[17]。
(二)文书背景
早在漠北回鹘牟羽可汗时期,回鹘君臣就可以自由出入西域的高昌—焉耆一线。《宋史·高昌传》载:“高昌……唐贞观中,侯君集平其国,以其地为西州,安史之乱,其地陷没,乃复为国,语讹亦云‘高敞’,然其地颇有回鹘,故亦谓之“回鹘。”[18]及至元和年间,随着吐蕃、葛逻禄势力被从高昌—焉耆一线逐步荡除,回鹘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进驻若羌。实际上,这些回鹘军队驻扎于此的目的,就是封堵吐蕃进入丝路北道的主要通途。关于吐蕃进入西域的道路主要有三条:东道出柴达木盆地西北,沿阿尔金山北麓到若羌绿洲,从若羌向西北去焉耆或向西去和田均需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道有两条路线,一条大致就是今天新藏公路所经过的路线,即穿过夹在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的阿克塞钦地区;另一条是从西藏高原西北的拉达克向北翻越喀喇昆仑山口、苏盖提山口,过赛图拉向西北直下塔里木盆地西南斜坡上的叶城,或者直接向北由桑株达坂翻越昆仑,再向东去和田或西去叶城。从上述线路可以看出,由东道进攻高昌和北庭,是吐蕃的最佳途径。因此,守住若羌,就是守住了高昌—北庭的南大门。
至于学界通常认为:直至9世纪中叶,吐蕃势力才撤出和阗地区(包括且末—若羌一线),这一观点似乎并不准确。首先,元和年间,漠北回鹘就对西域的吐蕃和葛逻禄联盟进行反击,此役应当重创了二者。或者至少稳定了回鹘在丝路北线的统治,进而能够随时攻击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地。其次,在今拉达克德兰茨村发现的粟特石刻铭文曰:“二百一十年,来自撒马尔罕(samarkander)的诺斯凡作为大使,致礼吐蕃可汗(khagan)。”[19]据研究,这件铭文的年代当在825年4月24日至826年4月12日,它反映了9世纪上半叶,吐蕃与康国交使的情况[20]。康国使者出访吐蕃,不走自然条件较好的东线,反而去走条件恶劣的中线,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和阗已不在其控制范围内。至于汉文史料提及元和三年吐蕃占据安西,因为回鹘的反击,时间不会太久。《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部分载:“……复(后)吐蕃大军,围攻龟兹,天可汗领兵救援。吐蕃落荒,奔入于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尸骸臭秽,非人所堪,遂筑京观,败没余烬。”[8]160根据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题记中载有回鹘在西域的统治区域北庭、高昌、龟兹(包括佉沙即喀什和拨换即阿克苏)、焉耆、于术等地可知,其在846年前已经较为牢固地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北缘。在这种情况下,吐蕃军队孤守和阗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是时其已经退出了和阗,或者说其影响力已经大为减弱了。
(三)米兰守军
长庆元年(821)回鹘保义可汗死后,回鹘国势就日益衰落。据此可知,这些黠戛斯人可能是在821年之前来到米兰一带的。大历年后,葛逻禄的势力日渐强盛,徙居碎叶川。突骑施黄、黑二姓势力衰微,以致后来臣服葛逻禄。半个多世纪之后,突骑施黑姓基本上已经完全并入葛逻禄。突骑施黄姓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似乎更长一些,大概直到元和年间。薛宗正认为,至于黄姓突骑施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好像更长一些,至安西都护陷落的前一年,即元和二年(807),仍与唐保持着宗藩关系[21]。很有可能就是元和年间,保义可汗西征时,将部分黠戛斯和突骑施黄姓征服并内属,进而安置在若羌一带,协助驻扎此地的回鹘军队守卫米兰古城。但是由于吐蕃势力较大,他们不得已而臣服。后来,当西迁的庞特勤率部到达焉耆并瓦解吐蕃势力之后,原驻米兰的回鹘军队及其仆从部落立即归顺,并继续防御吐蕃势力的再次恢复。
三、相关结论
(一)西倾回鹘与漠北回鹘的松散关系
自9世纪初,漠北回鹘的势力就不断西倾,至西迁前,其在塔里木盆地的实力达到极盛。彼时尽管其主体部落仍在漠北,但是已有部分部落在此建立地方政权。这些政权和漠北回鹘之间可能是一种羁縻关系,或者较为松散的隶属关系。这主要体现在漠北回鹘受到内部分裂和黠戛斯攻击的威胁时,并未见到前者回防或援助行为。但是对于西迁的回鹘,他们抱着欢迎的态度,这也使得较为落魄的后者很快站稳脚跟。漠北回鹘的西倾,主要是填补唐朝中央政权被迫退出西域后所留下的权力真空,旨在为唐朝继续镇守边关,守卫丝绸之路的安全。其主要表现就是通过西征,击败天山以北的黠戛斯人、天山东部和塔里木盆地的吐蕃、吐火罗、七河流域的葛逻禄、突骑施联盟等。这些被击败的部族,有些臣服于回鹘,有些则在一些孤立的据点继续抵抗。同时,位于河西的一些回鹘部落则是在漠北回鹘覆灭之前就已迁居至此。他们早在840年前后,就曾一度占据肃州、甘州。后因吐蕃在当地的势力较大,他们要么是撤出四处流窜,要么就是归附吐蕃。这些民族之间的分分合合,是西域各民族在唐代中央政权有形无形主导下的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
(二)西州回鹘和高昌回鹘的区别
在高昌回鹘之前,即840年初至860年之前,存在一个很重要的回鹘地方政权庞特勤部。西迁不久的庞特勤部政治中心先在安西(即焉耆),其辐射范围东至甘州、北至高昌、南至若羌、西至七河流域。但是庞特勤政权的统治力量较为薄弱,且由于其统治中心不断游移,故在史书中记载得较为混乱。大概在850前后,受到盘亘在高昌和焉耆之间的吐蕃残部的牵连,他们遭到回鹘仆固部的攻击,被迫离开焉耆,向西迁徙,并在安西驻扎。10世纪中叶,庞特勤部在葱岭以西建立喀喇汗王朝。此前其驻地安西非彼安西,当为今库车和新和之间的通古斯巴西(意为“猪首”)。这是因为唐代不同时期安西位置有所改变,而汉文史书不加分辨所致。唐朝中央政权于856年计划册封的嗢禄登里罗汨没密施合俱録毗伽怀建可汗不是庞特勤,可能是仆固部可汗。860年,唐朝中央政权册封的云麾将军颉干伽思宇合逾越密施莫贺是西州回鹘首领,但是他并非隶属于仆固部。866年,北庭回鹘仆固俊攻克西州,并降服包括胡、汉在内的诸部。因此,从严格意义上看,840-865年属于西州回鹘时期,其特点就是西州地方政权的统治者不是同一王统;866年之后才属于高昌回鹘时期,其特点就是王统的一致性。
(三)回鹘文在西域的普遍使用时间
回鹘文来源于古代粟特人使用的草体粟特文,粟特字母是由一种地区性的草体阿拉美字母或早期巴拉美字母演变而来。在塔里木盆地首先使用粟特文字母书写古突厥语的是黄姓突骑施,地点是在安西(今库车)及其周边地区。9世纪初西倾的回鹘人以及西迁至此的庞特勤部受到黄姓突骑施的影响,也开始使用粟特文字母拼读回鹘文。是故,回鹘人对回鹘文的大规模使用时间为西迁西域之后,即846年或848年以后。使用回鹘文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使用粟特文的粟特人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均占优势,出于沟通和交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西迁回鹘人积极从事丝路商贸、更加主动融入丝路文化和共享精神生活的需要。及至9世纪60年代,无论是西迁安西,亦或是葱岭西的回鹘人都放弃古代突厥文,已经普遍使用回鹘文。反观西迁河西的回鹘诸部,直到10世纪还在使用古代突厥文(古突厥文《占卜书》出自敦煌藏经洞,写作时间9-10世纪)。
(四)西域回鹘的定居和城市生活
公元800年前后西倾以及840年西迁的回鹘人都选择了相对稳定的定居和城市生活,这与其在漠北高原的普遍游牧生活形成一定的反差。同时,随着定居城镇的开始,其行政管理水平也有所提高。采取这一生活模式,与塔里木盆地的绿洲生态相适应,也是对漠北回鹘覆亡的政治反思,更是对唐代中央政权、吐蕃在西域的社会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继承和发展。前述西域各地回鹘与漠北回鹘之间的松散关系实际就是中央政权羁縻制的一种地方体现,其后的高昌回鹘亦如此。在其职官体系中,有相当多数都是虚职,这与中央政权带有荣誉称号的虚职一脉相承。安西都护府和吐蕃治下的土地分配制度、经济契约协议得到继承和发展,以致于回鹘文世俗文书中处处可见其身影,从契约中的词汇、短语或套语的借贷,一直到契约文化的影响。此外,作为安西都护府四镇之一的焉耆以及西州,原本就有大量的汉族居民,发达的农业经济和生产技术也对回鹘产生巨大影响,促进其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
(五)西域回鹘的二重化军制
漠北回鹘实行的是军民一体制,即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使用的兵器是游牧射猎的工具(普通的刀和剑),以骑兵为主。西倾和西迁的回鹘诸部则采用军事供给制,即由兵站集中供养财富和兵器。尤其是甲胄和刀剑的普遍分配,这表明其武器配置和作战形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弓箭主要用于骑兵远距离进攻,刀剑则用于身着甲胄近距离交手。唐朝军队在近战时多为重甲化,即穿着铠甲,手持重刀(即陌刀,全长1丈,重15斤)。这些重甲化的唐朝军队在与敌人骑兵的交战中,屡屡造成对手人马俱碎的恐怖杀伤力。这些身处西域的回鹘人在与唐朝军队的合作中,学习其布阵战法、兵器配备,用于战斗。不过该文书显示:其军政一体制仍沿用漠北回鹘,主要有两套官职系统:突厥旧制和中原官制。即便在突厥旧制中,还有部分官职来源于中原王朝。由此可见,唐代中央政权的军事和行政管理体制也同样被其所吸收。
(六)米兰是民族交流的重要区域
处于丝路南道的米兰在回鹘西倾之后就成为其一个主要聚居地,西迁后更成为回鹘庞特勤部军事和行政副中心。彼时真正的中心可能距此并不远,但不会是高昌和甘州,焉耆的可能性比较大。米兰副中心的位置,是由其在中央政权经营西域的地位(楼兰之伊循)和吐蕃经略的基础(修筑军事堡垒)所确定的。同时,米兰也是一个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地,这主要表现在该文书所记载的部族上。文书中不仅记载有回鹘人,还有他们的宿敌突骑施和黠戛斯人等。从历史上看,米兰应当还有汉族遗民,只是他们不是官吏而已。这些曾经的敌手是时在回鹘人的协调下,和谐地进行政治和军事活动。戍堡附近佛教遗址上的壁画有翼天使的创作风格属于犍陀罗艺术,它是西域佛教艺术和希腊艺术的结合,更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体现。西倾和西迁回鹘的较早汇聚中心焉耆更是汉民族和当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舞台,其中的一个代表就是具有中原艺术风格的焉耆佛坛顶部的绘画。
[注 释]
①文中的古代突厥文部分是参考土耳其学者奥尔浑的转写,笔者也对其中个别词语进行了重新转写和解释。奥尔浑的转写是依据斯坦因所获文献,于20世纪30年代完成。近年来,IDP(国际敦煌项目)对斯坦因所获文献进行高清晰度还原,并进行展示。根据笔者的文献常识,IDP的还原度不可能达到奥尔浑所获文献的清晰度,毕竟二者相隔近百年。
{2}关于石城居民为粟特移民一说见羽田亨的《中亚文明史》:据敦煌出土的一件文书可知,在此数年(694年)前罗布泊的石城镇的首领为撒马尔罕出身的摩尼教僧侣。
{3}对于白桂思的学术观点,尤其是带有典型的西方式双标的言论,本人并不苟同,甚至强烈反对。本文只是转引白桂思著作中的历史资料,对于其观点并未参考引用。
{4}王媛媛在《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跋文译注》(原载《西域文史》第二辑2006年,第134页)中提及冯·佳班(Gabain)、黄盛璋对cyyg的看法,本文对二氏的观点表示怀疑。本文有关čik的论述,均引自洪勇明的《古突厥文碑铭中čik刍议》,原刊于《新疆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141页。
{5}在前期的研究中,本人也对回鹘人在西域使用回鹘文的时间表示过怀疑。经过详细考证,我们认为:《乌兰浩木碑》的竖立时间当为863-866年,以865年为宜。当然,考虑到张义潮奏折的传递时间,也可能为864年。据此可知,回鹘文在西域的普遍使用时间当在回鹘西迁之后。
[参考文献]
[1]斯坦因著,巫新华译.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4.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Beckwith,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Ag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pp. 92.
[4]白桂思.中亚的吐蕃帝国[M].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92.
[5]王尧.吐蕃文献选读(增订本)[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74.
[6]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16.
[7]白桂思著,付建河译.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
[8]林梅村.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J].欧亚学刊,1999(1):160.
[9]杨铭.新疆米兰出土的一件古藏文告身考释[J].敦煌学辑刊,2012(02):18.
[10]佚名著、王治来译注:世界境域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82.
[11]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149.
[12](俄)威廉·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5.
[13]洪勇明.《摩尼教赞美诗》宗教信息考[J].北方考古,2024(01):224.
[14]Bailey, SAKA DOCUMENTS(Ⅴ),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pp. 107.
[15]Bailey, THE STUDY OF KTⅡ42-48 PLATES,JRAS,1912:186;Bailey, THE STUDY OF KTⅡ42-48 PLATES.
[16]杨圣敏.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99.
[17]洪勇明.回鹘文文献西域史料辑注[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2:118.
[18]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2.
[19]王尧.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35.
[20]Geza Uray, Tibets connections with Nestorianism and Manicheism in the 8th-10th centuries,in: Ernst STEINKELINER and Helmut TAVSCHER(eds.),Contributions on Tibetan Language,History and Culture,Wien: Arbeitskreis für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y Wien,1983,pp. 107.
[21]薛宗正.中亚内陆——大唐帝国[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