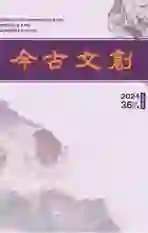跨文化视角下毕飞宇《青衣》法译本的改写与误译
2024-09-20李玟静
【摘要】中国当代作家毕飞宇所著的中篇小说《青衣》于2003年被翻译成法语,在法国读者中收获了较好的反响。《青衣》原著糅杂了中国文化、传统艺术和女性问题等元素,这些元素既是小说《青衣》的亮点,同时也是该作翻译的难点。译者克劳德·巴彦在翻译过程中基本保留了《青衣》原本的面貌,但为了克服作品中跨文化元素给翻译带来的困难,也对原文进行了一些改写,同时不可避免存在误译的情况。本文从跨文化视角出发,简要梳理了法译本中的改写和误译,并分析其原因,总结翻译策略。本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应该回到文学自身,译本需要尽可能保留源语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特色,文学作品的域外传播应该循序渐进,才能收获真正的读者。
【关键词】《青衣》;法语翻译;跨文化;改写;误译
【中图分类号】H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6-009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28
基金项目:本文为李巍主持的2020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毕飞宇作品在法国的译介研究”(项目编号:20WWB006)的研究成果之一。
一、引言
2008年,中国作家毕飞宇的中篇小说《青衣》入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复评名单,收获国际文学界的好评。这部作品能得到外国读者认可,其外语译本功不可没,尤其是美国译者葛浩文的译本(The Moon Opera)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作品跨文化传播的一个典型案例,成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
目前国内对《青衣》译本的研究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围绕《青衣》的英译本,探讨译者的翻译策略,如张琳琳结合英译本中对“青衣”及其他京剧行当的翻译,解析文化翻译中“归化异化”,并总结京剧术语的翻译策略。[1]二是以《青衣》为案例,讨论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如吴赟通过剖析《青衣》在英语国家的译介过程、译本形态与接受情况,为当代中国文学对外传播提供了思路。[2]三是结合《青衣》英译本,解读翻译现象和翻译理论,如康美玲、陈芳蓉以《青衣》英译本为例,分析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的具体表现。[3]
不难看出,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以《青衣》英译本为对象,其他语种译本的研究相对不足。《青衣》英译本的版权由英国电报书局购得,而“电报书局之所以选择购买英译版权,原因正在于他们读到了这两部小说的法语译本,认为非常出色,应当引入英语世界”[4]。法译本作为《青衣》最早也是相对完善的外语译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尝试从跨文化视角出发,探究《青衣》法译本对原著的改写及误译,分析其原因并总结翻译策略,以期对《青衣》的翻译研究添砖加瓦,为中国文学作品域外传播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青衣》在法国
《青衣》由克劳德·巴彦(Claude Payen)翻译完成,经由毕基埃出版社(E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于2009年5月首次在法国出版发行。译者巴彦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文学翻译家,法国教育骑士勋章获得者。[5]2003年,毕飞宇与法国毕基埃出版社签约,出版社随后翻译发行了《青衣》《推拿》等多部毕飞宇的小说。
毕飞宇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日常的、俗世的、带着烟火之气的中国经验[6]。在法国亚马逊网站上《青衣》评分是4.8分(总分5分)。其中署名为“Ladybug”的读者评价道:“这是一部简短而有力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女主人公内心的挣扎……毕飞宇极为擅长描写他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7]
另一位署名为“antigone”的读者评价道:“我喜欢这部小说的氛围,以及它对于京剧世界的展现,同时这部小说还带我们走进了当下的中国。”[8]在《青衣》中,京剧无疑是西方读者最感兴趣的文化元素。京剧作为一种中国传统艺术,带有独特的东方神秘感,引起了法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对中国文学的探索欲。
“相较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规模更大,受到的关注更多……当代文学之所以相较于现代文学更受法国读者的欢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具有更大的认知价值,它可以满足法国读者了解中国社会现状的欲望和好奇心。”[9]“他们试图通过作品中的‘中国元素’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地域文化。”[10]《青衣》一书受到法国读者的好评,不仅因为其较高的文学价值,还因为它以京剧、神话传说以及中国现当代社会为舞台,向法国读者展现了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传统之美,也为法国读者了解中国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提供了途径,具有一定的认知价值。
三、法译本《青衣》中的改写及其原因分析
《青衣》这部作品糅杂了中国文化、传统艺术和女性问题等元素,并且蕴含了作者毕飞宇对于诗性语言的追求。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这些元素既增加了《青衣》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也使其不得不面临文化差异的困境,因而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作出一定改写。
例1:“十九岁的燕秋天生就是一个古典的怨妇……对着上下五千年怨天尤人,除了青山隐隐,就是此恨悠悠。”[11]
翻译:Elle semblait faite pour exprimer la douleur...exprimait naturellement la tragédie et toute la douleur de cinq mille ans,les vertes montagnes et les regrets éternels.[12]
“怨妇”形象常常出现在古代诗歌当中。当女子被弃,或当丈夫因功名、游历、征戍、经商等因素离家远行,她的心中常常充满愁怨。唐诗中的怨妇形象多姿多彩,它蕴涵着深刻的悲剧意蕴。[13]原文“古典的怨妇”可以唤起中国读者的联想,但在法国文化中没有可以与之相对等的概念或形象,因而译者将“古典的怨妇”改写为“她为表达痛苦而生”。
“青山隐隐”取自唐代诗人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这句诗描绘了扬州山清水秀的风光,给人以隐约迷离之感,极具柔情。“此恨悠悠”取自唐代诗人白居易《长相思·汴水流》,这句则是描绘了一位妇人思念她未归的丈夫,饱含情意与愁怨。在译文中,这两句典故被简化成“青色的山岭与永恒的悔恨”,译者在此处不译诗歌,因为中国古典诗歌中包含的韵律和意蕴难以被完全移植到法语中,且法国读者鲜少接触中国古典诗歌,无法感受原文的意蕴。
《青衣》原著中存在多处诗歌的引用,而译者巴彦在翻译诗歌时大多采用了意译和省去不译两种方式,主要原因在于:诗歌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往往会变得臃肿,损失掉原本的美感、韵律。小说中的诗歌翻译则更加困难,诗歌会被赋予超出其本身的含义,描绘景色的诗歌不再会是单纯的景色描写,而是与文学作品的情节、主题、文本逻辑相关联起来。再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很难体会到诗歌所营造出的氛围,以及诗歌所具备的历史气息。因而文学作品中的诗歌翻译以意译为佳,省略诗歌的形式,旨在翻译诗歌的本义,并力求还原其在文中起到的作用,如塑造人物、情节隐喻等。在不重要的篇章中,译者也可以选择省去不译。
例2:“《奔月》阴气过重,即使上,也得配一个铜锤花脸压一压,这样才守得住。后羿怎么说也应当是花脸戏,须生怎么行?就是到兄弟剧团去借也得借一个。否则剧组怎么会出那么大的乱子,否则筱燕秋怎么会做那样的事?”[11]
翻译:Dans cet opéra,l’élément féminin était trop fort.Il aurait fallu trouver un tongchui hualian pour le contrebalancer.De toute façon,le rôle de Hou Yi devait être tenu par un hualian et non par un xusheng.Si on avait emprunté un hualian à une autre troupe,l’incident ne se serait peut-être pas produit et Xiao Yanqiu n’aurait pas eu cette réaction qui devait causer sa perte.[12]
“阴气”也指女子之气,后文写道“用铜锤花脸压一压”,实际上就是指在戏剧中加入男性角色调和。在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中,阴与阳对立,阴气同样也含有抑制、负面、阴郁的意思,阴阳失衡在中国文化中意味着混乱,所以后文写道“剧组出大乱子”。译者将“阴气”译为“女性元素”,一方面是“女性元素”比较符合“阴气”所表达的女人之气的意思,另一方面改写成“女性元素”,也是与“铜锤花脸”所代表的男性角色相照应。然而,由于舍弃了“阴阳”的表达,“阴气”代表的丰富含义流失了,没能传达出剧组阴阳失衡,造成混乱的寓意,不能与后文照应,译本读者将难以理解剧组没有“铜锤花脸”和剧组出大乱子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这段叙述中,译者采用音译的方式翻译“铜锤花脸”,再利用注释对其加以解释,而这种翻译策略也被译者广泛运用于本书中其他许多京剧术语的翻译。文化术语由于其专业性,使译者难以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找到其对应概念,而音译可以填补汉语和法语间存在的词汇空缺,成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音译直接作用于语言文化的不可译现象,具有明显的身份优势……某些专有名词并非成分意义的叠加,必须求助音译。”[14]此外,因为音译保留了词汇原本的读音或书写形式,它能更好地传达文学作品本身的美感和韵律。
尽管音译会造成不同文化读者的阅读障碍,例如音译可能会带来过多缀于文本后的解释性注释,但这种“障碍”能促进两种文化之间的交融,使得文化概念能够以其本来的面目与读者见面。
四、法译本《青衣》中的误译及其原因分析
(一)正文中的误译
面对中法文化的差异,《青衣》的法译本中也不免存在一些误译。
例1:“气得团长冲着导演大骂,谁把这个狐狸精弄来了!?”[11]
翻译:Aussi le metteur en scène avait-il souvent piqué des crises,se plaignant qu’on lui avait donné une actrice qui eût été plus è sa place dans un rôle de séductrice que dans celui d’une héroïne révolutionnaire.[12]
在原文中,由于筱燕秋的表演不佳,戏剧团团长批评导演选角出了差错。而在法译本中,译者译为“导演抱怨”选角的问题。说话的人物与原文不符,原文是团长说的话,译文则是导演说的话,由团长批评导演变为导演自己抱怨。译者混淆了戏剧团中团长和剧目导演的分工与定位。根据《青衣》中的细节描写,团长一般负责戏剧团的整体运作,而导演主要负责某一出剧目的排练与演出。
例2:“嫦娥在众仙女的环抱之中做无助状,做苦痛状,做悔恨状,做无奈状,做盼顾状。”[11]
翻译:Désemparée,vulnérable,en proie aux regrets,malgré son malheur,elle garde encore l’espoir.[12]
“无助、苦痛、悔恨、无奈、盼顾”这五个词语实际上描绘了筱燕秋在扮演剧中嫦娥时所流露出的神态,在原文中可以将“无助、苦痛、悔恨、无奈、盼顾”理解为并列的状态。而译者巴彦在译文中增添了逻辑连词,将此句译为:尽管遭遇不幸,绝望、脆弱而又充满遗憾的嫦娥依然怀着希望。之所以出现这种误译,可能是因为译者对《嫦娥奔月》剧目的了解不全面,从而产生了理解偏差。
(二)注释中的误译
在《青衣》中有一处对筱燕秋的弟子春来的描写:“虽说只是嫦娥的B档,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二郎神的灵光已经照亮春来了”[11],译者巴彦采用音译将“二郎神”译为“erlangshen”,随后在注释中译者解释其为:一位拥有三只眼睛的神仙,可以驱逐恶魔,并给他看到的人带来好运。但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二郎神并不被认为能够为人带来幸运。“二郎神的灵光照亮春来”可能意指春来受到戏曲之神的青睐,因为自宋代开始,二郎神因被形容为相貌英俊、性好游逸的男子,形象类似梨园中俊美的戏曲表演者,也被当作戏曲之神,受到民间戏曲行业的信奉。
译者巴彦对于二郎神的误解,一个原因可能是原文的叙述具有一定迷惑性,容易使读者将二郎神理解为带来好运的神仙;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神话传说历史悠久、版本众多,二郎神的形象更是复杂多变,对外国译者理解原文造成了障碍。
当文本翻译涉及宗教神话相关内容时,译者不妨向原作者寻求帮助。为了避免因知识储备不足和文化背景差异而产生误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同作者进行充分沟通与交流。《青衣》英文版的译者葛浩文谈及他与作者毕飞宇的交流时说道:“像毕飞宇的《青衣》,恐怕我们两个人电子邮件里交流的字加起来,比整部小说的字数还多。”[15]由此可见,一本完善成熟的文学作品译本是离不开译者与作者的充分交流与沟通的。此外,译本在出版前也可先由具有源语文化背景的读者进行审阅,减少误译的出现。
五、总结
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还是应该回到文学自身,尊重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以更多的具有独持中国文学美学精髓的作品,渐进式地吸引读者,召唤读者,影响读者。[16]《青衣》的成功,既是由于作品自身的优秀,也是由于《青衣》译本的优秀。从《青衣》的跨文化传播来看,优秀的翻译不仅需要译者保留作品本身的精髓,还原作品中的文化特色,同时还需要对原文进行改写,使之适应外语文化生态和外国读者的阅读。
对于中国文学作品而言,本土性是不可割舍的灵魂,民族文化更是逃不开的母题,它们使文学作品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避免被扁平化、通俗化;同时文学作品外译的“水土不服”,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感,即所谓的“异域情调”,正是吸引外国读者的重要一环,它加速了中国文化及文学的对外传播。文学的“灵”极为重要,译本不应为了迁就读者而放弃作品特色,但也应当承认:翻译中的改写也是必要的,作品的传播应该尊重读者,倘若过于急切地向读者灌输中国文化,那么作品将很难获得真正的读者,无法使人自发去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学。“‘强推’往往取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可能引起文化接受者的‘逆反心理’。”[17]
此外,好的翻译当然需要好的译者。目前法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汉学家在研究和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如何碧玉、安必诺等。但中国文学在法国的进一步传播,需要有更多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译者参与其中。文学翻译是一种双向的文化建设,但又不得不注意到东西方的文化间的重大差异。应当承认,相较于法国译者,中国译者更能理解和发掘出文学作品中的中国美学。
综上所述,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青衣》的法译本是中国文学作品域外传播中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它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张琳琳.从“青衣”等京剧术语的英译看文化翻译的归化和异化[J].上海翻译,2013,(04):41-43.
[2]吴赟.西方视野下的毕飞宇小说—— 《青衣》与《玉米》在英语世界的译介[J].学术论坛,2013,36(04):93-98.
[3]康美玲,陈芳蓉.解读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葛浩文《青衣》英译本为例[J].英语教师,2017,17(19):135-139.
[4]胡安江,胡晨飞.美国主流媒体与大众读者对毕飞宇小说的阐释与接受——以《青衣》和《玉米》为考察对象[J].小说评论,2015,(01):86-94.
[5]吴攸,张玲.中国文化“走出去”之翻译思考——以毕飞宇作品在英法世界的译介与接受为例[J].外国语文,2015,31(04):78-82.
[6]赵坤.泛乡土社会世俗的烟火与存在的深渊——西方语境下的毕飞宇小说海外传播与接受[J].当代作家评论,2016,(03):191-199.
[7]Ladybug;Puissant[OL].Amazon Book Reviews,2011.https://www.amazon.fr/gp/customer-reviews/R1GU6R6B03AZ2D/ref=cm_cr_dp_d_rvw_ttl?ie=UTF8&ASIN=2809700893.
[8]Antigone;Orgeuil et théâtre chinois[OL].Amazon Book Reviews,2007.https://www.amazon.fr/gp/customer-reviews/R28F4GNBDFUCRQ/ref=cm_cr_dp_d_rvw_ttl?ie=UTF8&ASIN=2809700893.
[9]许钧.我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J].中国外语,2013,10(05):1+11-12.
[10]李巍.译者、评者与读者:毕飞宇在法国接受的三维透视[J].上海翻译,2022,(04):66-71.
[11]毕飞宇.青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12]Bi Feiyu.L’Opéra de La Lune[M].Trans.Claude Payen,Paris:Philippe Picquier,2003.
[13]胡秀春.唐诗怨妇形象的悲剧意蕴[J].芒种,2013,(22):102-103.
[14]葛林.音译的身份[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39(01):137-142.
[15]赋格,张英.葛浩文谈中国文学[N].南方周末,2008-3-27.
[16]季进,周春霞.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何碧玉、安必诺教授访谈录[J].南方文坛,2015,(06):37-43.
[17]李巍.从地域性看江苏作家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J].小说评论,2018,(03):129-133.
作者简介:
李玟静,女,汉族,安徽合肥人,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法作家译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