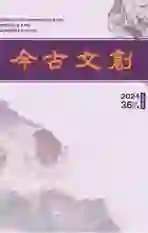曹禺剧作中黑暗意象的延续与个性化塑造
2024-09-20王瑶洁
【摘要】《雷雨》《原野》《日出》《北京人》是曹禺戏剧创作的代表,它们中出现的典型黑暗意象有四个,分别是关着窗户的房子、黑夜、雷雨和黑森林。这些意象在反映社会影响下作家普遍性压抑心理的同时,又体现出曹禺个性化的意象群塑造特点。同时,剧作中的黑暗意象与光明意象并不是二元对立的,黑暗具有生与死的双重意味。黑暗和光明构成了曹禺的生命意识,体现了他对原始生命活力的追求和对黑暗的反抗。
【关键词】曹禺;戏剧;黑暗意象;光明意象;生命意识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6-008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24
20世纪30年代,曹禺创作《雷雨》《原野》等剧作,才真正奠定了话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受到易卜生的影响,他擅长借助意象进行象征,彰显戏剧主题,反映自身对所处时代集体无意识的探索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其中的一类是黑暗型意象,这类意象象征着主人公内心深处挣扎的欲望和对于死亡的本能恐惧,以及一种独特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希望。曹禺的《雷雨》《原野》《日出》《北京人》中始终笼罩着一层悲剧的“命运意识”,通过塑造这类黑暗型意象,而又在这些意象内部生发出人物对于理想和光明的向往,则象征着人对于命运的反叛和洋洋洒洒的生命活力。
一、四部剧作共同的黑暗意象:
关着窗户的房子和黑夜
关着窗户的房子和黑夜是四部剧作共同的黑暗意象,它们在时代的集体特征之下,又体现了曹禺自己的选用偏重。
(一)空间指涉:关着窗户的房子
周公馆永远是这样闷气。但即使这样,整个公馆的窗户依然紧闭着。焦家老屋窗户深深掩下来,屋内烛火跳动,映衬着祭祀香案和鬼神壁画更加诡异。陈白露不喜开窗,所居住的小旅馆,虽有着宽阔的窗,屋里也显得过于阴暗。曾家喜欢将大半壁通大客厅的门扇整个掩闭。房子实际是一种空间上的指涉,限制着人的活动空间,在文学作品中,则代表着一种精神和生存上的困境以及自我的封闭。而关着的窗户则加重了屋宇本身的压迫感。封闭空间自古便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与外界有所隔绝给了文人独处的空间,精神遨游从而文思勃发;另一方面,也有“深院锁清秋”下封闭空间所带来的压抑与焦虑感。这个意象发展到近代,有了鲁迅的铁屋子,巴金的家,钱钟书的围城。密闭的屋子成了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与近代作家的心理境况密切相关。20世纪中国文明迎来了转型的阵痛期,旧秩序分崩瓦解,国家衰败、异族入侵。处于低压状态下的知识分子,既无力于国家的衰败,又迷茫于本土文化的断代和外来文化的泥沙俱下。因此整个心理处于极端压抑之中,进一步反映在作品创作之上,就体现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基调以抑郁低沉为主。所以关着窗户的屋子是包括曹禺在内的近代作家所处时代下自身心理压抑的投射。在曹禺的创作中,关着窗户的屋子作为一种原型意象不是独立存在的,有很多外在因素叠加,加强了其本身的封闭感。《雷雨》中天空上低沉的黑云连同消失的太阳,使得天空在视觉上向下沉。《原野》中秋天萧瑟的黄昏以及狰狞可怖的黑云低低压着地面,黑暗限制了广阔的视野,使人处于恐惧状态之下,带来呼吸急促,增添了原本意象的窒息感。秋天是生命萧瑟的季节,日暮又象征着逝去的光阴,这些意象的使用都是一以贯之的。《日出》中紧紧贴在旅馆前的大楼,不仅人为阻挡了阳光的照射,还在空间上营造了一种逼仄的压迫感。《北京人》中的棺材,是缩小版的曾家。前两部作品,作者采用自然意象,后两部作品,作者使用人造事物,其目的都是辅助主意象关着窗户的屋子,进一步压抑主人公的生活空间,渲染人物所处的生存困境。但是,这些屋子都不是全然封闭的,窗户的存在暗含了和外界沟通的可能性。因此剧本中总会有相对应的广阔的意象存在,消解了过度的压抑情绪。代表工人阶级反抗的鲁大海、黎明前工人们嘹亮的叫号声、呼啸而过的火车和积极的袁教授一家,在新文化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人成了划破黑暗的先驱者。和其他作家不同,鲁迅铁屋子之中的人,在熟睡中不知被闷死的命运;巴金“家”中的年轻一代,都在为追求自由、真理和爱情而激烈的抗争;钱钟书的“围城”有无数人想进去。在曹禺的文学世界中,密闭的屋子有着双重的独特指向。一方面主人公手握打破窗户的选择权,但无一例外,所有人都选择将窗子关上,自我毁灭。周朴园、焦母和曾家,无视社会的发展,固守封建的枷锁束缚。陈白露则是在纸醉金迷下消磨了意志,得过且过。因此,虽然选择将自己封闭的原因不同,但他们全都是主动闭塞而非被动囚禁;另一方面屋内和屋外是截然对立的,周朴园和鲁大海,陈白露和方达生,焦家和仇虎以及曾家的三代人,他们之间的冲突最终都走向了死亡,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展现了那个时代,挣扎与觉醒的血腥和残酷。
(二)时间指涉:黑夜
《雷雨》中外面没有阳光,天空灰暗;《原野》中仇虎和花金子迷失在黑夜之中。《日出》中潘月亭一夜破产,陈白露选择在太阳升起之前吞药自杀。与关着窗户的房子不同,黑夜是一种时间上的指涉,相对于白昼而存在。从原始人追寻火种开始,我们对光明的尊崇是一以贯之的。远古神话夸父逐日体现了先民的太阳崇拜,火种的珍贵以及森林险恶的生存环境又让我们产生了对黑夜的恐惧。从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开始,夜就代表了污秽、恐怖,孕育着各种祸乱现象,例如《异苑》中写道:“夜闻磕磕有声,瓮中如血,中有丹鱼,长可三寸而有寸光。”到了明清时期,黑夜叙事则开始孕育出一种反叛精神。在千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秩序之下,黑夜为诸如男女私会、杀人行凶等反秩序行为提供了土壤。曹禺对此进行了继承,四部剧作故事的高潮大多发生在黑夜,所有的戏剧冲突掩盖在夜幕之下,然后又在黎明之际归于平静。曹禺笔下的黑夜,因视线遮蔽而带来的未知恐惧从外在想象的鬼魅转变为自身心理的孤独。弗洛伊德冰山比喻下,血腥、暴力、嫉妒等等人性的阴暗面藏在水面之下。黑夜是一个触发的契机,精力的衰竭再加上独处时社会道德准则的压制作用放松,被抑制的无意识就有了活动的空间。黑夜背景下,《雷雨》中的暴风雨,《原野》中的巨树和森林,来自自然的强大威慑都加剧了黑夜的恐怖氛围。《日出》中附着在窗户上的白霜,冷得那样清爽。《北京人》中呼啸的大风,这二者带来了一种感官上的寒冷,例如易水送别的风萧萧兮,它们加剧了黑夜意象下的悲凉之感。
20世纪30年代,社会上的政治倾轧和精神上的奴性与反叛,使得陷入矛盾的作家更喜欢在黑夜中进行自我剖析,黑夜意象以集合的形式出现,融入了作家群的集体无意识,存在有恐怖、阴森的共性和作家自身影响下的个性,所以每个作家笔下的黑夜都有着独特性。曹禺的黑夜就不是寂静的,有着共同的声音意象作为叠加,但这些声音不全是典型意义上能够代表黑夜氛围的声音,例如呜咽声、哀鸣声。《雷雨》中雷声轰隆,每个人都在周家的饭厅里歇斯底里,嚎啕大哭声和咒骂声交织;《原野》中焦母若隐若现的叫魂声、枪声、稽查队的嘈杂声。《日出》中灯红酒绿下上层社会人们觥筹交错的应酬声,以及底层百姓的无奈呐喊。《北京人》中曾家和杜家两大家族你死我活的争夺棺材声。曹禺的黑夜人声鼎沸,如同热闹的白昼,有了人声与人群的聚集,打破了黑夜的死寂,生命力也就渐渐高涨。所以这些声音意象成了黑夜代表下死亡的对立面,它们暗含有黎明之意,代表着高潮之后的平静与死亡之后的新生,消解了黑暗意象所带来的阴森感。同时也体现了作家的独特心理倾向,始终保持着丰沛的生命意识。
二、《雷雨》和《日出》中的独特黑暗意象:
雷雨和黑森林
在《雷雨》的整个故事中,轰隆的雷声都作为背景音时隐时现。鲁侍萍逼迫四凤发毒誓时,天空闪过一道惊雷。当周萍和四凤互诉衷肠时,一道惊雷闪过,印出窗户外繁漪苍白的面庞。周朴园作为丈夫的冷血与作为资本家的罔顾人命,鲁侍萍身份的揭露,周萍与四凤之间的亲兄妹关系,都在这个雷雨天中被揭露。最后所有人都在雷声轰隆中“死”去,有的是肉体上的陨灭,四凤、周冲触电而亡,周萍吞枪自杀,有的则是精神上的寂灭,两个女人的疯癫。雷雨这个意象,首先是“雷”。在不同时代的文学创作中,雷呈现为不同的形象。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雷公为天神,只要他向人间投下一个大响雷,那么人间作恶多端的罪人便会立刻身首异处,雷的这种惩戒性便发展成后世的誓言天打五雷轰。在现代社会,雷就体现为一种外来警示,作者通过这种方式,让人物顿悟以实现情节的转折或向读者暗示人物语言的真假。与雷相伴而来的便是狂风暴雨,原始农耕社会,暴雨是威胁人类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过度的雨水在人类氏族早期,可能会导致火种的熄灭,粮食的毁坏,进而促使生命的消亡。《雷雨》中雷雨意象是和黑夜意象叠加的,在黑夜环境下的无助增强了雷声的威慑性和对暴雨的恐惧。
而在《原野》中,黑森林成了整个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森林里充蓄着原始的生命,巨大的枝叶遮断天上的星辰”。高耸的巨树遮挡住了月光,不见一点光亮,就像一个巨大的牢笼,将仇虎、花金子、焦母困在这里。黑森林的压迫感强于关着窗户的房子,因为人物失去了是否被禁锢的选择权。仇虎是被黑森林囚禁的,他迫切想要前往铺满金子的理想世界,但他始终无法冲破黑森林的禁制。森林承载着先民最初的生命意识。在高大的树木上修建房屋可以躲避猛兽的攻击,森林中的飞禽走兽又是人类发现稻谷以前主要的食物来源,伊甸园、乌托邦中都有生命之树的存在。所以说,人类文明在此发源,并逐步向外扩展,因而马克思称森林为人类的童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走出森林,在大平原上聚集而居,被遗弃的森林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禁地,因而也就代表了个人心中不愿被人发现的隐蔽角落,趋向理想的超我与趋向快乐的本我在这个无人之境中不断斗争,迷茫、绝望随之而来。茂密的巨树所带来的压抑感,会不断给人负面的心理暗示,所以走投无路的仇虎才会在这片森林中看到死去的亲人。森林意象中原有的鲜活的生命力消散,取而代之的是生命陷入困境后的陨落,仇虎最终开枪自杀。无论是雷雨还是黑森林,他们都有一个共性——自然物。从盘古劈开黏着在一起的混沌天地开始,天人合一的种子便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种下了,先民对于永恒的自然和个体的死亡这两样东西始终保持着敬畏,将个体蜉蝣置身于天地之间,这种对于自身命运无法掌握的渺小感渐渐发展成华夏先民独特的自然意识,进一步渗透到文学中,就是各种自然意象的广泛使用。从伏枥的老骥到英雄暮年壮志难酬,从海上升起的亘古明月到世事变幻的望月人,中国人眼中的自然早已与自身个体息息相关。
三、与黑暗意象相拉扯的光明意象
在这四部剧作中,即使有大量黑暗意象的存在,也始终夹杂着光明的意象与其进行拉扯。一方面是受到传统大团圆情结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来自作者自身浩浩荡荡的生命意识。中国人有着独特的大团圆情结,因而悲剧中也总会有希望的存在。《雷雨》中周冲所说的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这与封闭、沉重的周公馆是相对立的;《原野》中,那个金子铺满的世界以及火车冲破原野,冲向理想的世界;《日出》中太阳一如既往地升起来了,在这个黎明时光,伴随着工人们雄浑的叫号声,新的世界即将来临。作者将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的浩浩汤汤的生命意识又往前推了一步,使其充塞了整个宇宙。包括《北京人》中的袁教授一家在内,他们都是理想的载体,与上文所提到的黑暗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光明的意象在不同的作品中有不同的呈现方式,但从共同点上而言,其特征都带有与雷雨、黑森林等恐惧、阴森的黑暗意象不同的明亮、轻松与自由,以及喷薄而出的生命力。所有驱使人寻找快乐的本能都被弗洛伊德称为力比多,它与生俱来而且活力十足,但是它时时受到超我的压抑,从而使个体产生负面情绪,如何才能走出困境?最好的升华渠道就是文学艺术创作。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有的人执着于大团圆结局,因为寻找快乐就是人类的本能。曹禺将这种本能通过戏剧的创作进行升华,所以在悲剧的内核之下,才会始终存在有希望与光明。这种创作手法在中国是一脉相承的,悲剧与喜剧的兼容可以纳入广义上的悲喜剧范畴,即使是冤如窦娥,也依然能够召唤出六月飞雪,最终沉冤昭雪。
除此之外,与西方文学相比,“五四”新文化时期提出的“孩子时代”这一概念,附着了更强烈的家国情怀与历史使命,所以这一系列意象所代表的生存氛围会更加浓烈。从鲁迅的“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开始,曹禺对此进行了继承。《原野》中花金子和仇虎青梅竹马的少年时代,是宁静的田园和其乐融融的一家人。《日出》中由方达生唤醒的少女竹均的记忆等等。森林是人类的童年时期,机遇与挑战的并存促使原始先民迸发出雄浑的生命意识。阶级的分化、道德的束缚,人类的这种原始性在工业化下逐渐丧失。因此曹禺的原始生命力的追寻从《原野》中对于原始巨树的尊崇开始显露,逐渐发展成他的生命意识——对于自由的追求和对于黑暗的反抗。
曹禺的四大悲剧创作,初看时,文本基调都是抑郁的。死气沉沉的周公馆、诡异的黑森林、纸醉金迷的小旅馆以及漆了一遍又一遍漆的棺材,但即使作者使用了大量黑暗意象,它们都不是创作的核心,这些黑暗意象的存在一定要与穿插于文本中的光明的意象进行关联,“死”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雷雨和黑森林两个黑暗意象同时具有生与死的双重性意味,雷雨过后是焕然一新的世界,森林中弱肉强食的背后是鲜活的生命气息。面对着机械化时代造成的个体生命的萎缩和衰败,沈从文选择去湘西边城构筑希腊神庙,而曹禺则试图去寻找一个个体生命的突破口,重建精神家园。因此,无论故事如何死寂,生命的活力与未来的曙光始终闪耀。
参考文献:
[1]潘纯琳.儿童的发现与发明:作为文化概念的“儿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面形塑[J].探索与批评,2020,(02):84-105.
[2]宋苏云.论曹禺戏剧《原野》的意象类型[J].今古文创,2023,(42):13-15+55.
[3]陈书涵.曹禺剧作中牢笼与黑幕的意象分析[J].文学教育(上),2022,(11):30-32.
[4]池楚昀.曹禺戏剧中黑夜意象的延续与重构[J].文学教育(上),2023,(07):32-35.
作者简介:
王瑶洁,女,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语文学科教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