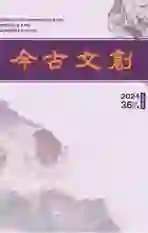追寻“真诚”
2024-09-20刘婧
【摘要】现代人对自我的肯定和推崇、对如实展现自身的渴望,可以理解为一种“真诚”崇拜,后者作为一种现代产物,它的起源与卢梭密切相关。卢梭不满于18世纪法国社会弥漫的虚伪风气,对主流文化观念发起了挑战,他认为,人类主体性的真正基础是“对自我的存在的感觉”,这种感官真理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所拥有,然而在现代社会中遭到遮蔽和异化,换言之,“虚伪”是整个现代文明的必然后果。卢梭对“真诚”的追求、对资产阶级虚伪的批判曾经是一种“异端思想”,如今却被广为接受,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自恋文化”的盛行和“公共人的衰落”。尽管如此,卢梭对真诚的讨论依然具有重要价值,身为“最早的现代个体”,卢梭的追寻反映了现代人在这个混乱、无序世界的某种深层渴望,它依然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也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词】卢梭;真诚;自我;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6-0076-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2S9noXGLvzDGO25sz7ye7EQ==2
德尔斐神庙上铭刻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对古代欧洲人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无数西方先哲毕生努力的目标,如果说现代社会也有一句同样不容忽视的箴言,那恐怕就是“做你自己”。作为现代社会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做你自己”反映了一种心态,即对自我的肯定和推崇、对如实展现自身的渴望,倘若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真诚”崇拜,它把保存和捍卫自我视为个体的终极任务。
事实上,“真诚”并不是一种自古就有的美德,而是18世纪以来才逐渐进入社会主流思想的一种观念,当我们回顾“真诚”的历史时,必然与卢梭相遇,卢梭对“真诚”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借用查尔斯·泰勒的说法,他是现代“本真性”讨论的先驱。①卢梭的思想具有异乎寻常的复杂性,而“真诚”一词几乎贯穿了其作品的始终,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卢梭笔下的“真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这对我们理解卢梭的思想、理解现代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一、“真诚”的起源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与“人”有关,然而“个体意识”却并非亘古即有的老话题。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城市扩张等一系列社会变化,传统的阶级壁垒、家族模式和经济关系纷纷受到冲击,人们在社会当中不再具有一个稳定的归属,成了漂浮的原子化个体,因此,现代人不得不试着重新为自己寻找定位、塑造自己的角色或寻求人生意义。②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周遭环境的快速变化刺激了人的欲望和野心,而社会规范、道德风俗的移易却相对落后,在社会行为准则和个人欲望之间由此产生了激烈而持久的冲突,这一冲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譬如小说这种现代文学形式就诞生于此: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对这一冲突进行展现并尝试(在不颠覆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弥合的产物。③
外部环境和内心世界的激烈交锋,还引发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特里林指出:“在历史发展的某个时刻,欧洲的道德生活为自身增加了一个新的要素,我们称之为‘真诚(sincerity)’,它指的是公开表示的情感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 ④之所以要强调“真诚”的现代性,是因为在过去,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环境之间尚未出现巨大的鸿沟,人与外部世界大致上处于一种和谐状态——在《圣经》或《荷马史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几乎不需要额外的心理活动描写,因为他们所思所想即是他们所言所行。⑤古典作品中的人物也很少对自己的身份、对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深思熟虑,史诗和传奇中的主人公是帝王将相,他们的英雄身份是无可置疑的,具有一种先定性,而对现代小说中的人物来说,在故事开始之际,“我要做什么样的人”“我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些问题依然摆在他们眼前。⑥换言之,现代人始终逃不开有关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这种焦虑的背后是一种渴望,即对“成为自己”的渴望。因此,“真诚(sincerity)”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诚实(honesty)”,它是个体意识崛起的产物,表现了现代人对自我的肯定以及如实展现自我的愿望。
随着对“自我”的关注逐渐升温,从17世纪开始,自传、回忆录、肖像画等表现个人内心世界或展现个人形象的艺术作品大量涌现,美国学者凯利指出,“自传(autobiography)”完全是一种现代产物。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古代就没有传记作品,而是说古代极少出现以第一人称创作的传记。即使是像《高卢战记》(恺撒)、《长征记》(色诺芬)这样带有明显自传色彩的作品,作家也常常假托他人的经历来描绘自我的历史。似乎可以这样说,过去的人并不习惯总是谈论“自我”。⑦与古人相反,现代人对自传相当迷恋,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自传是卢梭的《忏悔录》,在这本书中,卢梭决意“把自己赤裸裸地展现在公众眼前,没有丝毫隐瞒或歪曲,好让读者原原本本地了解此人心灵中发生的一切” ⑧。尽管《忏悔录》的内容引起了诸多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卢梭在此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对“真诚”这一品质的重视,事实上,卢梭是现代“真诚”理想最早、最有力的推动者,他在塑造现代人的自我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如果不理解卢梭,我们就无法理解自身。
二、卢梭与作为“反文化理想”的真诚
卢梭的思想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复杂性,他那卷帙浩繁的作品是否具有一条内在的连贯脉络,或者,他的种种主张是否能得到系统性的概括,学者们对此常常表示怀疑。然而,斯塔罗宾斯基指出,尽管卢梭在他的著作中就不同问题提出了诸多设想,他在具体阐述中也存在矛盾和犹豫不决的情况,但这些作品都可以被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意向,即保卫或者修复“被损害的透明性”。⑨这里的“透明性”指的正是一种绝对真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们可以脱去所有伪装,自由地“示其所是”。
在卢梭笔下,“真诚”及相关的词出现得是如此频繁:“我将要说的话,出自一个虽然一无所知、但并不因此就妄自菲薄的诚恳的人。”(《论科学与艺术》) ⑩“我在这里向你们——日内瓦共和国的执政者们——致以敬意,只凭借鼓舞我的一片热诚,而不考虑我的身份和权利。”(《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⑪“我想做什么,只问我自己的心灵:良心是我们最好的导师与朋友,我一切行动都服从于我的内心。”(《爱弥儿,或论教育》) ⑫到了晚年,卢梭更是致力于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忏悔录》《对话录》《遐思录》这“告白三部曲”中,卢梭对自己的生平经历、思想变迁进行了详细的描绘,也对论敌的指责做出了回应。在卢梭看来,这些文字都是他内心真实想法的写照,充分表明了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卢梭对此总结道,“我的全部作品都是我的自画像” ⑬。
卢梭如此强调“真诚”,其直接原因在于,18世纪的法国上流社会充斥着虚情假意的社交礼节,助长了人的表里不一,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指出:“今天,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都仿佛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我们再不敢表现真正的自己。对于其他人的真面目,不等到关键时刻,我们是绝对认不出来的。” ⑭其他启蒙思想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孟德斯鸠显然与卢梭感同身受,他专门写了《赞美真诚》(A Praise of Sincerity)一文,其中他讽刺地将奉承和表面上的风度称为“我们这个世纪最受推崇的美德” ⑮。在《拉摩的侄儿》中,狄德罗塑造出了一个复杂的现代人形象:“他是高尚和卑鄙、才智和愚见的混合物……没有什么比他自己更不像他自己的了。这是一种最奇异的人,然而在我们国家,这种人比比皆是。” ⑯拉摩的侄儿性情高傲、才华横溢,却不得不依附于权贵;他痛恨上流社会的惺惺作态,却又深陷其中,在面具和面具下的自我之间摇摆不定。可以说,现代人的分裂和异化,在这位侄儿身上展现得最为彻底。
在卢梭看来,“虚伪”与其说是个人的道德缺陷或某种特定社会制度的产物,不如是说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灾难性后果。导致人们深陷虚伪泥沼的根源在于腐败的现代文明,它与“自然”和“真实”背道而驰,在两篇应征论文——《论科学与艺术》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描绘了“原初社会”的景象:“当我们回顾太古时代的淳朴风光……那时人们清白而有德,并且愿意有神明在侧洞悉他们的行为。这些人的风尚是粗野的,然而却是自然的。” ⑰卢梭认为,人类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自然的阶段,一个是文明的阶段,“自然状态”中的人们有着明澈、通透的心灵,他们不知伪饰为何物,其存在与表象之间尚未出现鸿沟,然而,人类“被表面上的正确所欺骗” ⑱,在“文明”的诱惑下抛弃了纯真的美德,滑向分裂的深渊。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视其为哗众取宠者不在少数,甚至伏尔泰也在回信中对论文作者施以嘲讽。⑲卢梭的观点之所以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主要在于它所蕴含的双重颠覆性:首先,卢梭以一个处在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对主流文化发起了挑战,他谴责当时社会的因循守旧和唯利是图,对成规和“体面”不屑一顾,这种表露自身、直言不讳的态度在上流社会的“文明人”看来无疑是一种冒犯;其次,卢梭不相信历史进步论,而后者正是启蒙运动和现代理性的基本信念之一。在卢梭看来,历史无法证明任何事物的合理性,他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与道德判断相关,建立在一种伦理绝对的基础之上,正如贫富悬殊的人类状态是历史逻辑的必然,然而在道德上却不可接受。⑳换言之,从“自然”向“文明”过渡的进程,在启蒙思想家看来是一种进步,在卢梭看来却是一种深刻的悲哀,它意味着“透明性”的丧失。作为第一个对“现代文明”进行全面指控的人,卢梭的批判是一种“否定之否定”——他否定文明,因为文明否定了自然。㉑因此可以说,卢梭的“真诚”实际上是一种“反文化”的理想。
需要指出的是,卢梭并不是第一个赞美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不弄虚作假的思想家或文学家,但卢梭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赞美的不是真诚的副产品,而是真诚本身:按照过去的观念,一个人袒露心中高尚的思想是值得褒扬的,而表现自己的真实欲望依然是可耻的——换言之,值得赞美的不是“真诚”,而是“令人愉悦的真诚”。㉒卢梭则不然,在他那里,“真诚”本身成了最高的原则,他会说,一个坦率的强盗比一个虚伪的好人更值得敬佩。㉓卢梭之所以把“真诚”作为最高的理想,与他对人之存在本质的特殊看法有关: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提出,原始人的基本情感是“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和“同情(pity)”,而现代文明把这种朴素的“自我保存”本能异化成了彻底的自私自利,同情也遭到遮蔽,现代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来源于这种纯粹利己主义。㉔卢梭对“自我保存”的强调隐含了一个基本观点,即他相信,存在着一个“本质性的自我”需要我们去发现和保护,在论文中,他用“格劳克斯神像”作喻来说明这一点:“在时光流逝和大自然的摧残下,格劳克斯神像的面容已经严重变形……人的灵魂也是如此,可以说,经历了漫长的文明洗礼,它已经改头换面,几乎认不出来了。” ㉕卢梭在这里用了“几乎”一词,它表明,卢梭相信,即便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个“本质性的自我”始终存在。那么,这个“本质自我”究竟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许多思想家都尝试过给出答案。亚里士多德有个著名论断:“人是政治的动物(Man is a political animal)。”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真正自我是公共的自我,一个人必须在城邦中、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来成为自身;圣奥古斯丁提出,我们最真实的自我来源于上帝,只有在对上帝的爱中我们才能认识自己;笛卡尔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他的理性,就如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㉖而在卢梭看来,人类自我的真正基础不是上帝、理性或社会,而是“对自我的存在的感觉”,是一种无中介的、纯粹直观的感知㉗,就像“自然状态”中的人一样,他们过着一种“未经反思的生活”,“其灵魂不为任何事物所扰,只沉浸在对其当下的感受之中” ㉘,如果要为卢梭设计一句同样响亮的口号,他会说,“我感受,故我存在”。因此,卢梭对“真诚”的追求不仅仅是道德伦理层面的思考,也不仅仅是对于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相反,这是一种关于人类存在本质的最深刻的主张。卢梭认为真诚是一种终极理想,因为它要求我们贴近自己最真实的感受,而这正是通向真正自我的必经之路。概言之,卢梭对“真诚”的思考具有一种存在主义的维度,它与对个体救赎与生存意义的追求(或者说“存在之体验”)有关,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克尔凯郭尔的先驱。㉙
三、“真诚”的危机
卢梭对“真诚”的思考建立在对现代文明的全方位批判之上,显示出超越时代的深刻意义,对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特里林指出:“在卢梭生活的时代,市民社会逐渐兴起,‘大众’开始出现。生活在城市中的个体不断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他人的观点左右了个体的意志,导致人们的自主意识遭到削弱,变得随波逐流……这就是现代大众统治的心理后果。” ㉚这一现象引起了卢梭的深切担忧,他追求“真诚”、崇尚“真我”的背后,是对一种理想的“独立自主型人格”的追求,这种人“想方设法要坚守中心,试图保持自我的完整性” ㉛,就像古代哲人苏格拉底和加图(Cato)一样,在他看来,这才是“灵魂的力量”的体现,而在现代社会,这种人已经近乎绝迹。卢梭的自我观还启发了后世的浪漫主义运动,他推崇“感官真理”,认为“感觉”才是自我的坚实基础,这点正中浪漫主义作家下怀,美国学者拉尔夫和伯恩斯评论道:“卢梭是第一个强调感情/感觉得出的结论具有可靠性的重要思想家,因此,他通常被认为是浪漫主义之父。在他逝世后的五十年里,欧洲文学界都在为他哭泣。” ㉜
然而,卢梭对“真诚”的追求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真诚本身是“内向性”的,通常情况下只有行动者自己才知道他的言行举止是否发自内心,如果“让别人信服自己的真诚”这种愿望过于强烈,有时就会陷入“制造真诚”的悖论㉝,正如斯塔罗宾斯基所言:卢梭用华美的言辞宣扬了一个真理,而这真理恰恰谴责言辞的雄辩。㉞卢梭希望自己是表里如一的,更希望自己的“表里如一”能够被世人看见,由此他陷入了一种角色扮演的陷阱,他的“真诚”不可避免地含有夸饰的成分,这也是《忏悔录》历来颇受争议的原因。事实上,早在卢梭的时代,就有人对这种“彻底的真诚理想”进行了反思。在《恨世者》(《愤世嫉俗》)中,主人公阿尔塞斯特宣称自己推崇真诚、追求真理,他也愿意相信自己是美德的捍卫者,但正是这种夸张的姿态使他显得滑稽可笑。借用特里林的说法,阿尔塞斯特的真诚实际上是一种“自欺的真诚”,他“欺骗”的对象不是别人,而首先是他自身,他想让自己相信,他就是他所宣称的那个样子。㉟这部作品反映了一种特殊的、幽深的现代意识,只有内心处在分裂状态却又不自知的现代人才会这样不顾一切地尝试弥合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面对莫里哀的(无意的)嘲讽,卢梭显然认为自己受到了冒犯,在《致达朗贝论戏剧书》中,他对这部作品进行了严厉的指责。然而,无论卢梭如何批评莫里哀,他都无法否认自己就是一个现实中的阿尔塞斯特:他一心追求自己眼中的至善,最终却“因为善而显得荒谬” ㊱。
卢梭对“真诚”的推崇还导致了“自恋文化”的盛行和“公共人的衰落”。亚瑟·梅尔泽强调,卢梭所谓的“真诚”不同于“诚实”:后者具有一种公共属性,以对他人负责为出发点,而“真诚”本质上是对自我的肯定,具有一种私人属性,以对自身负责为出发点。现代人对“自我”怀有一种持久的狂热,克里斯托弗·拉希称之为“自恋文化”,大众对精神分析、星座、人格测试等事物的喜爱,以及不厌其烦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个人动态,这些现象都与某种“自恋”心理有关。㊲以近年来出现的“十六型人格测试”为例,它之所以在年轻人中如此流行,表面上是因为人们试图给自己贴上标签以寻找可以相互理解的同类,实际上它反映出人们对某种自我特质的肯定和推崇,他们相信自己拥有某种区别于他人的特征,并且以此为豪。
倘若人们对“展现自我”的迷恋止步于此,那它还算不上有害——然而它走得更远。作为一种新的美德,“真诚”鼓励人们抛弃羞耻、展示自己不堪的一面,它让我们接受自己的软弱和可悲,甚至让人们为敢于暴露阴暗面而自豪——由此形成了一种“卑鄙”和“高尚”的倒置:当一个人袒露他的道德缺陷时,他在某种程度上就变得“高尚”了。㊳这种看法为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开辟了道路,它暗示,只要一个人是真诚的,那么他就有权得到他人的尊重,而不应当遭受指责。㊴这种观念显然是危险的,桑内特意识到,这种沉溺于自我世界、孤芳自赏的态度会妨碍我们对社会的理性认识,进而导致对公共生活的冷漠,这是一种更微妙的专制主义,它会导致欲望的彻底放纵,最终“摧毁一己之善和至善” ㊵。
四、结语
卢梭以一个“边缘人”的身份,对“资产阶级虚伪”和现代文明发起了批判,他对“真诚”的思考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悖论性质:它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却因此摧毁了所有的个性。卢梭的观点也在这种悖论性中得到“发展”,他的思想曾经是对主流文化的反击,如今却被普遍地接受和内化了,成了他所坚决反对的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㊶面对现代“真诚”崇拜导致种种的社会危机,一些持悲观主义态度的学者建议人们彻底抛弃卢梭和他的遗产,对此,查尔斯·泰勒的看法更加中肯。他指出,我们不需要否定“真诚”这一理想,而应当思考如何超越“浅薄、平庸的本真性”,去实现“本真性的更高、更充分的模式” 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在肯定个体的同时重视与他人的对话,进而在尊重公共生活之普遍性的基础上实现一种更加积极的“真诚”。㊸概言之,卢梭的设想未必尽善尽美,但他为实现“真诚”所做的一切努力依然值得我们尊重,身为“最早的现代个体”,卢梭具有某种分裂的意识,却固执地追求单纯的灵魂㊹,他的追寻反映了现代人在这个混乱、无序世界的某种深层渴望,它依然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也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①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本真性的伦理》,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60页。
②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7页。
③Nancy Armstrong,How Novels Think:The Limits of Individualism from 1719-1900,Columbia UP,2005,pp.3,8。
④莱昂内尔·特里林著,刘佳林译:《诚与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⑤莱昂内尔·特里林著,刘佳林译:《诚与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⑥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8页。
⑦克里斯托弗·凯利著,黄群等译:《卢梭的榜样人生——作为政治哲学的〈忏悔录〉》,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⑧卢梭著,黎星译:《忏悔录(第一部)》,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9-70页。
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汪炜译:《透明与障碍——论让-雅克·卢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4页。
⑩让-雅克·卢梭著,何兆武译:《论科学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8页。
⑪让-雅克·卢梭著,李常山译:《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0页。
⑫J-J Rousseau:Emile or On Education,trans. Allan Bloom.Basic Books,1979,p.290。
⑬菲利浦·勒热讷著,杨国政译《自传契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页。
⑭让-雅克·卢梭著,何兆武译:《论科学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4页。
⑮See Arthur Melzer:"Rousseau and the Modern Cult of Sincerity"in Clifford Orwin,eds.The Legacy of Rousseau,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p.280。
⑯狄德罗著,陆元昶译:《拉摩的侄儿》,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⑰让-雅克·卢梭著,何兆武译:《论科学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48页。
⑱此为《论科学与艺术》正文开头的引言,出自贺拉斯《诗艺》。何兆武译本有误,正确的译文应是“我们被表面上的正确所欺骗”。参见刘小枫《卢梭与启蒙自由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03期,第3-4页。
⑲See Nannerl O.Keohane, "The Masterpiece of Policy in Our Century:Rousseau on the Morality of the Enlightenment"in Political Theory,Vol.6,No.4,Special Issue:Jean-Jacques Rousseau(Nov.,1978),p.470。
⑳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汪炜译:《透明与障碍——论让-雅克·卢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7-48页。
㉑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汪炜译:《透明与障碍——论让-雅克·卢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
㉒See Arthur Melzer, "Rousseau and the Modern Cult of Sincerity",ibid.286。
㉓See Timothy Brennan, "The Strength and Vigor of the Soul:The Broader Meaning of Virtue in Rousseau’s First Discourse" in The European Legacy, Volume 26,2021 Issue 5,p.471。
㉔吴增定:《卢梭论自爱和同情——从尼采的观点看》,《哲学动态》2019年第02期,第73页。
㉕让-雅克·卢梭著,李常山译:《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2页。此处译文部分参考了《透明与障碍》第28页。
㉖See Arthur Melzer, "Rousseau and the Modern Cult of Sincerity",ibid.p.287。
㉗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汪炜译:《透明与障碍——论让-雅克·卢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0页。
㉘让-雅克·卢梭著,李常山译:《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6页。
㉙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汪炜译:《透明与障碍——论让-雅克·卢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7页。
㉚莱昂内尔·特里林著,刘佳林译:《诚与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㉛莱昂内尔·特里林著,刘佳林译:《诚与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㉜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07-308页。
㉝范昀:《追寻真诚——论卢梭与现代自我认同》,《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5期,第54页。
㉞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汪炜译:《透明与障碍——论让-雅克·卢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3页。
㉟莱昂内尔·特里林著,刘佳林译:《诚与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1页。
㊱此为卢梭《论戏剧书》原文,参见《诚与真》第61页。
㊲See Arthur Melzer, "Rousseau and the Modern Cult of Sincerity",ibid.pp.276-277。
㊳See Arthur Melzer, "Rousseau and the Modern Cult of Sincerity",ibid.pp.285。
㊴范昀:《追寻真诚——论卢梭与现代自我认同》,《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05期,第56页。
㊵艾伦·布鲁姆著,战旭英译:《美国精神的封闭》,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㊶See Arthur Melzer, "Rousseau and the Modern Cult of Sincerity",ibid.p.291。
㊷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本真性的伦理》,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13页。
㊸范昀:《追寻真诚——论卢梭与现代自我认同》,《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5期,第56-57页。
㊹莱昂内尔·特里林著,刘佳林译:《诚与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参考文献:
[1]Armstrong,Nancy.How Novels Think:The Limits of Individualism from 1719-1900[M].New York:Columbia UP,2005,pp.3,8.
[2]Brennan,Timothy.The Strength and Vigor of the Soul:The Broader Meaning of Virtue in Rousseau’s First Discourse[J].The European Legacy, Volume 26,2021 Issue 5.
[3]Keohane,Nannerl.The Masterpiece of Policy in Our Century:Rousseau on the Morality of the Enlightenment[J].Political Theory,Vol.6,No.4,Special Issue:Jean-Jacques Rousseau(Nov.,1978),p.470.
[4]范昀.追寻真诚——论卢梭与现代自我认同[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0(05).
[5]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6]克里斯托弗·凯利.卢梭的榜样人生——作为政治哲学的《KtZBHffYSOe3xfe0Xac7LA==忏悔录》[M].黄群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7]卢梭.忏悔录(第一部)[M].黎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让-雅克·卢梭.论科学与艺术[M].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9]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0]让·斯塔罗宾斯基.透明与障碍——论让-雅克·卢梭[M].汪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11]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M].程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12]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M].刘佳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13]吴增定.卢梭论自爱和同情——从尼采的观点看[J].哲学动态,2019,(02).
作者简介:
刘婧,女,广东佛山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