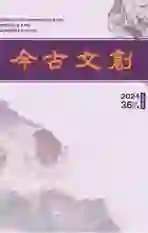论艾青诗歌的语言艺术
2024-09-20杨文琴
【摘要】艾青是中国现代自由体诗人的重要代表之一,其诗歌的语言艺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自然纯朴、简约集中的口语;具体鲜活的意象语;语言的张力形态。
【关键词】艾青;诗歌;口语;意象;张力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6-005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17
基金项目:本文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2023年度校级质量工程项目“课程思政背景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的创新研究与实践” (项目编号:2023046ZLGC)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古典诗话中有“诗家语”的说法,表明诗的语言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由于语言自身的复杂性,语言的发展也具有时代性,因此,对诗歌语言特质的认识往往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艾青作为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由体诗歌的代表诗人,对诗歌语言也有独到的追求,并且形成了自己孤标独秀的艺术风韵,对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一、口语之美
从现代诗歌创作实践和诗歌理论探索来说,诗歌语言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形态,可以是以古语为主的,也可以是以外来语为主的;可以是以书面语为主的,也可以是以口语为主的。艾青关于诗歌语言的最高标准是“纯朴、自然、和谐、简约与明确”[1],要做到这一点,口语无疑是其最佳的选择。他认为:“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2]这可谓是他关于诗歌语言的纲领性宣言。
在创作实践中,艾青对于口语的实验取得了相当重要的经验,在运用口语入诗上艾青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他的诗能够顺应时代与人民的需要,能够与其诗歌阔大的诗情和宏大的主题相适应。总的来讲,艾青诗歌中的口语之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自然纯朴和简约集中。
(一)自然纯朴之美
自然纯朴即不事雕饰,以日常的语言表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在《大堰河——我的保姆》[3]中:“大堰河,是我的保姆。/她的名字就是她的村庄的名字,/她是童养媳,/大堰河,是我的保姆。”这样的语言明白如话,像是对人介绍自己的保姆一般,但其实质却是诗人对保姆最深情回忆的开始——大堰河出生卑微。纯朴的语言看似得来毫不费工夫,实则饱含了诗人深切沉痛的感情,其实质是以语言上的纯朴自然来表达情感之至真。再看《村庄》[4],诗人是这样表现村庄的贫穷的:“偶然有人为了奔丧回到了家乡时,/他的一只皮鞋就足够使全村的人看了眼红”,所以“自从我看见了都市的风景画片,/我就不再爱那鄙陋的村庄了”,伸手可触的生活实感和坦诚的情感,残酷地表现出“村庄”是如此的贫穷,贫穷得可能使人丧失人生的意义。这种语言去掉了一切外在的加工,其感人的魅力正是诗人情感的真挚和深沉。如果采用另一种文言或外来语言,这样的情绪表达是不可想象的。艾青所看重的正是这种语言的自然本性及其与生活的接近性、与现实的血缘性、与人的情感的无距离性。艾青的创作实践说明自然纯朴的口语是很有表现力的。
(二)简约集中之美
简约集中指语言的精练与通俗,是以最省略、最易懂的文字“唤起一个具体的事象,或是丰富的感情与思想”[5]。这种语言类似谚语,适用于说明道理或表达对事物本质的看法。诗当然不是直接地说明事物的本质,但诗人的眼光可以看透事物本质,并能以具体的形象和意象加以暗示和有意味地表达。艾青的诗歌语言特别注重简明集中,凡是一个词可以表达的东西,就不再用第二个词,读他的诗没有那么多的反复,也没有那么多的语词的装饰效果,但你就是能够感觉到它的美质。他的《城市人》[6]:“人创造了城市/城市又创造城市人”,语言很简单,但其中的内涵却相当丰富,好像表现了一代的历史,表现了城市与一代农民的关系一样。由69首小诗组成的《无题》[7],几乎首首都是简约明快之作,“风筝飞得再高/摆脱不了儿童的手”。艾青早期的《向太阳》《太阳》《黎明的通知》《我爱这土地》《乞丐》《北方》等诗,不论是长篇的抒情诗还是短诗,不论是叙事诗还是抒情诗,虽然不一定都达到了增之一字则多、减之一字则少的地步,但其语言大多做到了精练、甚至精确。
艾青将诗的语言的口语之美当作诗歌散文美的重要内容,他甚至直接说过,他主张的散文美就是诗的口语化。总之,自然质朴的口语并不像有的人所说的不能入诗,艾青的诗歌又一次实践了中国自古就有人主张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道理,也说明了以具有自然之美的口语写诗是诗之大道。
二、具体鲜活的意象语
意象是主体情感在客体上的灌注,是客体主观化的结果。通过意象,能表现抽象的情思,极大丰富想象空间,增强诗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使诗歌意蕴深厚、情思生动。从语言的角度考察意象,意象无非是语言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它凝练、富于暗示、具有生命活力。
艾青将意象的选择与创造作为诗歌艺术的关键环节给予重视,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意象世界。艾青往往用诗歌的形象化、语言的具体性来表达意象化的内涵,他所说的形象化对于诗来说就是意象化,他所说的具体性也只有意象化的诗歌语言才能表现。
根据意象在其诗作中的地位,其诗的意象可分为两大群落:中心意象群落和边缘意象群落。前者在其诗歌中具有普遍意义,能体现艾青基本的情感价值取向;后者更多的是语言修辞意义上的表现形态,他们不直接包含主体的中心价值观念,但指向中心。中心意象群落以“土地”和“太阳”意象为其基本意象:以土地为中心意象,又包括旷野、池沼等一系列与土地有关的意象群;以太阳为中心意象,包括黎明类、光明类等具有新生和理想意味的意象群。两大类中心意象群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土地意象群寄托了对祖国现实苦难的关注与对民族、人民深沉炽热的爱;太阳意象群象征诗人对光明理想的渴望与追求,也体现了诗人对理想的坚定信念。艾青诗歌两大意象群落的成功创造,与其所使用的意象化的诗歌语言密切相关。如果没有语言选择的意象化,则没有其诗歌独到而深厚的意象的形成。
(一)中心意象群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一些诗作。“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8](《我爱这土地》)。土地的苦难就是人民的苦难,“悲愤的河流”和“激怒的风”是中华民族的呼喊与反抗;而“我”即使无力为他们做什么,即使喉咙嘶哑,也要为他们不停地歌唱、鼓劲,直至生命最后一刻,“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死后也要与他们一起。诗中没有一句话与祖国、民族、人民有关,都是与自我、与大自然的河水、与鸟儿和土地有关。其实,诗人正是通过上述自然和人世的意象来表达自我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深情。意象化正是此诗在语言上最大的特色。
有恨就有爱,有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就有对光明的追求。“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9] (《太阳》),“这时候/我对我所看见所听见/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宽怀与热爱/我甚至想在这光明的际会中死去……”[10](《向太阳》),对人民的爱有多深,对祖国未来之光明与人民理想之实现的渴望就有多强。诗中说的“太阳”和 “光”的意象既有自然界的原型,但又绝对不只是对自然物象的一种实写。正是通过意象化的语言,诗才真切而深厚地表现出了对自我之根的爱与对理想之爱,这种意象化的语言使诗歌情感饱满、元气淋漓。
(二)边缘意象群
边缘意象群虽不似中心意象群意义重大,但其中体现了诗人敏锐的感觉、独特的想象与高超的表现技巧,使中心意象群意义更突出,使读者感觉更加强烈,诗歌趣味倍增,是非常有价值的意象语言。明喻性意象如“不平的路/使车辆如村妇般/连咒带骂地滚过……”[11](《马赛》),隐喻性意象如“巴黎,你——噫/这淫荡的/淫荡的/妖艳的姑娘!”[12](《巴黎》),借喻性意象如“岁月在血泊中浮游/死亡在追赶着生命”[13](《我想念我的祖国》),通感性意象如“村,/狗的吠声,叫颤了/满天的疏星。”[14](《透明的夜》)等等。凡意象,多少具有象征意味,但是这些意象一般出现在特殊的语境中,没有普遍性与固定性,因此,其象征性仅局限于修辞手法,其运用仅限于个别诗作,属于诗人独特的灵感捕捉。
语言的意象化或者说意象化的语言是艾青诗歌独特艺术的主要表现之一,中国新诗一路走来,从20世纪“五四”初期的白话诗、三四十年代的各体新诗、十七年的政治抒情诗到八九十年代的现代派诗,如今的“精英化”写作和民间写作,其百年历程无不彰显出诗歌语言意象化对于诗的重要性。而艾青正是主张并实践了诗歌语言意象化的最成功的现代诗人之一。
三、语言的张力形态
“张力”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指同一物体内部相互作用而又方向相反的拉力,引申到诗学中指一句诗或一首诗同时包含两种冲突因素而又相反相成的现象,比如词的内涵和外延,爱恨、悲喜等相反的情感,虚实,内外等等。艾青并没有关于诗的语言张力的明确主张,但其诗作大多呈现出语言的张力形态。
(一)利用词的本义和象征义生成张力
利用词的字面义与象征义之间的距离生成张力,是艾青语言张力的主要来源。如《煤的对话》[15],以拟人的手法、对话的方式让“煤”表白自己:“我住在深山里/我住在万年的岩石里”“我的年纪比山的更大/比岩石的更大”,“从恐龙统治了森林的年代/从地壳第一次震动的年代”就开始沉默,但“我”却“不曾死在过深的怨愤里”,而是热烈的呼唤燃烧:“死?不,不,我还活着—— /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字面上是对煤这种物质的形成、性质、特点的描述;其内涵则是诗人对献身民族解放事业之心迹的热烈表白。整首诗语言的字面义与其内涵不一致,但两者间存在引力,因为“深埋在地下的煤”与“渴望献身的青年”有着某种共性,由前者能够联想起后者,在诗人创作的意图以外,我们还可以将“煤”看作是“受压迫深重而蕴含巨大反抗力量的中国人”的象征。在“煤”的字面义的深层具有多重丰富的意蕴,给予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也就是说,语言字面义与其内涵的不一致,不仅未阻碍其内涵的表达,反而使其内涵得以凸显、发挥、更加丰富。诗的最后一节与前几节的意思也存在对立,前面描述煤之艰难处境,最后一节揭示其内在巨大的生命力,对照之下,后者生命力的健旺与反抗得到了强化表现。在诗的内部,两种意义相对的语言是有主有次的,次要方由于与主要方之间存在意义上的对立而与之产生一种张力,从而突出主要方。
语言字面义与内涵间的距离使语言充满弹性和张力,弹性和张力以语言间的空隙为前提,充分发挥出语言的丰富性、暗示性,很好地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
(二)利用相反或相对的词语生成张力
艾青擅长使用相反或相对的词语生成张力,这种张力外化就形成情感冲击力,让读者被打动、被震撼、去思考或者共鸣等等。比如《我爱这土地》[8],其中张力就无处不在。如“用嘶哑的喉咙歌唱”,既然喉咙“嘶哑”,为何还要歌唱?为何要歌唱“悲愤的河流”和“激怒的风” ?为何将“悲愤的河流”“激怒的风”和“无比温柔的黎明”并列?“常含泪水”原来却是因为“爱”,那么,为何因爱流泪呢?诗中处处都是看似相对或相反的词语和词义,但其实它们又是紧密联系的,即使喉咙嘶哑也要歌唱,正因为歌唱的是自己的祖国;即使河流悲愤、风儿激怒,但受苦的祖国仍是我爱的祖国;即使河流悲愤、风儿激怒,但祖国大地上也有温柔的黎明,仍有很多美好,且并不曾丧失希望;正因为爱得深沉,所以才会因祖国遭受蹂躏而万分痛心、悲伤、悲愤,所以才会“常含泪水”,相反或相对的词语形成一种紧张关系,两种矛盾的因素相互拉扯而形成张力。
艾青新时期创作的《鱼化石》[16]《虎斑贝》[17]等诗也充满语言张力,如鱼儿本是“活泼”“旺盛”“跳跃”、自由、充满生命力的,但多少亿年后却“沉默”“不能动弹”“绝对的静止”;虎斑贝是那么的美好—— “光”“亮”“细腻”“坚硬”“滑润”,但一直“绝望”地呆在深深的“海底”,艾青通过鱼前后的巨大反差与虎斑贝美好而不能为人知、为人赏的矛盾表达对社会某种现象的批判和思考。艾青诗歌语言的张力形态来源于诗人对于外在矛盾的捕捉、对自我情感的体认以及对语言的纯熟运用。
四、结语
艾青的诗歌语言以语言能否充分表现形象为核心,以“口语美”的发现为突破口,擅长利用张力增强表现力。
艾青对诗歌“口语美”的提倡有其现实针对性,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中国诗坛追求诗的格律化的风气日益严重,诗歌由于语言问题而日益走向偏狭的小道;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处于火与血中的新生时代,需要时代的大手笔崛起于诗坛,为民族、为人民、为国家呐喊。同时,为了避免口语入诗的“散文化”,艾青强调诗的形象性,也就是意象化的语言表现,正因为对诗歌艺术的双重要求,艾青得以实现诗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统一,也因此成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诗坛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
参考文献:
[1]艾青.我怎样写诗的·艾青选集(第三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93.
[2]艾青.诗的散文美·艾青选集(第三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44.
[3]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选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17.
[4]艾青.村庄·艾青选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478.
[5]艾青.诗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03.
[6]艾青.城市人·艾青选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369.
[7]艾青.无题·艾青选集(第二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525.
[8]艾青.我爱这土地·艾青选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207.
[9]艾青.太阳·艾青选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122.
[10]艾青.向太阳·艾青选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178.
[11]艾青.马赛·艾青选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35.
[12]艾青.巴黎·艾青选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26.
[13]艾青.我想念我的祖国·艾青选集(第二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47.
[14]艾青.透明的夜·艾青选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11.
[15]艾青.煤的对话·艾青选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124.
[16]艾青.归来的歌·鱼化石[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12.
[17]艾青.归来的歌·虎斑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28.
作者简介:
杨文琴,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