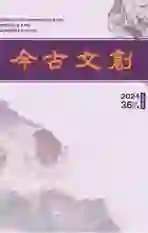论柳宗元、 苏轼流寓心态之异同
2024-09-20邢若琳
【摘要】柳宗元、苏轼是中国古代流寓文人的典型,二人历经政治打击而流寓“蛮荒之地”,其心态却有明显差异。柳宗元流寓永州后的心态是悲愤、愀然无乐的;而苏轼的流寓心态则表现出安之若素,以顺处逆的达观倾向。总的来说,二人流寓心态不大相同的原因主要受其性格、追求及责任使命这三方面的影响,但二人都努力从自身的困难中挣脱,完成了自我的人生救赎。流寓生活虽给流寓者带来极大的精神创伤,但同时也提升了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水准,是其文学创作影响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柳宗元;苏轼;流寓心态;流寓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6-0052-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15
所谓“流寓”,多是因政治原因而遭贬谪,自请外放到非本土的地方做官,或因天灾人祸而迁徙别处。①古代的入仕文人经历流寓生活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受这种疏离与不适环境的影响,文人往往借助文学创作的方式抒发自己“不平之鸣”的情感,流寓文学得以产生。因此,流寓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流寓者的人生走向,对其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轼一生羁旅宦途,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而一贬再贬,二人皆是流寓文人的典型。然二人虽遭流贬,因其成长环境、人生经历的不同,其贬谪后的心态亦有所不同。
一、柳苏流寓心态的异中之同
(一)艰难的生存环境对其心态的打击
贬谪是历代帝王对待不合时宜官员的一种常见的惩处方式,而距中原较远且尚未开发之处,环境艰苦,貊乡鼠壤的地方便成了朝廷安置流贬官吏的最优选择,借此显示天子的威严不容侵犯。永州,地处楚南,在中原人眼里,这是个不折不扣的“蛮夷”之地。“永州实为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圩”“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蝨,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种种词句表明,当时永州自然环境着实恶劣。况柳宗元此次加贬为“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即编制之外的人员,在唐代编制之外的官员公府一般不安排住所 ②,因此柳宗元初到人生地不熟的永州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便是住无所居。好在唐代的佛寺多有容留俗客的习惯 ③,柳宗元便只能携家先寄居在永州佛寺。且自柳宗元遭责逐以来,“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遂而疾病缠身,身心俱创,可见艰难的生存环境对柳宗元来说确是不小的打击。
提到苏轼的流寓经历,最典型的便是其因“乌台诗案”而被责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政治仕途跌入低谷的同时生活也陷入困境。与中唐时期不同,宋朝实行文治,优厚士大夫,所以对于责授散官的官员,朝廷还是会发放俸禄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但苏轼虽有俸禄,实际情况也不乐观。面对“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的难题,苏轼“私甚忧之”,痛自节俭,规划日用所需不得超过一百五十钱。时人往往将其视作俭约的典范广为流传,但侧面也可反映出苏轼生活之拮据。面对一家老小,苏轼那微薄的俸禄难以维持生计,幸得故人马正卿哀其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一卜亩,使得躬耕其中”,才稍稍缓解了苏轼的生存压力。
“自来官司廨宇,皆以所管职事为名,其下便为治所,未有无职事而得廨宇者。” ④在宋代,贬官是没有官廨的,也不会对贬谪官员提供住房,所以在苏轼流寓黄州后只能暂居在定慧院的破庙里,“间一二日辄住”安国寺,过着“随僧蔬食”的日子。而当其家眷入黄后,定慧院住不下,苏轼一家才不得不蜗居在闷热潮湿的临皋亭。“剑米有危炊,针毡无稳坐”便是此时苏轼一家人食宿生活的真实写照,遂发出“饥寒未至且安居,忧患已空犹梦怕”的感叹,面对乐景抒发哀情,命运的瞬息万变,置身流寓之地的苏轼也难免黯然神伤,落寞惆怅。
(二)逐渐认同其贬谪身份
遭贬谪的流寓者从繁华的京城辗转来到僻陋蛮荒的流寓地,内心多是痛苦不适,颇有寄人篱下的孤独之感,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痛苦与不适终会被时间冲淡,流寓文人逐渐适应流寓地,也渐趋认同自己流寓者的身份,柳宗元如此,苏轼亦如此。
苏舜钦在《沧浪亭记》中云:“人固动物耳。情横于内而性伏,必外寓于物而后遣。寓久则溺,以为当然;非胜是而易之,则悲而不开”,人本就会受外物影响而感动,内心充斥情感使得性情受到压抑时,则需借助外物来排遣,固山水景色便是流寓文人的最佳选择。李商隐“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用寄人离思的景物表达对妻子的无限思念;韩愈“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用“秦岭”“蓝关”这些自然景色之美表达其愁苦悲戚的心绪,柳宗元也不例外,流寓永州的他常常“仆闷则出游”,借助山水景色抒发心中的忧愤。柳宗元刚来到永州时称“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将永州比作木笼牢圈,现在却称“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一个“最”字,说明了永州这里的山水风光极佳,也表明柳宗元不再沉溺于自己苦闷忧愁的情绪无法自拔,而是逐渐认同了自己的贬谪身份,于大自然的山水当中寻求心灵的抚慰和精神的解脱,作者流寓永州十年,心境渐趋平和,不再如刚来到永州那般不适,自然永州的山水也由“恶”转为“善”。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是苏轼流寓黄州心境的真实写照,想要退避社会,寻求彻底解脱的出世理念,旷达而又伤感的情绪展现在众人面前。劫后余生的苏轼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仕途上的失意和世间的纷扰皆不值一提,寄情山水自然中,心灵平和自在,方能从抑郁不平的苦闷中获得解脱,他开始试图融入当地生活,“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黄州虽僻陋,但自然景观极好,《赤壁赋》便是其流寓黄州时期所作,蕴含着深厚的哲思。苏轼跳脱出人生渺小而短暂,人生的价值得不到体现这一局限,认为人生在世不能单看一刹那中的形象变化,而要以巨眼观彻物我心灵交辉中所妙悟的大道,这才是永恒所在。⑤或许苏轼在劝慰客人的同时也是在劝慰自己,若苏轼真的忘怀于得失,又岂会写下艳羡周郎,抒发壮志难酬的感叹呢?显然,这只是苏轼身处逆境的自我安慰,是与自己贬谪身份和解的无奈之举。
(三)流寓异地的精神孤独
对于流寓文人来说,精神上的孤独远比物质生活的匮乏更痛苦。杜甫“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以乐景写哀情,以天地间孤零零的沙鸥象征着自己的漂泊无依;苏轼“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贬谪的苏轼如同遭遇不幸的“孤鸿”,以苦闷忧郁的心态度过一个又一个漫漫无际的长夜……此种精神孤独并非物质生活能解决。
柳宗元作为永贞革新的核心成员,自永贞元年加贬为永州司马后其精神状态一直是困顿失意的,是在山水景色中寻找精神寄托的无奈之举。《始得西山宴游记》中记载:“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 ⑥自从贬居永州后,内心常常忧惧不安,造成柳宗元忧惧的原因除了上文提到的外部环境的艰苦,更重要的是至亲的相继离世带给柳宗元的打击。永州复杂的自然环境难免使人水土不服,况柳宗元的母亲年岁已大,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身体自然吃不消,在抵达永州后不久便病逝,作为戴罪之身,柳宗元也无法将母亲的灵柩奉归长安,不久后他的女儿也夭折。个人的理想抱负无法施展,朝堂之中又有奸佞小人的诋毁指责,加之至亲因自己的贬谪遭遇而亡,故交好友避而远之,种种事件堆积起来怎能不令他痛苦与悔恨?原本身体就不好的柳宗元此时“形容枯槁”,几近万念俱灰之下写下千古孤绝之篇《江雪》。可以说,“孤独”二字贯穿了整首诗,也贯穿了柳宗元的一生。所谓“诗穷而后工”,在流寓地永州,柳宗元的确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中不乏风格轻快的山水游记,“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最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从山水景物中得到暂时的解脱,于孤独苦闷中寻得短暂的快乐,这何尝不是一种自我催眠式的孤独呢?此外,柳宗元的诗文中多是幽树、愚溪、毒蜃、羁鸿等意象,大多渲染了忧惧、幽怨、孤寂等情绪情感,甚至隐喻了某种绝望心理。⑦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曾言道:“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存在,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柳宗元终其一生,始终未曾走出忧郁孤独的精神天地。“恬死百忧尽,苟生万虑滋”,强烈的失落感使他不甘心从此蜗居在偏僻荒芜的永州了却余生,可悲惨的境遇却时刻提醒着他作为有罪之臣已无翻身之日,诸多难以解脱的苦痛和悲伤怨愤形成心理动力,加上不甘心的生命意志,发之诗文,蕴藏着一股激切孤愤的情绪。
苏轼历来被认为是旷达文人的典范,在其刚流寓黄州时便写下“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但联系时代背景便知这并非苏轼此时深层的内心世界。此时的苏轼刚经历过政治的摧残,流寓到“不闻乡国信息”的偏远陌生的隔绝之地黄州,苏轼内心定然忧惧万分。在启程去往黄州的路程中作下《游净居寺》一诗,“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回过头频频望向吾家山,行将老去的“我”该身归何处呢?不仅流露出苏轼的思乡情切,此刻流逝光阴的无奈和流寓异地的彷徨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可以说,《游净居寺》诗中所呈现这种孤独迷茫的心境才是苏轼此刻深层而本真的心态。且苏轼为避免再惹出祸端,不仅不再作诗文,还劝谏友人少作诗文,甚至放弃交游,闭门谢客。“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开口得罪,不如且已,不惟自守如此,亦愿公已之”“自惟罪废之余,动辄累人”。几近隔绝与外界之联系,以至于外界竟荒谬传言他已去世,可见苏轼在流寓黄州时期内心的孤独寂寞。
二、柳苏流寓心态的同中之异
古往今来,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遵循着“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原则,作家的情感心态可从作品中得到展现。柳宗元、苏轼年少成名却仕途坎坷,流寓偏僻荒凉之地,二人有着类似的人生遭遇,可反观柳苏二人的诗文可知,柳宗元诗文中反映出的心态多是以怨愤、愀然无乐为主,而苏轼则是以顺处逆的达观倾向。因其二人所处时代及人生际遇的不同,故在此对其二人之不同点仅作简要分析。
(一)柳宗元愀然无乐
古人立身处世讲求“立德立功立言”。在柳宗元眼里,立德、立功的分量要远胜于立言。自其因永贞革新失败流寓永州,又逢宪宗不断打压,便已知晓自己济世救国的理想难以再实现,诗文创作透露出内心淡淡的忧愁,就连以写景取胜的山水诗文都被其当作抒发孤独幽怨情怀的载体,风格较苏轼而言更为深重。翻开柳宗元奇异的山水诗文,“始至稍有得,稍深邃忘疲”“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不难发现他对这奇观异景的喜悦之情,如痴如醉,但作为一个内心深处更喜建功立业的政治家来说,柳宗元面对这美景内心却是复杂的。他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内心深处更希望能够“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实现建功立业的理想,又怎会甘心蜗居在这小小的永州做个闲散官员,他始终跨不过心里的那道坎,无法真正与秀美的风景融合,因此他笔下的景物总是带着一种幽怨的色彩。“杳杳渔父吟,叫叫羁鸿哀”,渔父之吟正因有了“羁鸿”的哀鸣做陪衬,便更显悲凉;“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将尖山比作利剑锋芒,能够割断人的愁肠,想象奇特,突出了其高耸入云的特点,古人常有悲秋之感,更加突出了自己的悲愤之情;“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层层叠叠的远山和弯弯曲曲的九江象征着作者人生道路上的阻碍,景中寓情,愁思无限;“谪弃殊隐沦,登陟非远郊”“惜非吾乡土,得以荫菁茆”点明作者谪居永州的郁闷心情,一种遭遗弃的感觉涌上心头……此外,柳宗元流寓永州时,由于“寓居湘岸四无邻”,备受孤独寂寞的煎熬,故其诗文当中常有“独”字出现⑧,如“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江雨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看似闲适的生活,实则透露出柳宗元深深的孤寂悲愤之情。
(二)苏轼安之若素
在唐代,三教一直处于兼而未融的状态,而宋代实行的是三教合一的政策,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使宋代士人热情参与政治,而道家顺应自然的思想和佛家舍弃欲望、寻求解脱的思想又促使他们能理性地看待人生的荣辱得失,深刻影响着宋代士人的价值观念与处世心态,这也是苏轼较柳宗元豁达的重要原因。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苏轼最为人乐道之处就在此,尽管生命中有着太多无可奈何之事,他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平和接受,接受世事无常和事与愿违,他坚信“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人生是一场体验的旅程,就应该顺势而为,随遇而安。谪居黄州并非苏轼自己所能选择的,虽有苦闷,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命运带来的波折,顺应自然天道。
经过时间的沉淀,在黄州的四年里,老庄哲学深刻影响着苏轼,促使他以超然的态度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内心由初入黄州的恐惧忧愁转向平静安和。流寓黄州,本是责罚,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救赎呢?他可以远离政治的喧嚣,过上真正隐居安宁的日子,“近于城中葺一荒园,手种菜果以自娱”,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于朴素的田园生活中亦能发现生活的美好。
在经历政治挫败之后,苏轼并没有逃避,而是直面痛苦,努力从老庄哲学寻找超脱。流寓黄州的这些年,苏轼渐渐明白仕途上的失意和自己的人生比起来不过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正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所言:“苏轼扬弃悲哀的宏观哲学,始于人生并非只是充满了悲哀这样一种认识。如果人生的离别和团聚如循环一般相互交错,那忧愁和喜悦也是相互制约的。把这看作是人生,就是循环哲学。” ⑨所以,与其说苏轼豁达,倒不如说他平静地接受这个世界应有的起伏,接纳生活,获得了属于自己真正的平静。
三、柳苏二人同遭贬谪心态却大不相同之原因
(一)性格使然
个人的性格是受一定的文化形态陶冶的结果。⑩中唐时期提倡儒释道三教合流,但就个人价值取向而言,柳宗元虽信佛,也曾说过“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但他之所以研究佛学,是为了将其融合进儒家思想体系中,以儒学为价值标准,取其有益于世者,即援佛济儒。儒家强调积极入仕,那么建功立业,致君尧舜则是封建士人的首要人生追求,即便流寓永州困顿失意时也不曾打消他事功的执着,佛教远离纷争追求清净的禅定思想对柳宗元也有深刻的影响,他山水诗文中清冷幽寒的意境恰恰是他孤傲性格的映衬。
经过唐代的融合发展,儒释道三教在宋代已呈现出三教合一的趋势,对宋人的人生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释道三家思想贯穿苏轼的一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苏轼不像柳宗元一般执着地追求仕途的通达,在失意困顿时以佛道思想宽慰自己,虽有苦闷忧郁之情,但他能从悲伤的情绪中尽快抽离,转向能够抚慰心灵的事物中去,“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苏轼自觉地于山水景物中寻求美,慰藉心灵,享受人生的乐趣。
此外,不同的时代风貌对文人的性格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唐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虽然中唐时期略有削弱,但唐帝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宏伟的气势往往使得唐代士人拥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功利心较重,所以当柳宗元即使创作了众多山水游记,试图表明他已将得失忘怀于山水景色之中,可其诗文当中意象却还隐隐透露出他孤傲的品格。而宋朝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动荡,国家实力也不如唐帝国,所以宋代士人的精神面貌往往是理性客观的,较之仕途的失意也能坦然面对,这也是二人流寓心态差异的重要原因。
(二)人生敬仰不同
《沧浪诗话》云:“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 ⑪屈原生活在“世混浊而不分,好蔽美而嫉妒”的时代,奸佞小人当道,屈原的美政理想不能实现,政治革新也以失败告终,流放异地,终投汨罗而死。相似的时代环境和人生经历是柳宗元接受继承屈原精神的前提。他和屈原一样怨愤不平,遂发出“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的呐喊。面对流贬的政治打压,柳宗元“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苟一明大道施于人,死所无憾”,坚定自己的理想不改变,坚决不放弃他所推崇的“大中之道”,颇有屈原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之气概和百折不挠的坚韧意志。明人陆时雍评柳诗称“深于哀怨”,堪称“骚之余派”,柳宗元流寓永州时期的辞赋,如《惩咎赋》《闵生赋》《囚山赋》《骂尸虫文》等或抒发怨愤之情,或讽刺现实,或表明自己高洁的品格,是其幽怨苦闷情感的真实流露,明显继承屈原骚怨的传统,表现出与屈原辞赋的一致性。
由于宋代儒学的发展,特别是理学思想的兴起,人们对于传统的儒家思想有了新的认识,陶渊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因而受到宋人的广泛推崇,成为宋朝士人的精神寄托和文化象征。陶渊明旷达超脱、冲淡平和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气质对刚刚经历了重大政治贬谪遭遇的苏轼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依靠,苏轼流寓黄州时为缓解全家饥寒交迫的窘境,过上了躬耕的生活,正是开荒种地的艰辛生活让苏轼对陶渊明有了深深的敬意,然而更重大的意义在于苏轼能从陶渊明身上找到精神慰藉。陶渊明的洒脱悠然,淡泊名利,“纵大浪化中,不喜亦不惧”的人生态度和与天地同流、与万物合一的澄明境界正是苏轼所向往的,于是流寓黄州,躬耕东坡的他常常以渊明自况,半醉半醒半梦半真之间,顿觉自己“只渊明,是前生”。这种跨越时空的心理共鸣,是苏轼面对这种颠沛流离生活的精神支撑。苏轼对陶渊明人生境界的向往,终使其获得生命廓然无累的自得与自适。
(三)责任使命不同
河东柳氏是唐朝“五姓七望”的世家大族,因政治漩涡的冲击而逐渐没落,“柳氏号为大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的窘迫局面促使着柳氏子孙必须承担起复兴家族的重任。“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踣弊不振,数逾百年。近者纷纷,稍出能贤,族属旍曜,期复于前”皆表明柳宗元想要重振柳氏,维持世家大族地位的愿望。年少成名的柳宗元仕途顺畅,这为他复兴家族带来了一点希望,可一朝天子一朝臣,永贞革新运动的失败无疑给了他一次重创。柳宗元妻杨氏婚后不足三年便因“孕而不育,厥疾增甚”亡故,在他心中便只剩下才学兼优的堂弟柳宗直还有希望能够复振宗族,但事与愿违,柳宗直因受到自己的牵连而始终未能进士及第,柳宗元对此极为憾恨:“兄宗元得谤于朝,力能累兄弟为进士,凡业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举,艺益工,病益牢。”最后的一点希望也被浇灭,复振家族的愿望与个人的执着理想融合,是柳宗元艰苦流寓生活的悲愤来源。
和柳宗元相比,苏轼倒幸运多了。宋代以文治国,对士大夫较为优厚,所以尽管苏轼犯下大罪,宋神宗也并未将其处死,而是流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且苏轼并无复兴家族之使命,其父苏洵曾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弟弟苏辙也和自己同登进士科入朝为官。在苏轼流寓生活当中,常常将自己内心的感受与弟弟子由诉说,也正因为有弟弟子由的陪伴,苏轼内心的痛苦才得以稍稍缓解,这也是苏轼较于柳宗元流寓心态豁达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总结
柳宗元流寓异地的悲愤,苏轼则以达观的人生态度去面对坎坷的生活,柳苏二人同为流寓文人,心态却不相同,然二人都努力从自身的苦难中挣脱,悲愤寄寓山水之间,才造就了诗文的千古流传,创造了更加辽阔广袤的天地。人也许会陷于孤独,但同样人也会在绝境中完成自我救赎。
注释:
①张学松:《“流寓”论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5页。
②李芳民:《空间营构、创作场景与柳宗元的贬谪文学世界——以谪居永州时期的生活与创作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95-108+196页。
③李芳民:《佛宫南院独游频——唐代诗人游居寺院习尚探赜》,《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
④(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379页。
⑤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54页。
⑥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载《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2页。
⑦周水涛、张学松:《论柳宗元流寓文学创作的意象图式与隐喻编码》,《江汉论坛》2023年第4期,第76-83页。
⑧王德春:《柳宗元的贬谪生涯与他的山水文学》,安徽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页。
⑨吉川幸次郎著,章培恒等译注:《中国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4页。
⑩王德春:《柳宗元的贬谪生涯与他的山水文学》,安徽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2页。
⑪严羽:《沧浪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