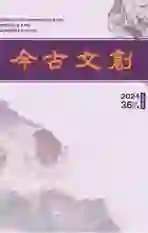《最蓝的眼睛》中的身体意象及女性审美价值观分析
2024-09-20赵燕
【摘要】托妮·莫里森(以下简称莫里森)是美国当代杰出的女作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女作家。在莫里森的作品中,身体意象是至关重要的写作对象之一。本文以莫里森的代表作《最蓝的眼睛》为例,通过分析该作品中的多重身体意象及女性审美价值观,揭示强势的白人审美文化对黑人女性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制和迫害。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身体意象;美国黑人女性;审美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6-0027-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08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莫里森笔下美国黑人女性的身体困境研究”(项目编号:2019SJA1615)的阶段研究成果。
一、引言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 1931—2019)是美国当代杰出的非裔女作家,在20世纪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莫里森的主要成就在于她的长篇小说,经过60年的笔耕,她创作了11部长篇小说,成就斐然,影响巨大并获得多项殊荣。莫里森的作品大多以美国的黑人生活为主要内容,黑人女作家的独特身份使莫里森对黑人女性的生存境遇有着深刻全面的了解,并用细腻而诗意的笔触,淋漓尽致地加以描绘。她凭借“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充满诗意特征的小说,生动地再现了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1]24,一举获得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莫里森以独到而敏锐的女性视角和自身丰富的女性体验,对黑人女性的命运进行了更透彻、更深情的审视。她坚定地表示,黑人与女性这两种身份的相互交融构成了自己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使她“能进入到那些不是黑人和女性的人所不能进入的一个感情和感受的宽广领域”[2]243。
托妮·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于1970年正式出版,立即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故事讲述的是发生在1941年美国俄亥俄州洛林市某个黑人社区一个11岁的黑人小姑娘佩科拉的悲剧生活。小说主人公佩科拉是一个肤色深黑、外貌平凡的女孩,她在家庭暴力、教育忽视、同伴欺凌和成人的冷漠中苦苦挣扎。佩科拉错误地以为自己的黑色皮肤是痛苦的根源,因而渴望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以赢得众人的喜爱。她虔诚祈祷,却未料到现实的残酷,在遭受生父的残忍侵犯后,她生下死婴,遭到社会的遗弃,精神崩溃,幻想自己拥有了梦寐以求的蓝眼睛,最终迷失在虚幻的世界中。《最蓝的眼睛》不仅具有深刻的象征意蕴,更是美国黑人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之作,标志着一次创新的飞跃。
蓝色的眼睛、黝黑的皮肤是该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身体意象,富有丰富的内涵、寓意非常深刻。本文以《最蓝的眼睛》中的身体意象为切入点,分析在白人文化和审美价值的“精神奴役”下,黑人女性的身体被鄙视与贬损、抑制与弱化,致使黑人女性身躯日益麻木、审美价值逐步扭曲、心灵蒙上白人文化迫害之尘,最终沦为白人文化的牺牲品。
二、《最蓝的眼睛》中的身体意象分析
著名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Bryan S·Turner)从社会学角度指出:“身体,乃是人的本体,它既为个体存活的肉体之躯,也是社会观念和话语实践的产物。”[3]2因此,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身体的内涵是不同的,身体是社会关系与话语的产物。罗伯特·弗朗克尔(Robert T·Francoeur)认为个体的身体形象铭记着“自我的观察、他人的反应及本人的倾向、情感、回忆、幻想、经历”[4]71-72,身体也是产生自我认同、他人认同以及主体建立的物质基础。《最蓝的眼睛》中,在强势的白人文化和审美价值下,黑色的眼睛、黝黑的皮肤和黑色的身体一直被凝视、被规范、被否定、被贬损、被抑制,黑人女性无法借此正确认识自己、建立自我主体,而逐渐沦为白人文化的受害者。
(一)最蓝的眼睛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人类心灵的映射和精神状态的直接体现。在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中,眼睛一词作为标题的一部分,在文本中多次出现,至关重要,意义深刻。
故事主人公黑人女孩佩科拉生活的黑人社区里,蓝眼睛的白人小女孩形象随处可见。在刻板的白人审美标准之下,“蓝眼睛”是美,是高贵,是身份的象征,它意味着被认可、被接纳和被珍爱,就连蓝眼睛的白人布娃娃也因人们爱屋及乌,备受喜爱,然而黑人女孩却因没有蓝眼睛而遭受不公与不幸。佩科拉把父母的争吵和伤害、老师和同学的排挤、白人的傲慢漠视以及生活的贫穷困顿全部归因于自己的“丑陋”。她时常凝视着镜中的自己,陷入沉思,竭力探寻丑陋的根源。这份外貌上的不安,如同无形的屏障,把她和她的黑人父母、黑人同胞远远地隔离开。她认为只要自己的模样不变,继续丑陋,就只能继续忍受糟糕的生活,继而萌生出想要拥有对一双蓝眼睛的想法,并虔诚地祈祷。佩科拉意识到如果她有双美丽的眼睛的话,她本人会变得不同,她的爸爸妈妈也会不同。佩科拉把蓝眼睛看作摆脱苦难的救命稻草与一线生机,但是对于黑人女性而言,蓝眼睛是触不可及的虚幻妄想和使人陷入绝境的深渊。佩科拉终其一生都没有放下对一双蓝眼睛的渴望,她将自己禁锢在执念里,永远无法了解自身的美丽,而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我憎恨的误区。当佩科拉被酗酒的父亲乔利强奸怀孕,最终婴儿早产,父亲去世,母亲家暴,佩科拉也精神失常,但仍然将生活希望寄托在蓝色的眼睛上,沉浸在拥有一双蓝眼睛的幻梦之中,事实却每况愈下,直坠深渊。
佩科拉的悲剧命运是无数黑人女性的缩影和真实写照,她们生存于贫穷苦难、种族歧视、男性凝视之下,全盘接受“白人之美”,而自卑于“自身丑陋”,甚至幻想与崇拜“白人之美”、过分地将“蓝色的眼睛”视为救赎之道的行为与观念在黑人女性群体中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代代相传,逐渐演化成为准则与陈规的悲剧。由此可见刻板的白人审美在黑人群体中根深蒂固,体现出白人主导的社会之下,种族观念大行其道、白人审美价值观无孔不入、平等价值观无地自容、黑人话语权与意志备受压迫。主人公佩科拉无疑是在这种审美观念之下、在“蓝眼睛”的美梦之中,在无尽的沉默与祈祷中,被现实压垮,逐渐走向了自我消亡的晦暗之路。
(二)黝黑的皮肤
小说里反复出现的身体意象,不仅有白人的蓝眼睛,还有非洲裔人群黝黑的皮肤。肤色是种族区分的鲜明标志,在小说中,黝黑的皮肤则以一种“丑的烙印”的形式,深深地刻在每个黑人女性的心中,使她们沦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种族歧视始于殖民时代,在美国政府强制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时期达到了顶峰。而美国的种族歧视——特别是黑人歧视——尤其严重,具有持续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基本特征,严重威胁着美国国内黑人各项人权的保障和实现。虽然,美国白人贩卖黑人到美洲充当黑人奴隶的“肉体奴役”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却留下了美国南方黑人的贫困潦倒和处处隐含着的种族歧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黑人女性的身体仍然被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身体政治支配。作为黑人文学的代表作,《最蓝的眼睛》就是以1941年前后美国黑人遭受到美国白人竭力推行的以白人文化泯灭黑人古老传统的“精神奴役”为背景的。
《最蓝的眼睛》中,黝黑的皮肤无疑是黑人女性群体眼中丑的典型、苦难的发端,从出生开始被天然地否定、甚至视为罪恶、黑人甚至对自身天生的肤色表示深深嫌恶与无限自卑。因为黝黑的皮肤,佩科拉一生下来就遭到母亲波琳的嫌弃,几乎得不到母亲的关注和疼爱。波琳从早到晚都在白人雇主家干活,并乐在其中,而不愿回到自己的家。即使回到家,不是和酗酒的丈夫吵闹打架,就是厉声呵斥孩子。佩科拉的哥哥为了逃离这种糟糕贫穷的生活而多次离家出走。
与身为男性的黑人哥哥不同,年幼的佩科拉不能、也不敢离家出走,因为外面世界对黑人女孩的敌意更多、更深,这种敌意与厌恶最多来自白人。佩科拉去白人店主开的菜蔬果品店里买糖,遭到白人移民老板充满厌恶的漠视。白人老板不愿意浪费眼神看一个黑人小女孩,在空洞犹豫的目光之下是深深的厌恶。虽然佩科拉只是一个小女孩,“可是她在别的成年男人的目光里曾见过好奇、厌恶,甚至愤怒的表示……在下眼帘的某个部位表现出来的厌恶之感,在所有的白人眼里都曾见过。他们的厌恶一定是针对她的,针对她的黑皮肤的……正是这黑皮肤引起了白人眼神里带有厌恶之感的空白”[5]31。当佩科拉把零钱递给白人老板时,他犹豫迟疑,不想碰佩科拉黑色的手,使佩科拉陷入深深的羞耻感和愤恨之中。
即使身处有色人种和黑人同学、邻里之中,黑人女孩受到的敌意丝毫不减。有色人种虽然肤色不是白色,但因其浅棕色的肤色而自认为不同于黑人,比黑人高贵许多。在白人文化和审美价值的渗透下,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尽善尽美地替白人干活”[6]54——为白人做饭,教育黑人听话顺从、安抚白人雇主。为了更好地融入白人的主流社会,他们刻板地模仿白人的行为举止,盲目地推崇白人的生活方式,极力地靠近白人的审美价值,而将其纯真简朴的本色和纯真情感彻底抛弃,成为白人进行精神奴役的共犯。有色人种男孩裘尼尔因佩科拉黝黑的皮肤而欺负她、捉弄她,在戏弄的过程中彰显自己浅棕色皮肤所带来的优越感。裘尼尔的妈妈将佩科拉叫作“讨厌的小黑丫头”,并怒吼着将其赶走。这样的有色人种比比皆是,他们和白人一样,认为黑人“像苍蝇一样成群结队地飞行,像苍蝇一样散落下来”[7]60,极力排斥与压制黑人。
白人至上的审美价值使黑人群体变得愚昧、自憎且无望,而这些愚昧、自憎与无望是白人长期施加精神奴役和文化渗透的结果,被黑人吸收、内化为扭曲的审美价值。黑人男孩把对自己肤色的鄙视转化成对黑人女孩的诅咒、辱骂和欺凌,他们把佩科拉像猎物一样围在中央,念着自编的打油诗,嘲笑佩科拉是“小黑鬼”,尽情享受捉弄同胞的快乐。面对来自同胞的羞辱与欺凌,佩科拉只能屈辱忍耐、无助哭泣,感到更加自卑,甚至自我厌恶、自我憎恨。
面对生活的贫苦困顿、学校里的欺凌羞辱与家庭的暴力冷漠,佩科拉将一切苦痛归结于黑色的皮肤与丑陋的外貌,因此她对白人审美中的蓝眼睛、白皮肤的漂亮女孩充满无限崇拜和向往。黑人们一度把蓝眼睛、黄头发和粉红色皮肤的白人娃娃当作心肝宝贝,并把这样的标准深深刻在心里,甚至佩科拉喝牛奶就只是为了触摸和欣赏白人女孩的美貌。佩科拉对白人外貌的向往使她厌恶自己丑陋的外貌,但实际上真正的丑陋并非她的外表,而是她内心深处的自我偏见。由此可见,黝黑的皮肤既象征着偏见、弱势、不平等,也象征着全盘接受白人的审美价值观的黑人们在不知不觉的麻木之中抛却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陷入内心的阴翳与雾霾,坠入自卑的无底深渊。
(三)麻木的躯体
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是知觉的载体,个体的人只有在自己的身体中才能发现自己的意识、经验及身份;没有身体,人的主体将处于无所附依的状态,个人乃至人类的经验、生活、知识和意义都不复存在。”[8]20对孩子来说,身体不仅是他们探索世界的媒介,更是自我认知的起点。通过观察、探索和感知自己的身体,孩子们开始将自身视为一个可以被审视的对象,逐渐接纳社会对他们的审美标准和评价。然而,在一个深植白人文化霸权的社会评判体系中,对黑色身体的规范和否定无处不在,造成黑人女孩的心灵日益扭曲,身体日渐麻木。
小说讲述者弗里达、克劳迪娅姐妹视月经初潮的第一想法是“肮脏的”,由此可见处在社会底层的黑人群体们对于生理知识的缺失与匮乏,并且无故地否定自己。这种自我否定、自我厌恶是“自卑”种子的萌芽,沾染在裙子上的月经血迹是黑人孩子人生中的偏见烙印。克劳迪娅面对被房客亨利先生的猥亵,第一反应不是身体受到侵害,而是“被毁掉”的无尽的自我惶恐,因为在她们眼中,只要被男人以非自愿的方式触摸,身体就会臃肿肥胖,好似堕落的妓女。佩科拉面对自己父亲的不伦的侵犯,选择服从与自承苦果,面对学校男生们的暴力与屈辱选择沉默不语,面对白人店主的厌恶和漠视,感到深深的羞耻……和佩科拉一样,弗里达也是黑人女孩,她对自己的肤色和身份也常常感到困惑。她不明白为何周围的大人和小孩如此迷恋甚至崇拜白人女孩;不明白为何在聚会上,自己的父亲和白人小姑娘跳舞,而不选择她;不明白为何她弄坏了一个蓝眼睛的白人布娃娃后,大人会大发雷霆地斥责她;不明白为何大人从不考虑她的感受,不征求她的意见,而是想当然地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喜爱白人布娃娃。一切对于自我和本民族躯体的无知、麻木、不珍惜,源于长期的白人文化与审美的渗透,造成黑人丧失主体意识、否定自我价值、缺乏反抗意识。
在暴力而残酷的社会现实之下,黑人女性的躯体备受白人社会的轻视与侮辱,遭到黑人群体的冷落与忽视,也成为黑人男性发泄欲望、施暴玩弄的对象。出于对安全的奢望、对暴力的恐惧与内心的自卑,广大黑人女性陷入了躯体的麻木,而麻木仅仅是徒劳,甚至变本加厉,使得苦难接踵而至、不断扩散与内部循环,渐渐吞噬人心、泯灭一切黑人女性心中对美好的些许向往。
(四)蒙尘的心灵
小说主人公佩科拉姓布里德洛夫(Breedlove),从字面上理解是“哺育爱”,可事实上恰恰面临爱的缺失。面对苦难的深渊,她只是祈祷自己的身体消失,消失在那张冰冷而脏污的床上。佩科拉正是黑人种族内部的极端自卑、不自信、不自爱的典型,她麻木地顺从歧视与压迫,试图通过逃避来摆脱苦难的命运。然而,她却错误地将希望寄托于外在的美貌和蓝色的眼睛,误以为这是摆脱苦难的“灵丹妙药”。但最终,对蓝眼睛的幻想之光,并未能照亮黑人女性内心那片阴霾与黯淡。
以白人为主流的美国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宣传白人至上的文化和审美价值,企图渗透到美国社会各个阶层。佩科拉的母亲波琳,盲目推崇白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价值,逐渐迷失自我,也无法给予孩子应有的关爱。在她眼中,黑皮肤的儿女是她与丈夫的复制品,时刻提醒自己黑色的皮肤、黑色的身体是丑陋的、卑微的、低贱的,是白人主流审美所鄙视和厌恶的。正是白人文化和审美价值观的侵蚀扭曲了波琳的心灵,使她迷失自我,同时也丧失了母爱。事实上,“黑人母亲是黑人文化传统的养育者和传承者,她们应该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环境下学会如何养育孩子,保护孩子,知道爱孩子,教导孩子们在种族歧视下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向种族主义发出挑战”[9]115。波琳作为母亲,理应引导女儿正确理解生活与文化价值,让她在母爱的滋养下健康成长,领悟人生的真谛和民族文化的精髓。但波琳未能履行这一职责,她为了迎合主流文化,抛弃本民族文化,丧失种族自尊和爱的力量。波琳传承给女儿的,仅是“黑即丑”的错误观念,不仅自我身份模糊,母爱错位,更让女儿承受了不应有的悲剧。波琳的母爱并非不存在,而是在种族偏见的社会压力下被扭曲和扼杀了。没有母亲的关爱、照顾和引导,佩科拉自幼就被灌输自己是丑陋的想法,不仅遭受身体的歧视和贬损,更饱受精神的煎熬和折磨,最终被吞噬、毁灭。
蒙尘的心灵源于白人施加的“精神奴役”,这种奴役与压迫无时无刻、或无形或有形,其恶果是一部分黑人全盘接受了白人的价值观,而在不知不觉之中抛却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造成黑人的精神自主性几乎荡然无存,使自卑生长、软弱加剧、悲剧频频上演。而莫里森将这一颗颗蒙尘的心灵一览无余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正是希望读者反思,能够将自爱与自强的光芒引向黑人群体的心中,为黑人种族的未来,照见微弱渺茫的星光。
三、结语
在莫里森《最蓝的眼睛》中,“失语”状态贯穿了身体意象的描写与塑造,白人文化的强势不仅贬损、压制黑人的身体,同时也剥夺了黑人的话语权利,让白人的“蓝眼睛”审美标准渗透到学校、家庭、文化、语言、衣着之中,使得黑人群体的自我否定蔓延扩散,继而加入否定其他黑人的白人权利机制中。卷曲的头发、黑皮肤、曾经为奴的身份、民族的传统、自我意识,都被黑人群体一样一样抛弃,剩下的只有自卑感和渗透在“他者”中的一具身体,这无疑是可悲可叹,而又让人怒其不争的。这种悲剧对于黑人女性尤其具有毁灭性。唯有在年幼时深刻植入黑人文化的传统与审美观念,才能对自身的黑色身体形成正确认知和自我认同,才能不被强势的白人文化所控制而困惑迷乱、丧失自我,才能用本民族文化对抗并瓦解白人的文化渗透和精神奴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黑人民权运动的汹涌发展与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女性主义思想在美国逐渐盛行并广为传播。黑人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并开启了抵制白人文化和审美的漫长之旅,逐渐重拾本民族非洲传统和审美价值,正确认识自我的身体和身份,重新构建自我主体。在平权运动与黑人运动情绪高涨的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个独立强大的黑人女性正吸引着世界的关注,引领着不同领域的潮流,莫里森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莫里森的出现,颠覆了以往对黑人女性固有的传统观念,她把黑人文学经典延伸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在文学领域中,她用正义的方式捍卫着黑人肤色的尊严,用尽毕生的心血为黑人群体遮风挡雨,她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同时更是一颗功勋卓著的“黑人良心”。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看见莫里森呼吁心灵美、自尊自爱、以知识与勤奋改变命运的正确价值观,正是这份向上向善的信念,让莫里森在摆脱种族歧视的枷锁,向着美好奔去的同时,还不忘给逆行的黑人女性同胞们有力而温暖的勇气。
参考文献:
[1]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创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Taylor-Gutlirie,Dallill.Conversations with ToniMorrison[M].Mississippi: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
[3]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M].马海良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4]Francoeur,Robert T.and Timothy Perpereds.TheComplete Dictionary of Sexology[M].New York:The Continnum Publishing Company,1995.
[5]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M].胡允恒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6]丹尼尔·T·普里莫兹克.梅洛-庞蒂[M].关群德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7]O’Reilly,Andrea.Toni Morrison and Motherhood[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ress,2000.
作者简介:
赵燕,女,汉族,江苏淮安人,南京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淮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