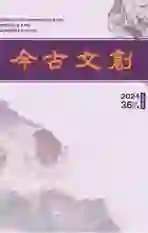束缚与沉沦:《围城》《妻妾成群》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2024-09-20石莹莹
【摘要】《围城》从男性方鸿渐的视角窥视了新旧思想交替之际各类女性对于婚姻爱情的不同看法,《妻妾成群》从女性颂莲的视角呈现了封建礼教压迫下庭院中已婚女性的生活剪影。两部作品中塑造的多位女性虽在生活空间、受教育程度以及思想性格上各有差异,但由于自身局限、外界压迫等原因,最终都走向悲剧的结局。同时,由于性别视角及创作主旨的不同,观察主体对于女性形象的评判与塑造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关键词】《围城》;《妻妾成群》;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6-0024-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07
《围城》以方鸿渐为中心塑造了新旧时代交替下或遵从传统礼教或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形象,《妻妾成群》以颂莲为主体叙述了陈家庭院中四位妻妾的钩心斗角。虽然两部作品的创作主旨、叙述主体均不同,但其中各位女性在婚姻爱情中的经历及结局有着共通之处,通过对比研究其命运成因,对于当下女性反思婚姻爱情、实现自我突破有着警示及借鉴意义。本文将选取两部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从生活空间、受教育程度以及思想性格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归纳其悲剧命运的成因异同,探究女性在婚姻中悲剧命运形成的主要因素,同时论述性别视角差异及不同创作主旨下对于女性形象描述及塑造的差异所在。
一、《围城》《妻妾成群》女性形象对比
(一)生活空间
1.封闭的庭院
《妻妾成群》主要围绕陈家庭院中陈佐千老爷娶的四位妻妾展开,整部作品中四位女性都被局限在了固定的狭窄空间里,行为举止皆受束缚。
这四位女性中,作品并未提及毓如和卓云进入陈家前的经历,而梅珊在进入陈家前是戏子,在京剧草台班里唱旦角,颂莲嫁入陈家前正在上大学。然而,无论是前期生活未知的毓如、卓云,还是曾经有过一定空间自由的梅珊、颂莲,嫁到陈家后均被困在了一方小小天地中,在住所厅堂间徘徊。陈家庭院就似一口深井,掉进去便无法出来,直至死亡都无法逃脱。在这样的封闭空间里,毓如、卓云选择将情感寄托在丈夫与孩子身上,维护好贤妻良母的形象;梅珊追求自我,选择与医生出轨以寻求精神慰藉,却不幸被卓云揭发;而颂莲则在目睹梅珊被投井后成了疯子。
2.开阔的世界
《围城》中主要塑造了与方鸿渐爱情经历相关的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四位女性,与《妻妾成群》中女性所处的封闭空间相反,《围城》中的女性在生活空间上享有极大的自由度。仅在前文出现的鲍小姐能够在未婚夫的资助下出国留学;苏文纨前期出国留学,后期虽已嫁人却仍能够去各地经商;唐晓芙可以自由出入家庭,到苏家做客;孙柔嘉可以跟着赵辛楣越过大半个中国去三闾大学任教,与方鸿渐结婚后也不必住在方家,吵架后更是能够直接出走。《围城》中的四位主要女性人物不会被空间禁锢,她们的归属从不在一方庭院,而是能够见识到更开阔的世界,加之时代影响,因而能够拥有一定的主体意识。
(二)受教育程度
1.封建礼教
《妻妾成群》中的毓如是封建礼教影响下的传统女性,她早早地嫁入陈家,侍奉丈夫、生儿育女,终其一生困于庭院之中。她是封建礼教的捍卫者,也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受害者。出嫁从夫,她需顺从丈夫,即使丈夫纳妾、宠爱小妾,她也不能直接表达不满,只能通过礼佛排解苦闷,借断珠无视新入门的颂莲;在家为主母,她既要能够管理家庭,又要彰显当家主母应有的气度,故而她虽居于家中,却又仿佛处于世外,三妾间的钩心斗角她不曾在意,置身事外反倒落得一身清静。从始至终她都未曾以毓如的身份活过,封建礼教教她为人妻为人母,却不曾教她做自己。
《妻妾成群》中的卓云亦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但她不同于毓如,作为无儿的妾室,她始终坚持争宠。母凭子贵,她没有儿子便没有依靠,所以她只能选择在陈佐千那获得一席之地。她有心机有演技,为了在一个又一个年轻女孩的威胁下获取丈夫的喜爱,她装作人畜无害却暗地策划,揭发了梅珊的出轨也吓疯了颂莲,成功获得了暂时的胜利。
2.新式教育
《妻妾成群》中的颂莲在嫁入陈家前正在上大学,她接受过新式教育,有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尊与傲气,所以当陈佐千第一次去找她时,她“闭门不见,从门里扔出一句话,去西餐社见面”;然而她又未曾真正认同过新思想,根本上仍遵从传统礼教,面对父亲去世后的归属抉择,她选择了无需受苦受累的做妾,放弃自由自尊,甘愿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从此陷入牢笼。初入陈家时,她尚有过自主意识,不愿一味顺从陈佐千,耍着小性子享受陈佐千基于新鲜感的宠爱;但渐渐地,她被腐朽的陈家同化,开始在意权名,在争宠中逐渐堕落,最终落得个发疯的下场。
《围城》中的孙柔嘉同样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虽然她受到封建礼教的迫害,坚持要和方鸿渐结婚,但她本质上是厌恶封建礼教的,结婚于她而言不是爱情使然,而是外界施压所至的必经之路。婚姻并不能束缚她追求自我、实现独立的脚步,反而为她的自立行为提供了便利。虽然她在婚姻上并不如意,但在女性意识觉醒的道路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几位女性。
3.国际视野
《围城》中的鲍小姐与苏文纨都是接受过国际教育的女性,但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鲍小姐出生在一个不算好的家庭,身为长女,她“从小被父母差唤惯了,心眼伶俐,明白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她想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选择与年长于她12岁的医生订婚,以此换取出国留学的机会。她留学并非是单纯地为了增长知识,与选择男人一样,她的作为根本在于改变自己的命运。
与之相反,苏文纨不如鲍小姐有反叛精神。她留学虽是为了增长见识,但她并未脱离封建礼教的束缚。她学着传统女性的作为,试图以此获取方鸿渐的婚姻,但同时她放不下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高傲身姿,所以在被方鸿渐拒绝后愤而投向曹元朗,最终跟随他成了投机倒把的商人,不复清高孤傲。
(三)思想性格
1.封建礼教的拥护者
《妻妾成群》中的大太太毓如是陈佐千的元配夫人,在陈佐千十九岁时就娶进了门,年纪较大,育有一儿一女。颂莲与毓如初次见面时她在佛堂里捻着佛珠诵经,之后毓如出现的场景主要是在重阳节、陈佐千五十大寿、春节等重要场合,以及颂莲不让烧秋叶和醉酒两大违背传统事件中。作品中对于毓如的描写并不算多,但从文本中可以看出她对颂莲有着明显的敌意,她是传统礼教的卫道者,而颂莲是带有一定自主性的反抗者,两人冲突的本质在于新旧思想、传统与突破的对抗。作品中毓如的数次出现均代表着正妻地位的展示,然而无论是重要场合的出席还是对于颂莲行为的约束,其行为本质上都围绕着陈家父子二人展开,是典型的传统礼教下的妻母形象。
2.勇于突破的反叛者
《围城》中的鲍小姐和孙柔嘉都是典型的封建礼教的反叛者,她们同样出生于较为传统的家庭,受家庭影响不得不做出一定的牺牲行为,但两人反叛的行为却迥然不同。
鲍小姐的反叛主要表现在她对于性欲的开放,她敢于展示自己的身材,以自身外貌和大胆的行为勾引方鸿渐,与她度过了简短的船上时光,她对方鸿渐的感情基于性的需求,所以在下船见到未婚夫时她直接脱离方鸿渐的女友身份,转投未婚夫的怀抱。她的反叛是片面的、极端的,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她将女性的束缚归于性欲的禁锢,以随意的性生活进行强烈反抗,但归根到底不过是个人欲望的肆行。
与之相比,孙柔嘉的反叛要更成熟。面对家庭中的婚姻观念,她选择以柔和的方式进行反抗,她主动出击,设计让方鸿渐成为自己的伴侣,走完婚姻这一必经路,接着展示出自身实力,打破方家对于儿媳的传统规训,去追求自身所期盼的自强自立,实现真正意识上的女性意识觉醒。
(四)结局对比
然而,综观两部作品,无论拥有多少自由度、受过何等教育、秉持何种思想,这八位女性都走向了或轻或重的悲剧结局。
毓如虽置身事外生活平和,但她终究失去了成为自身的机会,一生陷在了陈家的泥潭里;卓云打倒了梅珊、颂莲两个竞争对手,然而陈佐千还在继续纳妾,来了一个文竹也许又会来一个惠菊,只要陈佐千不终止纳妾,她就要一直与其他女性争斗,沉浸在自身打造的牢笼里,永无绝期;梅珊出轨被投井、颂莲被吓疯;鲍小姐嫁给年老男性、苏文纨从夫行商、孙柔嘉婚姻不顺……
她们在外界与自身打造的牢笼里,或麻木,或反抗,却最终未能逃出重重陷阱,行不至女性觉醒的光明道路上。
二、女性命运悲剧归因及其异同
(一)外界压迫
1.环境限制
《妻妾成群》中的女性受困于陈家庭院中,与外界基本脱离,她们没有经济来源,在家中无话语权,所能依靠且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陈佐千,她们要想在陈家生存、受到下人的恭敬对待,就必须取得陈佐千的宠爱。她们所处的环境促使她们不得不依附于男性,臣服于男权。在陈家,陈佐千便是统治者,作为正妻的毓如是帮助他管理家庭的助手,而卓云等妾不过是一件物品,喜爱时可以捧上天,厌恶时便可随意处理,当颂莲为出轨的梅珊求情时,陈佐千只是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转而将其投井。在这样一个无法度制衡的极具男性统治色彩的家庭中,女性不得不进行内部斗争,以获取那为数不多的资源,故而环境所带来的限制对《妻妾成群》中女性悲剧命运的产生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2.传统思想
无论是在《围城》还是在《妻妾成群》中,传统礼教思想都极大影响了女性的悲剧命运。
《围城》中的女性处于新旧思想交替、独立解放思潮渐起的时期,相较于封建社会时期,彼时女性自由度已有了极大的提升,可以入学从教从商。然而,多数人尤其是老一辈人对于女性的规训以及婚姻爱情观仍旧固守传统。张先生在洋行做事,吃穿用度以外国货为主,喜欢中英混杂着讲话,显示其与外国的亲近,但在婚姻上他仍认为“女孩子到二十岁就老了,过二十还没嫁掉,只能进古物陈列所供人凭吊了”;董斜川认为“女人做诗,至多是第二流,鸟里面能唱的都是雄的,譬如鸡” ……男性对女性的贬低以及对男性抬高在文中并不少见。数千年遗留下的男尊女卑思想怎会在短短几年间改头换面、革除一新?而在家庭及外界一致的传统思想中成长出的女性又有多少能够意识到女性觉醒?《围城》中四位主要女性已接受过新式教育尚不能免疫,更何谈方鸿渐未婚妻、张小姐等人。
不同于《围城》中较为开放的社会思想环境,《妻妾成群》中的传统礼教思想更为顽固,社会固有思想的影响及家庭权利的集中,使身处陈家庭院中的女性不得不将传统思想奉为圭臬,说服自己并以其为准则规束自身行为,最终导致女性内部的斗争。
3.家庭施压
家庭施压对于女性悲剧命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围城》中。方鸿渐的丈人认为“自由恋爱没有一个好结果的”;方鸿渐也在父亲提起他与苏文纨之间的婚事时想到“许多人谈婚姻,语气仿佛是同性恋爱,不是看中女孩子本人,是羡慕她的老子或她的哥哥”;方鸿渐写信告知家中要与孙柔嘉订婚时,方老太太第一反应是“不知道孙家有没有钱?” ……可见婚姻不只是夫妻二人之间的感情交易,还掺杂着家族与家族之间的互利互惠。婚姻中的利益交换使得女性成为被贴上价格的交易品,在“父权”“夫权”的掌控下陷于牢笼,难以逃脱。此外,原生家庭中女性的角色定位也影响着女性的思想意识与命运选择。鲍小姐从小被父母当作女佣使唤,她清楚地知晓自己的处境。为了摆脱家庭,她不惜将自己当作交易品,选择嫁给一个年长的丑男人,以婚姻为筹码换取了短暂性的物质自由。这一婚姻缘于利益而非感情驱使,而鲍小姐也因此投入了男性的庇护下,依附于男性生存,丧失了觉醒女性意识所必须的物质基础。
(二)自身局限
外界对于女性的压迫不仅能够直接促使女性悲剧命运的产生,也间接影响着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从而导致其形成自身局限。
《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根本上固守着封建礼教思想,虽然她并不事事顺从陈佐千,但那不过是表现自身独特性格的手段,而其大多数行为仍可见封建礼教的痕迹。比如她在看见飞澜后希望自己也能为陈佐千生个孩子,而且最好是个男孩;再如她认为雁儿要争宠便百般刁难她;又或是为了获取陈佐千的宠爱改变自身喜好……颂莲从未抛弃过这些腐朽的思想,她在家中依靠父亲,嫁人后依靠丈夫,她自身的局限及自我意识的萌芽注定了她的悲惨结局。
《围城》中的苏文纨明明是出国留学归来的女博士,知识、眼界要远高于其他女性,却不求女性独立自强,偏偏坚定不移地要做传统意义上的贤良妻子。为此她放下高傲的身段,在鲍小姐抛弃方鸿渐后主动照顾方鸿渐,对他百般示好却不被认可,最终怒而嫁给曹元朗,并且在嫁人后“嫁鸡随鸡”,跟着丈夫经商,沾染上了铜臭味。
(三)总结
究其本源,虽然外界压迫在女性悲剧命运的形成中占据较大比例,但最终导致其悲剧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外界压迫是表象,自身局限才是里子,纵使表象消退,若里子不变,其结果也将是不相上下。
三、不同性别视角下的女性形象以及创作主旨驱动下的人物形象塑造
由于叙述主体的性别差异以及作品创造主旨的不同,《围城》与《妻妾成群》两部作品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及描述亦有较大差异。
《围城》以男性视角描述女性,其首要关注对象是基于审美评判的外貌,方鸿渐初见四位女性,首要突出的就是外表,如苏文纨初登场时这样写道:“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其次关注的便是其性格展现“苏小姐一向瞧不起这位寒碜的孙太太,而且最不喜欢小孩子”。从男性视角对于女性的描述本质上基于上位者对下位者的评判,这种评判在理性描述时多带贬低,而在《围城》中又增添了对于其是否符合传统意义上妻子形象的评判。
《妻妾成群》以女性视角描述女性,其首要感知的是对方的态度,颂莲见毓如时毓如有意无视她,所以颂莲对其的印象是“毓如肥胖的身体伏在潮湿的地板上捡佛珠”;而她在卓云那里受到热情礼遇时,她对卓云的印象是“卓云的容貌有一种温婉的清秀,即使是细微的皱纹和略显松弛的皮肤也遮掩不了,举手投足之间,更有一种大家闺秀的风范”。在《妻妾成群》中,颂莲观人先感其态度,由此形成不同的初印象,而这一过程中感性占据了较大地位。
由此可见,不同性别视角下的女性形象描述差异主要在于描述主体对感性与理性的先后分配上:男性作为主体进行描述时理性先行,强调被描述者的客观情况;而女性作为主体进行描述时感性先行,更多关注对被描述者的主观情感。
此外,在创造主旨上,《围城》意在凸显新旧交替时期知识分子的迷茫与困境,故而塑造的女性形象多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而《妻妾成群》意在展现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和命运,故其塑造的女性形象均为受传统封建礼教思想压迫严重的典型女性。
四、结语
无论是对于两部作品中塑造的女性,还是对于当今社会上的女性而言,自身树立起独立自强的意识都尤为重要。女性独立与解放不仅要在思想上具有独立意识,在经济上具备独立能力,还要从心理上、精神上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克服自身的性格弱点,找准自身价值定位,以实现真正的自我解放。
参考文献:
[1]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2]苏童.妻妾成群[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3]吴俊熹.论苏童《妻妾成群》叙事空间与颂莲悲剧成因[J].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1,22(01):27-32.
[4]魏雍.从性别视域解读《围城》女性形象[J].现代交际,2017,(12):89-90.
[5]温纬. 《围城》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研究[J].城市学刊,2015,36(06):121-122.
[6]何冰冰.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残缺——论钱钟书《围城》中的女性形象[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5,24(09):104-107.
[7]李昕潞.苏童小说的女性形象及其文本艺术[D].辽宁师范大学,2011.
[8]汤溢泽,李建南. 《围城》:女性形象跌落的滑铁卢[J].理论与创作,1999,(04):5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