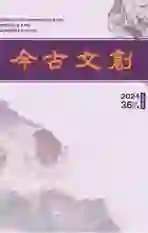叶基莫夫短篇小说《寒水之侧》的艺术特色
2024-09-20王双凤杨玉波
【摘要】叶基莫夫是俄罗斯当代现实主义作家,擅长描写农村,尤其是顿河地区的风土人情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创作中善于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有“一流的俄罗斯短篇小说家”之称。《寒水之侧》是叶基莫夫获得“莫斯科—彭内奖”的系列短篇小说之一。
【关键词】叶基莫夫;《寒水之侧》;人物形象;象征;主题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6-002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06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重构视域下当代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研究”(23WWB193)。
叶基莫夫是俄罗斯当代现实主义作家,1938年出生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伊加尔卡,后迁居顿河地区。他最初的工作是电工,后到高尔基文学院的高级文学进修班学习。1965年首次他以散文作家的身份出现,1976年加入俄罗斯作家联盟,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开始在《星》《我们的同时代人》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和20余部中短篇小说。曾获《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奖(1976年)、《文学报》小说奖(1987年)、布宁小说奖(1994年)、《新世界》杂志优秀小说奖(1996年和2004年)、首届“莫斯科—彭内奖”(1997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家文学奖(1987年和1998年)、俄罗斯国家及全俄文学“斯大林格勒奖”(1999年)、卡扎科夫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2004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文学奖(2008年)等。①
短篇小说《寒水之侧》创作于1993年,1997年叶基莫夫凭借包括这部作品在内的9篇短篇小说荣获“莫斯科—彭内奖”。《寒水之侧》主要讲述了因受伤变成傻瓜的独立渔民萨什卡在受到渔政监督员欺辱后挪动芦苇标志而导致监督员和司机死亡的故事。作家通过立体的人物形象体系、象征手法和丰富的主题构建了独特的艺术世界。
一、立体的人物形象体系建构
巴辛斯基曾评价叶基莫夫为“一流的俄罗斯短篇小说家” ②,建构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体系是他创作的特点之一。在《寒水之侧》中作家塑造了四类人物形象。他们分属两个不同阶层——官员阶层和底层劳动人民。渔政监督员和司机属于官员阶层,他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欺负和压榨底层老百姓;萨什卡和米哈雷奇是底层劳动人民,他们勤劳肯干,却不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一直过着拮据痛苦的生活。四类人物各有特点。渔政监督员多次欺压劳动人民,他已经习惯了为满足一己私欲损害他人的利益;而司机则大多数时候冷眼旁观,面对施暴的渔政监督员既不支持也不制止,面对受辱的百姓既不欺负也不帮助。劳动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傻瓜萨什卡是一个没有自保能力的人、完全的受害者,更多时候是在接受帮助;而米拉雷奇则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力帮助他人,是一个拯救者的形象。这四类人物形象相互交织,构成了丰富立体的形象体系。
第一类为施暴者形象,即渔政监督员这种官僚制度下欺下瞒上的官员。在塑造这个形象时,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和对比手法,使其更加丰满立体。在肖像上,渔政监督员和司机身体结实,穿着温暖厚重的短皮袄坐在车里;而渔民穿着单薄的帆布雨衣和防水袋站在风雪中打渔,萨什卡就像一只可怜的小鸟:“头上扣着一顶编织帽,细瘦的小腿上套着胶皮靴,瘦削的脸上有一只红里透青的鼻子和一双病态发红的眼睛。” ③在行为上,渔政监督员为了完成上级的命令,不想“再去跑跑”,常常在执行公务期间想方设法开出几张罚单。在面对可怜的傻瓜萨什卡时,他非但没流露出一点同情,反倒将萨什卡看作是自己完成任务的工具:给他开罚单,没收他的渔具,在看到萨什卡的困窘生活时没有显露出一丝同情和后悔,反而对他的住处进行一番羞辱,说他是“兽穴里的活法”,当萨什卡错愕之时又加上了一条“拒不签字”的罪名。他在农场里所谓的“公务”就是大吃大喝,奢侈地在中午就打开电灯,临走时带走了主人存储的冻鲈鱼和鳊鱼。可见,欺凌弱者、搜刮民脂民膏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的身上已经看不出任何的良知,他的一切行为都只是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是一个残忍贪婪的人。作者通过肖像和行为描写,从静态到动态凸显了渔政监督员是官僚制度中既得利益者的形象。
第二类为旁观者形象,这类人既看到了施暴者的残忍,也能看到承受者的苦难,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最终选择冷眼旁观。小说中的司机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在渔政监督员提出给萨什卡开罚单时,司机适时提出了“这可是萨什卡呀”的提醒,但是在渔政监督员坚持要对萨什卡下手时他就没有了下文,只是耸耸肩就听话地将车开向萨什卡。当渔政监督员对萨什卡的房子发表羞辱性的评论时,司机既没有附和也没有反驳,对此不屑一顾,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眼前的工作,司机无疑是一群冷漠淡薄的人的缩影。值得一提的是,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同,“叶基莫夫在表现生活中的冲突时会使读者感到忧伤” ④,他在描写这个角色时不仅仅持批判的态度,同时还带有同情和无奈。作者在司机死后借米哈雷奇之口道出了“司机留下了两个孩子,他还年轻”这样的慨叹,言辞间流露出惋惜,不是对于萨什卡,也不是对司机本人,而是对不公平的官僚制度下所有身不由己的人的命运的惋惜。正是这样畸形的管理制度,让心中仍存善念的人没有发声的权利和机会,冷眼旁观成了他们最好的自保方式,不仅底层百姓可怜,一些官员也有可同情之处。不难看出,叶基莫夫认为是环境造就了人,凭一人之力很难改变环境。
第三类为受难者形象,即像萨什卡这样无所依靠,甚至有残缺的底层劳动人民,他们在受到委屈之后申诉无门,只能自己忍耐。可怜的萨什卡在被没收渔具时只能无措地嘟囔着、挥着手,转头向米哈雷奇求助。萨什卡并非是完全依附于其他人,虽然智力残缺,但他也不靠别人过活,在得了渔民们的恩惠之后没有索求更多,而是选择独自在废弃的房子里居住,靠打渔为生,仍是一个有个体意识的人。受欺负之后,他向米哈雷奇求助无果,最后极大的愤怒和不解刺激了他,竟想出谋杀渔政监督员的“绝妙办法”。这个情节既荒诞又合理,加重了萨什卡这个人物的悲剧色彩,叶基莫夫似乎将对社会的讽刺与挖苦集中到了这个角色身上——被苦难折磨到失智的人,又在苦难中荒唐地成了阴谋家。作家在塑造萨什卡这一人物时多处运用细节描写、语言描写和动作描写,使这一形象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第四类为拯救者形象,即像米哈雷奇这样在苦难中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人。米哈雷奇只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普通渔民,同样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和官员的压榨。但他并没有丢失自己的善良,面对可怜的傻瓜萨什卡,他竭尽全力地帮助他:给他合适的穿戴;萨什卡受到欺负时他虽然没法帮他讨回公道,但还是给他提供捕鱼的工具,邀请他吃热饭,尽量让他还能过上正常的生活。米哈雷奇对萨什卡的关心和照顾不仅体现在身体上,他也竭力帮助萨什卡摆脱精神上的痛苦,当萨什卡恢复记忆后被痛苦的回忆所折磨时,他忍住好奇心不让萨什卡回想过去的经历,可见他对萨什卡的关心无微不至。在故事的最后,渔政监督员和司机死了,萨什卡离开了,米哈雷奇意外发现了事故的真相,此时他仍然关心着杳无音讯的萨什卡,做起了平常不会做的事——看电视新闻,关注这件事的发展动向。米哈雷奇也是一个敏感细心的人,在整个故事中他从客观的角度细心观察着周围的细微变化,敏锐地感知到巨大的变革正在悄然酝酿。在塑造这一形象时作家采用了简洁直白的语言,正是朴素的语言衬托了米哈雷奇澄澈纯净的心灵。
二、象征手法的运用
象征手法是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借助某人某物的具体形象,以表现某种抽象的概念、思想和情感。叶基莫夫在《寒水之侧》中多次使用象征手法,突出了渔政监督员的病态和萨什卡的可怜,表达了对官僚制度下社会发展的担忧。
首先是颜色的象征。渔政监督员乘坐的汽车是黄色的,“区渔政那辆显眼的黄色‘小嘎斯’从区中心出发,正沿着封冻的顿河那高低不平的白色冰面行驶。” ⑤叶基莫夫选择黄色绝非偶然,在俄罗斯文学中,黄色往往象征着不祥。例如,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黄色象征着死亡、毁灭和阴暗;在契诃夫的小说中,黄色则象征着社会的虚伪和病态;在《萨金特人与财主》中,许多人在外表上是享受幸福和繁荣的,但他们的内心都是非常空虚和荒谬的,这种空虚感和荒谬感往往会以黄色的形式表现出来。《寒水之侧》中的黄色正是象征着渔政监督员这类人虚伪、病态,最终走向灭亡。小说中,黄色多次出现,不断与周围的白色产生视觉上的碰撞,而最后一次出现黄色是车子掉进水里时“车灯在水下依然发着黄色的光”,这说明“黄色势力”的消灭并非易事。
另一个明显的象征则是鱼。萨什卡在接受渔政监督员关于为何违法捕鱼的审问时,“刚出水的鱼在白雪上显出淡淡的红色” ⑥,白雪与血水混合形成的淡红色放在一起,更加突出了凄惨冷淡的氛围。冰上奄奄一息的鱼象征着此时萨什卡任人宰割、毫无自保能力的状态,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比喻。而造成这种凄惨景象的是上位者的冷酷无情,是下位者的难以自保,是当时社会阶层间难以跨越的鸿沟。
小说中出现得极其频繁的冷与热也有各自的象征意义。冷更多的是代表冷静与忍耐,而热则代表狂躁与失调。这在司机与渔政监督员身上有所体现,他们在整部作品中一直都处在“热”的状态中:坐在车里时热,到了农场吃饭时也很热,掉进冰河里时呛的水都是略有暖意的。相应的,他们从始至终都处于狂热失调的状态,从欺辱傻瓜到大吃大喝,行尸走肉一般狠狠发泄恶的力量。而萨什卡因身材瘦小、衣着单薄、处处碰壁而给人一种很冷的感觉,他谋杀了渔政监督员和司机之后独自一人坐在家里,此时这是他唯一一次感觉到了燥热,而此时他内心刚刚经历过失调与混乱。
大坝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象征元素。小说中,大坝是一个被摧毁的残破形象,是萨什卡一切悲剧的源头。小说结尾处,米哈雷奇在面对曾经萨什卡贴在墙上的大坝的海报时的感受是这样的:他无法去看它,他的头脑中总是浮现出可怕的场面:“爆炸……一切都崩塌了……大水汹涌而至,一路吞没人群、房屋。” ⑦大坝崩塌的场景实际上象征着社会秩序混乱、人们内心失调的现状,混乱的社会把正常人逼成傻子,把傻子逼成杀人犯,一切都变得混乱而荒唐。
综上可见,作家在《寒水之侧》中恰当地运用象征手法,将抽象的感受化为具体的可以感知的形象,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作品寓意深远,令读者回味与反思。
三、反战反官僚的主题思想
罗德尼娅扬卡娅认为,叶基莫夫的小说“因其对现实的敏锐批判而显得生机勃勃” ⑧。叶基莫夫十分关注俄罗斯社会生活,对现实的描写和批判贯穿其创作生涯。在《寒水之侧》中,叶基莫夫结合历史事实,正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表达了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思想,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予以尖锐批判。
叶基莫夫的反战思想是通过萨什卡这一形象表达的。叶基莫夫出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经历了从苏联到俄罗斯的时代变迁,他本人十分注重描写人民生活的真实状态,因此他的作品中涉及大量的历史事实。追溯出这些历史事件更有助于理解作品的主旨。
首先,小说中多次出现“农庄”一词,可以推测出故事发生的背景是苏联时期。其次,还出现了“现在满世界流浪的人不少:一些人被战争和痛苦驱离故土”这样的话语,加之萨什卡经历过大坝被毁、自己受了枪伤这样的情节,可以推断出作品中涉及的是1941年8月18日第聂伯河水电站由于战争被炸毁的事件。第聂伯河水电站对苏联意义重大,修建共耗时12年,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1941年卫国战争时期为了切断德军的电力供给,斯大林下令将其炸毁。水电站的毁灭虽然阻碍了德军的进攻,但也给苏联人民带来不小的创伤。这条历史暗线更加突出了萨什卡命运的悲惨,同时也展现了叶基莫夫眼中战争对人造成的恶劣影响,表达了其反对战争、倡导和平的思想。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会将自己的作品与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叶基莫夫正是看到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对国家的影响,将形式主义、公款吃喝、欺压百姓、生活奢靡等现象在小说中一一展现并加以批判。
作家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是通过渔政监督员这一出形象实现的。小说中渔政监督员的一系列行为生动体现了官僚制度下特权者工作上形式主义、脱离人民、贪腐成风的状态。故事的起因就是渔政监督员奉命去抓捕非法捕鱼者,在没有渔民违法的情况下,还是要强找理由开出几张罚单,只为走个形式,却让许多的百姓承受无妄之灾。他在看到渔民们衣着单薄地在冰上打渔时没有丝毫的同情,面对萨什卡困窘的生活还大加嘲讽,显示出他们已经将自己划入更高的阶层,开始看不起普通老百姓,完全脱离了人民,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是服务于人民。在认定傻瓜萨什卡非法捕鱼之后就以处理公务的由头到农庄里大吃大喝,吃完后还带走农庄的财产,可见公款吃喝、搜刮百姓的财产成了其主要工作内容。
四、结语
“叶基莫夫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的继承者,他的小说不仅迅速和真实地反映当今俄罗斯社会生活和俄罗斯人的思想,而且还有朴实的创作风格,语言简洁,具有表现力等特点。” ⑨在这部作品中,叶基莫夫用简洁的语言讲述了在混乱的社会大背景下官民之间的矛盾,在有限的篇幅内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也引起读者的广泛思考。作家在渔政监督员和司机身上表达了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担忧,在萨什卡身上表达了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米哈雷奇这一形象中蕴藏了对人性和善良的希冀。
注释:
①孙超:《浅析叶基莫夫短篇小说〈费季西奇〉的艺术世界》,《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05期,第65-66页。
②Басинский П:《По ту сторону простого и сложного》,《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1996,№46,С.4。
③鲍·叶基莫夫著,隋然译:《寒水之侧》,《俄罗斯文艺》1999年第03期,第4页。
④孙雪:《舒克申与叶基莫夫农村题材小说对比》,《北方文学》2019年第27期,第74页。
⑤鲍·叶基莫夫著,隋然译:《寒水之侧》,《俄罗斯文艺》1999年第03期,第3页。
⑥鲍·叶基莫夫著,隋然译:《寒水之侧》,《俄罗斯文艺》1999年第03期,第4页。
⑦鲍·叶基莫夫著,隋然译:《寒水之侧》,《俄罗斯文艺》1999年第03期,第9页。
⑧Роднянская И:《Род людской》,《Новый мир》1996,№11.С.238。
⑨邓雨:《论叶基莫夫短篇小说〈治疗之夜〉的诗学特征》,《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11期,第165页。
参考文献:
[1]Басинский П.По ту сторону простого и сложного[J].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1996,№46,С.4.
[2]鲍·叶基莫夫,隋然.寒水之侧[J].俄罗斯文艺,1999,(03):3-10.
[3]孙超.浅析叶基莫夫短篇小说《费季西奇》的艺术世界[J].俄罗斯学刊,2011,1(05):65-69.
[4]孙雪.舒克申与叶基莫夫农村题材小说对比[J].北方文学,2019,(27):72-74
[5]Роднянская И. Род людской[J].Новый мир,1996,№11,С.238.
[6]邓雨.论叶基莫夫短篇小说《治疗之夜》的诗学特征[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6,32(11):163-165.
作者简介:
王双凤,女,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杨玉波,女,汉族,黑龙江青冈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