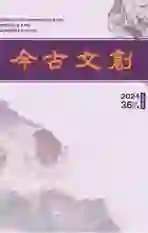创伤理论视角下《大地之上》中的多重创伤研究
2024-09-20张文灿
【摘要】《大地之上》是印度裔加拿大作家罗欣顿·米斯特里的长篇代表作之一,作家以1975年前后女总理英迪拉·甘地的铁腕统治下混乱的印度社会为背景进行创作,那时的印度陷入政治、经济的双重危机之中,在紧急状态期间,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产生了强制绝育以及暴力拆毁贫民窟运动,社会动荡不安。小说以一女三男的命运纠葛为主线,描绘了在特殊的年代中小人物的苦难和坚韧。本文运用创伤理论的相关观点,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对小说中主要人物遭受的创伤进行剖析,旨在通过对主人公造成创伤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父权制、种姓制度以及社会政治环境对个体的摧残,并寻求摆脱创伤的方法。
【关键词】《大地之上》;创伤理论;父权制;种姓制度;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6-0013-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04
《大地之上》是罗欣顿·米斯特里创作的长篇小说之一,该小说出版仅两年便荣获了加拿大最高文学奖吉勒奖以及英联邦作家奖。印度裔作家米斯特里虽在二十多岁时移民到加拿大,但对印度的底层社会仍有着切身体会。小说中的四个主要角色,有拒绝再嫁、谋求自立的美貌寡妇迪娜,一对出身“贱民”阶层、在种姓冲突的灭门惨案中幸存下来的裁缝伯侄伊什瓦和翁普拉卡,还有一个出自山区商人家庭、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腼腆大学生马内克。小说中的四个主人公见证了1975年前后印度进入紧急状态时期社会历史的变迁,也是不同家庭背景、性别与种姓的人所承受时代烙印和创伤的缩影。在迪娜身上,集中了印度社会对于单身女性的看法,反映出无法消弭的女性群体之伤,从迪娜少女时期的生活到她亡夫后独自在外工作,都可见一斑。作为印度种姓制度里面“贱民”族群之一的裁缝伯侄伊什瓦和翁普拉卡,他们一生挣扎在种姓制度的阴影下,为此流离失所,身心饱受摧残。而大学生马内克则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城市化变迁等因素家庭受到影响,命运急转直下。他们的人生经历都与外界的环境紧密相连,经历了暴动、宗教斗争以及社会的种种不公,每个人都在社会中受到创伤。
创伤理论兴起于战争频发的20世纪,由于两次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战争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导致了创伤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创伤”也是精神分析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对于弗洛伊德而言,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患者,都经历过某种身体和心理的创伤。如今,创伤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战OHA7c96KAbjMcXWu8luZtGTmQhILid7wt4U9gPUi8Gc=争等大规模创伤事件对个体心理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小规模创伤事件,这些事件既有突发性的,例如交通事故,也有持续性的,如家庭暴力等。创伤理论作为一个跨学科的人文研究领域,近年来,逐渐受到文学领域的关注,文学评论家运用创伤理论分析文学作品的覆盖面颇广,包括殖民创伤、战争创伤,也包括女性、少数族裔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经历的创伤。
《大地之上》作为一本两年前才出版的新书,学术界对此书的关注度还不高。目前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相关论文也不多,学者们主要还是集中于对小说中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进行解读。其中朱希的《平衡与希望之歌——解读罗欣顿·米斯特里〈大地之上〉》以“平衡”一词为切入点,讨论了四个主人公在人生和社会的双重失衡中如何努力找到自己生命的平衡。综观有关《大地之上》的学术成果,可以发现落脚点几乎都在探讨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与他们面对苦难时的韧性,但是缺少对于造成苦难原因的分析。因此本文运用创伤理论,深入研究《大地之上》中造成底层人民受到的多重创伤及其原因。从创伤理论这一角度剖析文学著作,一方面可以研讨文学著作中是如何体现和反映创伤的,另一方面可以分析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有关个人、群体或社会的困境,并寻求解决方法。
一、无法消弭的女性群体之伤
“创伤”即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者受到死亡的威胁,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的情境。而个体在面对事件时产生的无助、恐惧等情感,或因创伤事件导致的长期对自己或他人的负面信念和预期,则被认为创伤的主观体验。个体在创伤事件之后的反应在情绪层面则表现为失去信心、失去自尊等。由于迪娜的家族属于富裕的帕西族家庭,所以她并没有像其他低种姓的印度女人受到来自宗教和种姓制度的双重压迫,但是迪娜的生活经历仍然反映了印度社会中妇女的低下地位给女性带来的创伤。
(一)创伤表现——迪娜的成长之痛
迪娜出生于印度小康之家,是一个医生的女儿,她的父亲比同行都更加热忱地践行着希波拉底誓言,迪娜梦想像爸爸一样做个医生,但是父亲的离世断送了迪娜的梦想。迪娜的母亲沉浸于失去丈夫的痛苦中无法自拔,并且她将导致丈夫死亡的责任推到了女儿身上,她认为是由于女儿没有成功劝说自己的父亲不去参与医疗活动,进而间接导致了丈夫的丧生。面对父亲的离世和母亲的责怪,迪娜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创伤。来自家人的指责让迪娜不断陷入“是因为我做错事,他们才会责怪我”这一心理困境,导致即使她已经长大成人,脱离了父母的世界,也难以摆脱愧疚的阴影。
父亲死后,迪娜便沦为了哥哥努斯万的奴隶,她遭受了哥哥的凌虐,这种凌虐带给迪娜的创伤,不仅是在身体上,更多的是精神上。因为迪娜的哥哥,需要的是迪娜绝对的服从。由于努斯万向来把父亲看作厉行纪律的人,所以他认为既然他要接过父亲的角色,就必须让其他人感到同样的恐惧。当迪娜的行事稍有不顺自己的心意,他便暴跳如雷。并且当努斯万从父亲手上接过监护迪娜的职责后,迪娜便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她的梦想就此夭折了。在追求纪律的道路上,尺子成了努斯万最常用的工具。除此之外,哥哥努斯万还禁止迪娜剪短发,禁止她拜访朋友。年幼的迪娜在哥哥父权制的压迫下,只能遵从哥哥的要求,没有自由也没有独立的思想。
长大后的迪娜在一次次的压迫中奋起反抗,拒绝了哥哥介绍的相亲对象,与兴趣相投的药剂师鲁斯图姆自由恋爱结婚。年轻时她本以为遇到了可以遇到托付终身的伴侣,但是结婚三年后,丈夫遭遇车祸意外身亡。此后的几十年,她独自一人寡居在丈夫留下的一套小公寓中,靠缝缝补补的手艺勉强维持生计。但最终迪娜还是由于印度社会对于女性不平等的眼光,被没收了房子,回到了哥哥家,又一次成了哥哥的用人。
迪娜的成长过程中充斥着来自哥哥努斯万的暴力、伤害、虐待,这些都对迪娜的身体和心灵造成了无法消除的伤害。一旦有人试图与迪娜建立亲密关系,迪娜就会担心自己再次受到伤害,变得多疑、易怒、神经质,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毫无缘由地发脾气,并且习惯性地逃避。迪娜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就被宗教与传统束缚得透不过气,她一直试图摆脱这种传统,不管是与丈夫结婚,还是丈夫离世后回到公寓靠自己生存。但最终在生活的压迫下,她不得不屈服,回到哥哥家寄人篱下,回到那桎梏的枷锁牢笼中。
(二)创伤原因——父权制的牢笼
印度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度,宗教和印度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摩奴法典》作为古印度有关宗教、道德、哲学和法律的汇编之一,在印度次大陆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是古代婆罗门祭司为了维护种姓制度,强调婆罗门至高无上地位而编纂的法论,对各种姓的地位、权利义务等做了种种规定。涉及女性方面,权利方面的叙述几乎没有,但义务方面却有大段的赘述。此外,婆罗门教认为女性是罪恶的,是邪淫的源头,会造成男性的堕落,因此印度的女性,常因为印度特有的历史与文化,被迫陷入性别、战争、种姓冲突以及宗教冲突的压迫中,进而丧失了弱小的话语权。宗教和种姓是加在印度女性身上的两道枷锁,但女性遭受苦痛的根本原因,是男权思想下的极端父权制。同时印度对女性的道德要求极高,经常把女性视为父亲和丈夫的附庸,并且不能与外界有任何接触,这导致印度女性的成长环境往往非常封建闭塞。小说中的迪娜一直以来只能被哥哥编造的谎言所恐吓,承受着哥哥的暴力虐待,而丧父后母亲的不作为更加剧了哥哥对迪娜的压迫,进一步加深了迪娜的生存困境。迪娜的哥哥就是印度男权压迫的典型人物,他从来没有把迪娜视为一个平等的、有独立人格的人。在迪娜的丈夫意外去世后,迪娜为了谋生主动去学习了裁缝的技术,她竭尽全力在男权社会里寻求生存空间,但又频繁地被房东骚扰,被商人欺骗,她去法院起诉,却被房东抢先申请强制令,被赶出公寓,不得不回到哥哥家寄人篱下。
家庭本应该是最温暖的避风港,一旦家庭里的其他成员变得面目狰狞,家人这一身份就会变成加害者的保护符,让他们有恃无恐,只要被伤害者不想失去自己的家人,那他们就永远不会逃离这一牢笼。迪娜对爱的渴望,让她难以反抗哥哥的虐待,血缘和亲情就像拴在迪娜身上的锁链,让她只能忍受糟糕的家庭带给她的伤痛。迪娜是印度社会中的小部分女性,但她有摆脱当下的传统眼光的勇气,她想要在社会的夹缝中努力生存,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她做出的反抗代表着印度女性也在逐渐努力进入到男权社会,是印度女性觉醒的标志。
二、难以磨灭的种姓制度之伤
可能导致心理创伤的事件有自然灾难、意外灾难、人为灾难等。除此之外,来自他人的情绪忽视与情绪虐待也会给个体带来一定的创伤。这种创伤主要表现为文化氛围中的某些观念在个体身上的投射,导致小说中裁缝伯侄伊什瓦和翁普拉卡产生创伤的原因主要是极端的种姓制度对他们生活各方面的控制。
(一)创伤表现——裁缝伯侄的生存之痛
裁缝伯侄伊什瓦和翁普拉卡,作为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民”,祖祖辈辈只能从事最低贱的职业,他们与死去的牛打交道,剥皮、鞣制皮革、加工成各种成品,他们祖上几代人的毛孔里都浸染了皮毛的臭味。小翁的祖父以非凡的勇气,打破种姓的隔阂,送小翁的大伯和父亲去学裁缝。然后也正是这富有远见的安排,给家族招来了灭门惨祸。在小翁年少时,同镇的高种姓一把火烧掉了小翁全家。伊什瓦和小翁去警察局报案,但由于涉及高低种姓纠纷,警察置之不理。灭门惨案,无处申冤,丧失亲人的痛苦给伊什瓦和小翁伯侄带来了第一次由于种姓制度引起的创伤。
小翁和大伯侥幸逃脱后几经辗转,从北部一个小镇来到迪娜这个海滨之城,作为迪娜的雇员得以谋生。并且经人介绍两人在棚户区租到了一间小房落脚,可突然政府以维护市容为由,将棚户区强拆。两人被迫在药房门口露宿,却被警察当作乞丐抓走,送去一处灌溉工程的工地干活,两人向官员解释是误抓,可根本无人理睬,只有重体力活和无法下咽的餐食。两人回来后,迪娜因两人失踪两个月,缝纫活中断,不得不向哥哥伸手借钱。她担心两人再次露宿街头再有什么意外,善良的她让叔伯两人住在门廊。
裁缝伯侄与迪娜、马内克四人度过了幸福的几个月,有了一点积蓄的伊什瓦突然要给小翁找媳妇。伊什瓦带着小翁回到城镇,在集市上买东西,却遭到警察把集市上的人全部带去做节育手术。高种姓贵族达拉姆西库塔库尔认出了小翁,不仅命令医生给还未结婚生育的小翁做了结扎手术,还切割了他的睾丸,让小翁失去了生育能力。由于消毒工具出现了故障,官员们命令医生用还未消毒的工具手术,致使伊什瓦术后感染,双腿被截肢。而此时迪娜的缝纫机也由于欠款被拉走,迪娜自己也被赶出公寓,不得不回到哥哥家寄人篱下,伊什瓦叔侄则沦为乞丐。
(二)创伤原因——种姓制度的禁锢
种姓制度是印度的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们按照自己的出身分别属于不同等级的社会集团,并且终身固定不变,在职业、婚姻、社会交往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其严格制约。印度社会有四大种姓,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贱民”是被排除在印度四大种姓之外的,他们没有种姓身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备受印度种姓的压迫和凌辱。他们在经济上受剥削,在政治上受压迫。小说中伊什瓦一家都在为了能生活得更好一点而努力,但是这努力带来的却是几乎整个家族的灭顶之灾。心理学家赫尔曼认为:当创伤患者曾目睹其他人的痛苦或者死亡时,负罪感会特别严重。因为他会感到自己从灾难性的事件中逃生,而无力拯救他所热爱的人。裁缝伯侄眼看着全家人被烧死,却无能为力,这样的负罪感使得他们更加坚定了摆脱低种姓制约的决心。
裁缝伯侄认为到了城市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却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他们承受不完的苦难。他们在大城市睡了几个星期的大街,终于遇到了雇主迪娜。有了工作的伊什瓦和小翁终于可以住进贫民窟,却又遇到了英迪拉·甘地政府的一系列“城市美化运动”“计划生育”政策。明明有工作但贫穷的叔侄俩失去了暂居之地,被赶到大街上,但是又因为“影响市容”而被带走“建设城市”。
当然,面对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印度各地的“贱民”也会为自己的生存展开了斗争,他们采用的比较普遍、历史较久的斗争方式便是脱离原来信奉的印度教而改信其他宗教。历史上在1981年2月19日泰米尔纳杜邦米纳克西普拉姆村的1000多名“贱民”便皈依了其他宗教,并以此为起点,在以后几个月中,很多其他许多地区也掀起了“贱民”改信宗教的浪潮。种姓制度维护者在国民志愿团的组织下,对很多“贱民”进行了劫掠和残杀。小说中阿什拉夫叔叔的裁缝店便险遭厄运,是纳拉扬和伊什瓦站出来冒充店铺的主人而保护了阿什拉夫一家。种姓制度下的“贱民”们认为只要摆脱不平等的印度教,皈依其他主张平等的宗教,他们就能摆脱压迫。然而宗教皈依并没有给“贱民”带来自身的解放。政治上,不仅印度教徒仍把他们当作贱民,即使他们所皈依的宗教的其他教徒也仍把他们当作不可接触者。种姓制度的毒素已渗透到印度的各种宗教之中。
裁缝伯侄俩安安定定地在迪娜女士家工作了一段时间,攒了些钱,眼看着日子越过越好,他们开始盘算给小翁娶媳妇。回到家乡的伯侄二人却遇到了镇上负责计划生育运动的,也正是当年烧死家人的高种姓,于是小翁被阉割,而伊什卡也因为结扎手术感染,不得不截肢。二人再次无家可归,做起了可怜的乞丐。
小说中伊什瓦与小翁这个恰马尔家庭的越阶行动虽然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个家族两代人与种姓制度的斗争,也是很多“贱民”的缩影。伊什瓦的父辈们斗争的对象是高种姓的地主,而伊什瓦和小翁斗争的是由于处于低种姓而带来的无形的规章制度,他们的反抗更多是出于对自我的保全,虽然于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而言,这样的反抗是无力的,但也反映出“贱民”们对于种姓制度这一社会滥觞的不满。
三、难以逃脱的现代化之伤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社会造成创伤的事件并不仅仅局限于战争、大屠杀等,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上的双刃剑与政治上的腐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固有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被重构,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面对社会变化,有些人无所适从,在理想与现实的错位中被扭曲,马内克受到的创伤便是由于自身无法融入现代社会带来的。
(一)创伤表现——马内克的成熟之痛
马内克的父辈皆是家境富裕,地产颇丰的阶层。然而因为印巴分治的一道国境线,一夜之间,马内克家族所有祖传的土地全都被划了出去。于是,马内克的父亲只能靠一间杂货铺和自己制汽水的独门技术养活妻儿。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父亲法鲁赫·科拉喜欢的群山被过度开发,独家的科拉汽水也遭到国外品牌竞争,销量每况愈下。父亲为了儿子的远大前程,将十一岁的儿子送到远离家乡的大城市求学。
突然来到城市的马内克与城市的喧嚣格格不入,唯一的朋友阿维纳什是他学习生活唯一的慰藉。可是阿维纳什在为学生呼吁奔走中突然失踪。马内克也遭到同学霸凌。他无法忍受宿舍,本想借机回家,正好母亲的同学迪娜寻找房客,于是他搬到了迪娜家,与同龄的小翁成了朋友。
马内克毕业返家后,前往迪拜工作八年,由于父亲去世,他奔丧返家。从迪拜回到家后的他发现家里的商店经营惨淡,父亲引以为傲的汽水被新的品牌取代,母亲每天都郁郁寡欢。回到孟买后,他以为会看到小翁结婚,子女成群,但在亲眼见到迪娜阿姨顶着哥哥的压力还在接济已沦为乞丐的伯侄二人时,马内克的内心崩溃了。最后他不堪忍受生活的磨难,抱着同学阿维纳什的棋盒,选择和他同样的方式,卧轨而亡。
(二)创伤原因——现代社会的压迫
作品创作的背景即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政府突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紧急状态期间,国家实行新闻审查,逮捕了成千上万的持不同政见者,此外无数弱势群体的权益受到了侵犯而无人顾及,剥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不合法行为到处弥漫。此外,由于印巴分治导致次大陆亿万人群固有的生活边界一夜间被改变,大量的难民匆匆离开世代生存的家园,去往陌生的地方。马内克的父亲便是由于印巴分治的一道国境线而导致家产尽失,并且由于二战后大量的军事和军需刺激了印度的经济,在印度建立了金属冶炼加工、机械制造等工业,马内克一家安逸的乡村生活也被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打破了。随之而来带给马内克的是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创伤。
在慌乱的工业化发展中,印度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躁动不安,村庄里没有地的人来到城市,导致城市人口激增,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马内克的朋友阿维纳什便是由于在学校参与抗议活动而丧失了生命,马内克便是在目睹迪娜与伊什瓦等人的不幸结局后走上了与阿维纳什同样的道路。
心理学上认为大部分患者的创伤问题,往往都涵盖人际关系、童年经历及亲人朋友离世等其他创伤性事件多种创伤源。创伤的概念也不局限于特定的生命阶段或特定的事件,即一个人可能在任何时间,被任何事件所压倒而感到创伤。伊什瓦伯侄虽然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但其乐观精神却使他们在每个苦难阶段都能渡过难关,而马内克在遭遇了屠杀锡克教徒事件、父亲去世以及故人巨变后选择了自杀。伊什瓦伯侄之所以与马内克的结果不同,是因为伊什瓦伯侄尤其是伊什瓦自小就生存在低种姓身份的阴影下,见惯了社会的不公,而马内克童年的幸福生活给了其极高的生活与社会期待,一切破灭的落差使其精神崩溃,最终卧轨自杀。
四、结语
《大地之上》通过讲述寡妇迪娜、大学生马内克以及裁缝伯侄伊什瓦和翁普拉卡四位主人公的命运,刻画了特殊历史时期下印度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这部作品中的四个主人公,几乎每个人都带着创伤生活,没有一个能够逃过劫难。故事的发展正如最后一章的题目“完整的轮回”最终形成了闭环。迪娜在努力工作之后还是失去了一切回到了哥哥家;满怀希望地离开遭受极度迫害的裁缝伯侄最终还是沦为了乞丐;而出国务工的马内克八年后返乡了解到朋友的悲惨遭遇后还是选择了不归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印度让人窒息的不是贫穷,而是人权的践踏。底层的群众像蝼蚁一般,都在被无情践踏,成为历史的牺牲品。本文从创伤理论这一视角切入,关注主人公身心创伤的同时,从父权制、种姓制度以及现代化等角度分析导致创伤的原因。通过研究可以得出,迪娜等人的创伤不仅仅是特殊家庭环境造就的个体创伤,背后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社会制度的腐朽与社会快速发展的弊端。小说中主人公受到的创伤与他们的人生悲剧,让读者看到了历史与现实之于个人的偶然性。在此意义上,迪娜等人的悲剧连同的可能是许多印度家庭的悲剧,也都是对于印度腐朽的制度与社会的一种反讽和质疑。
此外,故事的主人公都曾或多或少的受到过创伤,陷入过精神困境,对于他们而言,往往很难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出来,此时人生过程中的一点点温暖都显得至关重要,这些温情就像一颗种子,一旦受害者有走出来的决心,就会变成支撑他们的参天大树。万幸的是,他们彼此成了对方黑暗道路中支撑勇敢前行的力量,给予了彼此对抗混乱而又充满压迫的生活的非凡勇气。因而小说主人公们的互相疗愈也启示我们,不要忽略治愈创伤的重要性。作者罗欣顿·米斯特里用真实自然的笔触,将畸形又略显荒诞的印度社会环境呈现出来,将创伤治愈中那些痛苦挣扎赤裸裸地摆在读者眼前。小说既不励志,也不热血,充满了压抑、困窘和自我怀疑,却能给予读者无限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加拿大)罗欣顿·米斯特里.大地之上[M].张亦绮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21.
[2]张呈敏.论《微妙的平衡》的底层叙事[D].天津外国语大学,2017.
[3]张磊.《灿烂千阳》的创伤解读[D].黑龙江大学,2015.
[4]姚斌洁.创伤理论视角下的海明威战争小说研究[D].吉林师范大学,2017.
[5]朱希.平衡与希望之歌——解读罗欣顿·米斯特里《大地之上》 [J].文学评论,2023,(46):15-18.
[6]赵凤英,李凤.《纵横交错的世界》中的多重创伤研究[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7(3):6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