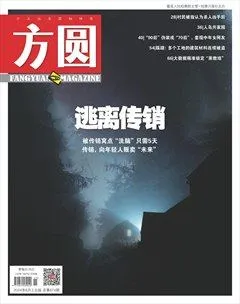从宋词中感知宋朝的环保情怀
2024-09-19肖爽

公元960年(后周显德七年,赵匡胤即位后改元建隆元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代周建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和百年藩镇割据,经历了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至1279年被元所取代。宋朝经济发展、人口增多,人与环境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于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制度也有了新的发展。宋朝还产生了与唐诗争奇斗艳的宋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词以其丰富的表现手法、优美的语言、深邃的思想,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赞誉,既有豪放派词人的磅礴气势,也有婉约派词人的柔情蜜意。宋词的内容丰富多样,反映社会现实,抒发个人情感,还体现了宋人对于自然环境、山水田园的热爱。
1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苏轼《浣溪沙》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俱佳,其词开创豪放派,并多有描写田园风光和农村生活的词作。这首《浣溪沙》是元丰七年(1084)所作,苏轼由黄州调任汝州(今河南临汝),赴任途中,曾于泗州小住,与友人在泗州附近南山游玩时所写。上阙写沿途景色,南山天气微寒,风斜雨细,稍后天气放晴,烟云浅淡,冬日河滩成片的柳树柳叶稀疏,尽沐晴晖,似作“媚”意,眼前淮水由清洛而入,一片浩茫渐流渐远。下阙写午时小休,烹茶野餐。乳白色的香茶伴着春盘中的新鲜野菜,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宋朝建立后,定都汴京(今开封),人口最盛时超过百万,需消耗大量木材与燃料,因而对林木资源的重要性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制定了很多法令及相关措施,保护林木资源、劝课农桑、推广林木种植。立国之初,宋太祖就诏令百姓按户等种树。据《宋史·食货上》载,“太祖即位”,“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又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 即对垦荒种植者推行免租税政策,以鼓励种植经济林木。同时,对不履职的官员给予惩罚。《宋刑统》卷十三《户婚律》中专门有“课农桑”条:“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受而不授,应还而不收,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法者,失一事笞四十。”并加以解释:“一事,谓失一事于一人。若于一人失数事及一事失之于数人,皆累为坐。”在“议”中又进一步解释:“一事,谓失一事于一人者,假若于一户之上不课种桑枣为一事,合笞四十。若于一人失数事,谓于一人之身应受不授,又不课桑枣及田畴荒芜,及一事失之于数人,谓应还不收之类,在于数人之上,皆累而为坐。”“三事加一等。县失十事笞三十,二十事加一等,州随所管县多少,通计为罪(州县各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各罪止徒一年。故者,各加一等。”即按官员的级别以及是否故意明确刑罚。《宋刑统》在“课农桑”疏议中还明确每户应种植棵数,里正检查时间方式都加以详细规定,以便于执行,即:“依田令:户内永业田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每亩),榆枣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又条: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对共给授。又条:授田,先课役后不课役,先无后少,先贫后富。其里正皆须依令造簿、通送及课农桑。若应合受田而不授,应合还公田而不收,应合课田农而不课,应课植桑枣而不植,如此事类违法者,每一事有失,合笞四十。”
宋朝法律对乱砍滥伐林木的行为予以严厉处罚。《宋大诏令集》卷198《禁约上·禁伐桑枣诏》载,建隆三年(962),宋太祖下诏:“桑枣之利,衣食所资,用济公私,岂宜剪伐,如闻百姓斫伐桑枣为樵薪者,其令州县禁止之。”对盗伐者从严惩处,“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 毁伐桑枣严重者罪可处死,可见对桑枣等林木的保护力度之大。《宋刑统》“杂律”“贼盗律”篇中有大量关于破坏林木加以处罚的规定。在“杂律”八“食官私瓜果”条规定:“诸于官私田园辄食瓜果之类,坐赃论,弃毁者,亦如之。即持去者,准盗论。主司给与者,加一等。强持去者,以盗论。”疏议解释:“称瓜果之类,即杂蔬菜等皆是,若于官私田园之内而辄私食者,坐赃论。其有弃毁之者,计所弃毁,亦同辄食之罪,故云亦如之。持将去者,计赃准盗论,并征所费之赃,各还官、主。”对于擅自吃公私瓜果或损坏的以“坐赃”或“盗”论处。“杂律”九还规定了“弃毁官私器物树木”条,即:“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穑者,准盗论。”还规定:“如有因仇嫌,心生蠹害,剥人桑树致枯死者,至三功(于木身去地一尺,围量积满四十二尺为一功),绞;不满三功及不至枯死者,等第科断。”按此规定,致他人林木枯死可以处绞刑。在“贼盗律”中设有“发冢盗园陵内草木”条规定:“诸盗园陵草木者,徒二年半。若盗他人墓茔内树者,杖一百。”在“贸易官物取人山野刈伐积聚物”条规定:“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疏议解释:“山野之物,谓草、木、药、石之类,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谓知准积聚之处时价,计赃依盗法科罪。”即以当时当地价格为准予以处罚。《宋刑统》对于失火毁林的予以重罚,在“杂律”四“失火”节规定:“诸于山陵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疏议还进一步规定:“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
2
溪边白鹭,来吾告汝,溪里鱼儿堪数。主人怜汝汝怜鱼,要物我欣然一处。
白沙远浦,青泥别渚,剩有虾跳鳅舞。任君飞去饱时来,看头上风吹一缕。
——辛弃疾《鹊桥仙·赠鹭鸶》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杰出的爱国词人,其词豪放,风格多样,除有怀古抒情、金戈铁马的词外,也有运用比兴,赋予山水草木动物等以人的情感和性格的田园词。这首词以人鸟对话的形式,上阙写词人把白鹭招来,对白鹭晓之以理,告诉它,门前小溪里的鱼儿寥寥可数,不能再捉了,应当像主人体谅它一样体谅鱼儿的命运,表达了对游鱼的爱怜,抒发了词人对自由自在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物我欣然一处”理想的追求。下阙写词人劝白鹭去“远浦”“别渚”,以“虾”“鳅”为食。
宋朝对于动物保护方面的法律诏令比较完善。《宋史·太祖本纪一》载,建隆二年(961)二月,宋太祖下诏:“禁春夏捕鱼射鸟。”《宋大诏令集》“禁约上·二月至九月禁捕猎诏”载,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下诏:“方春阳和之时,鸟兽滋育,民或捕取以食,甚伤生理,而逆时令,自宜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持竿挟弹,探巢摘卵。州县吏严饬里胥,伺察擒捕重置其罪,仍令州县于要害处粉壁,揭诏书示之。”诏令不但规定了禁猎时间,而且要求州县官员在公共场所显著位置张贴诏书广而告之,对于违犯者处以重罪。《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天禧三年(1019)十月,宋真宗诏:“禁京师民卖杀鸟兽药。”以防止对野生动物过度捕杀。
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北宋上层人兴起了戴鹿胎冠的风气。一时间杀鹿取胎,制作冠帽十分盛行,大量鹿类被猎杀。宋仁宗为制止此股不良之风,下诏:“宜令刑部遍牒施行,应臣僚士庶之家不得戴鹿胎冠子,今后诸色人不得采杀鹿胎,并制鹿胎冠子。如有违犯,许人陈告,犯人严行断遣。告事人如告获捕鹿胎人,赏钱二十贯。告戴鹿胎冠子并制造人,赏钱五十贯。以犯人家财充。”此诏令不但禁止士民戴鹿胎冠,而且还鼓励百姓告发佩戴及制造鹿胎冠的人,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宋代上层社会还曾流行乘坐用绒毛皮缝制的绒座,“绒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长,色如黄金,取而缝之,数十片成一座,价直钱百千”。绒座主要用绒脊皮毛制成,制作一个绒座要用数十片绒脊皮毛,而绒座柔软舒适,色彩金黄,高官贵族竞相采买,造成对野生绒的大量捕杀。在天禧元年(1017)为限制捕杀绒制作绒座,下诏:“禁捕采取绒毛。”该法令对捕杀绒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
3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欧阳修《采桑子》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诗文革新运动领袖。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欧阳修移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有感于此地“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时慨然已有终焉之意”。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出知亳州,特意绕道颍州。数年后,终于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得以如愿归居颍州。北宋时颍州西湖清澈幽美,据《正德颍州志》载:“西湖在州西北二里外。湖长十里,广三里。”欧阳修在几次游览后,创作了十首《采桑子》咏西湖景物,此词便为其中第一首。全词以轻松淡雅的笔调,描写春色怀抱中的西湖,色调清丽,风格娟秀,充满诗情画意。
宋朝经济发展对农业灌溉、水路漕运的需求大增,对水资源的管理和利用更为迫切。《宋大诏令集》载,开宝五年(972)二月,宋太祖颁布诏书:“自今开封府、天雄军、郓、澶、沧、滑、孟、濮、怀、郑、齐、棣、德、博、淄、卫、滨十七处各置河堤判官一员,即以逐州通判充;如阙通判,委本州判官兼领之。”即在开封府天雄军等十七处设置河堤判官,负责水利管理。《宋史·仁宗本纪》载,嘉祐三年(1058),宋仁宗为解决水官失职问题,诏令:“置都水监,罢三司河渠司。”设置专门负责水利管理事务的京都水监,以加强河防,“凡内外河渠之事悉以委之”。都水监相当于河道总督,对各地方政府的河道治理进行监督、指导,对占用河道、影响泄洪的行为加以整治。治平三年(1066),宋英宗颁诏:陂泽之地,不得壅塞、侵耕,妨碍蓄水疏流;各州、县,分派“乡耆”,逐季巡查,不得容纵侵耕;告发者按侵耕面积,每亩赏钱三千,以犯事人家财充给,并将侵耕所的地利入官;违者,有关官吏及侵耕人,以违制之罪处罚。
在法律上,《宋刑统》“杂律”,有“不修隄防”条:“诸不修隄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三等(谓水流漂害于人。即人自涉而死者,非)。”疏议对此解释:“依营缮令:近河及大水有隄防之处,刺史、县令以时检校。若须修理,每秋收讫,量功多少,差人夫修理。若暴水汎溢,损坏隄防,交为人患者,先即修营,不拘时限。若有损坏,当时不即修补,或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谓因不修补及修而失时,为水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谓失十疋杖六十,罪止杖一百。若失众人之物,亦合倍论。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三等,谓杀人者徒二年半,折一肢者徒一年半之类。注云,谓水流漂害于人,谓由不修理隄防而损害人家,及行旅被水漂流而致死伤者。”对于有责任的官员因不修或不及时修隄防,要处以杖责,造成人员、财产损失的,也要追究相应责任。此条还规定“盗决隄防”罪:“诸盗决隄防者,杖一百(谓盗水以供私用。若为官检校,虽供官用亦是)。若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坐赃论;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致毁害者,亦如之。其故决隄防者,徒三年;漂失赃重者,准盗论;以故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疏议对此解释:“有人盗决隄防,取水供用,无问公私,各杖一百。”“若毁害人家,谓因盗水汎溢,以害人家,漂失财物,计赃罪重于杖一百者,即计所失财物坐赃论,谓十疋徒一年,十疋加一等。以故杀伤人,谓以决水之故杀伤者,减斗杀伤罪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致毁害、杀伤者,一同盗决之罪,故云亦如之。”此条还有一补充规定:“臣等参详:今后,盗决隄防致漂溺杀人,或冲注却舍屋、田苗、积聚之物,害及壹拾以上者,头首处死,从减一等。溺杀三人,或害及伯家上者,以元谋人及同行人并处死。如是盗决水小隄堰,不足以害众,及被驱率者,准律处分。”对于盗决隄防破坏水利设施的予以严惩。
在水资源的分配上,宋朝在《庆元条法事类》“农田水利”卷规定:“诸田为水所冲,不循旧流而有新出之地者,以新出地给被冲之家,虽在他县亦如之。两家以上被冲而地少给不足者,随所冲顷亩多少均给。其两岸异管,从中流为断。”在《宋刑统》“户婚律”中也有相关规定,即“诸田为水侵射,不依旧流,新出之地先给被侵之家”。这些规定确立公平用水原则。在灌溉用水方面,《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以水灌田,皆从下始,仍先稻后陆。若渠堰应修者,先役用水之家,其碾硙之类壅水,于公私有害者,除之。”即确立了下游优先于上游、水田优先于旱地、兴修水利以受益者优先、漕运灌溉优先于碾硙(利用水力磨茶的装置)的原则。
4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
柳永(约987—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善为乐章,长于慢词,以描写城市风光、歌伎生活以及羁旅行役离别感伤题材为主。这首《望海潮》即描绘了杭州繁华的盛况,上阕鸟瞰杭州全貌,之后从各方面描写了其“形胜”与繁华。下阕先歌咏西湖,无论白天晚上,泛舟西湖,有优美的羌笛和采莲的歌声。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载:“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此说虽有些夸张,但此两句确实把西湖以至整个杭州最美的特征概括出来了,从此诗可以想见当年对于城市环境管理的效果。

北宋东京汴梁(河南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浙江杭州)作为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居民生活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和污水,面临着极大的环境压力,宋朝对于城市环境卫生的治理主要从建立垃圾清理制度、规范排污行为及城市绿化三方面开展。北宋时期即设置街道司,据《宋会要辑稿》载,街道司主要职责为“掌治京师道路,以奉乘舆出入”。其人员编制主要置“勾当官二员,以大使臣或三班使臣领之”。同时,下属人员以“五百人为额,立充街道指挥例物,每人交钱二千,青衫子一领”,即统一着青衫子服装负责京师道路卫生养护事宜。据《梦粱录》载,南宋临安除街道司外,还“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每去钱犒之”。即政府出资雇用贫困者、流浪者,专职负责垃圾、污物的清理。
宋朝还以法律形式禁止影响市容市貌的排污行为。《宋刑统》“杂律”“侵巷街阡陌”条规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其穿垣出秽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进一步解释此条:“侵巷街、阡陌,谓公行之所,若许私侵,便有所废,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谓于巷街、阡陌种物及垦食者,笞五十。各令依旧。”“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主司不禁,与同罪,谓侵巷街以下,主司并合禁约,不禁者,与犯罪人同坐。”这一规定即对随意排污、占地种植者进行处理,对于不作为的官员也同样处理。北宋天圣二年(1024)六月,针对汴京城内众多居民侵占街衢的现象,宋仁宗下令“开封府榜示,限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此项诏令中“立表木”指的是在街道两侧树立表木,沿表木测量距离。以此来作为侵街的警戒线,继而限制官民侵街违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