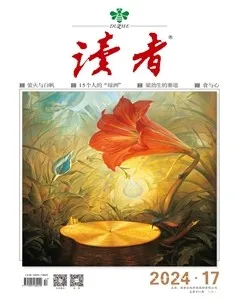食与心
2024-09-11扶霞·邓洛普

在中国待了这么长时间,我经历了不少情感危机。也不记得具体是哪一次了,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我亲如姑姑的李树蓉对我悉心照料,让我窝进她成都公寓的扶手椅里,给我端来绿茶,削皮切水果,一边准备她拿手的美味川菜,一边东拉西扯地聊些有的没的。像许多中国人,尤其是老一辈,她对我表达爱的方式不是拥抱或恳切热烈的言语,而是食物和唠叨。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习惯这种表达爱的方式。起初,我觉得有点粗暴专横——“吃稀饭!喝汤!多穿点儿!”——但日子慢慢过去,我逐渐理解了其中包含的深情。现在,我总算能觉察到一个中国人是不是开始喜欢我、在意我了——只要对方开始喋喋不休于我的生理需求,催促我吃东西、喝水、保暖、休息。要是一个厨师板着脸叫我早餐多吃点包子,或者李树蓉催促我再吃一口她做的红烧肉,我就知道,他们正在给我口腹上的拥抱。
中国人赋予了食物很多含义:可以是对神灵和祖先的庄严祭祀,是连接我们与神灵世界的供品;也可以是等级和政治权威的象征,是治国之道的隐喻。食物是滋养身心、治疗疾病的良药。它体现了风土和时令、永不停歇的阴阳消长、我们与宇宙的联系。食物标志着不同地区和文化之间、文明世界和蛮夷荒野之间的界限。提供食物是统治者和国家的主要职责。
食物是艺术,是工艺,是魔法,是厨师刀下霜雪般飘落的鱼片,是升腾的锅气中舞动的肉丝,是在蒸笼中膨胀的小米或大米粒,是酱缸酒罐中训练有素的微生物大军,是小小厨房中百味的幻化,是原材料的七十二变。从鸭舌到柚子皮,万事万物都能变成食物,给人们带去愉悦。这是人类智慧的一大结晶。
最重要的是,食物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关键。正如先哲告子所说:“食色,性也。”又如源自《礼记》的俗语所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我们都是动物,都有舌头、胃、肝脏和性欲,都需要安慰和关爱。先哲孟子认为,内心善良的本性,而“口之于味也”,人才为人。对中国人来说,饮食既是生理需要,也是生而为人最值得探寻的乐趣之一。如果生活泛若不系之舟,食物就可以成为锚,在人遭遇幻灭时成为避难所,在承受压迫时提供自由与创造的方寸之地,成为人生的慰藉。致力于向西方读者解读中国文化的著名学者林语堂,在1935年出版的著作《吾国与吾民》中写道:“人世间倘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人的慎重行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吾们曾公开宣称‘吃’为人生少数乐事之一。”
中国人把食物作为人生的核心,因此总会从美食、哲学、道德和技术等不同角度来对其进行认真的思考。中餐充满深思熟虑和高雅品位,颇似法国菜,但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广,对饮食与身体健康之间关系的理解也更深刻。“法国人的吃是热烈地吃,而英国人的吃是歉疚地吃,”林语堂这样写道,“中国人就其自谋口福而论,是天禀地倾向于法国人的态度的。”(之后他又有些残酷地写道:“其实际是英国人不大理会肚皮。”)
在中国,并不是只有富人才会在食物中寻找乐趣。虽然富人愿意花重金购买珍馐异材,培养私厨,品尝要花上好几天慢工细活做出的菜肴,这的确促进了高级美食的发展,但中国民间的烹饪传统同样令人着迷。在绍兴,很多菜肴的起源故事,主角都是想从吝啬东家那里偷生的困难奴仆、一穷二白的文人或叫花子、流浪汉之流,他们在饥饿与走投无路之下,有了烹饪方法的新发现。成都的街头货郎与北京御膳房的厨师,都发明了很多诱人的小吃。山西的平民厨师们手中幻化出的面食种类,与意大利厨师发明的不相上下。在中国各地,无论贫富贵贱,人们都以当地的腌菜和酱料、小吃和菜肴为荣。人人都会充满热情地谈论美食与烹饪,陶醉于舌尖口腹之乐。
龙井草堂的红烧肉,取名“慈母菜”。据说,从前有位妇人,她的儿子去京城科考了。焦急等待儿子归来的她,准备了儿子爱吃的一道菜——文火慢焖的猪肉和鸡蛋。但路途遥远,一路上状况不断,儿子没有如期归家。于是她把炖锅从炉子上撤下,去睡觉了。第二天,她把炖肉热好,继续等着儿子,但还是没等到。第三天,儿子终于回家了,炖肉已经热了三次,肉质软烂油滑,酱汁深沉浓郁。
《礼记》中记载了通过食物对长辈尽孝的方式:儿媳应该侍奉自己父母与公婆的饮食,孝以“、酏、酒、醴、芼羹、菽、麦、、稻、黍、粱、秫,唯所欲。枣、栗、饴、蜜以甘之”;做儿子的,清晨要向父亲请安,奉上佳肴表示孝敬之心。在紫禁城寒冰般的宫墙之内,皇帝、皇后和嫔妃们都会从自己的私厨房中送出菜肴至某处,以示宠爱或情谊。
亲朋好友做的菜也许有着一种独特的味道:据说有杭州人,流亡多年后归来,尝到一种有甜味和醋味的西湖鱼菜,认出这是当年嫂嫂做的,才与失散的亲人相认,这便是名菜“西湖醋鱼”的传说。据《后汉书》记载,官吏陆续获罪入狱,一天吃到一道羹汤,便知道母亲来探望自己了,因为只有她才会这样做菜:“母尝截肉,未尝不方,断葱以寸为度,是以知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与中国的朋友们长期分离,就试着让食物跨越这重洋之距。封控在伦敦家中的时候,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用心地惦记着中国农历的节气和节日。春天,我自制春卷;端午节,我包了粽子,也吃红苋菜和咸鸭蛋;春节前,也要自己做腊肉预备着过年。每一道菜都满载着回忆,吃一口就会想起我最初在某个地方尝到它的美好心情,想起给我方子或教我其中秘诀的某个人。我给这些亲手制作的菜肴拍了照片,发给中国的朋友和老师,或者发在社交媒体上,想要传递这样的讯息:“我还在,烹制着我们分享过的菜肴。我在想你们。”朋友们给我回信息,邀请我再“回国”去吃饭。“下次你来,我们就去开化吃白腊肉!”“扶霞,我在广州的餐厅可等着你的!”“来河南吧,很多新菜等着你尝呢!”这些讯息之中的情感,和两千多年前屈原写下的精彩招魂诗句如出一辙: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胹鳖炮羔,有柘浆些。鹄酸臇凫,煎鸿鸧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也许,全世界的众多民族中,要数中华民族最了解熟悉的美食带来的归属感,它们不断拨动最深处的心弦,带我们回家。四世纪时,是家乡的莼菜鲈鱼羹让张翰弃官不做,从北方回到江南。宋嫂鱼羹让一位皇帝回忆起失却的北都,沉痛不已。几十年后再回到杭州故乡,去龙井草堂用餐的美籍华人们,喝到温热的石磨豆浆和藕粉,无不喜极而泣。那是他们难忘的童年味道,穿越许多年的时光,萦绕在舌尖。至于我,虽然中餐并非“祖传”,却是伴随我青春与成长岁月的事物,塑造了我的舌尖记忆和厨艺,其中充满了爱与情谊、回忆与憧憬。
(白夜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君幸食》一书,本刊节选,黎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