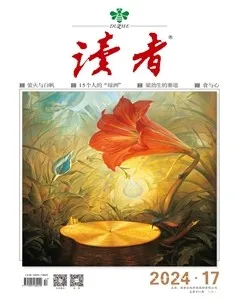鱼骨非骨
2024-09-11胡烟

8岁那年,我坐在一条大鲸鱼的脊背上,在太平洋流浪。它带着我一跃而起的时候,可比一匹马更威风。它前进时不追求速度,而是沉浸于游戏时的激情。跃起,俯冲,激起巨大的海浪,我们享受征服海洋的快感。尤其夜晚,我们腾空的时候,高度直逼那轮耀眼的月亮。它光滑的背,在夜色中发出幽蓝的光。我牢牢抓住它的鳍,一点儿恐惧也没有,我们一次次撞击天堂的大门。有那么几个瞬间,我干脆闭上眼,享受这一切。令我遗憾的是,这么刺激的场景,却无人驻足欣赏。
路过我们身边的,大多是些刚卖了鱼揣着钞票赶回家歇息的渔民。他们每个人肩上都搭着一个人形的皮叉子,像背着自己的躯壳,靴子在屁股的位置晃荡。他们身体疲乏,精气神却很足,大约脑袋里还回忆着鱼贩子点钞票时的情景。渔妇们则是一手拎着鱼篓子,里面盛着卖剩下的小杂鱼,一手拎着秤盘子,叽叽喳喳,嘴巴闲不住,东家长西家短,议论着其他渔民的收成。
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一个骑着鲸鱼只身在太平洋探险的小姑娘,尽管有时候他们和我的距离不到3米。还有,这条体形庞大的鲸鱼,竟一点儿也吸引不了他们的注意。他们的眼里只有钱。我的世界和他们的世界,那么近,又那么远。
声明一下,这不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而是我童年经历的真实场景。
彼时,爷爷赶海的时候捡来一块鲸鱼骨,足有七八米长。爷爷费了好大气力才把它扛回来。进门有照壁挡着拐不过去,他只好将鲸鱼骨横在家门口的羊圈边。爷爷说,要等考古队或者博物馆的人来收这块骨头。这条可怜的鲸鱼,爷爷竟也说不清是蓝鲸还是虎鲸,它死去已经有至少100年的时间,骨头被海浪漂得雪白,周身布满了不均匀的蜂窝孔。这可是一条鲸鱼,叱咤万里、搏击风浪的鲸鱼!放了学,百无聊赖,我就骑在这块月牙形状的骨头上,上下晃荡,像坐了跷跷板。一会儿在渤海,一会儿在黄海,去往太平洋,通向无尽的深蓝宇宙。
爷爷是个老渔民。这是渔村男丁的普遍命运。爷爷疼我。我出生的时候妈妈没有奶,爷爷便为我养了一只奶羊,每天挤羊奶给我喝。村里人屡次向我描述,爷爷一手抱着我,一手牵着羊,那场面真温馨,叫我以后一定要孝顺爷爷。
我最近一次想念爷爷,是因为读了苏东坡的诗。“莹净鱼枕冠,细观初何物。形气偶相值,忽然而为鱼。不幸遭网罟,剖鱼而得枕。方其得枕时,是枕非复鱼。汤火就模范,巉然冠五岳。方其为冠时,是冠非复枕……我观此幻身,已作露电观。而况身外物,露电亦无有。佛子慈闵故,愿受我此冠。若见冠非冠,即知我非我。五浊烦恼中,清净常欢喜。”
时空转换至1081年的黄州。在一次聚会中,老友陈季常对着天才作家苏东坡调侃说,苏东坡你什么文章都会作,唯独不会作佛经。苏东坡不服气,谁说我不能呢?陈季常说,“佛经是三昧流出”,与你平时靠思虑谋篇布局不同。苏东坡摩拳擦掌,那就试试,你随便出题!陈季常随手指指头上的鱼枕冠说,就以它为题。由此,苏东坡写下这首《鱼枕冠颂》。
鱼枕冠,是以鱼枕骨作为装饰的帽子。那是一种特别的鱼骨,是从淡水大青鱼的头部取下的骨头。这种鱼骨经打磨之后,呈半透明状,像玛瑙,又像蜜蜡。古代王公贵族戴的帽子,常以这种鱼骨作为装饰。
当时,苏东坡沉吟片刻,作了这首《鱼枕冠颂》,意思并不难懂。鱼骨,离开鱼身,成为帽子上的饰品。鱼骨的身份,不断地转换,没有定则,像我们的身体,如露如电。苏东坡所作,当然称不上佛经,因为这非佛亲口所说。但诗文很切题,也很通透,有点《金刚经》的意味。
或许正是靠着这种理念,在幻灭中暗含乐观,苏东坡在跌宕的人生旅途中收获了许多快慰,不然他不可能将这首诗脱口而出。我怀念爷爷的时候,这首《鱼枕冠颂》也多少宽慰了我的心。
当年我骑的那块鲸鱼骨,终究没有被博物馆的人收走,而是在渔村搬迁的时候被推土机压断,跟普通的石块、泥土一起填进了大海。威武的鲸,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回归海洋。
爷爷还跟鱼骨发生过一次密切的联系。爷爷视力极好,在岸上能看见50米以内海域中的鱼。我们当地有一种土鱼,沙黄色,身形扁平,游动的时候贴着水底的沙滩,靠着保护色很难被发现。年轻时,爷爷拿着钢叉,站在齐腰深的海水里,专叉这种鱼。土鱼的尾巴上有毒针。偶然一次,挨了一叉子的大土鱼痛极了,一挣扎,将毒针扎进爷爷右手的大拇指。爷爷了解那种毒性,立马斩断拇指。到了县医院,医生在爷爷肚子上开了一个洞,将拇指插在洞里,长好了,再将拇指取出来。最终,拇指保住了,却丢了指甲。
爷爷跟我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自打我记事起,爷爷右手的拇指便没有指甲。当时,爷爷一边抿着黄酒,一边道出上述情景。我怀疑爷爷是喝多了,抑或是评书听多了,开始乱编故事——如何能将拇指插进肚子里生长呢?爷爷见我不信,便撩开衣服给我看那道伤口缝合之后留下的疤痕。最关键的是,爷爷还保留着那根有毒的土鱼针。它像绣花针那么长,不太起眼。那根针,是另类的鱼骨。冰山一角,诉说着海洋的凶险。
爷爷晚年得了胃癌。我放暑假回家,得知这一消息,痛哭起来。再去看爷爷,他人瘦了一大圈,依旧闲不住手脚,乐呵呵地摆弄他的渔具。爷爷掀起衣服,给我看手术的刀口。爷爷说,他这辈子吃的鱼太多了,鱼骨便长在了肚子外面。只见那刀口是竖着的长长的一道,加上针线缝合的印记,歪歪扭扭,很像一条鱼的骨头。
如今,爷爷故去已经10年。我经常在梦里见到他,有时见他在认真地叮叮当当修理一条渔船,有时见他沿着长长的海岸线行走、赶海。爷爷是个倔强不服输的人。但是,任凭他再坚硬,也抵挡不住岁月柔软的磨砺。如同苏东坡的《鱼枕冠颂》所写,坚硬的鱼骨,被打磨成帽子上的装饰,又在时空里不断地转换身份。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这具如梦幻般脆弱的身躯,不可能长久保有。肝肠寸断的别离,只是万物演化中最微不足道的环节罢了。
(庭南摘自《福建文学》2024年第6期,王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