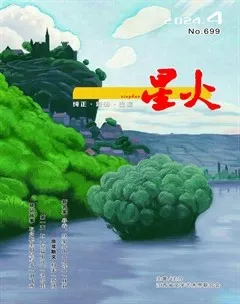嵊州炒麻糍
2024-09-11陈瑜

陈瑜,浙江嵊州人。作品散见于《星火》《山东文学》《野草》《文学港》《海燕》《美文》《散文百家》《散文选刊》等刊。曾获第二十四届孙犁散文奖。
嵊州人将年糕叫麻糍。做麻糍是冬日里一件极具仪式感和叙事性的盛事。套用小茶老师的说法,四十多年前的冬天,天冷得气派。在冷得气派的时节里做一件热腾腾的事情,日子便也气派起来了。晚稻归仓后的某一天,像有人扯了下电灯开关,村里的加工厂开始灯火通明地忙活起来,村户们按小队抽完签,便开始落米浸泡准备做麻糍。一户接着一户,加工厂日夜不停,机器不断吞吐,麻糍像拔节的春笋不断生长,流向各家各户。孩子们的快乐也在心底生长,他们雀跃着进进出出地吃热麻糍团,并不拘于哪一家。用麻糍将红糖或者腌萝卜一裹,嚼起来柔韧鲜香;哪怕什么也不包裹,也自有稻米的芬芳在口舌间汪洋。最让人兴奋的是,有巧手的师傅,用“糕花”随手捏出兔、鸡、鹅、猪等动物形状,好吃又好看。人口多的人家百多斤地做,少的也会做上五六十斤。无论多少,该有的程序一样也不能少。浸泡过的晚粳米肥肥白白、松松脆脆的,毫不费力地就被碾成米粉,在蒸笼上蒸熟了,就是芳香四溢的“糕花”,将“糕花”倒进碾压机的“斗”里,很快,下方出口,方形的热麻糍就源源不断地挤出来了。切麻糍的师傅,戴双白手套,坐在边上,将麻糍挥刀斩成长度匀称的段块。“跑堂”的人端了长条木板,将麻糍排在板上,不断地送至等候在旁的主家边,有帮忙的阿婶阿嫂七手八脚地将之摊到的竹簟里,一段一段隔着间隙铺排开,免得粘连。一排排、一列列整整齐齐的麻糍,像是节日的图腾,气势十足。等“大气”透过,各家将麻糍挑回家,再在簟上、匾上继续摊凉,算是完成一桩大事。
麻糍,可做省事的简餐,也可登隆重的待客之堂。最简单的是汤麻糍,嵊州人叫“放麻糍”。麻糍入水,水煮至沸,放进青菜、草籽、荠菜等时令蔬菜,也可以是笋干菜、雪里蕻、腌白菜等腌制、晒制菜,最好吃的莫过于经霜的乌油菜,或者春天的菜薹。菜梗碧绿,麻糍瓷白,弹点盐花,或者加勺美味鲜酱油,再来一笃猪油,感觉整个春天都在口中山高水长。在一日三餐米饭的四季弦歌里,一餐放麻糍就像一阕清新的小令,让肠胃得以享一刻的清欢。嵊州向有正月十四夜吃“亮眼汤”的习俗。民国时《嵊县志》载:“十四夜各社庙悬灯,妇女结队同游,谓之游十四,以菜煮麻糍食之,谓之亮眼汤。”“亮眼汤”就是青菜汤麻糍,它让食物有了美好的寓意。
大姨娘从南京归来,“接风宴”必定是母亲精心制作的炒麻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车马慢的年代,南京到嵊州要一天一夜。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上海转车到曹娥,曹娥再转乘汽车到嵊州。母亲到县城北站接了人,再走上十几里路到外婆家。大娘舅早早就切好了一淘箩的麻糍,洗好了配菜,翘首以待了。这一顿炒麻糍,母亲必定是铆足了劲的。先将鸡蛋煎成薄饼,切成细丝备用。接着是炒雪菜,自家腌制的雪菜墨绿中带点金黄,加冬笋一翻炒,香气能飘得老远,起锅备用。然后将切成条、不带水的麻糍放入热油锅,翻炒,炒至软糯,加少许酱油提色,再加入炒好的雪菜冬笋豆腐,加足量水,猛火煮开后调成文火慢炖。待汤色渐稠,次第放入肉丝、蛋丝、大蒜。大铁锅里咕嘟嘟地冒着香气,经过高温翻炒,低温慢炖,此时的汤水细腻绵滑,汤体有一定的黏稠度。汤汁像一件轻薄的外衣,将食材本身的鲜香紧紧包裹。汤底吸收了食材的精华,粥汤样浓郁而丰富,喝上一口,会让人生出“香于酪乳腻于茶,一味和嘈润齿牙”的感慨,感叹这简直人间美味。浸润着山水精华的时令菜蔬,再配以柴火灶,这一碗麻糍无疑是有魂灵的,谁又能忘怀有魂灵的食物呢。大姨娘每次都吃得无比满足,仿佛与故乡唇齿相依的情感立即被唤醒,在鼻尖、在舌尖、在唇齿、在味蕾,在整个身体、血液和灵魂里奔突。那一刻,食物,除了内涵,还有无穷无尽的外延。对大姨娘来说,这碗嵊州炒麻糍早就不仅是美食本身,它还是一缕光、一帧影像—妹妹在灶台上忙碌,弯了脊背的长兄坐在灶前,一把一把地添着柴禾,将一锅亲情煮得滋味悠长。
我和弟弟自小都寄养在大姨娘身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姨娘从贫穷而飘摇的村庄走出,辗转在城市扎下了根。她拼命地想把我们从乡土的泥巴里剥离,以一己之力给我们一个“城里人”的童年—事实上,这抹鲜亮的人生底色,如秘密的源泉,不断丰盈着我们的内心,滋养着我们的成长。俗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抚养孩子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这在我当上母亲后体会更深。作为薪资微薄的列车员,大姨娘要撑起的不仅是几个孩子的衣食住行,更是工作与生活的兼顾。就这一点想想,这种无私的爱是再也没有别人能给予我们了。列车员跑长途是有补贴的,但大姨娘为了方便带我,就常年跑交通车。那趟交通车是南京西至栖霞山,为方便铁路职工上下班而开,每天早出晚归;有一部分乘客是沿途郊区的农民。铁路职工乘车免费,农民乘车两毛钱。我每天跟着大姨娘上下班,坐在小小的乘务室里。小几上放着云片糕或者盐津枣,让我吃着解闷,夏天会有火车上供应的酸梅汤喝。在哐当哐当的节奏声中,绿皮火车像根长长的拉链,沿途的树木、村庄、田野、作物像一颗颗的链牙,每一天的朝阳与晚霞以同一种方式打开。车内乘客的面容总是大同小异,生活在他们脸上循环往复。通常我都乖巧地待在乘务室里,偶尔也会憋不住,走到车厢的过道上。乘客们就会逗弄我:“你大姨娘将你送给我们啰,今晚带你家去。”我就嚎啕大哭起来。大姨娘是个十分珍惜工作的人,她是那样热爱自己的岗位,穿着那身深青色的制服,在车厢里不停歇地忙来忙去。但当青春叛逆期的表哥不愿读书闹着要顶职时,不到50岁的大姨娘提前内退,这成了她一辈子的遗憾。此后,闲不住的大姨娘在小区看过自行车,帮人家做过针线活。有几年,流行旗袍,大姨娘做的盘扣漂亮精致,针脚匀称细密。她有双绵软无骨的手,这双手将针线活做到像艺术品,菊花扣、琵琶扣、蜻蜓扣、盘香扣……就像一颗颗星星,在岁月深处闪烁。大姨娘想方设法地挣钱,又省吃俭用地将每一分钱都用在了我们身上。她从不吃牛羊肉,甚至不吃鱼—不知是不是因为长久的克制,而丧失了欲望。每次吃饭,她会将荤菜不断夹进我们碗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吃,脸上流露出一种陶醉的慈爱的表情。我只能说这种目光对我的照耀,今生今世也不会再有了。母亲时常说:“你们除了没有从大姨娘的肚子里出来,她把能给的都给了你们。”我幼时多病多灾,就连隔壁最喜欢我的玲娣姐都忍不住对着大姨娘喊:“丁阿姨哎,这是人家的孩子哎。”言下之意是说大姨娘何苦来哉。
我穿着大姨娘买的上海产的鹅黄色灯芯绒外套,扎着大姨娘托同事从芜湖带回来的丝绸蝴蝶结,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春天里,像一幅行走的年画。
大姨娘每次回来,都是大包小包肩扛手提的,穿的,吃的,用的,仿佛她长久的积攒都在为这一次返乡而准备。而走的时候,母亲总是在那只印着上海外滩的灰色人造革拉链袋里塞满麻糍—这在如今看来简直是冒傻气的行为。扛着一大袋砖块一样的麻糍,上下转几趟车,这滋味绝对不好受。但在那些年月,麻糍是一块上等的羊脂白玉,装点着贫穷的光阴。经历过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的人,最是惜物,大姨娘过日子精打细算,尤其表现在对食物的格外珍惜。带到南京的麻糍,很长时间,像观赏鱼一样被养在水桶里动也不动,隔几天换一遍水。大姨娘总是舍不得将麻糍趁新鲜吃,非得等浸泡的水换了又换,甚至发出酸馊味儿时,才挑时拣日地捞出来切上半块或一块。她每次切麻糍的时候,几乎带着一种虔诚,像孩子舍不得将糖果一口吃掉,总是想尽办法延迟着那份满足感。她把麻糍吃得细水长流,吃的早就不是麻糍的本身,而是被时间和地点拉扯的亲情和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