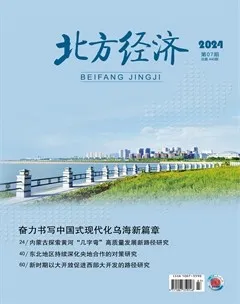法制化草原管理体制的历史渊源探究
2024-09-11郝益东贾幼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草原畜牧业发展历程中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和重要措施上升为法律法规,形成了以“三权分置”和“草畜平衡”为中心的法制化草原管理体制,保障了牧区草原畜牧业及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然而,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现了牧区是否应该恢复游牧的争议话题。有些学者认为草原传统游牧可以自由迁徙,完全依赖自然环境就可以维持畜群生产,从而对现行草原管理体制产生了种种质疑。本文依据《蒙古秘史》①这一被誉为游牧民族实录巨著中的有关信息,还原蒙古高原统一后草原管理和建设的真实状况,以便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认知误区,正确把握草原畜牧业的发展规律,增强牧区同步完成“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主动性和自觉性② 。
一、《蒙古秘史》中的相关信息解析
(一)有序管理草原的开端
成吉思汗对建国功臣委任为千户官进行封地封户,分配百姓(忽必 亦儿坚)。除森林百姓外,把统一后全蒙古的百姓分配给所指定的95个千户官③。从上到下形成万户、千户、百户、十户的官职系统,统管人畜草场。将分配百姓统一记录在青册的措施,进一步从国家制度层面消除了不同群体间争夺草场引发的混乱。成吉思汗指令说:“把全国分领百姓和所断案件都写在青册白纸上面…子子孙孙永远不得更改④”。在此基础上颁布“大札撒”等法令严厉处罚私自越界。
(二)驻营放牧许可管理的信息
成吉思汗对几个有特殊之恩者授予“自由自在者(答剌罕)”,许以免罚九次犯罪、免除税赋等特权。其中只对自己的救命恩人锁儿罕失剌一家在其他人的特权之外,准予其子子孙孙在薛凉格河之地自由选择营地放牧的请求⑤。说明除此一例之外,当时所有草原的放牧都处于相应的许可管理之下。
(三)国家保护百姓草场权益
斡歌歹罕继承汗位后对社会生产生活加强系统化管理,在一个施政指令中明确说:“还有,国家要给百姓分配(忽必牙)营地草场和水,从各千户中选择营盘官执行”。
(四)草原建设的开启——打井与驿道
蒙古高原统一后推行了几项重要而有效的管理措施,使游牧有了免受社会动荡破坏、维持正常生产秩序的稳固基础。牲畜的增加必然要求放牧草场的扩大,有史以来依赖河湖水源放牧的草场已经无法满足游牧生产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斡歌歹罕在指令中说:“还有,旷野地方除野兽外别无牲畜和人烟。以派察乃、委兀儿台两个营盘官为统领,找水砌井,让百姓能够散开住得宽展”。斡歌歹罕还指令各千户设置驿站,使臣驰骋和运输物品沿着驿站来往,不得烦扰百姓。
(五)设立管理营地草场的官职
《蒙古秘史》中的营盘官(嫩秃兀臣,嫩秃兀赤)是管理营地和草场的官职。依据有关文字可知其职责:在汗宫和王府负责宫帐选址和搭建,在各千户管理草场水源,宗王聚会时为挤奶马群管理马驹(兀讷忽臣),统领草原打井(忽都兀惕),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有职责分工(嫩秃兀臣 亦勒合)的官职系统。
二、讨论与结论
(一)与官制结合和围绕百姓权益是古代管理草原的基石
从成吉思汗设置官职系统封地封户开始,稳定草原权属关系成为国家行为,草场的分配、管理、使用的权限已具有系统化雏形。斡歌歹罕关于国家要给百姓分配草场和水源的指令,意味着把保障百姓的草原权益提到了最高统治层面。营地草场官的设置及其职责的规定,无疑会加强草原管理的实效性。可见现在有些学者排斥政府对资源管理的主导作用,认为游牧民能够自觉管理草原,甚至引入国外游牧话语将所谓“社区自治”强加到中国牧区,显然完全违背《蒙古秘史》所展现的与官制结合自上而下主动规范和管理草原的历史事实。古代即已形成的有序管理草原、维护社会生产的精神在我国现行法制化草原管理体制中也得到应有体现。
(二)草原打井开启了为游牧注入建设要素的历史进程
从斡歌歹罕指令为百姓打井、开发无水草场开始,游牧生产迈出了通过建设摆脱完全依附自然的第一步。随着人口和牲畜的增加,单纯依赖河湖水源导致可放牧的草场严重不足,只有在地表无水的草场找地下水砌井,才能使百姓的营地草场变得宽展,适应更多牲畜的牧养。斡歌歹罕的这一创举得到后世继承,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继续大量“派军士漠北浚井”。然而,真正把无水草场变为四季都可以正常放牧的有水草场,只有到现代化机械和器具普及之后的当代才得以实现。
(三)中国的草原管理体制弥足珍贵
纵观蒙古高原的历史,凡是统一和安定时期,草原都处于有归属、有管理、有许可放牧范围、放牧利用者关联制约的基本状态。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草原管理和建设的演进,与《蒙古秘史》中有关管理建设草原的核心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现行法制化草原管理体制顺应历史传统,适应发展要求,兼顾生态、经济、社会、民生多重效益,既能长久、公平维护牧民的草原权益,又能保障草原畜牧业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基础上,向现代化迈进。反观欧亚草原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有的草原闲置、放牧畜牧业消亡;有的疏于公平性管理而放任强者随意占用;有的名为维持游牧,但实际上既无应季搬迁的能力,也缺乏促进发展的制度安排。
(作者1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作者2系原国家农业部总经济师、国家首席兽医官)
责任编辑:张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