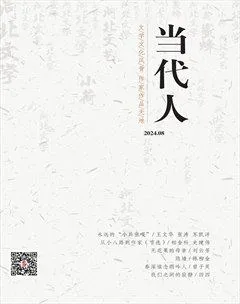果壳里的故乡炉火正旺
2024-09-06冯艳冰
曾经长满了“金子”的南方稻田,被乍起的秋风一遍一遍地吹拂,在谷粒归仓之后显得有些落寞有些寂寥。倒是寒露刚过,北方的冬小麦开始抢占辽阔的黄土,它们要在漫长的凛冬里蛰伏。想象冰雪覆盖下的麦苗,正静静等待春的到来,北方冬天的深处,也有寂静深沉的美呀。这个时节,我们收拾行囊要到作家李浩的家乡河北沧州海兴辛集村去。那是他的城堡和果壳。
果壳里有一粒能生根、抽芽、长叶、开花、结果的种子吗?
一
我是在我的家乡广西认识李浩的。
2016 年的春天,因为一行文人的到来,太阳还没有西斜,才下午四点,热情的乡亲们已燃起了烟花,把寂静安宁的乡村搅得纷乱而热闹,直到深夜,整个村子都没有睡意。正是春末,那时稻田蓄满了亮旺旺的水,禾苗已长有三四寸高,在梁晓阳的家乡——广西北流天堂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里 (同为北流人的林白和朱山坡也在),我第一次见到了李浩。
面对旺盛的炉火,李浩敦厚温和的笑被映得通红,他那两道浓密的眉和短而齐整的头发似乎被烤得热乎乎的,让微胖的他充满了喜感。一位跟他有深厚交情的朋友把他邀请了过来,与时任《散文选刊》主编的葛一敏和后来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弋舟一起,参加我操持的“重返故乡”文学采风活动。这时他酒酣耳热,讲话已不太利落,他虽有河北文坛“四侠”之一的美誉和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的光环,但此时因不胜酒力而笑憨语迟。顺着职业练就的讨稿惯性,我向他开了口。
“给我们刊物写个稿呗,写写你的故乡。”
“没问题。”
这么爽快的答应着实让我感到既惊喜又意外,甚至担心他会立刻补上一句“我在写长篇,你得等等”之类的话。好在,我接二连三地等来了好消息。他先是给了他的诗歌、散文,我约他为我责编的评论小辑写一个评论他也答应了。作为一名编辑,有什么比拿到好稿更让人高兴的呢。李浩的鲁迅文学奖是靠小说拿到的,但他却认为,自己的评论比小说好,诗歌比评论更好。在书面上他是这样表达的:“诗歌一向是我最看重的文体,甚至对我而言是‘最为看重’的文体,就现在的完成度而言,我的诗歌特色是最为明显的,它不会有混淆感,并且它的个人性在我的写作中也是最强的。”
他说的也许是对的,在我的理解里,对于一位写作者而言,诗歌是他的精神状态,小说是他的行走状态,而评论,则是思想状态。显然,李浩三者俱佳。
我知道,写小说的作家中有许多写诗歌的。早些年,中央电视台一档《文学的故乡》节目,讲述了六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如何把生活的故乡转化为文学的故乡。这档节目播出那会儿正值七月,微信群里的成员对节目关注的热情似乎更高于当时的气温,大家躲在空调房里刷屏、评论,其中的一个话题是关于这六位被邀请的作家与诗歌的联系,莫言、贾平凹、阿来、毕飞宇都有诗歌创作经历,阿来曾参加过青春诗会,有新诗集出版;毕飞宇大一时就是凭着闲暇创作的诗歌,入校没几天,一脸懵地被学长推到了文学社社长的位置。
李浩似乎没有“对诗歌热爱又没有时间进行”的遗憾。常常,李浩是以小说家的身份满天飞,文坛中的“河北四侠”之一多指认的是他是一位编故事的高手、善于思考的智者。人们通常用“周身刀”比喻一个人本事多本领强,而真实的情况是,以魔法师自诩的李浩,在他魔法一样的黑色斗篷下,小说、散文、批评、诗歌,每一把刀都闪亮锋利。
二
在晓阳家乡一栋民宿的露台上,乡下春天的晚风凉爽而惬意,我把参加此次活动的几位广西诗人介绍给李浩。屋子里其他的宾客也在晚餐尽兴之后,纷纷来到露台喝茶聊天。厨师把夜宵——天堂山农民喜欢的牛肉萝卜粥端到茶桌上。面对这碗既有萝卜的清香又保有牛肉醇厚的稀薄粥水,即便是酒足饭饱刚刚离开饭桌的我们,仍胃口大开。主人介绍说,晚餐后茶是主角,萝卜牛肉粥只是助兴而已。大家又摆开了龙门阵,兴之所至,好几位朋友亮开嗓子唱起歌来。弋舟唱陕北的民歌《兰花花》唱得投入,动情处让好几位听者眼里直闪泪花。我们在另一旁聊到了诗歌。2006年开始到 2016年,《广西文学》的“广西诗歌双年展”已举办六届十个年头,每每举办诗展,广西诗人都跟过节一般,当然也仅限于广西本土诗人的自娱自乐。我向李浩提了一个设想——要不河北与广西一北一南两省 (区) 一起来个诗歌联展?李浩迅疾收起了笑容,表情从松弛自在的绽放到振奋严肃的凝重。他说很好很好,而且他本人会参加这次活动。他是认真的,随即掏出手机将冀桂两省 (区) 诗歌联展事宜告知著名诗人郁葱老师,当即得到其首肯。当时我和李浩都各自端着茶杯,轻碰了一下以示合作开始。这是历时六届十年的广西诗歌双年展第一次与外省的“走动”与“往来”,算不算一次破冰之旅?偶尔想起,我会把这桩“盛事”归因于2016年——似乎也不算什么太特殊的年份——“2016”是可以被4整除的闰年,也就是说四年才一闰呢,是极珍贵的,遇上不易。冀桂两省 (区)联展由此拉开序幕。
事后,李浩甚至认为,联展或多或少也有“擂台”的性质,对抗与挑战的意味是明显存在的。在第七届广西诗歌双年展研讨会上,李浩道出实情:“没有人愿意在这样的展示中被比下去。我承认我在对河北诗人的约稿中强化了这一点。我暗暗逼迫他们认真对待。”我忽然发现,温和敦厚的李浩还有“争强斗狠”的一面。实际上,广西也不过是诗歌大省 (区),而河北则是诗歌强省,如大解、郁葱、李南等一干著名诗人都参与到这次的诗展中,而且拿出的是他们在那个时段创作出的最好的作品。也因此,对于李浩所谓的好胜,我更多地理解为是对文学的尊重。一南一北的诗歌擂台,诗歌强省河北,尽管占据了实力的优势,但对每一次文学创作,都不轻慢不随便;而我更多地希望借助联展的契机,让广西的作者摆脱旧有的写作惯性,观照对手更审视自己。
幸亏遇到李浩,他什么文体都可以写,而且有一副热心肠,把河北组稿的事一并张罗起来。
三
码字的人聚在一起,光是吃酒喝茶是不够的,在露台上就有人提议说,村子前有条小溪,三月的河水还是瘦的,我们可以到那儿去讲故事。
果然,小溪只有四米来宽,溪水异常清亮,水中错落有致的鹅卵石在月色下泛着白光。枯水期的鹅卵石是可以当作天然石桥的,三跳两跳就可以到对岸。我们三三两两地,选了心仪的石头盘腿坐下,溪水从我们盘坐的石头下流过,当时的那份惬意,还真有苏东坡夜访张怀民写的《记承天寺夜游》的情景。那一刻月光如水,我们如水中藻、水中鱼。相约来到水边原是要讲故事的,不料,大伙儿被乡下夜晚的静默所震撼,一夜无话,倒是听了一晚上的溪水潺流,露水厚重了才各自散去。
当晚我们分散住到了农人的家里。第二天早餐,主人上了豆腐酒。客人们便好奇,觉得天堂山下的农民真是幸福,吃酒这件事情,可以变着花样从早到晚地进行。主人说,倒也不是,平时都忙手上的活计,有来客才可以这个样子任性一把。说到吃酒,话题又转到李浩的身上。不胜酒力的他昨晚醉得兴高采烈,朋友把他送回房间,他毫无睡意,拿着水性笔,往墙上的瓷砖写了一大版书法。
我好奇地问他:“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学的美术。”他答得有些漫不经心。
居然是美术!
李浩跟跨栏运动员似的,从一个领域跨到另一个领域,而且成果丰硕。2004 年的《封在果壳里的国王》,他尝试将“小说”放置进他的诗中;2015年,他试着在自己的长篇 《镜子里的父亲》 中“增添”一些东西,即为其中的每一章节相应地“配”一首诗。我见过他书写得娟秀雅致的小楷,向他索要字画时他给我寄来了他的新诗集 《果壳里的国王》,倒是诗集的名字有趣,褐色的封面里藏着凝重与神秘,他的小说《封在果壳里的国王》和同名长诗 《封在果壳里的国王》,我想应该是互相诠释互为证词的,不可想象他用不同的文体能在一个题目里兜兜转转。倒是他坦然承认,“一向,我将自己看成被封在果壳里的国王,这个想法似乎没有来由却根深蒂固。”
他说“没有由来”?!
也许是。
但从他出生的那个寒冷的时间说起,兴许会找到答案。李浩出生在大年夜里的那一刻——家家户户的鞭炮齐鸣迎接新年,他正好落在辞旧迎新的那个时间节点上——如推开门栅跨入另一个世界的一瞬。李浩在为我《重返故乡》栏目写的那篇《时间树,父亲树》中,谈到那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时强调说,“对我有过潜在的影响,我承认,它影响着我的心理,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可能’是一个大人物,我会像某某某、某某某那样创造人生的奇迹……这一暗示现在依然会悄悄地起些作用,包括在文学上。我承认自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在我的文学中,我愿意并始终坚持‘创造一个世界’,让我部分地在那个自我所创造的世界里容身”,而且“我不知道,我说不清楚。但它,真的是有持续的影响。一直。虽然我也曾一次次地对这一影响进行嘲笑”。
李浩以僻乡“午夜之子”的身份自居,平日里,李浩最是谦逊诚恳,他的心无挂碍和周到妥帖让你不由自主地把他当亲人看待。如此待人接物的行持作风平移到文学评论上,自是文笔犀利又不使被批评者的文艺之心破碎,甚至心生感激与欢喜。无疑地,他更认同自己是能创造奇迹的王!不可思议的出生时辰,给了他怎样巨大的心理暗示。当大年三十跨进大年初一的那一刻,就像从旧到新的那道分水岭,他正好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于是他野心勃勃起来。一旦坐到电脑前,他这一天的“江山”就稳固了。可以想象,他头戴“皇冠”,气定神闲,中国有这么多的汉字任他调遣,因此他也可以骄傲蛮横,怒气冲冲。在文字的王国里,手握权杖的他,是自信的,甚至有小小傲慢。后来观察,这傲慢确实有些小,要不他怎会把自己封在果壳里呢?而且这傲慢一而再地出现。倒是我分不清,他说的是哪一种果壳。尚在年幼阶段,我们更钟情于细小的事物,也玩耍过果壳的游戏:夏天吃了荔枝攒下一大把的荔枝核,用两三分钱买来的削笔刀,把比小拇指还小的光滑软脆的荔枝核,雕刻成各式各样的小水桶、小凳子、小桌椅;当姐姐把一颗花生米剥开,我惊喜地发现,里面住着一位长着胡子的老爷爷!倘或把李浩果壳里的王与花生米里的老爷爷做一个链接,这会不会就是那位有着小小傲慢的王?如果把果壳理解为他的精神世界、理解为文学的自由王国,这果壳又无限宽阔了,这样的猜测也是合理的。又或者,果壳里的王是从小就住进他的心底里的。这王可真淘气啊。
四
真正体会到李浩的淘气,是在他给我的《时间树,父亲树》里。他选择中国农历家家户户迎新的时刻来到这个世界,让全家上下手忙脚乱又欢快异常;经过传奇般的三死三生,才平安地长到成年。家乡辛集村承载了他童年的所有记忆和情感。
岁末时节,由作家、批评家、诗人组成的广西文学采风团穿州过省,来到了河北省沧州的辛集村——李浩从小居住的土坯房、农家院。
我们乘坐的大巴停在村子边的公路上,前一晚我们住在沧州。公路到村子有百来米的距离,前来接待我们的是位可爱的小姑娘,她告诉我们,听说有名家要来,我们脚下的这条路前天才刚修好呢。
“原来是泥沙路?”我好奇地问。
姑娘呵呵一笑说是的。
悄悄地我用力跺跺脚,试试脚感,路面已经硬化好了。十二月,沧州的风还没冷到刺骨,跟南方湿冷的天气比,清冽而干爽,很是惬意。月白色的新道向村子蜿蜒而去,隐隐地有热气升腾,真是感叹辛集人的尊师尚学,能够为了一次文学活动修一条路,真了不起!
五
初识李浩,除了他大体量的身板,总觉得他过于温和谦逊的性格不太像北方人。酒量差更是让作为北方人的他颜面尽失。在北流那年,喝醉了的李浩第二天仍没清醒过来。我们去登天堂山,“无情”地把他一个人扔在了民宿里。
在辛集村,我见到了李浩的弟弟李博,一位典型的北方汉子,脸庞宽大微醺,身高与体重都超过了兄长。性格也爽朗,光是那身材声线,就给人很排场的印象。李浩跟弟弟的感情极好,在李浩的作品里不时看到李博的身影。我好奇兄弟俩怎么都长得彪悍壮硕,大概率是源自北方强大的基因,当然还跟他家的吃食有关系。我悄悄地专门到他家的伙房瞧了瞧,很平常,跟以往北方乡下我们见过的伙房没什么两样。印象深刻的是那体量庞大的灶台,又粗糙又黝黑,结结实实的,用力一嗅,还能闻到灶台散发出来的特殊的麦香味。这跟梁晓阳家乡那个临时搭建的煮萝卜粥的“玩具”灶台、周龙家煮玉米粥的简易土灶的气息是相同的——最朴素最简单的五谷把这些孩子养大。
每一个人的成长之路都有每个人特别不同的缘由,但相同的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深深包裹着自己灵魂的故乡。在李浩的内心一定存在着两个故乡。一个是以他的父亲、其他亲人以及乡亲们为实际存在的故乡。在这个故乡农家院的土坯房里,尘染烟熏黑柴红火炽热非常,有躲在灶台后的灶王爷或行善或作祟,伴他度过了童年和后来的许多岁月。常常回家看看,撬开你的果壳,拨拨家里的灶膛,你才会发觉什么才是只属于自己人生的理由。认识李浩时,我们在桂东南乡村,我们一同感受了桂东南火灶的传说和现状。也因此,我特别能感受到李浩《灶王传奇》所深埋的寓意。灶神崇拜是中国平民百姓最普遍的一种心理寄托,民以食为天,炉灶当然为王,百般的灶台烟火,孕育的也是百般民风民俗和民子民孙。今天,城市化的步履和现代科技的日渐浸润,煤气炉电磁炉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灶台不再有火膛,厨房不再冒草木黑烟,这里还会有灶王爷的栖息之地吗?我们的寄托还能得到灶王的回应吗?当然!因为人间的烟火可以洞穿时光,凡间的人性可以拆除空间的壁垒。《灶王传奇》便是李浩从中国的灶王那里获取的文学经验。
这部《灶王传奇》,也许是我们得以最深入地把握这些年在文学领域里上下求索的李浩内心秘密的一把钥匙。李浩是在他文学创作进入左右逢源、顺风顺水的阶段,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近于呼风唤雨的时候创作的这部长篇——有长达十年的写作准备,在进入文本时是如此的理性周全,一切都考虑得成熟妥帖。从创作思想到主要形象的设置、故事框架的构建、情节场景的铺陈、语言风格的追求等等,可以说事无巨细。在他的灶王身上,我们不难看出伟大的《浮士德》中浮士德与魔鬼梅菲斯特的影子。歌德的浮士德在魔鬼梅菲斯特的帮助下,历经天堂、人间和地狱;李浩的灶王混迹于天庭、人世和地府三界。西方博士与中国式知识分子,在两种相似的情境中所形成的浮士德精神与灶王精神不无神似之处。李浩的思考在中国当代“70 后”作家中显然是具有代表性的,那就是完成了在哲学层面的深度开掘和历史深远探寻的多元而立体的主题设计。我喜欢李浩的这部长篇,尤为欣赏他在谈到创作这部小说时坦诚的写作经验。在《前前后后:写作〈灶王传奇〉过程的几个相关词》里,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创作野心——愿意自己的写作属于歌德式的那种“世界文学”,期望用一生的探索为人类提供未有和新质的发现。对文学的这番表白,得有怎样的赤诚与执着才能做到。
这个形而上的故乡——已被李浩用汉字的砖块垒起来的故乡,这故乡里有数不尽的灶王以及无限大的疆土,且以文学寓言的方式存在着。果壳和城堡,则成了他这两个故乡的象征。只要在这个时空里,李浩就会脱胎换骨,成为与哈姆雷特共语“我可以被困在一个果壳里,却仍把自己看成无限的宇宙之国”的文学之王。而在诗歌自我建造的“白色城堡”里,有时他更像“一只侧卧在雪地上舔自己愁容的老虎”。他在诗歌和小说硬壳里搭建了一个让他躁动的、倔强的、多愁善感又不停追问和奔走呼号的灵魂的栖居之地。那也是他的文学故乡。
(冯艳冰,编辑、作家。曾获 2023 年“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奖·骨干文学编辑奖”。在《民族文学》《诗刊》《作家》《美文》等发表诗歌、散文及文学评论若干。出版有文化随笔《名编访谈》《〈红楼梦〉与为人处事》、名著注释《〈水浒传〉妙语》及散文集《在目光的尽头》。)
特约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