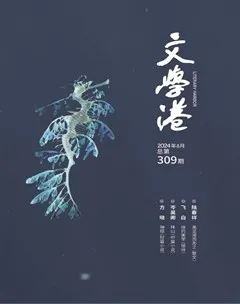竹上风雅
2024-08-28陈瑜
一
三月的江南,院墙外的龙梅已谢,观音竹苍翠依旧。鱼鳞瓦、粉墙、漏窗的映衬下,清竹秀逸,风中自带律动;龙梅虬枝寒瘦,风骨自显。左右依墙而立,各如一幅写意小品,显示“诗意的栖居”。
一身布衣的俞田自门内迎了出来。俞田是嵊州竹刻(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这是他城郊的一间工作室。一幢四层民居,迎面一张做雕塑的大操作台,熙熙攘攘的大堆工具中间,两尊似佛非佛的半身像垂眸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竹做的扶手像索引,沿楼梯盘旋而上。清瘦简约,触手温厚糯润,竹色暗黄,泛着玉泽的亮光。会客室里木雕、石雕、泥塑、陶瓷、紫砂、竹艺,还有近年来的油画、水墨作品、陶艺人像以及林林总总的小玩意儿,挤挤挨挨站在一起。当然,主题还是陈列架上的竹刻雕作品。
对坐饮茶,竹椅是定制的,清凉苍老,简约端方。俞田说:“想做同样两把,但材料难凑。”瞬间便觉身下贵重。甘美的茶汤,禅一样滑入喉间,我们仿佛穿行在长长的竹林中,听见竹子的深呼吸。架上的竹雕以各种造型表达着自己,与它们对视,你会惊讶于竹子对万物的包容。
竹子,是人类的密友。从桌床椅筷的日常,到竹简卷帙浩繁的书写。从竹楼广庇天下寒士,到竹杖芒鞋助人生修行,竹子以其虚中洁外,筠色润贞的风姿,扶助oinGO8llvMgkUKCIrKXVFg==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竹艺则让人想到云锦,一种艺术生活美学的极致表现。
民国收藏家赵汝珍说:“竹刻者,刻竹也。其作品与书画同,不过以刀代笔,以竹为纸耳。”人类从使用工具开始,似乎就具备雕刻家的技能。远古时期,先民用刀在竹子上刻符号记事,这大概是最原始的竹刻了。
作为一株葳蕤的植物,竹子注定无法像玉石一样沉默而恒久。因此,大多的竹刻雕艺术品被送回了时空回收站,保存下来的极少。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龙纹彩漆竹勺,可说是我们见到的最古老的竹艺了。两千多岁的竹勺纹饰精美、榫接巧妙,闪耀着神秘的光。制作的匠人,使用的主人,都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一如其他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我们想以此对时间之中的人的行迹进行揣摩和研究,其实都是徒劳——事实或许与真相大相径庭。唯有美,仍是直观的,通感的,直抵人心。
更多竹艺的美存在于古书和诗文的褶皱中——我们也习惯了这种若隐若现的浮现。比如古书记载,王献之有一个叫“裘钟”斑竹笔筒,形若钟,斑纹若裘皮,十分精致。《南齐书明僧绍传》载,齐高帝萧道成曾将一件用竹根雕成的“如意笋箨蔻”,赏赐给当时的大隐士明僧绍。北周文学家庚信《奉报赵王惠酒》:“野炉然树叶,山杯捧竹根”。说明竹雕艺术已经开始装点人们的生活。到了唐代,工艺更趋精美。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唐代德州刺史王倚家有一支毛笔,中间刻军行一辅,人马毛发、亭台云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诗两句,精致到“似非人功”的地步。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也只有鬼斧神工能解释了。而现在,日本正仓院还能见到一支中国唐代竹制的尺八,43.6厘米的一根竹管上,仕女、树木、花草、禽蝶栩栩如生。
宋代是古代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文人士大夫视竹为精神象征,认为竹子中虚劲节、清高,堪比君子。苏轼浩叹:“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文人雅士以此喻德,广做竹刻,笔筒、笔搁、笔洗、扇骨、储盒……宋高宗时有个名叫詹成的竹刻名家,能在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花鸟、纤毫俱备,精妙绝伦。陶宗仪在《辍耕录》情不自禁地赞扬詹成:“求之二百余年,无复此一人。”
竹艺是人与竹子的灵魂交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们有的变成珍贵的文物,有的变成了一个名字的传说……但是,有消逝就有创造,有中断就有传承。就像竹子,生生不息。俞田,让我对竹刻雕这门古老的艺术产生了格外的尊重。
二
56年的人生回望,如河流汤汤,忙于酝酿,忙于奔涌,忙于在前进中保持充沛的活力。人生道路或许平凡,但是艺术之路从不平坦。俞田聊着他这些年来的故事,听着他一路走来像竹子一样,有力地拔节,不断地雕琢自身。
俞田讲得最多的两个字是喜欢。俞田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浙江医科大学毕业生,母亲在教育局工作。一个体面的家庭可以带给人精神和物质上很大的自由度。父亲爱书法、爱画画,耳濡目染,俞田也从小喜欢涂画,爱玩泥巴。中学就读于石磺中学美工班,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有名气的职业中学,老师有著名画家王炳初先生、俞雨汀先生等。俞田在此受到工艺美术的启蒙教育,为他日后的雕刻生涯夯实了美学基础。中学毕业本来立志考浙江美术学院(1993年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专业成绩过关,却因英语6分之差惜败。那个年代,“居民”户口有着十足的优越感,高考失利后的俞田就业、入伍、退伍,又进食品公司工作。
工作清闲,薪资不俗。但过于闲适的生活同样对时间和心境构成侵犯,俞田常觉得心中有无边的空虚。一次,他去剡江工艺美术厂玩,看到琳琅的木雕工艺品,他意识到自己缺失的正是那画笔或刻刀。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下,他停薪留职,拜木雕大师袁水法为师,学习木雕技法。仿佛命运打出了一枪号令声,俞田开始朝着一个方向奔跑。如果用蒙太奇的手法来展现——迎着箭矢般的阳光,年轻的俞田奔跑的每一步肌肉紧绷,矫健有力,身上像一张鼓满风的帆。他是那样迫切,那样如饥似渴,那样焚膏继晷。雕刻、画画、做泥塑,双手在木头、黏土、纸张上抚触,时间被他压缩。三年出师,他三个月就开始上手雕刻。第三年他的月薪已令很多人艳羡。那是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嵊州木雕呈现空前繁荣,也催生了郑剑夫、吴筱阳、张立人、郑兴国、周扬等一批工艺美术大师,在全国各种艺术展览中屡获嘉誉。到了90年代末期,许多人纷纷另谋高就或下海创业。俞田却不急不躁,不争不羡,像一枚蚕蛹,将自己沉潜在木雕技艺里,一干就是十年。
2000年初,俞田开设了根雕工作室,这里成了他现实与梦境交织的舞台。虽然作为谋生之业,也受市场所囿,但他始终没有忽略对于自我内心的珍视、倚重。他目光灼灼,内心在燃烧。从传统中来,又像野马一样,从传统根雕人物的神仙、佛教类题材中突围,俞田的作品涉猎村夫野老、顽童美妇到英雄才子;以至引车卖浆之流、无赖帮闲之辈,渐渐显露出气象。其时,有一位颇有见识的老先生常来串门。某天,他感叹:“树根雕不能做啊,子孙米饭都让你们吃光了。”这话犹如醍醐灌顶。“不做树根雕,那做什么?!”老先生说:“做竹雕。”“竹子从来都是雅玩的上品,你得先了解竹子的文化、历史。”
一个人的情怀、才气、悟性、灵气是一件复杂幽微的事情,在人生旅程中或许还带有点宿命的意味。当年这位绰号“范仲淹”的文士或许也看到了这点,他的点化,导致另一段艺术的缘起。
2004年,俞田将目光转向了竹根雕。
施艺于竹,要熟悉竹的品性。“竹之性,一直,二节,三中空,故为雅器,多以其喻德。”(胡竹峰《临本》)竹子那种澄碧明净、苍翠深蔚的清逸优雅,向来是文人高洁的精神追求。竹艺的表达从来都是谦逊、洁净的,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和坚硬的思想。因取材不同,竹艺雕刻细分到竹根雕、竹(竿)雕,又分为浮雕、圆雕等技法。
我们将目光转向竹艺最成熟最繁盛的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写竹、画竹、种竹、刻竹蔚然成风。因着清乾隆帝的重视,竹雕艺术受到朝廷推动,更是空前鼎盛,精品迭出,星芒满天。可以看到留青、贴黄、镶嵌等精美的工艺背后的一个个或模糊或清晰的身影。因地制宜,可以看到两大流派在南方如峰峦崛起:以南京竹刻为代表的“金陵派”,以上海嘉定竹刻为代表的“嘉定派”。金陵派竹刻以濮仲谦为首,风格开始简朴,后渐工细。嘉定派竹刻影响更大,创作者多为文人雅士,大都擅长书画,用刀如笔,雅俗共赏。嘉定派的鼻祖朱鹤是一位诗书画兼修的文人,他以笔法运刀法,竹刻雕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木根雕到竹根雕,意味着走上全新的开垦之路。也只有由衷的热爱和底气,才能无畏无惧地从头起步。俞田买来了一拖拉机的竹根,开始“试水”。但直到一拖拉机的材料全部用完,始终突不破那层技法壁障。那些在木雕上熟稔的动词——刻、雕、挖、削、凿……在竹雕上始终不能恰如其分。俞田的韧性和狠劲上来了,整整七天七夜,他将自己粘在了竹根上,完全忘我。三个月后,他摸索出了竹雕的语言,从姿态各异的天然竹根中捕捉灵感,终于完成了第一件作品。而后,又连续完成了“地主”“磨豆腐”等六七件作品。一经问世,就被上海客户相中。即便高于市场价10倍的定价,仍被一抢而空,客户催着下单。
然而一个星期后,一通电话令他从兴奋的巅峰跌至谷底:“不能做了,竹根雕发霉长毛了,除非材料处理过。”纯天然的竹子湿度高,含有丰富的竹纤维、淀粉等营养物质,未经处理,很容易就霉变了。
竹子,以原材料的身份向俞田发出了挑战。遥想古人治竹,削竹为简册时,为了防止开裂,易于保存,有火烤杀青的工序,谓之汗青。西汉刘向《别录》中说:“陈楚之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亦治也。”俞田一边查资料,一边四处寻访取经。浙江、四川、福建、安徽……只要有竹制工艺品的地方,他都去。却始终找不到理想的方法,便又跑回来自己研究。他在竹山上建起土窑,水煮火烤,千百次地尝试,甚至花光了积蓄,眼前仍是一片荆棘,找不到出路。谁能想到,一根竹子,看似淡逸平和天然偶得,却有着不甘屈服的灵魂——艺术之路,注定在困境、冒险与突围中前进。
正当俞田彷徨之际,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了上海嘉定博物馆的张伟忠先生,这位资深的竹艺研究人士告诉俞田,处理材料的方法有十多种,最好的方法是自然淘汰,但wLzaZPNGokjJYp+tnkFSYf+50ReCxAy0W3vmDdcACFw=很残酷。最终,俞田决定顺从美学旨意,顺从自然法则,选择了最接近天然,但也是最艰难繁复的淘汰法。
那一年,他采挖了4000个竹根,为了晾晒,每天在家和晒场间来回搬动,全家人像西西弗一样,日复一日重复做这件事。整整一年,除了阳光,俞田和竹根还承受了无数道目光的炙烤——常人无法理解这种傻气与癫狂。终于,98个竹根完成了向死而生的蜕变。4000:98!比玉石还珍贵。那一刻,“活过来”的俞田不禁有种“一将终成万骨枯”的慨然,也领悟到张伟忠所说的“残酷”。
三
每年冬至一过,俞田就会进山。
“一九二九,泄水不流,三九四九,冻破捣臼”。大寒时节的江南,一年中最冷的时候。西北风长驱直入,凛冽刺骨。群山深处,竹林在劲风中起伏流荡,犹如一汪寒潭。俞田顶风冒雪地在竹林中穿行,寻觅最适合的那株竹。嵊州是产竹的黄金地带,有着适合竹刻雕的上好材料,但地块稀少。“看山看水看风看土看天象,看竹子大小年。”俞田像个堪舆大师,在山水间跋涉。刚开始时,一整天都是徒劳。
隆冬的竹子,气场更强大。一株自成一帧风景,自成一个舍卫国,自成一个给孤独园。深深浅浅的幽妙绿色,诉说着年轮之谜。初生之毛竹,竿色油绿,有细密软毛,仿若有丝绒的质感;第二年细毛尽褪,竿色青绿,竹节下出现一道银白色粉环;第三年竿皮呈黄绿,节下粉环转为灰黑并渐至消失;第四年以后,竿上渐生雅灰粉末,皮色变黄;到了七年以上,表皮就变为老黄色。竹根雕刻最佳竹龄在五到七年,竹片刻材在三到五年为佳,做竹家具料则以七年上老竹为好。各种用度的竹材,不仅对时间的要求不同,对土壤和采光的要求也不一。“一根竹子,取上不取下,取下不取上,根节取用各不相同。”“做竹雕的竹还必须远避尘世、远离村庄,一旦林中有鸡鸭的粪便,便会影响竹子的品质。”像老农耕作,采料是门顺应天时地利的学问。
“秋冬选竹,隆冬伐竹。”入冬后的竹,竹肌敛缩,质地紧密。俞田挑选好无裂、无阴皮、无虫蛀的;粗细厚薄、节间长短,竹根形态、密度硬度等适宜的楠竹,在上面做好标记,就去请当地的老农挖。一根根竹子赶在立春前,带着使命被运往山脚。
经过翻山越岭的寻觅、采选、挖掘,紧接着是复杂严苛的处理。采伐下来的竹子,要及时处理,不然会“闷”坏。清洗、去根、挑选,12小时以上的水煮,然后静置室内,经见光不见水的四季温养。晒一年,藏两年,竹子去除燥湿之气,变得绵糯。直到第四年经再次遴选,方可用于雕刻。此时,一根竹子汇聚了金木水火土,它在抱缩收敛中藏起往昔的春秋,回归本和,一如人生五行,尽在其味。
特制的玻璃房里,摊晾着大小不一的竹根、竹节、竹片,正在和光同尘地蜕变着自己。
“其实几年下来,存下来的料,我一个人做的话这辈子都做不完了,但是不去走一遭,心里便空落落地发慌。”俞田习惯了每年上山,这是自然的馈赠,他要以最虔诚的姿态去迎接。在无数次交流中,他读懂了竹子的歌吟,懂得了尊重。他最大程度地保持竹材本真,不让任何添加剂破坏竹子的颜色、纹理、质地。竹材干净、细腻、柔滑、润糯、透亮。摸着它的肌理、体温,感受它的时间、温度、硬度、韧度,隐隐有美玉的光华。竹子静下来,物成为物本身,沉淀为时间的形式。
竹雕是雅玩之物,能砥砺其志,修洁其身。俞田说:“我做的是良心活。不管是进博物馆,进文人雅室还是自己留存,我都要对我作品的品质负责。”俞田对竹材处理形成了独门手法。竹雕的价值除了工艺本身,还有材质的金贵,治竹本身就是创作的一部分。物的品质需要由人的品德来保证。有人说,品是趣味和审美,德是态度和操守。俞田自有艺术家的诚恳和尊严。即便收藏下来的材料,俞田还要再次精选。这些年,他的作品常被市场上模仿,但除了形似神不似的工艺外,材质是难以超越的差别。
握刀为犁,耕耘竹上。一件竹刻雕作品创作问世,少一个月,长则数年。一刀一刀,一厘一寸。饱含着沉迷艺术的无悔,抵御诱惑的坚定。身怀一腔忘我的热爱,俞田有难得一见的纯粹,他的作品气息独特。2008年开始,俞田的竹根雕作品连续四届入围中国嘉德现当代雕刻艺术专场拍卖,皆以不菲的价格成交。上海博物馆专门跟拍了一部纪录片存放于博物馆内,以作为今后研究竹刻工艺的重要资料。“一年只能做几件作品,都被预订一空,身边根本留不下好东西。”俞田说。他的创作整体保持在从容的状态,严谨自律之下,难觅失准之作。他希望平心静气、不急不躁地把作品做到趋近完美,而不是去追求多快好省的利益极限。俞田心境淡泊,一生中能雕刻的终究有限,他更在意从中获得的乐趣。随着作品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俞田开始思考,无论是治竹还是雕刻,能为后人留下什么?
竹雕细活精工,太磨砺人了。几年来,俞田带过一些徒弟,但一些人坚持不了就半途而废了。俞田说:“学竹雕者不仅要有天赋,肯吃苦,更要心思慎密,耐得住寂寞。”市场的潮汐、环境的改变、观念的更新,没有可观的物质回报,还有几个人愿意沉下心来,默默地研习一门古老的手艺?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以竹言志。竹艺之路,除了以热爱为底色,当有此不移不屈的古典精神。
四
满室的竹料,部位不同,长短不一,年岁参差,出生地也不一。
大画案上,一排排,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刀具,房间里若有似无的清淡竹香,飘忽不定。
俞田坐在工作台前,慢慢举起那双劲健的手,抄起各式工具,将他们混沌的面目一一凿开,或衣袂飘飘、发髻高盘,或怒目金刚,力拔山兮,或小如蝼蚁,灵动巧妙……俞田将自己的心住进竹子里,他在里面目睹万物生动。
万物都在竹子里,在蠢蠢欲动,或作展翅欲飞,或作静默端庄,或作遗世独立,或作红尘热恋……一双手一把刀,从里面找出存在的物的形象——所有的巧夺天工只是把藏在里面的东西找出来而已。哲学、神学、美学不是虚无的概念,它有时候具体到一个造型艺术最细部——眉、眼、手、发丝、羽翼,让你在与它的对话中体验传达的意境。
竹雕多是小器,但大小只是空间形式,物质形制而已。一器之微,往往穷工极巧,精雕细琢。比之根艺随物赋形的雕刻方式,竹雕似乎多了自由度。对比度拉开,空间感增强,体现了高度概括的艺术造型能力,俞田称之为“面面不到面面到”。小形态、小丘壑,给人的不是惊呼震撼,而是暗暗叫绝,细细把玩。壶中藏日月,芥子纳须弥。一个艺术家在小的空间上构筑、表现,要延展出言外的意境,需要技法的力量、审美的涵养、表达的分寸,才能使人感受凝练之美,小中见大的意境。“有限的空间里有无限的想象”。竹雕的表达不是直白的,而是含蓄、点到为止。那些涓涓不绝的悠长意味,如丝如缕的幽微之美,无所谓震撼震惊,似乎寻常之至;但一颦一笑,一顾一盼,皆涵蓄有味。
周晓枫说:“艺术家犹如小神,他创造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彼岸世界,让我们信任、沉迷且向往。”创作一如其人,天赋、学识、修养、审美等的厚积,使俞田的创作在顺应竹子的本性和肌理的同时,内容和形式上更强调自我,多有超现实的神性表达。竹子的圣洁,人们想到神的面容。俞田对神、佛的具象或者接引,不在庙堂上俯视,不需要顶礼膜拜,而在表达志趣禅理,可以陪伴左右,无声教诲。作品《和合二仙》,气韵流畅,和谐生动,从衣袂的流纹到荷叶的根茎,每一根线条都显得宁静亲和。《哼哈二将》夸张了脸部,鼓目阔口,曲线格外饱满生动,张扬而庄重。神佛本无相,以众生为相。俞田对门神的多种表达,就体现了这种禅理哲思——一手拿钥,一手拎匙,只有人物轮廓,没有面相,暗讽进门不讲情面,惟有拿“孝敬”叩门的世故。或作孩童状,天真懵懂,表达出门神对世界的好奇、无畏和探求。
俞田刀下的美人风仪远离了木气、匠气,干净温雅。比如《琴棋书画》,仕女们高髻云鬟,姿态悠然,裙袍曳地,疏朗娴静,仅仅借了那么点“仙气”,味道就出来了。《贵妃》则形美而悦目,脂润肌满,气韵生动,风仪款款。《谆谆教导》俞田用一种精致、优雅的情感支撑起一个饱满的视觉世界,用最细腻的笔调将母爱表达得丝丝入扣。母亲俯首的温柔和稚儿仰望的孺慕,母子之间流动着温馨高尚的乐感,让人想起安东·德沃夏克的《母亲教我的歌》,心灵与之共鸣。
俞田观察细微,表达上也不会粗枝大叶,在细微的笔调中流露实在的内容——细节总会在人们耐心把玩时显示出充分的力量,满足人们探魅的需求。例如:笔筒上的蚂蚁,形体饱满,纤足毕现,每一只唯美得像精灵,小而微的躯体里蕴藏着巨大的灵魂,蚁否?人否?一种寓意在笔筒上交融流转,给人无穷的联想。这种雅趣天成,让文字贫弱。
俞田刻画民间艺人,吹唢呐,打鼓,汉子们袒胸露腹、发丝飞扬,激情澎湃,根须缕缕,充满玄机,只有深谙其美的人才能轻车熟路手到擒来,解读得亦庄亦谐,惟妙惟肖。
《逍遥游》,当一个古代的老者卧骑着青牛,牛背上挂着一壶古代的酒,缓缓而来,慵懒恣意,我们已经在想象,从何处来,到何处去?《鹅司令》,稚童高举竹梢,两只引颈曲项、追逐嬉戏的大白鹅,画面率性天真,喜庆可爱;岁月如流,童年如歌。《纳凉》,一张竹椅,一把蒲扇,瞌睡的奶奶——当一个人,被庞大的日常细节所淹,眯眼小憩是个惬意的顿号,这就是生活的味道。《再来二两》,一张酒桌,三两人生,不见陈腐,世故人情尽在其中。俞田说:“一件优秀的竹雕作品,雕刻之妙远非全部,器形、线条、比例、口缘也是关键的一环,这些是审美愉悦的来源,也是用心着力之处。”传统的民俗题材很容易油滑流俗,俞田的造型却始终意趣盎然,意象超拔。
当一截竹根变成了人,就变成了《两小无猜》“投我以木瓜”的天真,变成了《新嫁娘》的甜蜜,变成了《狗眼看人低》的市侩,变成《孔乙己》的耿介,变成了《磨剪刀》的沧桑……“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这另一棵是想象。竹雕还考量品鉴人的修养。”与俞田交流,颇见知识的积累和领悟的慧心。他优游不迫地表达着对生活、世象的观察和思考,使这项传统艺术呈现出独特的东方美学神韵。他的作品屡获国内大奖,2007年作为中国珍宝走出国门赴墨西哥等国巡回展出。
这几年俞田不断地游走,山西,陕西、西藏、福建、四川,吉林、辽宁、甘肃……莫高窟、云冈、龙门、麦积山等地的石窟,乐山、卢舍那大佛,霍去病墓前的石雕,西藏的唐卡,山西浮山的剪纸……一路走一路看,跟当地的手艺人、文化人、修道人、普通的老百姓交流。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一样重要,深入地理物候,百样人生,能拓宽我们的感知空间。华夏大地上这些丰富的文化宝藏给俞田无限的滋养,无论是雕、刻、剪、画……都带给他无限的感动。民间多奇才。很多地方,几十年上百年的技艺经验凝练成独门“口诀”,以家庭、家族的方式一代代传承。越深入,越觉深邃博大。中国人讲究走“心”,以心换心,俞田将内心的感悟和心境体现在创作上,意蕴更丰富,气息更平和。
秀逸、清雅、率真、醇和、端庄、诙谐、圆熟、爽利……这么多美,都是仁智之见。俞田的竹刻雕作品,清新自然,拙朴中透着灵气,圆润中窥见锋芒。无论端庄典雅还是清新烂漫,法度严谨还是恣意汪洋,都表现出一种自在的生趣和诗意,体现出一种竹的精气神。他身上有一种艺术家的静气和痴狂。除了外出游学和朋友聚会,他就窝在工作室里雕刻、画画、雕塑、陶艺。他的创作状态常常是“忘我式”“入定式”的,进入“我就是竹,竹就是我”与竹同频共振的境界。俞田认为在竹片上“刻”,是修行的方式,平和、安静、内敛、优雅。在竹根上“雕”,是情感的表达,一斧一凿,遒劲而酣畅。每一步他都在修炼自身。他揣摩汉画像砖、魏晋造像,也阅读西方美学,罗丹、贝尼尼、摩尔的雕塑,阿里的油画,基弗的当代艺术等。在雕、刻、塑中不断调整、修补、更替,推陈出新,将传统的雕刻技法融合雕塑、陶艺等手法,丰富、发展和创新了竹根圆雕的造型语言,开了现代竹根圆雕艺术的先河,具有强烈的美感和现代风格,极富江南雅澹之韵,尤其是竹根圆雕人物的创作,技简意周,风雅入骨,自成一派。
罗丹说:“雕塑的静止,其实是对永恒的谦逊表达。”所有的叙事并不宏大,却圆润通透,每一次的雕凿并不猛烈,却深邃锋利。俞田是最懂竹子的人,他们“相濡以沫”,彼此气息交缠,意韵融合。历经时间和水火,涅槃而来的竹子,清新润糯,如婴儿的肌肤。俞田的慧心领悟、玄机解读,让其以另一种形态诞生。像春天的一场约会,无数风物都在赶来的路上。
写到这里,我不禁也想像俞田一样,踏看一下生长出这棵瑰丽的竹雕之花的土壤。两千多年建城史的嵊州,古称剡,有许多声名赫赫的文化遗迹岿然故我,默默地显示着这一方山水人文辞尊居卑的富丽。中国最早的雕塑家戴逵就曾隐居剡中。戴逵是中国美术史上冠绝古今的人物,《世说新语·巧艺》《历代名画记》上盛赞他“词美书精,器度巧绝”“善图圣贤,百工所范”。此人“幼有巧思,聪悟博学”,堪称神童,长大后更是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声名远播。东晋的一个雪夜,王子猷来访戴逵,为中国文学史贡献了一个“乘兴而来”的成语。戴逵品性高洁,性情放达,是极具创造力的艺术家,他在雕塑上的改革,使佛教造像有了审美的感动力。
戴逵以丰沛的才情,充盈的想象力,以自身作文本将这块土地点化出绚烂的艺术光辉。他留下的精神浆汁,随时间不停流淌,喂哺了一代又一代后人。滋生了根雕、竹编、泥塑、紫砂等民间工艺,让嵊州这片土地更加深情而锦绣。但任何创作状态映衬着时代,许多非遗传承属于“慢”生活,难免受到时代节奏和商业潮汐的冲击和淘洗。产品可以量化,但艺术的生动还在于无数次抚摸下的灵性。我想起《竹人录》里的故事:庄绶纶年四十余不娶,绝无艳冶之好,偏偏喜欢竹刻的美人。正是这一生的钟情,这种高贵的孤独,才让一个创作者穿越平凡,抵达极境。传承,不仅是技艺还有精神。
当俞田一千次、一万次拿起刻刀,挥起凿子的时候,他也就成了一根瘦劲孤高的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