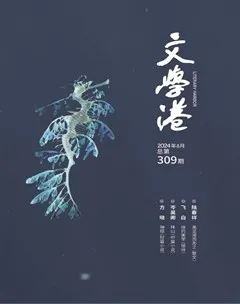煤油灯下
2024-08-28但及
1
墙朝东,发黄的墙上都是奖状,花花绿绿,占据了一堵墙的大部。
这是我的奖状,属于我的一面墙。逢年过节,家里会来许多客人,他们坐在八仙桌旁,谈天论地。八仙桌临墙,客人们抬头便见,要不看见也不行。奖状大部分是小学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或学习积极分子。别人总会说,哇,这么多奖状,厉害!我自豪、骄傲、沾沾自喜,内心无限小风光。
小学就读五泾完小,初中则进了公社中学,名称叫八泉中学。
中学在一个叫堰头的村庄旁,集镇后面,被成片的田野包围。每天我背着书包,穿着我妈做的蓝色布鞋,晃荡着进,又晃荡着出。校区开放,只有两排房子,前排两间灰色洋瓦矮矮的平房,我们初一就在那。贴近泥地操场,一跑,灰尘腾得老高。南边是桑园,绿油油的桑叶从窗前探进枝头,阳光也跟着落在我们脸上。北面一排是新房,两层,水泥结构。底层是初二,二楼便是初三。
读初一是1976年下半年,这一年悲天恸地,国家也经历事变。我们一会儿悲痛,一会儿喜悦,像过山车一样。学校松松垮垮,自由,放养,像缺了魂一样。学工,学农,拾稻穗,听忆苦思甜,吃苦大仇深的窝窝头。读书无用论蔓延,读书成了一场游戏,我们在田野里追逐与奔跑,时不时还会打上一架,弄得鼻青脸肿。放学铃声大作后,我们夺门而出,一哄而散。捉青蛙、泥鳅,在泥地或河水里漫游,书包早已扔得老远,留下一片空荡与寂寞的操场。
缺乏管理就意味着放纵,放纵就是自由。就像一群散养的羊,我们想干啥就干啥,犹如出入无人之境。
这种情状到1977年骤然大变。突然恢复高考,如同宁静的水池里扔进了一块大石头,浪花不绝,涟漪漫溢。知识在一夜间变得重要起来,甚至成了宠儿。我们还沉浸在那片自由与散漫里,无拘无束,突然发现不对劲了。风向变了,气氛变了,学校也好似从梦中醒来。
初二,换了班主任,一个叫钱绍增的老师来了。杭州人,下乡知青,成了我们的老师。他三十余岁,未婚,脸是绷着的,似乎从来没个笑容。这样一位冷冰冰的人来管理我们,我的第一反应是排斥。读书第一次成负担了。
他一来,就摸底。他教数学,就考数学。三大张,还有加试题,共一百二十分。
试卷发下,摆在面前,我一瞄,近乎崩溃。一道道的题目分明是一道道沟和一片片坎。薄薄的纸张里藏着一个未知的世界,我失魂,僵硬,空白。凝视题目,越看越陌生,连里面的字母都不认识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它好似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仿佛走进了迷宫,这条路不通,那条路更不通,我迷失其中,找不到一处出口。
抬头看同学,一个个在低头沉思,或闷头答题。空白越来越大,越来越膨胀,连身子都虚空了。我胡乱地答着题,汗水翻涌,连后背都是水。惊慌,手足无措,我盼着时间快快过去,但时间好似停滞了一般。教室里寂静到窒息,偶尔那翻动试卷的沙沙声,也异样,可怕至极。
考完,逃出教室。次日,校园晴朗,但望出去的太阳是斜的,连吸进肺里的空气也带着紧张和干涩。校园以一种千般陌生的姿态迎接我,更多的像是拒绝我。钱老师在走廊上轻松地走,还与其他老师说笑。我想不至于太坏,又不敢直视他,怕他叫我名字,怕他把我拎到面前。我甚至有些天真,想这一切可能并不存在,压根就没考过试,考试是虚拟的。然而,马上又清醒了,一天的心跳都在加速,撞在胸口。
成绩出来了。当试卷轻轻地落下,平躺在课桌上,我即刻沉入了黑暗。
只得了三分。是的,没有看错,就是三分。五味杂陈,更多的是怒火中烧,想撕碎那张纸,连邻桌也不给看,然而我又不能撕。我把分数藏在底下,用书本作挡箭牌。以前的荣耀、奖状都成了讽刺,仿佛跌入一个冰窟,除了冷,还是冷。钱老师在分析试题,我什么也没听进去。低头,看自己的鼻尖,那个小小的尖点,还有底下已模糊一片的试卷。
一百二十分的题目,只做对一题因式分解。一切就像在梦游。
2
班上通知,每个人,必须住校。
住校是为了节约时间,时间最宝贵,有的同学离家远,来回要花两三个小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发挥和扩展时间,钱老师决定我们班统统住校。这是个创举,开风气之先,在全校历史上从未有过。
学校没宿舍。只有一间仓库,堆满东西的杂货间,被腾了出来。男同学住仓库,女同学安排进了附近的农家。
生活从此改变。透过操场,能看到稻田后面呈长条状的集镇,那里有机电站、茧站、竹器社和卫生院。我爷爷在卫生院工作,我成了特例,被允许去卫生院用餐。卫生院距离学校几百米,我步行去用餐,晚上则必须住校。其他同学搭伙食堂,与他们豆腐、青菜、咸菜等简陋的饭菜相比,我已属幸运。
面对一种不熟悉的生活,我内心极度排斥。这一次的三分,让我的脸丢得精光。我甚至没有打听其他同学的得分,也没脸问。试卷团成一团,最后扔了,我不敢让它暴露在阳光里。我躲在内心的阴暗与失落里。
“当半年前他宣布我们班上的所有人一律必须住校时,我们所有人的欢笑就被凝固了。我们就睡在食堂边的一间平房里,那里充满了汗味、臭味和尿骚味,我们近三十个男生拥挤在一起。在我们的房间里压根儿没有床可言,我们把稻草均匀地铺在地上,然后往上面放几条大席子……然而有一天半夜王青突然叫了起来,那时我们都已经睡了,只有他还在被子里复习和预习。啊——我们只听到这尖锐的一声,等我们一片混乱地起来时,王青已经滚到人堆里。蜈蚣,蜈蚣,他在大声地喊叫。于是我们重新开灯,检查床下的情况,这叫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们在灰暗的灯光下仔细一查,竟然发现我们的地铺下隐藏了四条蜈蚣。”
这是我2002年发表的小说《七月的河》里描写的情景。小说就是以当年我们住校作为素材。我们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稻草打底,上面铺席子和棉被……席子底下有蜈蚣,蜈蚣弯曲着身子,在草席上大摇大摆。迎接它们的当然是死亡,然而会不会有更多的蜈蚣从墙角处、门缝里、窗台上钻进来呢?我们人心惶惶。第二天,学校拿来了石灰,沿墙角一路撒下去,又均匀地分布到了我们草席底下。这也是学校唯一能办到的事。
我们班和钱老师成了怪胎,二十四小时霸占学校。为了对付考试,为了考得更好,我们华山一条路。
笔在纸上“沙沙”地响。开始做练习,一遍遍地做。数学是主角,大部分练习都是数学,偶尔也会分给其他的科目。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试卷,本地的、外地的,一股脑儿全做。试卷太多,老师刻蜡纸来不及,学生就上手。我的字写得端正,常被叫去刻蜡纸。笔尖是钢做的,坚硬,蜡纸底下是钢板,两个硬度相碰,蜡子就像刨花一样一缕缕刮落。我像赎罪一样刻着蜡纸,每次刻蜡纸,都会想到那该死的三分,它像个耻辱柱一样无形地横着,也像警钟无声响彻在我脑畔。
试卷就像个百变女郞。试题会变出许多花样来,有端庄的,有妩媚的,也有板着大脸的,更有冷冰冰的。全班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在题海里摸爬滚打。此时,全国第一批文革后的大学生已经诞生,他们登上了报纸,在全国人民的期待里走向神圣的殿堂。他们成了我们的榜样、追赶的目标。
课余,我有片刻的休憩,就是从学校走到卫生院那短暂的时光。我会沿着一条小河走。
河边被草丛包围,还有片片桑园点缀其中,还路过一个机埠。机埠时常会有哗哗的水在翻滚,吐着泡沫被抽上来,流进延伸开去的水渠,再分布给各处农田。站在那,看翻涌的一团团水花,水花似花非花,挤成一团,瞬间又分裂成无数碎沫子。它就像我的内心。水在翻,在卷,好似也裹挟了我的内心,我不知道如何摆脱眼前的这一切。大量的试卷、枯燥的训练、一成不变的节奏,我被题海湮没,被各种公式围困和肢解。我要逃出来,必须要逃出来,从那困境与封闭里解放出来,然而我又无能为力。没有别的办法,我矛盾,彷徨,觉得自己就像那团水,暴躁,急烈,又无可奈何。
到卫生院是我唯一解脱的机会。诊所里都是人,阳光跟着门进来,照在灰色的水泥地皮和诊所的桌椅上,消毒水的气味好像也融进了那缕缕阳光里。食堂缩在围墙边上,狭小,阴暗,有个老虎灶,饭菜均是热炒。我拿着爷爷给的饭菜票,挑选我需要的。院子里有口井,饭后,我会打上一桶凉凉的水,井水清冽,映出我那张忧郁的脸。把碗筷洗干净,归位,再返程。我重复着这样单调的生活,不能回家,偶尔会与爷爷说上几句。当天色渐渐暗下来时,不情愿的脚步又在召唤我重返学校,重新去面对这堆奇怪的、枯燥的数字。
路上,会偶遇小玩伴,他们没有我这般折磨,依然在大自然里疯天疯地。我有点羡慕他们,但又退不回他们的生活。我仿佛悬在空中。
3
断电,是家常便饭。上一秒好好的,光簇拥着我们,下一秒就变了,我们在黑暗里头碰头、脚碰脚了。
班里购了煤油灯,两人一台,也即每张桌子一台。老式的煤油灯,弯曲的油瓶,表皮还有花纹图案。一根灯芯从里面爬上来,外面有个薄薄的玻璃罩子。平时,煤油灯贴在教室后排,一长列,列队检阅一般。边上有个铁皮桶,盛煤油,铁壳皮上积了层灰。刚开始,能闻到煤油味,时浓时淡,飘在空中和书本里。时间一长,气味好像被教室里的人气给吞了,啥也闻不到了。
煤油灯就是发电机,我们不怕黑夜,不怕拉电了。一根根小小的灯芯,自己发电,煤油灯灿烂地照亮夜色丛里,照亮班级的每一个边边角角。橘黄的光铺开来,让教室笼上一层陌生和迷离。光柔和,暗淡,连灯下的我们也变得陌生。光是游动的,火舌在微风里晃,望出去的世界有时是摇动的。教室在摇,人也会摇。笔在沙沙地摩擦纸张,光线幽暗、胆怯、闪烁,映出我们一个个变形的头颅。走动时,影子会跟着我们,把我们的身影拖得比自己的身高还长。
教室灯影飘忽,大家都伏在煤油灯下,人声寂静。那日,我的舌头长了疮,疼痛,发苦,且痒。舌头火烧火燎,难受极了,又找不出办法。我取出三角尺,把舌头伸出来,对着煤油灯闪烁的火苗,用尺子一遍遍刮擦那已溃烂的疮。刮擦时会有紧绷,也有一种麻木,仿佛能遮掩掉原先的那个疼……突然觉得,麻木也是一种快感,最好这样一直麻木下去。我告诉自己,坚持,再坚持,但又怕自己坚持不了。
冬天来临,北风呼啸,卷起来撞击门窗。大地在瑟瑟地抖,连窗子好像张着口在打颤。入夜后,二十几个人蜷缩在寢室里,风声在胡乱盘旋,里面却滚成一团,彼此顶撞,又彼此取暖。大伙早忘了蜈蚣,好像根本没存在这么一个毒性的东西。嘻嘻哈哈声弥漫,只有这时,愉快才会稍稍胜过枯燥,愉快战胜压力。一屋子人就是个火炉,会散发出巨大的热量。大家在玩笑声里入睡,说梦话,打鼾,甚至磨牙。寢室包裹在一片片奇怪的声响里。
早上,我们和太阳一起醒来。玻璃上罩了水汽,糊得一大片,看不透外面。大伙排队,食堂的大锅里热气腾腾,底下的老虎灶还闪烁着木炭的光芒。我们用脸盆打热水,蹲在被霜打过的草丛边,一起洗脸或刷牙。混合着牙膏的热水从我们嘴里吐出来,渗入地里,钻进草丛,无声地消失。
霜,白乎乎覆盖大地,近处和远处的植物都被冻得东倒西歪。田野苍茫,霜仿佛也落在我心头,在呻吟,也像在沉睡。
4
钱老师个性冷,沉默,大伙都怕他。
他的身影是个谜,平时会玩失踪,突然间,又如空降般来到教室边缘。只有在寂静时,才能偶尔捕捉到他的脚步声。脚步缓慢,带着节奏,但分明又蕴含着某种强势。声音从走廊深处荡开来,教室连同里面的人都会紧张,大伙的动作、言行、举止瞬间大变。闹腾腾的场景静止,收敛,所有人换上一副面孔:装腔作势,或埋头做作业、看书。钱老师巡视一通,出现,消失,又出现。
他如同后来出现在荧屏上的黑猫警长。
一天晚自修,他的身影出现在光线斑驳的教室。他伸出手,那手指就停在半空,点了三个同学:你,你,还有你,你们三个来一下。他指到了我。这是不祥之兆,有大祸临头之意。或许又考砸了,要挨批了。我们三个,脚步哆嗦,尾随他的背影。我们走到黑暗里,他没有把我们带进走廊尽头的办公室,直接上了黑乎乎的二楼。这是我第一次踏进他的宿舍,床笔挺,被子方方整整,油漆过的棕色水泥地上泛出片片光泽。
桌上摆着一个方形的铁盒子,我们从没见过那玩意儿。
插上电源,里面闪出片片雪花。我们不明白他要干嘛,在猜谜,但谁也猜不出来。他拉出一根线,线很长,戳在空中。当线调到一定位置时,那东西像是突然被唤醒一般,发出了声音,还有斑斑点点的图像。哇,能唱能跳了。我们才明白这个叫电视机,迷你,最小号的电视机。
图像清晰了,是两个人,在里面说相声。
电视就像个小小的迷你窗口,把我们的好奇心折腾着,揪进又揪出。世界变得不可思议,打开一个盒子,另一个世界就诞生了。许多年后,我进嘉兴电视台工作,报到的第一天就想到了那台小小的电视机。或许别人不会相信,踏进电视台时,这种神秘感依然存在,有点梦幻,仿佛那电视不是真的。这样的感觉持久了很久。
事后知道,钱老师是为奖励,才给我们看那稀罕的电视。前些天,我刻了许多蜡纸,还用滚桶机油印了众多试卷,油墨味弥漫鼻孔。钢做的蜡笔在蜡纸上蹦跳,我食指的皮肤都刻得下陷了。这会儿,他给我们放小假,看上一眼电视,算是犒劳。或许,他还看到了我身上的潜力,从三分起步,现在的数学成绩已明显改观。像是开窍了,面对数学题已不是一团乱麻。他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我,一个有别于过去,改过自新,且一点点走向既定目标的我。
犒劳的时间很短,很快,新的要求来了。他要求我们再努力一把,争取考上中专。考上中专与考上大学一样,都能改变我们的命运。这是贫穷中的一顿大餐,旱后的一场及时雨。从房间出来,我们恍惚、兴奋,同时又觉得很遥远,很飘渺。
能歌善舞的电视成了钱老师的招牌。谁能考好,就有奖励,奖励到他房间看电视。要看上那小东西一眼,不是件容易的事。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改变了这一切。那天,正在上课,火焰突然蹿起,噼啪作响,在空中卷起又扩散。钱老师的宿舍出事了。乌烟笼罩整个学校,我们从教室涌出,加入扑火队伍。大伙打水,传递,用水扑火。火势凶猛,已蹿至屋顶,钱老师的宿舍化成了灰烬,那台宝贵的电视机也一起变成了炭末子。
我们无比失落,怀念电视,怀念那片曾经的小小温馨。钱老师再也变不出电视了。
5
1978年第1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篇震动世人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作者徐迟,介绍了我国数学家陈景润如何求证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过程。一夜之间,全国知晓,报刊广播都在几何级地传播,陈景润和他的数学成了世人议论的焦点。
数学,第一次以这样的面貌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如此近距离地成为人们日常的话题。“向陈景润学习”的口号响遍大江南北。
钱老师没有因火灾而放松对我们的监管,他依然严格,寸步不离。他说数学就是如此,就是这般的重要。他引导我们打开数学之门,他成了引导风潮与时尚的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这样鼓励我们。我们热血,激昂,陈景润就是我们追逐的目标,我们要像他那样,做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我们蠢蠢欲动。
练习更多了,成了狂轰滥炸。我们被数学题包围,也成了数学的一部分,几乎也成了数字。
考,考,考。试卷一张张地发下来,习题一道道被解开或解不开。考,考,考。通过大量的训练,练就熟能生巧的技法。考,考,考。考试成了家常便饭,三天一小考,一周一大考,渐渐地,我从畏惧中走出来。考试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怕考试了。有考试的日子才是真正的日子,没有考试的日子变得慵懒,变得无趣。
如同一只只好斗的公鸡,迎接挑战,昂头,鸡冠充血,浑身充满力量。我们勇敢,好强,展开决斗的架势。
1979年的初夏,一条挂机船卷起浪花,我们全班一股脑儿挤在一条木船上。挂机船就像不可测的命运,奋力把我们拉离故乡。飘摇的船把我们载到了石门,我们迎来了会考这个日子。石门是个老镇,紧贴京杭大运河,处吴越分界之地。面对石门中学那陌生的教室,面对长满矮草的操场以及白晃晃的墙壁,我成了自信与不安的混合物。担心卷子发下来,头脑空白,担心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再度重演。
数学试卷发到手上,我便胸有成竹了。会,都会,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自信第一次以对比的方式呈现,内心轻松,且伴有一种喜悦。笔飞快落下,在纸上赛起跑,我想跑得快,想跑得远。
果真,那挂机船把我们拉到了远方。我们这个班,绝大多数进了高中,还有两人进了中专。
钱老师声名鹊起,他的题海战术得到了检验,把众多学生送入了高一级学校。他成了当地的名人。
6
“我没有年龄,但我有刻度尺
有时钟、有一日三餐、有日夜的观念
它们既在催生又在摧毁
几十年前没有我
几十年以后照样没有
恐惧来得比我自己高三寸
只要有数学,人们就能降服它。”
这是诗人、我的朋友李心释的诗——《数学》。数学能降伏时间这个妖怪,同样也能安抚人的内心。我深有同感。
从此,数学以一种美好在我的生活中存在,它代替了孱弱的我,成了自信的代名词。
1981年7月,我在桐乡二中参加高考。铃声响起,整个校园一片寂静。这是一种新奇的静,与平时迵异。两名监考老师神情凝重,轻轻打开层层封条包裹着的试卷。当数学试卷发下来时,我闭目凝神。我在放松自己,也在暗示自己。
试卷放到了桌上,试卷朝下,像谜团一样放在我眼前。窗外,骄阳正艳,树叶静止,我屏住呼吸,瞄了一眼眼前的那片白色。白色在弥漫,占领我整个眼帘。当第二遍铃声响起时,我用颤抖的手掀开这层薄薄的纸。三分那片阴暗又如阴霾般从脑中闪过,但前后一阅,便滋生大喜。就像站在跳高场上,面对一个刻度,这是一个平时能轻松越过的高度。
高中时光,数学不再是我的拦路虎,在所有的科目里,我的数学成绩最稳定。我找到了数学的路径,看到数字会涌上亲切感,那些字符很美好,像音乐一样流淌在我的前后左右。长久的接触与融入,能让我一探内在的奥妙与机理。我甚至觉得数学蕴含了一种诗意,里面的未知代表了一种高等的旋律。高一年级,我还担任了的班级数学课代表。这个代表,包含了某种资历,无以言说着我与数学间的关系。每天,我都会把同学的作业本收齐,交到数学教研室。数学老师是个中年人,近四十,精干,朴实。他喜欢我,有时会亲昵地摸我的头。他那间办公室,我太熟悉了,大圆规和三角尺醒目地挂在墙上,仿佛整个大地可以清晰地丈量,仿佛全世界都可以被纳入法则进行运算。
这次高考,我的数学几乎满分,为我的高考总分添分太多。感恩数学,数学为我推开了一扇门,并让我的命运发生改变。
然而,命运却在此又荡了开去,我与数学的故事竟戛然而止。
大学,我读的是中文专业,从此便与数学绝缘了。再也没有机会翻开数学书,再也没有了集训和大规模的做题与换算。坐在文科教室,阅读世界名著,剖开一个个字句,沉浸在诗歌带来的遐想与意境中,我突然涌上一种荒谬感。这些年,拼命强攻数学,与数学建立起了感情,甚至有了某种亲近与亲密。然而,我们竟然分家、散伙了……时光与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让时光重返我的家乡五泾,重返那只有两幢房子的八泉中学。那里正在进行一场作文竞赛。我们被要求在一堂课的时间里完成一篇竞赛作文。这次竞赛中,我第一次应用了虚构的手法,写了我们的班长肖炳兴。班长力挽狂澜,挺身而出,把班里的不正之风给压了下去。名字是真实的,情节却是虚构的,这可以称之为我的第一篇小说。现在再看这篇作文,肯定惨不忍睹,做作,矫情,不自然。然而,在当时,我第一次体会到虚构的乐趣,写的时候感觉后面被一股力量托着,人物、语言和情景会自然流淌出来。开了一个头,后面的情节就会自动续上了,像流水在喷涌。
虚构的乐趣以及虚构产生出来的那份张力竟如此巨大。我塑造了一个人物形象。这篇作文获得了全校一等奖。
作文竞赛无意间撞开了我的兴趣,开始拨动我的内在与外在。仿佛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它既是实的,也是虚的。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它的实比现实更实,它的虚比梦境更虚……那里有一股强大到令我窒息的引力。阅读文学作品,我会入迷,会沉浸其中。与人谈起文学作品时,内心会涌起波涛,裹挟其中,不能自拔。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民文学潮,中文系的学生被狂热裹挟,恨不得一夜间写出传世作品。我就是在那时踏入文学界的。当我投入其中时,常常会有一种恍惚,仿佛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着我超越现实。我既是当事人,又是局外人。这是一种绝妙的体验,文学把我带进的是一个奇异又陌生的世界。毕业后,我历经中学教师、国企团委书记、报社记者、电视编导,一次次偏离航道,又一次次奇怪地纠正。有时,我从事与文字毫无关系的工作,但那份热爱总在,就躲在角落,默默地注视我。它甚至不是静止的,燃烧起来的火苗会让我热血沸腾,感到一种前所未有过的充实与满足。
我写作,我发表。作品越来越多,最后我进了文学院,成了一名专职作家。
与数学那段短暂的缘分,既残酷,又温馨。它扶着我,让我从冰凉与冷漠里寻找到温度与热量,甚至还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当一道道题目解开时,眉宇会舒展,就像我把窗帘撩起了一角,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它不排斥我,接纳了我,还想让我成为其中的一员。然而,我明白终究不属于那里。那只是我的一块临时栖息地,与它还是没有缘分。
惠特曼的《回答者之歌》中有这样几句:“每一个存在自有它的特色,每一件事物自有特色和语言。他把所有语言化为自己的,并把它给予人们,人人进行转化,人人也转化自己。”
我与数学就仿佛是一场包办婚姻,而与文学,则成了一场广阔又无边的自由恋爱。
7
钱老师八十几岁了。过些时间,我们会通上一会电话,聊聊家常。
每次他都会问我,最近写了什么文学作品,并叮嘱,有新书出来一定要寄给他。他学生遍地,世界各地都有,有的成了学者、科学家,也有资产几十亿的企业家。我听说他前几年还在给学生上数学课。都这个年纪了,还那么认真,我总记得他给我们看那小小电视的一幕。那份鼓励是甜蜜的,是一个严厉老师的人性化教育的一部分。
最近,我做了几个梦,这些梦都不约而同地与数学有关。梦中的我走进了考场。试卷发下来,我一翻,头开裂了。数学题,密密麻麻,一道也答不出来。空白又出现了,无边无际,无处着落。我就这样坐着,背上全是汗。再次被抛到一片虚空之地,谁也救不了我。弗洛依德的《梦的解析》,对梦有详细的解说,或寄寓着什么,暗示着什么。我不知道我这个梦的意图,只觉得自己又被这数学绑架了。
梦中吓出一身虚汗,情有可原,因为那是虚幻的,是想象出来。然而当某一天,我重新拿起初中数学书时,真把自己给吓住了。我翻啊翻,看啊看,如坠梦境,我做不出题目了,如同当年,看不懂,更不会运算。我翻来覆去,努力分辨里面的数字,试图从记忆的深层把它们唤醒。我挣扎,扭曲,但终究徒劳。
忘了,居然全忘了。就像当年考三分时的模样,一筹莫展,如同面对一部天书。世道就是如此,多变,恍惚,又有趣……我宽慰自己,人的大脑容量有限,放下的事物必然会走向遗忘。然而,我终究会责怪自己,仿佛有违道德,抛弃旧爱,另觅了新欢。现在,连旧爱的名字和长相也遗忘了。
今年初夏,回老家五泾,在一个暑气还浓的午后,我去寻访当年中学的旧址。
中学早已搬迁,这里成了幼儿园的一部分,我家的一位戴眼镜的女邻居在里面任教。旧教舍已不复存在,幼儿园色彩鲜艳的墙面很是刺眼。集镇的老房子在远处隐隐约约,近处都是新房,农家宽敞的院子里停满了汽车。我呆立良久,熟悉与陌生混合,过去与现在交织。我依稀能找出当年些许的影子,熟悉源于那些老建筑留下的印迹。在与昏暗的老建筑的对比中,那个梦幻里的中学又登场了。我看到了当年的教学楼,扬起灰尘和青春躁动的操场,充满汗臭和稻草味的小寢室。当然,还有那在夜色里如眼睛般闪烁的煤油灯光。
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正牵手从路边走来,他们可爱、活泼,盯着我这个过路人好奇地张望。岁月在变,一切在变,但作为学校,也有某种不变存在着。这里是我曾经的学习地,也是我的沼泽地,更是我的起飞地。它是我生命里的一个节点,也的确曾改变了我。
蒙田《随想录》中有这样一段话:“一间书房、一座花园、餐桌、睡床、孤独一人、有人相伴、清晨、黄昏,任何时刻都是他学习的机会,任何地方都是他学习的场所……”我仿佛看到了这批幼儿即将成长,也瞧见了我曾经的过去和班级这群同学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