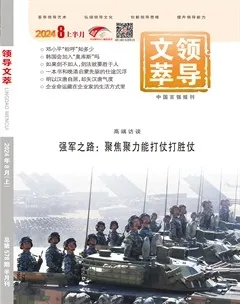在司天监工作是一种什么体验
2024-08-27首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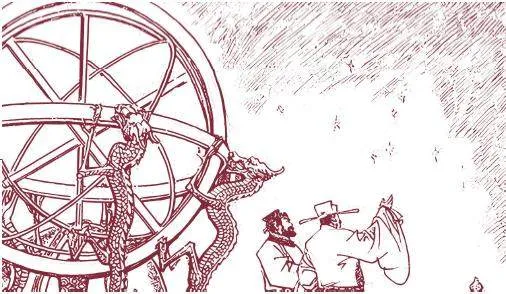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七月二十二日,整个北宋朝廷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原来这天,大臣杨维德进言,说最近天空出现“客星”,这是象征着“国有大贤”的吉兆。请皇上下令,让史馆记录下这桩难得的盛事。宋仁宗见大家这么配合地赞颂自己,当然也是乐不可支,马上准允照办。
所谓客星,就是忽然出现的新天体。按照《宋会要》的记录,这颗客星实则在当年五月就已经现身:“展出东方,守天关,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天关星,即今天我们说的金牛座的一员。有意思的是,就连大白天都能观测到这颗耀眼的客星。一直到一年又十个月后,它才彻底消失。
虽然以天象寓意吉凶的迷信说法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1000年前的这几条天文观测记录,却被现代科学家们挖掘出全新的价值:这是人类记录下的第一次有明确时间的超新星爆发。而它留下的遗迹“蟹状星云”,一直都是被研究最多的太空目标之一。
那么,大张旗鼓向宋仁宗汇报这一神奇天象的杨维德到底是何许人呢?原来,在大中祥符三年(1010),宋真宗曾经命天文官韩显符教授学生使用浑仪之法,杨维德正是其中一员。后来,他还一路做到了司天监春官正(掌司四时及其方之变异)。
司天监,看名字也能猜到,这就是宋代专门负责观测星象的机构,即当时的国家天文台。
宋太宗对于掌握观测天文能力的民间术士,有着极强的防备心理。太平兴国元年(976)十一月,刚登基不久的宋太宗就下达禁令:“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术数者,传送阙下,敢藏匿者弃市,募告者赏钱三十万。”
等于说,太宗试图将全国范围内有天文方向专业知识的人一网成擒,为此不惜开出举报一人即得三十万钱、藏匿者直接处死的旨意。从此以后,民间所藏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其他阴阳书,“限诏到一月送官”。朝廷计划彻底垄断研习天文知识的途径,从而将吉凶祸福的解释权牢牢把控在自己手上。
既然司天监作为国家天文台,朝廷自然会组织为其研发最为精密的观测仪器,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苏颂创制的水运仪象台,也号称是世界最早的天文钟。古代王朝有所谓五德始终论,宋朝自认属于火德,而水又克火,所以宋哲宗还为这座水运仪象台更名为“浑天仪象”。苏颂并非一位专业天文官,而是宋哲宗时期的宰相。所以,虽然水运仪象实际上是许多人共同协作制造的,但有苏颂这样出众的士大夫领衔,其他人的光芒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掩盖了。
宋代的司天监“制”约为20人,其中,监与少监因为官品高,分别为正三品和正四品,不经常设,而是以朝中高官为“提举司天监”等职兼理。此地的官员们并不负责治民理政,而是专掌天文术数。这类以某项技能服务朝廷的职业型人才,被叫作“伎术官”,我们熟悉的御医、御用画师都是同一群体。
可想而知,在官员团队之中,伎术官的地位较低,普遍容易受到轻视,往往不被视作士大夫,但他们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司天官中出现了不少家族世袭的现象。如此说来,司天监岂不是一个“学阀”林立之所。这种垄断性质的机构,因为有恃无恐,难免落入闭门造车、欺上瞒下的结局。
观测天象,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就好像出现日食会被解读为女主临朝、阴盛阳衰一样,倘若在一些敏感时期,司天监上奏发生了什么奇异的天象,那朝廷里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必然争相以此为武器,互相攻击,直指正是因对方乱政,才致使上天示警。
从这个方面讲,司天监的观测结果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着朝廷的安定与否。宋朝在历法上的变动堪称历朝历代之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追求预报日食的准确性。当司天监呈上会发生日食的预测之后,皇帝就要避正殿、减常膳、穿素服、罢歌舞,用一系列方式平息上天的怒火。可想而知,要是预告出错的话,会给朝廷带来多大的尴尬。可如果测得太准,如实报告各种凶象,那也纯粹自寻死路。准和不准之间,对于司天监来说,更多时候是一个人情问题。
堪称最没有底线的案例,发生在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这年五月,司天监称即将有日食,但此后日食却一直没出现。大臣们表示,这并非司天监预报不准,而是因为皇上的德政感动了上天,上天才特地取消了本该发生的日食,“中书奉表称贺”。
不过,倒也不必把古人想象得过于迟钝。宋太宗在打压民间天文学的同时,就意识到了需要设置一个跟司天监并行的机构,作为监督和参照。原本的司天台主簿郑昭晏被宋太宗改任为翰林天文官,在大内侍奉,以备皇帝咨询。这一制度在宋真宗即位后照样继承了下来,并在景德元年(1004)之前发展成了独立于司天监的翰林天文院。
翰林天文院设置于禁宫之中,拥有一套专属的观测仪器,“漏刻、观天台、铜浑仪”都和司天监的配置相同。每晚天文院的官员观测完毕后,要在皇城的城门开启前,将结果呈交。城门开启后,司天监的文书被放行入宫,两份文件一对比,便知天象观测的结果是否足以令人信服。
天文官们也很清楚司天监的观测结果会在朝廷政务中起到政治风向标作用,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这群技术岗的官员,竟然练出了一番察言观色本事。他们会预先准备好多个版本的解说之词,一看形势不对,就立马话锋一转,在这般有意造伪之下,有没有实际观测都并不重要了,反正都是拣好听的话说罢了。
即便如此,司天监与翰林天文院也依旧是皇家眼中自己独有的专利。宋代严禁天文官们私下为臣民占卜,学生以下令三人为一保,互相检举揭发。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