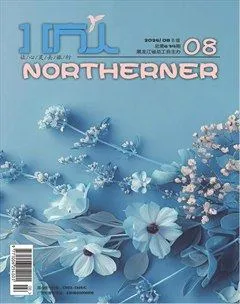眼睛看不见的人,是如何感知空间的
2024-08-22[日]伊藤亚纱
“大冈山果然是‘山’呢”
看不见的人所“见”的空间,和看得见的人用眼睛捕捉到的空间,二者有何区别呢?在与视力障碍者相处的岁月中,某一瞬间我突然弄明白了这个问题。
那是我和木下一起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一天,我准备在我的工作地点——东京工业大学大冈山校区的研究室,对木下进行采访。
我和木下在约好的大冈山站的出口碰了面,穿过十字路口很快就进了学校正门,朝着研究室所在的西九号馆走去。到了一个长约十五米的平缓下坡时,木下说:“大冈山果然是‘山’呢,我们现在正沿着它的斜面往下走吧?”
木下的话令我非常震惊,因为他说的是“山的斜面”。我每天都会经过那里,但对我来说,那不过是一段“坡道”罢了。
在我的认知中,那段路不过是从“起点”大冈山站到“目的地”西九号馆途中的一小部分,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意义上来说,都只是其他空间或道路的一个分节罢了,拐个弯就会忘在脑后。然而木下的描述,更像是在俯瞰整个空间。
对于看得见的人来说,要在脑海中形成那样立体的俯瞰图非常困难。坡道两侧,排列着社团招新的宣传看板。走在学校的路上总会与熟面孔擦肩而过。前方,拥挤的食堂入口映入眼帘。扑面而来的各种信息,夺走了看得见的人们的注意力。要是没注意到这一切,那大概是在看手机。总之,对于坡道上的行人来说,根本没空去想自己正走在何种地形的哪个位置。
没错,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我们的确是“行人”。确定好“通行路线”后,人就像在传送带上一样,在具有方向性的“路”上被运输着。相比起来,木下脑海中的概念更为开放,他就像一名滑雪运动员,可以自由地在宽阔的平面上画下线条。
即使身处物理层面上的同一个位置,人们赋予该位置的意义不同,体验也会截然不同——这便是木下那一句话带给我的震撼。人在物理空间里行走,同时也在脑海中的图像上行走。我和木下肩并肩走下同一段坡道,实际上却行走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也许可以这样说:看不见的人不受“路”的限制。道路,为人们指明前进的方向。虽说每个人的情况各有不同,但看不见的人能够通过回声和盲杖的触感把握道路的宽窄和方向。眼睛可以瞬间从近至远看遍路的全貌,与之相比,凭借声音和触觉所能掌握的范围是有限的。不受路的限制,意味着看不见的人需要加倍小心慎重,但他们也因此摆脱了道路的束缚,拥有更为宏观的视野。
大脑里有富余的空间?
在同行时,全盲的木下获取的信息比我少得多。何止是少,应该说他只获取了两条信息。一条是“大冈山”这个地名,另一条是“双脚感受到的倾斜”。然而,正因获取的信息少,他在理解这些信息时,才能够在脑海中构建眼睛看得见的人无法看见的空间。
对此,木下是这么说的:“可能我的大脑里还有富余的空间吧。看得见的人,大脑会被超市呀、路上的行人等等塞满,而我们的大脑里,很多地方空着。但我也想利用这个空间,所以会尝试将信息和信息联系起来,就形成了那种俯瞰的视角。某种程度上,可能看不见的人才有更多思考的空间呢。不然你一看就知道前面是个坡,转头便忙着欣赏周边的风景、蓝色的天空,还能看见晴空塔……这些就够你忙的了。”
这正是由少量信息产生特殊意义的实例。生活在城市里,我们眼睛捕捉到的信息大多是人造物。大屏幕里映出的偶像们、宣传新产品的招牌、地铁吊环上的广告……这些都是为了被看见而设计出来的,实际上和我们个人没什么关系,也就是说没有“意义”,纯粹是一种信息泛滥,是卷走一切视觉注意力的信息洪流。
确实,在看得见的人的脑海中,几乎没有木下所说的“富余的空间”。
看不见的人则与这种信息洪流无缘。当然,城市里也充斥着各种声音和气味,但木下仍然觉得“大脑里还有富余的空间”。前文中我提到,看不见的人不受“路”的限制,这个“路”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用混凝土或土做成的、字面上的道路,也是比喻意义上的道路。总而言之,是告诉人们“往这里来”、给人指明前进方向的“路”。
是我在利用信息,还是信息在利用我?
人并不是百分百自发地、根据自己的意志行动,很多时候都是不知不觉中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而行动的。
以“靠墙休息”这一行为为例,大多数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想休息而去寻找一面墙,而是看到了一面墙所以想靠上去。这一性质的行为在孩子身上尤为多见,比如“恶作剧”。因为看到了按钮,所以想去按一下;因为看到了台子,所以想要爬上去。隐藏在环境里的各种因素,成了诱发孩子某种行为的开关。
可以说,人的行为或多或少是环境设计出来的。
从一个开关到另一个开关,人就这样被吸引着注意力,眼花缭乱地在环境中移动。指明方向的道路就像环境中画出来的导线,说着“过来,过来吧”,持续引导着人的行为。
比如走进京都的桂离宫,你会发现它甚至连人们该看哪儿都设计好了,处处是引导人们行为的“道路”。实地参观后,我感觉桂离宫就像舞谱一样,从那以后便对它产生了兴趣。
桂离宫里有一条明确的道路,而在城市里,无数条道路纵横延展,其中大部分强烈地刺激着人的欲望。炎炎夏日走在路上,看到路边立着可乐的招牌,就会想喝可乐;看到“今日七折”的标识,便不自觉地走进超市,买一堆不需要的东西。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本就有这些欲望。视觉刺激之下,欲望在我们的体内生成,回过神来,我们已经变成了“带着欲望的人”。
毋庸置疑,正是这样过度的视觉刺激驱动着资本主义体系。否认它并非易事,我也不打算这么做。事实上,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就像提线木偶,很容易就会在这个装置的操控下起舞。
最近,在电脑桌面和手机页面上,类似的触发点越来越多。本想工作,打开电脑后却开始购物……这种事经常发生。我们每天都经历着轻度失忆,已经分不清到底是我们在利用信息,还是信息在利用我们。
(摘自南海出版公司《看见看不见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