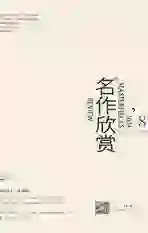“鸳鸯蝶蝴派”在银幕上的出路:张恨水致姚苏凤的一通佚信
2024-08-15金传胜
关键词:张恨水 姚苏凤 “鸳鸯蝴蝶派”
1934年9月1日,上海《晨报》的电影副刊《每日电影》以《一封信来自张恨水先生》(下文简称《一封信》)为题刊登了张恨水给该刊编者姚苏凤的一封来函。此函未见《张恨水全集》收录,《张恨水年谱》《张恨水研究资料》等均未著录,《张恨水书信集》亦未收入,故过录全文如下:
苏凤先生:
自那年冬在明星公司一会之后,这么久不见了,您好?弟半年浪游,由甘肃转到了江西,现暂住南昌两日。今天在×报看到宣传《到西北去》的文字里,有几句牵涉到了小弟:“
《狂流》以后,程步高却来了一部鸳鸯蝴蝶派的《满江红》。这片子虽然也卖了钱,而且因此张恨水的小说在银幕上,又多了几条出路,进步的观众,不免对他失望。”
这让我不能不向您报告两句。听说程先生拍《满江红》的时候,根本不愿意,因为不是拍《落霞孤鹜》的时代。那时,他成了名导演了。至于他到底拍了,那是他的环境要那么着,这个可以原谅他,也不必对他失望。而且那部片子,用火烧来点缀《满江红》这个戏名,也真是生吞活剥,笨得厉害,所以在影评上,先生对小弟曾指教过。可是,小弟很冤,原书并不是仅仅那么回事。这是过去的事,不用提了。要紧的一点儿,就是说小弟在银幕上,多几条出路。您是个对电影极有研究的人,您想,这年头儿,文化那么样进步,会许鸳鸯蝴蝶派在银幕上找得着几条出路吗?对于电影界的情形,您当然很熟悉。张恨水的小说,如人家拉去拍电影,您总可以相信,不是张恨水主动的。有道是:人怕出名猪怕肥,这年头,像我这样思想落伍的人,树叶子落下来,怕打破了头,那儿会在本行以外,去乱找出路?老实说一句,就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还能够卖几年稿子,那真没准儿。关于我和电影界合作的事,本来惹过不少的误会。再要说我在电影界多几条出路,这消息传出去了,我敢断言,那是找骂挨。我敢很坦白的向您说一句,别论什么时候,电影界不来找我,我决不找人。这并不是说,捧着肥猪头,怕找不出庙门来,我根本是剃头店里小司务,不作外活,您啦!那么,“电影界找你,你不会拒绝吗?”有人可以这样问。可是,朋友不怕多,对头冤家怕一个,若是可以帮帮人家忙的话,那就凑合凑合罢,那儿不交朋友?要说是图报酬,您想,中国电影制片者,能给多少钱买剧本呢?为了这个找骂挨,您相信,那是不值的。我是尽挨骂不回嘴的,几年来,在各刊物上,您可以用事实来证明。这回因怕惹出什么是非,所以向您报告一贴心眼儿里的话。太啰唆,这儿向你告罪,祝幸康健。
弟张恨水挥汗书(八月廿四日,于南昌)
《每日电影》创刊于1932年7月8日,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会编行,实际主编为姚苏凤(1934年9月至1935年初由舒湮、姚氏合编)。1934年8月12日晚,程步高的新片《到西北去》在中央大戏院试映a。“今天在×报看到宣传《到西北去》的文字里”中的这篇文字大约发表于1934年8月中旬,具体篇名和发表期刊待考。从信中摘录的部分可知,文章的作者显然是站在左翼的立场,断定“进步的观众”对于改编自张恨水小说的《满江红》一片感到失望,同时讽刺张的小说在银幕上“又多了几条出路”。张恨水在江西南昌读到此文后,对于文中提到自己的几句不乏意见,因而特意致函姚苏凤,希望借此澄清一下。
首先,张恨水指出程步高导演的《满江红》对小说原著有生吞活剥的地方,如“用火烧来点缀《满江红》这个戏名”。因而影片被姚苏凤等人批评,张恨水未免感到有点冤枉。其次,张恨水在信中强调自己“和电影界合作的事”并非出于主动,“本行”工作仍是写小说,不敢有其他奢望。如果电影界主动向他提出合作事宜,则采取不拒绝的态度。
张恨水与上海《晨报》的关系
身在南昌的张恨水为什么会关注《每日电影》副刊并且专门给编者姚苏凤写信呢?这就不得不提张恨水与上海《晨报》的密切关系了。《晨报》创刊于1932年4月7日,“以民办姿态出现,实际即以CC系为政治背景”,社长是潘公展。1932年至1935年,张恨水的两部长篇小说曾在《晨报》连载过,分别是《欢喜冤家》与《北雁南飞》。《张恨水年谱》谱文中说《欢喜冤家》1932年9月初至1933年9月23日在上海《晨报》副刊《妇女与家庭》连载,并注明:“因原报残缺,开始连载的具体时间无法查到,待考。1933年11月由上海晨报社出三十二回单行本,约23万字。1944年3月,作者增订后,于同年由重庆礼华书店出版,1947年建中出版社第1版,均改名《天河配》,二册,三十二回,约30万字。”《张恨水研究资料》一书中《张恨水著作(单行本)目录索引》对《欢喜冤家》的介绍是:“北平晨报社出版社1932年11月初版。”《张恨水小说图志》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很快,《欢喜冤家》开始在上海《晨报》副刊‘妇女与家庭’首发,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日又移至《晨报》晚刊《新夜报》连载,至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登毕。”实际上,上述三种关于《欢喜冤家》连载日期或单行本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需加以厘清。
首先,《欢喜冤家》先后跨越了两种报纸:1932年9月1日至本年12月31日先连载于《新夜报》,1933年1月8日开始转换阵地,移《晨报》“妇女与家庭”栏逐日连载f,至本年9月23日结束。《新夜报》与《晨报》属于姊妹报,均由潘公展主持的上海晨报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新夜报》原名《晨报晚刊》,初随次日《晨报》附送,1933年1月独立。因此,《欢喜冤家》由《新夜报》转到《晨报》连载,可能是由于《新夜报》版面有限,而《晨报》版面众多。在1934年的《欢喜冤家·自序》中,张恨水回忆道:“犹忆二十一年之秋,世界书局徐蔚南先生,一函相告:上海《晨报》潘公展先生需愚作小说一篇,体裁以社会言情。而背景以取材于北平者为佳。愚正以家人多病,二女夭殇,困于金钱,更增稿费,足资补救。即报函曰可,而以此《欢喜冤家》寄之,书布局即毕,且亦开始发刊于报端,殊不容中止。于是南北奔波,病苦相乘之际,卒以完篇,此即全书得成之所由起也。”1935年9月27日,张恨水在其主编的上海《立报》副刊《花果山》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欢喜冤家》的短文,开篇谓:“我作的一部《欢喜冤家》小说,曾在《晨报》上发表,上海人当然不都看见,但是看见的人,必然知道我的用意所在。”《张恨水年谱》误以为《欢喜冤家》仅在《晨报》连载,估计是受到此文的影响。其次,《欢喜冤家》单行本的出版时间比较复杂,是随小说的连载陆续发行的。1932年11月8日,《欢喜冤家》刊至第八回,读者因“定报参差不能得窥全豹,纷函要求补购”,《新夜报》“特将第一回至第八回印成单页”,“凡在本年内直接向本社定阅《晨报》者”,即奉赠一份(零售每份大洋二角)。所谓单页,并不是装订成册的单行本,故称“份”而非“册”。1933年3月,上海晨报社推出了《欢喜冤家》前八回的单行本,每册大洋二角,并预告小说“业已编成弹词,不日将在无线电话中弹唱播音”。4月初,晨报社决定在该报周年纪念日4月7日这天开始播音《欢喜冤家》弹词,并在《申报》《新闻报》等刊载广告。该弹词由戚饭牛改编,周凤文弹唱。4月下旬,“为应一般无线电听众及《欢喜冤家》读者要求”,晨报社又连忙赶印了第二集(第九至第十六回)。同年8月1日,《晨报》的《每日电影》中预告张恨水“生平第一杰作香艳长篇说部”《欢喜冤家》第一至三集单行本均已出版的消息:“本报逐日刊载之《欢喜冤家》小说,笔锋犀利,笔法温馨,布局则变幻新奇,结构则曲折有致,非特恨水先生自认为生平代表之作,即读者亦一致公认为说部中之鹤立鸡群者。”同年11月2日《晨报》刊载的广告称《欢喜冤家》“第四集第廿五回至卅二回不日出版”。由此可见,《欢喜冤家》最初的单行本共分四集,初版时间分别是1933年3月、4月、7月和11月。1934年,《晨报》社又印行了《欢喜冤家》单行本,分上、下两大册,每册十六回。
张恨水与姚苏凤的交往
“自那年冬在明星公司一会之后”,这里应该指的是姚苏凤、张恨水初识于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姚苏凤早年在苏州与赵眠云、范烟桥、郑逸梅等成立了著名的鸳鸯蝴蝶派文艺社团——星社。1927年来沪,在管际安的介绍下加入上海影戏公司,至此步入电影界。不久,姚氏进入《民国日报》任编辑,并为《电影月报》等撰稿。姚苏凤1932年10月20日发表的《评〈兰谷萍踪〉》一文开篇言道:“两个月前,我尚是天一影片公司的职员,虽然我始终不曾借了《每日电影》的地位自私自利地给天一公司做过任何的宣传;(同时,对于天一公司的《一夜豪华》和《游艺大会》也惟恐因私谊的牵制,而或者不能绝对的公允,所以把批评的事托了洪深和鲁思两先生去担任。)但,外间的猜疑的毒箭是纷纷地放射出来了;最有力的就是发表在《时报》上的菲菲先生等的一封公开信(其实,在此信发表时我已脱离天一。)几乎以为我是一个替天一公司包蔽过失者。”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读者,《每日电影》创刊时,由于姚苏凤是天一影片公司的职员,有所顾虑的他特意请洪深与鲁思对于天一公司的《一夜豪华》和《游艺大会》两片进行批评。直至两个月前(即8月份),仍服务于天一。等到“菲菲先生等的一封公开信”发表时,他已经脱离天一。这里所谓的公开信应是同年9月25日菲菲、来夫、尘无、聋人联名发表的《我们希望着有力的批评一封公开信》,文中曰:“有人说‘洪先生是明星的顾问,姚先生又是天一的职员’。”可见,姚苏凤向天一辞职的时间当在1932年9月上中旬,不过菲菲等写公开信时尚未获知这一消息。在次年的《付之一笑·宣传员》中,姚苏凤再次谈及自己离开天一的经历:“又有人说我写影评的目的,为要做宣传员,然而,没有人注意到我在编辑《每日电影》前是天一公司的职员(宣传亦是职务之一);而编辑《每日电影》后就向天一公司辞了职。”在一份写于1968年11月的个人简历中,姚苏凤自述:“1930年—1934年,由周剑云介绍,兼任明星影片公司宣传科长,又改任编剧。”学者张华采信了这一说法,其《姚苏凤与〈每日电影〉重要事件年表》显示:“1929年经李一鹤介绍,姚苏凤进入天一影片公司,编撰字幕,后又改任编剧,至1932年《每日电影》发刊时离去。1930年由周剑云介绍,姚苏凤兼任明星影片公司宣传科长、又改任编剧至1935年初离去。”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罕见的情况:1930年至1932年间姚苏凤同时供职于天一、明星两家公司。考虑到天一、明星存在商业竞争关系,姚同时服务于两家公司的可能性非常小。对此,还可以找到一些例证。如1934年的报刊在介绍姚苏凤时均说他先后加入天一、明星。有一篇题为《姚苏凤做导演》的文章云:“姚苏凤从前本是天一公司的宣传员,后来改就明星后兼任《晨报》电影附刊编辑。”另一篇文章曰:“姚苏凤是《每日电影》的编辑,从前也在天一公司吃过邵家饭,后来转入明星公司。”郑正秋在1932年6月的《提高与普及》中写道:“现在有一线曙光了。张恨水先生、严独鹤先生、姚苏凤先生,都肯替我们电影界尽一部份的力量了。”可知,这时姚苏凤已同意加盟明星影片公司。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姚苏凤于1932年9月上中旬离开天一,随即进入明星。
1930年,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连载,一时洛阳纸贵。11月中旬,张恨水南下,23日偕钱芥尘赴沪,“其最大目的,盖在遨游苏杭,次则因沪地报馆乞撰小说,有须面洽。明星摄《啼笑因缘》,亦请其指示。并有人以三五千金,拟购其《春明外史》版权,待其面予然诺也”。可见,张恨水的上海日程中包括与明星公司方面商讨《啼笑因缘》改编事宜。周瘦鹃在1932年的《我念恨水》回忆:“恨水在沪约一月,曾屡往明星公司,商略摄制《啼笑因缘》影片的事。搜罗了许多北平名胜的照片,以供明星同人的参考。对于书中人物的个性与身份,又细为说明。临行时特别郑重,更将编制剧本的事重重委托了独鹤。”描述的正是张恨水1930年冬的上海之行。如前所述,因姚苏凤此时尚未正式加盟明星公司,两人结识于1930年的可能性较小。
张恨水在《写作生涯回忆》中云:“二十二年春,长城之战起。我因为早已解除了《世界日报》的聘约,在北平无事(我在北平后十年来,除了《世界日报》的职务外,只作了《朝报》半年的总编辑,无关写作,所以未提)。为了全家就食,把家眷送到故乡安庆,我到上海去另找生活出路。而避开烽火,自然也是举室南迁的原因之一。”谢家顺《张恨水年谱》认为张恨水于1933年农历春节后“携周南、二水到上海”。若干文献表明,张恨水在春节(1月26日)前已经抵达上海。1933年1月23日《晶报》上刊出钱芥尘署名“行云”的《张恨水沪滨小驻》率先公布了张氏到沪的消息:“小说大家张恨水以沪上文债日多,担任长篇说部,除本晶外,如《新闻报》《晨报》《上海画报》《旅行杂志》等,新旧不下十种。近周瘦鹃先生主编《申报》‘春秋’,复挽张担任小说,故张乘寒假之便,来沪拂理一切。”张恨水当天就读到此文,马上写下一篇短文《别来无恙》,发表在24日的《晶报》。由于本文为《张恨水年谱》所遗漏,亦未见《张恨水散文全集》收录,不妨整理于此:
予尝自况为文字界之徐狗子,徐狗子者,北方杂耍班中,以形容下里巴人之曲,唱双簧得名者也。其为人殊不足道,而新闻纸上则常露其名。予以章回体小说为活,新兴文艺家,锡以礼拜六派,或思想落伍之人,而一举一动,同文喜为文以扬之,亦感受宠若惊。此次南来,有二义,一清理文债,二拟联合同文集金慰劳前线将士(金钱概不过手),稍有成绩,仍当北返。行云先生善善从长,首揭予之行踪于本晶,感谢之余,适增惭悚。惟上海人之醉生梦死,与恨水毫无长进相同,亦可谓为别来无恙耳。
“新兴文艺家,锡以礼拜六派,或思想落伍之人”中的“新兴文艺家”明显指左翼文艺人士。面对来自左翼的种种批评,“尽挨骂不回嘴”的张恨水不无自嘲地自命为“思想落伍的人”,通过“这年头,像我这样思想落伍的人,树叶子落下来,怕打破了头”竭力塑造出谨小慎微的自我形象。正是在1932年冬(或曰1933年春),张恨水认识了先前亦属“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姚苏凤。
“关于我和电影界合作的事,本来惹过不少的误会。”这里虽然没有明说,但不难让人马上联想到1931年明星影片公司与大华电影社围绕张恨水小说《啼笑因缘》改编权的官司。明星公司最终获胜,《啼笑因缘》导演张石川率团队远赴北平取景。“所拍的外景,张导演为尊重原书的真实起见,特请著作人张恨水先生通往。”同时在北平拍摄的还有张石川导演的《旧时京华》和程步高导演的《落霞孤鹜》。《啼笑因缘》一片虽然受到部分市民阶级的追捧,但不久爆发的“一·二八事变”,使得社会各界爱国热情高涨,观众对于电影艺术一味娱乐化的倾向日渐不满。明星公司于是开始主动向田汉、夏衍等左翼文人谋求合作,推出了《狂流》《春蚕》等左翼影片。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对当时的背景有这样的描述:“当时‘电影界’风气很坏,名声不好,当时的所谓国产电影又都是武侠、恋爱、伦理之类的东西”,“‘九一八’‘一·二八’之后,广大群众的爱国抗日情绪高涨,对老一套的武打片、伦理片失去了兴趣,于是,作为张石川的智囊人物的洪深就向‘三巨头’提出了‘转变方向’,请几个左翼作家来当编剧顾问的建议。”1933年1月《明星影片公司民国廿二年新贡献》广告中,编剧人员既有陈瑜(田汉)、丁谦平(夏衍)、洪深等左翼作家,也有张恨水、严独鹤等通俗文人,从“鸳鸯蝴蝶派”阵营“毅然地转变过来”的姚苏凤亦在其列。“转变方向”后的明星影片公司试图在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一方面努力制作反帝反封建的进步电影,一方面仍未放弃生产“鸳鸯蝴蝶影片”,如改编自张恨水小说、程步高导演的《满江红》。一位署名“茵弟”的影评人便将《满江红》的出现称为“鸳鸯蝴蝶的复活”:“自‘转变’之风侵入影坛,礼拜六派作家的鸳鸯蝴蝶,侠客剑仙等等,在银幕上几乎已经绝迹。但从明星公司的《满江红》出映以后,因为生意兴隆,卖座甚盛之故,最近张恨水的小说,又在电影界活跃起来了。”
姚苏凤评《啼笑因缘》与《满江红》
《啼笑因缘》影片共分六集,1932年6月至12月先后开映(第一集曾遭遇停映风波)。受左翼影坛的影响,姚苏凤陆续发表《论〈啼笑因缘〉》《〈啼笑因缘〉五集》《〈啼笑因缘〉总评》等,批评该片“只能为一种有闲者的娱乐物,而对于影片的必要的‘教育’意义上,可以说是‘等于零’”,然而承认导演“技术上的进步”和“演员的表演还不坏”。姚苏凤对《啼笑因缘》并没有完全否定,同一时期却严厉批评了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粉红色的梦》(蔡楚生导演)与《火山情血》(孙瑜导演)。一位署名“玄郎”的左翼影评家表示对他的态度“不能不怀疑”,“希望他有更进一步的觉悟”。
程步高执导的《满江红》于1933年8月30日午夜在上海中央大戏院试映,9月14日正式公映,随即受到诸多影评人的关注。《时报·电影时报》《申报·电影专刊》等著名电影刊物均有文章发表。由“在影评上,先生对小弟曾指教过”一句可知,姚苏凤曾经写过本片的影评。经查,《每日电影》围绕电影《满江红》共登有三篇评论文章。1933年9月15日同时刊载署名“伊娜”的《〈满江红〉评》、署名“麦英”的《〈满江红〉又一评》两文,9月17日刊出舒湮《〈满江红〉论故事剧本配音诸问题之分析的探讨》。舒湮实有其人,原名冒舒湮,彼时是《每日电影》的长期撰稿人之一。“麦英”显系笔名,目前没有关于其真名的任何资料。伊娜亦应是笔名,曾屡次露面于《每日电影》,诸多迹象说明他是姚苏凤的化身。首先,他在稍早发表的《喟然》中写道:“窃愿本刊诸同人加倍努力。”并以近于编者的口吻向读者征稿:“要怎样来整理电影批评?——我现在诚意地向一般的关心影评者征求一个具体的答案。”#6俨然传达出伊娜即姚苏凤的信息。其次,《〈满江红〉评》对《满江红》一片的总体评价不高,认为“一个无聊的故事,影响了影片的一切”,仅对导演“新颖的手法,圆熟的技巧”与演员“相当的努力”予以肯定。其基本观点与姚苏凤对影片《啼笑因缘》的评语类似,进一步揭示出伊娜可能就是姚苏凤。《〈满江红〉评》中有一句针对小说的批评曰:“甚至《满江红》这主题也一直到了最后的一回书中才生硬地把‘火烧轮船’来归入本题,这真是拙劣的手法。”这句话与张恨水信中的下列表述有呼应关系:“而且那部片子,用火烧来点缀《满江红》这个戏名,也真是生吞活剥,笨得厉害,所以在影评上,先生对小弟曾指教过。”可见,张恨水认为片子以“火烧轮船”来点缀《满江红》戏名的做法十分笨拙,并不完全符合原著。张恨水对影片的此处不满无疑是承袭了《〈满江红〉评》的看法,只是他将其误记为针对电影的评价。综合上述三点,笔者认为伊娜就是姚苏凤。以张恨水与《晨报》的关系,他在读到《〈满江红〉评》后即获悉伊娜的真实身份并不困难。张恨水从两年前初次相逢开始写起,又不忘提起一年前姚苏凤“指教”《满江红》一片的旧事,称赞对方“是个对电影极有研究的人”,既表达出珍视自己与姚苏凤的交情,又显示了他十分看重左翼影评人的意见。
结语
1938年初,张恨水抵达重庆,被重庆《新民报》聘为主笔兼副刊《最后关头》主编,1944年春兼任渝社经理。1943年,“应重庆《新民报》主人陈铭德之邀”,姚苏凤由桂林赴渝任该报主笔,先后编过《西方夜谭》《戏剧与电影》《万方》等副刊,由此与张恨水成为报社同事。1944年5月16日,值张恨水五十寿辰,姚苏凤撰《献赠恨水先生——祝其写作三十年纪念》一文以示祝贺。同年9月9日,重庆新民报社在中美文化协会举行茶会,庆祝该报创刊十五周年,渝社经理张恨水、主笔姚苏凤等人“报告报社创办经过及近况,并答致谢词”。张、姚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晚年,但两人的通信等文献多有散失。《一封信》作为目前仅存的一通张恨水致姚苏凤书信,显得极其珍贵。
总之,这封佚信围绕“鸳鸯蝴蝶派”小说在银幕上的出路问题,涉及张恨水与姚苏凤的交往、张恨水与《晨报》的互相支持、姚苏凤化名批评《满江红》等话题,真实反映了左翼电影运动大浪潮下张恨水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以“思想落伍的人”自居,真切地感受到“文化那么样进步”即左翼文化方兴未艾的势头,对来自进步文坛的批评声音极为敏感,希望保持自己小说家“本行”的尊严;另一方面,面对来自电影界的邀约,他秉持一种“不主动、不拒绝”的姿态,并不放弃自己的小说搬上银幕的机会。因此,继《银汉双星》《落霞孤鹜》《满江红》《啼笑因缘》,张恨水后来的《秦淮世家》《夜深沉》《金粉世家》等小说也都陆续被搬上了银幕。张恨水选择给姚苏凤写信,自然是希望借助《每日电影》在国内电影刊物中的影响力,公开向读者亮明自己的态度。发表这封公开信时,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北雁南飞》正在《晨报》连载。因此这封信很可能是随《北雁南飞》文稿一同从南昌寄到《晨报》社的。姚苏凤选择登载这封公开信,应该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不仅遵循该刊“凡关于电影之一切文字(除架空的宣传,明星起居注,及其他无关宏诣之趣味文字外,均所欢迎)”的用稿标准,而且和张恨水既是《晨报》重要供稿人而又与自己同系明星公司编剧不无关系。
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综合性报刊与现代作家佚文整理与研究”(22ZWC009)阶段性成果作者:金传胜,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神户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史料、语文教育史。
编辑:得一31217632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