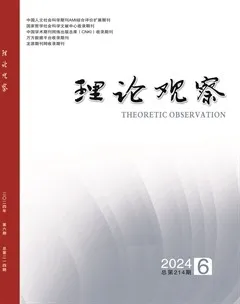东北作家城乡叙事的特点及审美价值研究
2024-08-15施华李茹
摘 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城乡叙事早已成为一个恒定的叙事母题。随着现实中城市与乡村的不断发展,东北地区基于悠久的农耕文明传统,城乡叙事话题自然也成了其文学创作的热门题材,城乡关系的书写也在发生着变化。东北作家关注人的生存境遇与精神成长历程的写作立场与姿态,使得东北城乡叙事承载了丰厚的人文关怀。本文将从东北文学的总体视角,考察作家的城乡文学版图,并以迟子建、梁晓声等作品中的城乡叙事为例进行具体分析,体味作家精神关怀和生存思索的深度,进一步分析东北城乡叙事的特色,用文学叙事为东北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格局寻找新的路径和方法。
关键词:城乡叙事;东北作家;迟子建;梁晓声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6 — 0130 — 0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报告还指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东北作家对乡村与城市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人的心路历程和行为活动做出了准确而深刻的描绘,使城乡叙事模式呈现诸多变貌,彰显不同的时代风貌与美学趣味。以迟子建、梁晓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东北作家把视角转向城乡关系的融合,在关注城乡发展之间的联系与差异的同时,描绘两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充分展现出自己由乡村走进城市后产生的情感变化,并以此为叙事起点勾勒了东北黑土地城市与乡村的变迁。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乡村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城与乡在空间上,逐渐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格局,城市的文明与价值观念冲击着乡土中国,冲击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城与乡相互纽结互相渗透的复杂关系成为当代作家城乡叙事的中心,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乡下人的身份焦虑等文化伦理的困境,更是成为作家书写当代城与乡的重要课题。当代作家在现实与精神领域都给变革中的人以极大的人文关怀,以一种新的叙事构建起城乡文学的独特表现方式,令这一百年叙事母题呈现出诸多变貌,文学以它特有的方式参与、讲述着城与乡的中国故事。
一、城乡叙事的内涵
在现当代文学中,城乡叙事一直是一个重要主题。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城与乡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生活现代化程度的加快,城与乡叙事的二元对立关系逐渐被打破,东北的城乡叙事表现出更复杂的姿态。美国学者罗伯特·塔利在叙事研究中开拓性地提出“文学绘图”的概念,“文学绘图”是以地图绘制喻指文学写作,包含了“叙事绘图”,而城乡叙事就是其中之一。城乡叙事通过反映城市和乡村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惯以及不同的价值观念,从而在城乡文化碰撞中探究社会现状、时代难题以及生存困境的一种文学叙事方式。城乡叙事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展现城乡空间;二是站在底层人民立场;三是以苦难为中心的独特叙事主题。城市和乡村作为人们现实生活的场所,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二者从来都不是完全独立的空间,而是存在着文化融合的矛盾冲突与对立统一。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城乡叙事构成了文学叙事的内在精神元素,释放着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与融合,彰显不同的时代风貌与美学趣味。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村承载着我们的历史、人文、乡愁等精神层面的丰富内涵。百年以来,中国人追求现代性的进程中,乡愁与现代相互纽结,拒斥又融合写就了人的精神历程史。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的城市化进程有着自己的特色,老工业基地的兴衰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东北故事,既包括了东北乡村城市化的历史,又记载了老工业基地的光荣与失落,东北地区特有的地理和人文因素深刻地影响着当地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审美取向,使得文学作品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以民间为中心的创作立场和对凡俗生活的人性分析的自觉传承,使得东北作家群体具有相似的文学气质。东北地区的大量文学作品表现了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城市和乡村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这些小说的叙述方式有着相似之处。从梁晓声到迟子建,再到双雪涛、班宇,再到更新生代的杨知寒,东北作家用他们的独有的方式讲述了东北的历史、东北故事,勾勒了东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的道义、情怀、格局,他们讲述着东北的情感史、精神史、文化史,让东北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中成为不容忽视的存在。
东北作家在代际更迭中始终保持着文学创作的青春的作家迟子建、梁晓声等无疑占有着重要的位置。与新生代的作家相比,他们的城乡书写关注点更为广泛写出了东北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与乡村的世态人情,写出了东北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与失落。他们的东北叙事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形成了一条特殊的叙事美学道路。我们可以从生命史、精神史的层面去碰撞生存和精神的创伤,从而引发更多人对城乡文学的艺术创作与传播问题的思考。
二、东北作家城乡叙事的特点
东北作家的城乡叙事根植于东北广袤土地上百年的沧桑巨变,这其中既有城乡变革进程中乡下人进城的文化价值观念冲突,也有东北乡民向市民的身份转换中的得与失,城乡一体化过程中,保有传统的乡下人进城的困惑与持守,彰显了作家的人文关怀。
(一)“乡下人进城”的叙事母题与独特的乡村体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走出乡村和回到乡村,成为乡村叙事中无法回避的永恒话题。城市文化与乡村传统的对立、冲突和交融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文学自然而然地承担着书写这一历史巨变的使命,形成了一种包含城乡文化与变革的大叙事趋势。“离乡”是城乡之间最早的障碍,也是最直接的矛盾,走出家乡是知识分子必须面临的生存选择和理想追求,于是,“进城者”的回望成为乡土小说普遍采用的叙述姿态。随着历史变革的出现,“乡村”意象在东北沦陷区文学创作中逐渐明显。“乡下人进城”这一社会现象所引发的文学审视,形成了城乡叙事文学,突出了作家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情感取向、个人思想动机。“乡下人进城”模式虽然反映的是农村人的城市生活,但其本质上是对现代农村叙述的一种自然延伸。不只是迟子建、梁晓声等如此,在当代许多有着乡村体验而又生活在城市里的东北作家那里,表达“乡下人进城”的作品的母题与变貌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
迟子建一直怀着陌生人的乡土情怀,深切关注乡村视角下的城市“异乡身份”,描写落入都市的乡村人所面临的生活境遇,巧妙地展现人的身份演变和传统与现代文明碰撞的内容,讲述了构成城乡叙事主要驱动力的文明差距的故事,关注进城的乡下人的生存困境。在《群山之巅》中,迟子建描述了人们面对现代文明入侵乡村后的社会变革,以及他们对不可避免的逝去的乡村生活的怅惘情绪。龙盏镇注定要在与都市文明的碰撞中告别传统,每个人的故事也将写上句号。正如迟子建在小说后记《每个故事都有回忆》中写道“一个飞速变化着的时代,它所产生的故事,可以说是用卷扬机输送出来的,量大,新鲜,高频率,持之不休。”在《月白色的路障》里,王张庄村民因热情招待过往司机而获得一点感谢的钱以后,便先后开了小饭店和小旅馆,方便过往司机。伴随着需求的增加,村民招揽生意的方式就改变了,通过在道路中间摆花圈等行为强行阻拦车辆,索要金钱。女教师王雪棋更是没有经受住金钱的诱惑,在丈夫的配合下,成为夜晚公路上月白色的路障。迟子建的小说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应该如何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以文明乡风赋能乡村振兴。
迟子建的小说充满了对辽阔的东北大地、自然山水、平凡人民的热爱与追忆,这些自然而又美好的乡村景象,使迟子建的小说充满了乡土情结。故乡北极村孕育了她丰富的文学想象力,甚至变成精神家园的一种象征。她根据童年的记忆,用孩子们的视角与语言将北极村构建成了一个色彩绚丽的理想王国,并赋予无限的热爱。淳朴善良的村民性格也像家乡自然风景一样干净美丽,对于村民的赞美也是对地方文明的认同。
梁晓声的小说同样也描写了独特的乡村人的城市体验。在《表弟》里,肖冰背负着全村所有人的期望,从一个偏远的西南山村考上了北京的学校。在城市里生活,他的骄傲敏感使得他几乎不对任何人提起他的故乡和过去,他在当下生活和毕业去处之间担忧抑郁,最终自己结束了生命。在《西郊一条街》中,乡村故事所展开的活动领域,贯穿城乡内部与边界,展现出更为广阔的视野。作品中的城乡交汇处充满了诱惑与变迁,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生活在城乡十字路口的年轻人的心境。作品从小人物与日常生活的细节入手,对于乡村生活与人物形象描写都展现了英雄命运的变迁与生活矛盾的变化,表达了在平常生活中的美好情感。梁晓声试图探索城市与乡村人民行为背后的一些因素,以及正在孕育的文化土壤,揭示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以及生活在这样文化交融的环境中一种别样的城乡体验。
(二)深植乡土的城市图景的绘写
从城市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人对“乡村”更加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关于“城市”的描述实际上是模糊而不连续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城镇”叙述才在东北地区大量出现,如《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小城之春》等。到90年代之后,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乡民”的时空位移和生命体验向“市民”转变,文学叙事呈现出“城市化”趋势,“城市”叙事因而趋于平稳。新时期以来,东北地区的作家关于城市叙事的作品也随之增加。例如:孙惠芬既注重乡土叙述,又注重以城市生活为乡村空间作注释;徐坤的文学创作中,身处城市心理困境是其表现重点;金仁顺描写大量现代都市生活的众生百相;皮皮的作品关注都市化进程下的男女关系与社会热点问题。
迟子建笔下的哈尔滨城市建筑尤具特色,存在着多面性,有着不同的映射。例如小说《起舞》,细致地记载了曾经的哈尔滨街头那些长条高窗、灰绿色橄榄顶、庄严美丽的俄罗斯古宅,通过怀旧的笔触表现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情怀。在文学艺术的渲染下,让人想要在历史的片段中探索它的人文价值。《烟火漫卷》将哈尔滨作为叙事主体,聚焦于现代化中的城市与人民、物质与文明。在作品中,叙事场域的张力表现为城市景观与乡村景观的互照,包括自然景观的互照与人文景观的互照。作家通过张力化的叙述,把哈尔滨的现实与历史、自然与人文、典型与普遍完美地结合起来,其美学价值不言而喻。
梁晓声从宏观视角完成了城市到乡村的场域转换。《人世间》通过对东北地区三代人民的生命史和精神史的深入描述,以民间视角呈现出时代发展的风貌。小说的背景是一个沙俄铁路兴盛的城市,作家利用周秉昆和他的青年视角,描绘了当时那个时代的真实生活体验,并把他们的命运和工业文明的兴衰联系在了一起。在《西郊一条街》里,作者精心构建了“西郊一条街”这一传统与现代元素融合的叙事空间,成功地构筑了一个“城里人下乡”的故事,使得这一空间成为观察整个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的舞台。
(三)城乡互动的人本关怀
都市和农村不仅仅是地域概念,更是文化概念。以地缘关系为依托的城市文化,在思想观念、人文风俗等方面,都与以血缘联系为纽带的农村社会存在着显著差别。然而,这两种对立不仅是时空上的对立,更隐含着“过去”和“未来”这两种时间维度的博弈,其强烈的张力涉及空间重构和社会重组的问题,它们在冲突和融合中展现出的人生脉络就是一幅文学的锦绣。在描写城乡题材时,东北作家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探讨了个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走向,在城乡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将两个不同的空间连接起来。孙惠芬笔下的都市与农村是多元的、立体的,它们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现代世界;北陵公园是女真小说中沈阳特有的文化空间,它以家庭故事为载体,赋予了作品强烈的生命力。作者们从具有乡村和都市两个身份的人的生活体验来展现城乡的二元对立,在城乡对比中呈现出文化差异,打破了以往单一不变的城市视野,从多元的角度来描述城乡人的喜怒哀乐,体现了作家深切的人本关怀。
迟子建将乡村书写融入城市生活的作品中,描绘了一幅幅意蕴丰富的乡村世界。小城曾经的历史风云,过去的城乡人家才有的风俗礼仪、生活样态,都在语言间隙流泻出来。迟子建带着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观察着乡土世界,积极探索乡土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从城市的角度探索乡村的贡献,将目光放置于底层书写上,通过对下层人民日常生活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温暖人性和历史温情。《亲亲豆豆》中的李爱杰夫妻,虽然历经了种种人生磨难,但始终能够分享财富和悲伤,从不放弃生活。迟子建在揭露城市文明的困境时,总是以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来书写城市文明的温暖,体现了人性的包容之美。在《北国一片苍茫》中,迟子建深刻地呈现出乡土世界边缘生活地带的生存状态,通过对几个人物的命运及其不合乎日常逻辑的民间、民俗文化心理描述,解析乡土人生、生存理念和方式在动荡年代里难以自新的困境。渐渐地,迟子建的文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审美阐释空间,对于小人物的描绘也展现了独特的人文关怀。
梁晓声的作品也时刻关注城市与乡村结合下的人类生存现状与困境。《西郊一条街》重点表现了户籍制度下城乡发展的二元性。小说不仅展示了“乡下人进城”的迷失,还开启了“城里人下乡”的叙事,在历史进程中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存状态,极力表现这两种境遇下个体的精神探寻与城乡关系的未来走向,传达了丰富的现实与文化内涵,探索了生命的价值,并给予人道主义的关切。改革开放中的城乡融合与差距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一一展现出来,小说利用西郊街道构建了空间符号的代码,还在更具体的意义上展开了人文关怀,彰显出历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成为城乡从对立到开始融合的历史见证。
三、东北作家城乡叙事的审美价值
东北作家的城乡叙事彰显着东北烙印与风格,他们根植于东北广袤的黑土地,写乡愁、写城市、写故土新变,使得东北的城乡叙事带有了鲜明的地域色彩,写出了东北人独有的精神气质,进而展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
(一)揭示乡土的温情表达的新形态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乡村也随之变化,从空间环境到人的价值观念、精神世界,城乡秩序受到历史烙印的冲击,传统的农耕文明逐渐远去,新的乡村文明正在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迟子建后期作品中更多地展现了城乡发展过程中的交融与碰撞,《烟火漫卷》中黄娥在找寻哈尔滨的同时,始终在精神层面向往着传统的乡村生活秩序,而她儿子杂拌儿在小说结尾回到了卢木头小酒馆的情节安排也体现出迟子建的乡下人的视角,这是作家的怀旧与持守,在迟子建笔下,温情从未缺席,只是表现更加多元化。
局部温情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人性中的温暖将被彻底消除,它们仍然可以在城市文明中被发现。梁晓声的作品观照了城乡矛盾及化解趋势,展现了一代人的精神困惑与信仰重建。在对于城乡的描写中,城市异乡的身份、乡村之美的烙印、城乡合一的希望,形成了城乡的双边互动。面对历史的变革,东北作家用自己的叙事方式,以小地方、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视角对大历史做出独特的诠释,揭示了历史深处的人的心灵状态,传达了作家个人的历史理性和人文情怀。在城乡叙事文学中,作家对笔下人物的现实质问,远远超出了道德判断的层次,涉及了生存现状与精神生态命题。
(二)提出城乡书写的新课题
传统的乡村生活渐行渐远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状况,从另一个角度和意义来看,是城市与乡村生活方式与观念的碰撞中日渐统一的一种新的态势。所以,城乡叙事作品又能引发新的反思,反思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影响、乡村文明如何在城市的快速发展与浸透中自处,以及城乡发展的新的平衡关系。新的城乡体验给迟子建带来了全新的审视和反思,因此,她的城乡叙事完善着乡村价值观的精神内核,不断进行现代城市文明反观下的城乡反思。梁晓声以当代视角看待乡村社会,探究城乡变革中一系列问题出现的原因,具有鲜明的思想启蒙特征,乡村治理问题的解决方式成为地方文学的重要命题并在很多作家的叙事中得以呈现。城乡思维的碰撞揭示了乡村并非是人的精神返乡的终点,而城市也并非是滋生罪恶的渊薮,从叙事上回归理性,重新审视并反思当代的城乡生活,成为新世纪东北作家如何书写新的城与乡,如何讲述东北故事的重要课题。
(三)透视历史进程中的人的境遇
随着城市文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观念与价值体系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在日渐丰富的物质文化面前,在日益发展的科技面前,人怎样在缅怀过去中看向未来是每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东北作家们关注到个体生命被裹挟的不适和困惑,在文学探索中寻找时间的真谛和生命的意义。面对改变现代人的精神困境的问题,迟子建努力在自己的城乡故事中创作了许多朴素的乡村人物,甚至包括一些智力或有缺失,但是却秉持着人类最初的童真的鲜活的文学形象,他们似乎始终保持着与外界的隔绝,秉持着传统的人文精神与信仰体系,维护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他们善良真诚的品格与现实生活中俗世的饮食男女成为鲜明的对照,也代表现代人对逐渐失却与遗落的美好的追寻。从城乡发展进程与现状的对照中,我们看到梁晓声对个体人生困境与精神状态的描写,以此展现社会历史的发展轨迹与人民的生存意识。梁晓声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时代的变迁,透视历史进程中人们心态的变化,展现年轻一代的精神样貌。正是由于城乡对照所造成的矛盾和融合,文学作品才具有精神生态意象和更高的价值取向,城乡叙事就是在展现这种发展境遇中发挥了自身的价值与魅力。
四、结语
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城乡人口、经济、功能等要素正在快速整合,城乡文化的模糊性越来越明显,闯荡都市的乡镇人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城与乡怎样弥合的问题,以迟子建和梁晓声为代表的一代东北作家,以浓郁的乡土情怀、对家乡的独特记忆和城市历史文化场景为创作素材,描摹具有不同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生活习俗的乡村,探索乡村的个性化发展之路,体现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融合与互动。他们以自身独特的文学视角,展现城乡文明的价值和意义,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城乡叙事特点,书写了富于时代气息又引人入胜的生活故事,呈现出理性精神与人文情感的双重渗透。作家们更加关注社会历史进程中人的精神状态,塑造出不同于土地改革时代、合作化时代、改革开放时代的新农民形象,刻绘新乡村中伦理道德、情感结构与感受方式的微妙细腻变革,在个性化中凸显出总体性的社会律动与时代精神,既表现城乡发展的一种新的可能性,也为文学艺术的展现创造了一种新的审美角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文学作品反映新时代中国乡村的变迁。东北作家的城乡叙事呈现了历史变迁中的时代症候和社会风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需要具备对现实广阔性的深度思考,来真正面对新时代乡村的种种结构性变化,用朴实的人文关怀达成对乡村和城市的理性观照,才能让这一叙事拥有更大的格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崔庆蕾提出:既可以从外部政策、行动和力量给农村带来巨变的重大事件为纲切入乡村社会,也可以将农村日常生活作为叙事的聚焦点来表达思想和认知,还可以在历史连续性中观照当下农村,展现乡村巨变的历史来路与所凭借依存的各类资源。
东北作家在城乡书写方面具有明确的多元化特性,具有观照社会和时代问题的本心,但透视现实的角度各不相同,这也使东北作家的文学创作仍然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参 考 文 献〕
[1]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J].文学评论,2005(01).
[2]王侃.“城/乡”现代化与现代性叙事逻辑——重读《哦,香雪》[J].社会科学战线,2015(12).
[3]王鹏程.从“城乡中国”到“城镇中国”——新世纪城乡书写的叙事伦理与美学经验[J].文学评论,2018(05):212-221.
[4]谷显明.游走在城乡之间——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的苦难叙事[J].云梦学刊,2010,31(04):109-112.
[5]韩雪.论迟子建小说的城乡叙事艺术[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9):107-110.
[6]杨漪竹,张福贵.东北女作家城市叙事的双重空间书写[J].当代作家评论,2022(02):20-25.
[7]车红梅.《西郊一条街》:城乡对立与融合的历史书写[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4):64-69.
[8]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视野中,写出新时代之“新”、新农村之“新”——“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 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发言摘登[N].文艺报,2024(03).
〔责任编辑:杨 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