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二师兄”相伴相生史
2024-08-06马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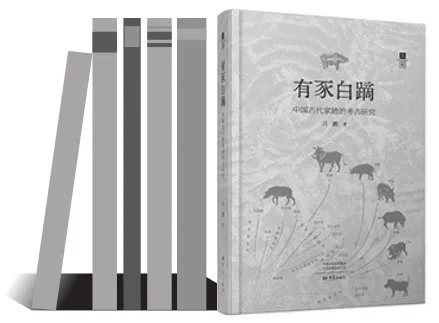
有豕方有家。这可以由汉字“家”的构成一目了然。中国古代先民在殷商时期所创制的甲骨文中,将“家”字分成两个部分,上面是“宀”字头,代表房屋,即居住之所,下面是“豕”字,即“猪”。从“家”字的构成可以看出至少在汉文字发明之前,“猪”已作为被驯化的动物,与人类同居一室,并成为人类家居生活的重要“伙伴”,乃至重要一员,是构成“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之一。
即以我个人而言,对猪抱有特殊的情感。在20世纪80年代的豫西南山村,粮食作物因“包产到户”可以自给,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生活用度中需要花钱的地方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好在二姨家赠送母猪秧子一头,几个月后开始抱窝下仔,且每窝大都在10只左右,以每只小仔10元计算,付后可得百元,且母猪秧特别“甜欢”人,以两年三窝的频率连续生产多年,极大地改善了我们家庭的经济状况,兄妹三人的学费及家里的日常开支基本得以满足。
或许是这种情感使然,当得知吕鹏所著《有豕白蹢:中国古代家猪的考古研究》(大象出版社2024年1月版)面世以后,在第一时间即得以拜读。
壹
该书作者吕鹏博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长期从事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吕鹏的研究方向即“锁定”动物考古方向,硕士论文为《试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后在考古所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广西邕江流域贝丘遗址动物群研究》在我国著名动物考古学家袁靖教授指导下完成,于2012年获得由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该博士论文以广西邕江流域的“贝丘遗址”为范畴。“贝丘遗址”,是一个考古学专有名词,贝丘是古代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大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或稍晚之青铜时代,其特征是此种遗址包含有古代人类吃剩食物抛弃的动物贝壳,一般位于盛产贝壳类动物的河流、湖泊、海洋附近。由于贝壳质地坚硬、富含钙质,可以长期存留,考古工作者可以依据贝丘遗存,了解水位线、海洋地质变化、古生物乃至气候以及人类生活的形态等等。
在博士论文中,吕鹏通过对邕江流域贝丘遗址群中动物种属构成、原始居民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包括对家畜饲养方式和人工鱼类养殖方式是否出现的探讨以及用“狩猎压”“捕捞压”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广西地区乃至全国贝丘遗址中所包含的丰富多彩的人地关系进行了仔细的爬梳及系统的研究。
贰
《有豕白蹢:中国古代家猪的考古研究》一书,沿袭作者硕士论文有关中国黄牛的研究路径,结合博士阶段对于动物考古、古生物研究的成果写成。全书37万余字,近450页码的篇幅,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每个章节所附注释共计页码146,注释数量共计1351)、活泼清新的语言、引人入胜的情节,从家猪的起源、饲养技术、资源利用以及如何有机融入中国文化的故事娓娓道来。
有关“六畜”等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驯化史远超过一万年。考古学界认为,狗是中国先民最早独立驯化成功的动物,距今远逾万年。
有关狗是中国先民最早驯化的动物的考古证据来自河北保定南庄头遗址。南庄头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遗址,其年代距今11500—9700年,是目前唯一一处同时发现动物驯化和粟黍种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袁靖等考古学家认为,该遗址出土狗遗存的下颌骨形态特征和测量数据表明这是中国考古遗址出土年代最早的狗,其主要依据便是南庄头遗址狗的下颌缘有一定的弧度,下颌骨及齿列长度与现生狼相比,牙齿排列紧密,却在尺寸大小上有进一步变小的趋势。同时,侯亮亮等人也对该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物中的碳氮稳定四位素进行了科学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此一时期狗的食物种包含了一定比例的C4类食物,这类食物极大可能来源于粟黍及其副产品。这足以表明距今10000年前的南庄头先民已经可以使用栽培农作物及其副产品对狗进行驯化。
在汉代以前,狗已经成为中国境内广泛存在的家养动物。其后向南扩散到东南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以及太平洋诸岛;向北则扩散到东西伯利亚极地地区。
狗的驯化成功,为人类所用,给中国先民驯化野猪,使其成为“家”畜提供了经验积累和技术借鉴,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从中国先民成功驯化“六畜”的时间先后顺序言之,猪是继狗之后的第二个驯化成功的动物,可谓名副其实的“二师兄”。
据作者介绍,著名考古学家罗运兵、袁靖等人通过对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第七次发掘中出土的猪骨遗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骨骼形态、年龄结构、数量比例、文化现象、病理学、几何形态测量、碳氮稳定同位素和古线粒体DNA等,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该遗址是中国最早的家猪起源地,由中国先民独立完成驯化,时间定位在距今9000—8500年前。
当先民们成功地将野猪驯化为“豕”之后,约束或者管理猪的方式不外乎放养、圈养以及放养+圈养三种方式。驯化初期,人类居住条件有限加之农业技术落后,不可能有太多“余粮”供猪食用,让猪在“家”或聚落周边自由觅食。自我解决温饱问题的“放养”方式应是主要的饲养模式。此种方式的好处,除了节约成本之外,尚有使其与野猪交配获得更加健康的后代等作用。
猪圈是中国古代先民的重要发明创造之一,其好处甚多。比如可以通过圈养保证猪的“人身安全”“食品安全”;积攒猪粪,可作肥料,提高农作物产量;有效控制改良品种,使其产肉率提高。对此,连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也赞叹不已。在其1868年出版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高度评价:“中国人在猪的饲养和管理上费了很多苦心,甚至不允许它们从这一个地点走到另一个地点”,认为用此种方法豢养的中国家猪“显著地呈现了高度培育族所具有的那些性状”。
在对猪的驯养过程中,先民们还掌握了对猪的阉割技术,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大都会对早年走街串户的“劁猪匠”“骟牛匠”印象深刻。正是阉割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对家猪品种的改良、肉质的提高、产量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献记载中有关家猪饲养者以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为最早。该书对母猪选育、护理、阉割、饲料、管理等方面均有论述。对后世中国的家猪养殖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字经》有言:“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后人《训诂》曰:“马能负重致远,牛能耕田,犬能守夜防患,则畜之以备用者也;鸡羊与豕,则畜之孽生以备食者也。”
作为与中国先民关系极为密切的驯养动物,家猪对人类的最大功用是源源不断地提供肉食。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猪骨遗存破碎且数量较多。考古发现其死亡的年龄正是人们食用的最佳阶段,证明贾湖先民在9000多年前已将猪肉作为主要的肉食来源,且已掌握了通过敲骨吸髓的方法将猪骨弄开,以获取其中更多的蛋白质。
此后,历朝历代猪肉的地位——在人们的食物结构中虽有些许起伏,总体来说,一直绵延不绝。时至今日,猪肉仍然在大部分国人的餐桌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除了肉食,养猪的第二大好处是积肥,即利用家猪圈养过程中产生的粪便给农田施肥。一头猪平均每年可以产粪一吨左右,将其积攒起来当作有机肥料,撒施在庄稼地里,既可以使庄稼长得更好,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土壤板结,改良土壤结构。考古学家在对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汉代猪骨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后发现其中的S15N值有显著提高,认为这是人类用施肥后的农作物“反哺”给家猪后的结果。此研究结果也表明,下王岗时期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积粪技术且已较为普遍地应用于农业生产中。
像其他动物皮被先民广泛用于制革,猪皮除了可以作为衣服蔽体御寒之外,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也被开发出了许许多多的用途,比如可以做成食物,用猪皮熬制后之皮冻至今仍是许多地方一道下酒佳肴;猪皮也可以在医药领域发挥作用,以猪皮等猪下脚料熬制而成的膘胶,作为黏合剂,可广泛运用于木材加工过程中。
猪鬃也较早被制成刷子使用,除用以制作日常清洁刷具和工业领域对机器进行清洗外,猪鬃还具有重要的军用价值。二战期间,中国出口的大量猪鬃被美国政府列入A类战略物资,用来清洗枪炮、给军舰等军用设备涂抹防锈漆等。
古代先民在将猪肉作为重要食物来源时,对其所包含的保健与营养等医药价值有着相当充分的认识。东汉名医“医圣”张仲景在其《伤寒论》中便记载有“猪肤汤方”“猪胆汁方”等由猪皮、猪胆制成的方剂,猪骨也常常被制成工艺品。
叁
在与人类长期相伴相生的历史进程中,“二师兄”除了为人类提供优质的动物蛋白,丰富了东方乃至世界各族的物质生活之外,还用浑身的宝物无私奉献给人类,可谓粉身碎骨死而后已。
物质层面之外,家猪还承载起了文化方面的担当,给予东方民族精神领域以深远的影响。
对于早期先民来说,猪与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猪牲的使用以及用以制作卜骨两个方面。
诚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之礼仪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发现表明动物祭祀所用多为家养动物。陈星灿认为此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家养动物是人类驯化和饲养的,而野生动物经由渔猎得之,是生的或非我的,因此不可以作为祭祀品献给祖先供其尊享。
社稷祭祀自周代开始纳入国家礼制体系,社稷在一定意义上演化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并为历代王朝所沿袭。大体而言,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民间社会,无论“大牢”“小牢”何种级别的祭祀物中,总会有猪的身影出现。尤其在民间祭祀中,献祭物中猪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牛、羊二牲。对于平民百姓,在家庙或祠堂中祭祀列祖列宗,在神龛、牌位、画像等物面前,陈豕于室,合家而祀,这正是“家”字含义的最佳诠释。即使在当下的大部分民间祭祀中,猪仍然是奉献给先祖和神祇的重要贡品。
猪的肩胛骨是制作卜骨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国最早的卜骨见于距今5800年前甘肃青海一带,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中出土的带有阴刻符号的6件卜骨中,主要由猪、羊和牛的肩胛骨或盆骨制作而成。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在1999—2006年共发掘出土卜骨160件,其中以牛肩胛骨制成卜骨80件,猪卜骨43件,其余为羊骨等制成。
在长期的相伴相生过程中,人类跟“二师兄”的关系从实用层面逐渐上升到文化层面,从而进入到人类生活的精神界面,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亲密朋友。“‘猪’字的演变折射出人类对猪的诸多关注——猪还是猪,却因为人类的所用、所思、所想而衍生出令人或惊叹、或可笑、或深思、或自豪的故事与内涵。”
肆
猪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其智力相当于人类3—5岁的小孩,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经过驯化,甚至可以像黑猩猩、海豚一样解读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它具有灵敏的嗅觉器官,可以帮助搜查毒品、危险品。法国、荷兰的科研人员发现家猪不仅能够理解一些简单的符号语言,掌握涉及动物和物体的复杂符号和标志,同时还具有某些情感特征。
或许正是有了上述这些特征,猪在中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圈中被赋予极其浓厚的文化内涵和多彩的文化形象。
考古学证据表明猪是中华龙的原型动物之一,猪龙主要借用了猪的头部特征,其形象主要在辽西地区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中得到传承与发展,黄河中游和长江下游地区的猪龙形象便深受其影响。
在生肖文化中,猪也占有一席之地。用十二个动物生肖与十二地支相结合,形象直观地记录时间和空间,是中国先民的重要发明之一,至今仍与来自西方“阳历”和平共处,以纪年。
在民俗文化中,猪是国人最重要最熟悉的家养动物,与人类生活有着极其亲密的关系。在创立文字时,把“猪”的形象置于“家”之下面,成为故土和家园须臾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从此层面解读,可以说,无猪,无以“家”为。
在吴承恩的笔下,猪八戒被称为“二师兄”,是广为人知的艺术形象之一,其好吃懒做、笨头傻脑、贪利好色,却又温和良善、憨态可掬的形象是猪作为文学人物在民俗学层面的最好注脚。
在作者的笔下,猪具有了更为深远的仪式性用途和文化内涵:它是祭牲和祭器,是礼制的标志,是龙的原型和十二生肖之一,是家庭富足的象征,是艺术创造的源泉。读者可以顺着此种思路,在其动物考古的视野之下解读猪型文物,进而领悟人类驯养和利用家猪的历史进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激发出来的人类精神与艺术追求。
伍
对家猪进行考古学研究,是动物考古领域中一个专门的学问,欲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研究,需要一定的专业背景知识,且对动物医学、分子生物学、食品工程学、文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等也多有涉及。因此,吕鹏能够在《有豕白蹢:中国古代家猪的考古研究》这样一部部头不大的著作里,对各种资料旁搜远绍、爬梳剔抉,在起源、技术、用途和习俗四个维度,在物质、精神两个层面,向普通读者全方位多角度讲述作为六畜之一的“猪”的价值及意义,实属难能可贵。
最令我这个非专业人士感佩的是,出生于豫北农村的吕鹏博士,以“小镇做题家”的身份,进入中国的最高学术殿堂,在动物考古领域打下一片天地。从他《后记》中对少年时期家乡院落里“有豕有家”诸多场景的回忆,反思成长过程中的热泪与足迹,望着再也回不去的山河故里,用专业明志,高声吟诵出“圈槽安乐,终不免引颈一刀;山野多险,却有别样风光”,着实令人动容。
是的,本来无忧无虑地生活于山水之间的野猪,被我们的先民们驯化之后,“由浪迹天涯到被拘泥于圈舍,由陶煮白肉到珍馐美食,由口中食到祭上牲,由实用功能到文化符号”,体无完肤地被人类榨干榨净。聪明却被人骂作“蠢猪”,尊贵却被斥为“猪狗不如”。对此,作者体现出了极度的人文关怀与文人情愫,发出如此清醒而发人深省的感叹:
人类不能凌驾于动物之上,无论人类还是动物,我们都只是地球这颗蓝色星球的匆匆过客,人类与猪相伴相行近万年之久,如何在未来继续和谐相处,人类或许会有远见卓识的选择。
在此,我愿意做一次“文抄公”,直接引用吕鹏著作《有豕白蹢:中国古代家猪的考古研究》第94页中描绘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先民们最早驯化猪的场景,作为这篇小文的结束语:
距今9000—8500年前,贾湖先民们开始饲养猪和狗、种植水稻,率先唱响了春天的故事。贾湖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及人工遗物的研究为我们鲜活地勾勒出史前生业图景:聚落内,猪和狗四处游荡,人们开始从事?“似农非农”的生业方式,喝上了用稻米、蜂蜜、山楂、(野生)葡萄等酿造的酒,一位巫师吹奏起用鹤的尺骨制成的骨笛,另一位巫师一手摇龟甲响器,一手握叉形骨器,指挥众人将猪下颌和整只狗埋下;聚落外,稻花飘香,鸟兽欢鸣……
(作者系文心出版社总编辑,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