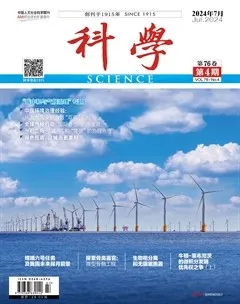一石二鸟:“减污”和“降碳”的协同治理
2024-07-29谢杨王溢晟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续和进展的基石,构建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从生态保护思想的启蒙阶段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到可持续发展阶段将其视为文明发展之内在要求,再到生态文明阶段将人与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在环境友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开发方面,这些生态保护理念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将其放置在突出地位,要求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融合,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迈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科学论断和战略选择,表明要从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解决我国环境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污染物协同控制,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
“减污”和“降碳”
减污,就是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新时代十年,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从2013年到2022年,全国重点城市PM2.5的平均浓度下降57%。地级及以上城市2020年、2021年和2022年连续三年PM2.5浓度降到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空气质量指导值》第一阶段过渡目标值35微克/立方米以下,我国已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尤其是十年来“2+26”城市(指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上的28座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巨大,2022年,京津冀三地PM2.5平均浓度为37微克/立方米,较2013年107微克/立方米下降了65.1%。
降碳,就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根本上还是高碳的能源结构和高耗能、高碳的产业结构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源头上发力,推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既降碳又减污,从而实现减污和降碳的协同增效。这是总抓手。当前,我国已形成一个“1+N”的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1”由《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与《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两大文件构成,在“1+N”政策体系中发挥统领作用,而“N”涵盖了多个重点领域及行业的实施和支持方案。
为什么需要协同治理?
“协同效应”又称增效作用,是指多种成分相加或调配在一起,所产生的作用大于各种成分单独发挥作用时作用的效能,简单地说,就是“1+1>2”的效应。为什么需要将减污和降碳协同起来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协同治理可以达到一举多得、一石二鸟的效能。2001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首次提出了协同效益(co-benefit)概念。
CO2排放和传统污染物的排放是同源的,主要来源都是我们熟悉的化石能源的燃烧和利用。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如果用更加清洁的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的同时,传统污染物的排放也会下降,这就产生了协同效益[1-3]。正因为如此,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将“协同效益”定义为“减缓政策所产生的并且明确地包含在减缓政策最初制定时的考虑之中的非气候效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其定义为“除直接气候影响效益外,减缓气候变化政策间接产生的空气质量改善、健康风险减少等广泛的并行效益”;美国国家环保局(EPA)则将其定义为“作为首要目标的气候变化减缓政策附属的多重效益,包括节约能源、经济效益、空气质量和公众健康改善。欧洲环境署(EEA)指出了协同各国的具体做法,发布了成员国根据国家减排承诺(NEC)指令报告所应实施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涉及减少细颗粒物、氮氧化物和氨这三种重要空气污染物的排放[4-6]。
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日益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主流做法,在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协同减排路径上,一些国家走出了独特的探索道路。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确定了雄心勃勃的“移动源零排放行动”计划,制定了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零排放行动计划目标,明确:到2035年,新销售车辆实现100%新能源,短途货运车辆实现全面电动化,非道路移动机械实现全面电动化;到2045年,客运、重型长途货运车辆实现全面电动化。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VOCs(挥发性有机物)和NOx(氮氧化物)协同减排对臭氧改善作用明显,现阶段臭氧由VOCs控制区转向NOx控制区。1987年以来,VOCs和NOx协同减排了接近80%。现在,虽然VOCs减排仍然有助于减少臭氧和颗粒物浓度,但是NOx对臭氧的影响更为凸显。
那么目前,我国在减污降碳上仍然存在哪些问题呢?尽管实施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能源清洁化、交通低碳化等措施后,污染物排放已有了很大改善,但目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仍处于较高水平,而且下降难度逐渐加大。经过此前的污染物排放治理后,减排空间进一步收窄,现在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此外,协同治理相关的法律、标准、路径有待进一步完善,尤其是“一省一策”“一市一策”“一行业一策”的政策路径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挖掘。
减缓气候变化措施可以显著改善空气质量,而发展中国家新兴的清洁空气措施也可以通过影响当地能源系统带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协同效益。协同治理除了带来生态环境改善、产业优化升级外,还能带来健康和经济效益,如减缓气候变化可以使人们因气候相关的致死率、致病率进一步减少,能够减少国家的劳动力损失。此外,一个国家的政策实施不仅对本国带来效益,对周边国家乃至全球都会有贡献。这些取得的效益,远远超过气候政策的相关成本。
如何实现协同效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处理好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要坚持系统观念,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同时强化目标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不断增强各项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我国国家生态环境部2022年6月也印发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明确了进一步加强源头防控、突出重点领域、优化环境治理、开展模式创新等具体举措。
怎么做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具体行动上,还需要政府部门和公众一起努力。
政府部门层面
政府部门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设时,应该将污染防治和碳排放监管一体化考虑、一体化推进、一体化考核,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上,走碳中和与清洁空气协同发展的路径。加强结构性减排措施,如用电、燃气等锅炉替燃煤锅炉[7-10]。加强对环境敏感地区的散煤治理,开展超低排放改造,淘汰落后重污染产能,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等。此外,还应该加强对新技术、新手段的应用研究。碳捕捉、利用和封存(carbon capture, utilisation and storage, CCUS)是一种可以从工业和电力设施的化石燃料排放中回收二氧化碳,并将其转移到可以避免进入大气的地方的技术。当前,不少国家加紧了对CCUS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同时,应该加快对多污染物系统治理、VOCs源头替代、低温脱硝等技术和装备的研究力度。从环境经济的角度考虑,还应该更好发挥碳排放配额、自愿减排量效能。目前我国碳交易市场有两类基础产品,一类为政府分配给企业的碳排放配额,另一类为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hina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CCER)是指对我国境内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利用等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进行量化核证,并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CCER 交易指控排企业向实施“碳抵消”活动的企业购买可用于抵消自身碳排的核证量。“碳抵消”是指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源或增加温室气体吸收汇,用来实现补偿或抵消其他排放源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即控排企业的碳排放可用非控排企业使用清洁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增加碳汇来抵消。抵消信用在通过特定减排项目的实施得到减排量后进行签发,项目包括可再生能源项目、森林碳汇项目等。
为了实现减污降碳的目标,政府部门需要整合多种手段,推进技术创新和市场机制,促进减排方面的合作与发展。
公众层面
公众应当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成为绿色生活的践行者。“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我们要从身边小事做起,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优先购买绿色产品,在消费商品时要尽量“三思而行”,购买耐用品,对于不再需要的物品,可以转让给别人,或者选择回收利用。尽量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塑料餐具等制品,不购买过度包装商品,还要及时关闭不用的电器电源,人走关灯、一水多用、节约用纸等,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设备,使用非节能电器,在做饭或用餐时,定量制作,避免浪费,在餐厅吃不完的饭可以打包带回。出行方面,多选择徒步、骑行、公交、地铁、拼车等环保出行方式。此外,尽量避免短途飞行,选择火车或公共汽车出行,减少“碳足迹”也是绿色生活的一种体现。最后,教育是保护环境的关键,尤其是对孩子的环境教育。通过向他们传授生态环境知识,并鼓励他们参与环保活动,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从而为创造可持续的未来做出贡献。
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是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我们认识到,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新和政策完善的挑战,也是一次全民参与的行动。从政府的顶层设计到个人的日常生活,每一环节都至关重要。通过政府与公众的共同努力,我们有望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迈向更加可持续的未来。
[1]Ma T, Zhang S, Xiao Y, et al. Costs and health benefits of the rural energy transition to carbon neutrality in China.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3, 14(1): 6101.
[2]Long Y, Wu Y, Xie Y, et al. PM2.5 and ozone pollution-related health challenges in Japan with regards to climate chang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23, 79: 102640.
[3]Xie Y, Wang Y, Zhang Y, et al. Substantial health benefits of strengthening guidelines on indoor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in China.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22, 160: 107082.
[4]Xie Y, Li Z, Zhong H, et al. Short-Term ambient particulate air pollution and hospitalization expenditures of cause-specific cardiorespiratory diseases in China: a multicity analysis.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Western Pacific, 2021,15:100232.
[5]Xie Y, Dai H, Dong H, et al. Economic impacts from PM2.5 pollution-related health effects in China: a provincial-level analysi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6, 50(9): 4836-4843.
[6]Weng Z, Tong D, Wu S, et al. Improved air quality from China’s clean air actions alleviates health expenditure inequality.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23, 173: 107831.
[7]Wang Y, Xie M, Wu Y, et al. Ozone-related Co-benefits of China’s Climate mitigation Policy.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2022, 182: 106288.
[8]Xie Y, Wu Y, Xie M, et al. Health and economic benefit of China’s greenhouse gas mitigation by 2050.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2020, 15(10): 104042.
[9]Xie Y, Dai H, Zhang Y, et al. Comparison of health and economic impacts of PM2.5 and ozone pollution in China.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19, 130: 104881.
[10]Xie Y, Dai H, Xu X, et al. Co-benefits of climate mitigation on air quality and human health in Asian countries.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18, 119: 309-318.
关键词:协调治理 协同效益 减污 降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