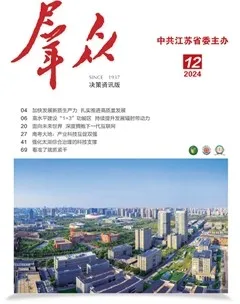积极推进数据场内交易提档升级
2024-07-22董宏伟孙灼昕
为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破局,我国积极推进建设数据产权制度、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收益分配制度和数据安全治理等基础性、顶层性的设计制度规范,已出台数据确权、分级分类、资产入表等利好制度,鼓励数据交易向产品化、市场化、合规化转型,但市场整体发展仍然缓慢。2023年全国数据生产总量达32.85ZB,占全球总量的两成以上,但数据交易市场规模仅占全球的13.4%。数据交易所(中心)本应在数据流通、数据应用和生态培育中发挥巨大作用。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运营和筹备中的数据交易机构共88家,但与交易所遍地开花形成对比的是,以数据交易所(中心)为主导的“场内交易”很少,占比仅2%—3%。亟待发挥场内交易“强心针”作用,强化数据要素市场的体系建设与治理。
数据场内交易正处于起步阶段
“数据二十条”发布后,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最显著的进展是各类数据交易所(中心)的建设。2022年我国数据交易行业市场规模已达876.8亿元,但大部分交易属于备案制,即企业间完成场外交易后,再经数据交易所备案,“场内”数据交易量较低。“数据二十条”提出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相结合,不断探索创新。可见,场内数据交易仍处在尝试起步阶段,数据要素存在“流不出、流不动、流不好”难题。
场内交易市场仍待盘活。供需不匹配、交易过程繁复、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仍是场内交易的“拦路虎”。数据质量不高是阻止“流出”的首要问题,场内往往难以采购到优质数据。采购企业要求高技术的数据采集和清洗,对数据可用性和可信度也有较多考量;极度依赖物联网高度信息化的产业,缺乏精准数据以支撑后续提取存储分析。数据匹配度不够,市场上普遍表现出产品质好价高、价低质劣的特点,采购后用不上、能用却不好用成为数据购买方的一大困扰。此外,场内难以直接评估产品质量,也缺乏可信评定标准,最终导致市场场内交易额不佳,不少企业观望后又无功而返。
场内流通壁垒尚未突破。场内交易受到地域采集限制。以公共数据为例,还有部分地方政府未开通数据开放平台,与东部地区的数据主力军不同,西部地区呈现滞后态势。大量公共数据无法经由各种合法渠道流通,也难反哺数字转型项目。场内交易面临流通范围限缩,由于地区间规范和标准要求不统一,行政壁垒成为全国一盘棋的主要阻碍,不少可用数据又沦为冗余的弃用编码。在2023年全年生产的数据量中,仅2.9%被存储,大量的潜在可流通数据从源头被截断。关键行业的数字鸿沟还未被弥合,专业性阻碍了数据价值深度释放,不少数据生成后未被整合处理。
场内市场不确定性加剧交易难度。基于商业秘密和合规经营考量,企业不敢轻易采购数据产品,阻碍了数字经济市场繁荣发展。尽管场内可合规审查和闭环交易,却仅对采集渠道、用户授权等进行程序性事前审查。部分源头企业收集数据时难免涉及个人身份或生物识别信息,本身已存在违规风险,进行分析加工将加重被诉可能。尽管已出台兜底性规定,对个体的侵权情形却难以精准把握判断。数据打包解析也面临技术挑战,既要保证数据质量,也需承担加密义务。企业安全维护成本随规模逐年增加,数据企业运营成本无形中提高,加深了中小企业进场难度。企业公平竞争的平衡被打破后,数据交易场内市场将面临垄断风险。
数据场内交易迟缓成因分析
数据交易市场遭遇场内流通障碍,不仅仅源于数据“不敢用、不能用、不好用”,受模糊规则影响,在交易过程中也面临不少现实争议。按数据市场交易流程,需进一步剖析数据场内交易迟缓深层次缘故。
需要完善交易前场内基础性公证。由于数据具有可复制性,数据持有和处理更为灵活。产权争议不只停留在“是谁的”,同时关乎背后的责任问题。数据的流动性,致使数据在收集、处理、购买、销毁等一系列流程中一直处于权利混同状态,实践中仍待判断各主体是否具有控制权限和违规可能。目前数据权属主要依靠审核、存证、确权、登记、出证的公证方式,这也是场内主要的争议解决方式。冗余的环节和复杂的程序会影响交易时效,公证效力和效率有待提高。
有待强化场内交易中程序性保护。从现有条件出发,可靠可信的交易结果依赖于双方技术强度,考验其对数据管理流程的熟练度和使用校验的技术力。具有可信力和积极评价的大型互联网企业是场内交易的主要组成,处于竞争劣势的中小企业更难入场,如何建构企业间信任是僵化市场的破局关键。场内普遍缺乏数据评估或担保的第三方机构,尚未建立起成套成体系的验证标准。交易市场未能充分给予供购双方广泛的交流渠道,而演变为备份形式的行政登记地,再次陷入在公共场域进行私域交易的怪圈。
缺乏交易后兜底性场内保障。尽管场内交易有区域主管部门背书,然而出现差错后却难以获得行政兜底。市场完全依赖双方自治达成交易,行政部门无法干预条款具体执行,不少交易合同中暗藏不公平条款和加重隐形责任。同时,数据经营权涉及范围较广,受数据要素的灵活性影响,企业较难完成自我举证,增加维权难度。在流通过程中也易出现篡改、欺骗、漏洞攻击等各类安全事件,有必要为交易双方提供安全后盾。此外,目前各地出台的条款中,尚未对违反情形和后果建立明确的处置程序,仅是作为倡议性条款,难以提供具体的实施指导。
借力改革提速数据场内交易市场
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应借力新质生产力先发优势,通过制度、市场、技术的改革深化,为数据场内交易提质增速。
革新制度完善场内数据资产管理。随着《“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数据二十条”等制度出台,我国从供给、流通、开发、产业化等环节着手指导数据要素市场。在此基础上,应细化各地区数据资产确权及管理制度,向优质交易抛出橄榄枝。完善场内数据留痕工作,实现交易过程中存储、管理、备份过程中的责任分配与第三方监督。建立市场统一定价标准,制定资产评估报告要求和项目名录。合规管理数据资产的投资和审计工作,如上市企业定期披露数据资产情况。结合标准合同和快捷审查通道,辅助场内优质产品快上快销。
革新产业释放场内数据要素潜力。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组建“国家级+区域级+行业级”多层次数据交易场所,从公共、企业、个人的实施数据多层级供给与监管,打造“交易场所+数据商+第三方服务机构”协同创新的多元生态市场。鼓励拓展产出下游,畅通高效市场循环流。支持智能家居、健康管理、AI助手等相关企业入场采购,抓稳数字市场直接用户群体。督促供应商清洗用户敏感信息,刻画特殊群体的需求画像,打造具有公益价值的数据产品。扩展企业端市场,延伸数据市场消费端,推动企业在许可范围内充分提取数据可用价值,提高整体利用率。
革新技术推动场内数据要素流通。数字政府建设先行,不少地区正试点探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打造技术优势,发挥新质生产力转型作用,贯彻《“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鼓励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继续加大研发力度,鼓励场内企业自主研发或采用安全可信的数据加密和脱敏硬软件,同时建立违规数据的智能监控和识别系统,保障交易全流程数据安全。紧抓数据质量,提高场内分级管理数据交易水平,引导质量不理想的数据流入学校、科研所等基础研究机构,辅助技术开发与市场分析。
(作者单位: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江苏分中心) 责任编辑:何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