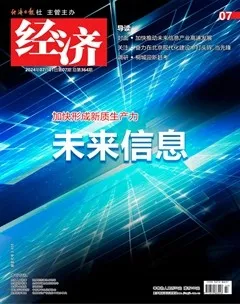把握好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中国机遇
2024-07-20韩力
当前,全球产业布局大洗牌、产业矩阵大调整的势头日趋明显。随着美国供应链不断向“友岸”“近岸”方向调整,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在美国供应体系中的占比不断上升,以“果链”为代表的产业外迁案例也频频出现,给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带来一定影响。
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动因与趋势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全球基本完成了四轮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且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新一轮(第五轮)产业转移逐步启动。以2018年为节点,我们将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8年-2017年,中国不仅仍然是全球最大的产业转移承接地,同时也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下开启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对外转移,但影响产业转移的动因仍然以经济因素为主。第二个阶段是2018年之后,受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叠加疫情和俄乌冲突影响,发达国家推行以供应链安全为名义的“再工业化”,全球产业转移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趋势和新特点,进而对我国产业产生深远影响。
三重动因:经济、技术和政治相互交叉融合加速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
其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贸易的收缩和受益不均逐渐破坏了主导全球产业转移的市场基础。一方面,中美经贸摩擦发生前,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代表的全球化虽未停止,但也已经进入缓慢下行通道。数据显示,2001年-2007年全球贸易平均增速为14.4%,2008年-2022年全球贸易平均增速仅为3.9%;全球出口总额的平均增速也从2001年-2007年的14.5%,降至2008年-2022年的3.9%。另一方面,第四轮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问题日益明显。分配不均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体现在发达国家内部。以美国为例,在第四轮全球产业转移中,受益于资本和高科技的航天航空等高端制造业和互联网科技企业迅速崛起,但钢铁等本土制造业逐渐消失。
其二,数字化、智能化趋势改变原有比较优势,使得部分产业回流发达国家成为可能。由于数字技术的兴起,数据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快速提升。数据要素相对位置的提升减少了劳动力成本对生产的作用,无人工厂、数字制造、机器换人等进一步强化了发达经济体的既有优势,为部分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提供可能。
其三,市场化路径失效催生各国“内卷”,大国博弈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及俄乌冲突等“黑天鹅”对跨国公司供应链布局产生影响。首先,大国博弈加剧,美国推出贸易牌、科技牌、人才牌、金融牌、地缘政治牌等一系列组合拳。其次,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客观上提高了各国对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要求,助推新一轮产业转移多极化、双向化。第三,俄乌冲突后,从跨国公司角度看,部分地缘政治风险已经转化为直接成本,对原有产业布局的效率造成极大破坏,企业必须重新布局以形成新的效率。调研显示,近年来企业对越南产业转移的趋势正在加速,尽管其中有企业主动布局的情况,但规避关税是最主要考量。以彩电为例,彩电从中国出口美国是原关税基础上加25%的关税,但从越南出口美国只有2%-2.9%,这种成本上的巨大差异成为左右跨国公司决策的重要考量。
五大趋势:政治化、多极化、双向化、绿色化和再垂直化。
非市场因素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力上升。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非市场因素在驱动美国制造业回流中的作用明显加强。
更多的转出国和承接国参与到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中。2018年以来,全球已经出现的局部性产业转移包括“中国—东盟、墨西哥”“美国、日本、韩国—东盟”“中国、欧盟—美国”等,不仅转出国和承接国的数量在各自增加,而且具有转出和承接双重身份的国家也在增加,多极化趋势明显。
部分产业低技术环节向更具成本优势的东南亚国家转移与高技术制造业向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回流并存。一方面,东南亚国家正在吸引大量的低技术环节。现阶段迁往东南亚国家的产业主要集中在手机、计算机、纺织服装、机械设备等加工制造业。
“双碳”目标开始影响产业转移底层逻辑。碳关税对产业转移最显著的影响在于,其缩小了不同国家之间碳成本的级差,高碳产品不再具备成品优势,跨国转移可能性大大降低。长期看,高碳产业更可能通过节能低碳升级来应对碳成本上升,而非选择跨国转移。
产业链重构从注重效率的“水平分工”向注重安全的“垂直分工”回归。以我国为例,伴随产业不断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对外转移,未来与欧美日发达国家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间贸易”必然大幅减少,而基于生产同类产品然后进行的“产业内贸易”将越来越频繁。“产业内贸易”要求我国和发达国家一样,均具有发达的国内消费市场,因此需要相互开放市场,以实现贸易利益的交换。这就意味着,随着中国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时对水平型分工的要求更加明显,由此与全球产业链重构出现的“再垂直化”趋势形成一定矛盾,需要在动态调整中实现平衡。
主要国家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的角色
中国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表现出双重身份和四重路径。
我国作为重要的一极深度参与第五轮产业转移,并同时承担了承接国与转出国的双重身份。
一方面,我国仍是全球产业的重要承接地,但2023年增速有一定下降。2022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万亿元,按照可比口径增长6.3%,其中制造业使用外资同比增长46.1%;2023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万亿元,尽管规模仍处历史高位,但也存在同比下降8.0%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正在成为对外投资大国,连续10 余年位列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三,但对外投资区域也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性。2023年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0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7%,其中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16.7%;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240.9亿元,增长28.4%。
新一轮产业转移中,我国形成了“内接-外扩-外迁-内转”四重转移路径。
内接,即通过自身优势吸引外资来华投资,是我国参与第四轮产业转移中的最主要形式。外扩,即中国企业在国内保留优势环节、在国外布局其他环节,是要素成本驱动和海外市场拓展的市场行为,主要表现为我国本土企业的“走出去”。外迁,即部分跨国企业将国内产能或潜在新增产能向国外转移布局,并进一步带动部分国内上下游配套企业转移。外扩和外迁的区别主要在于转移的动因,外扩主要是国内企业主动转移,外迁则是跨国公司推动的被动转移。内转,即由于东南沿海地区产业升级以及“腾笼换鸟”,部分产能向生产成本更低的中西部转移,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
从当前我国四重转移路径的情况看,内接方面,我国仍是国际资本的投资重点,但成本上升、政治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部分领域的海外资本来华投资意愿下降;外扩方面,高科技海外投资被干扰的同时劳动密集型主动布局节奏被打乱;外迁方面,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下,纺织、电子等产业被动外迁风险有所显现,但并非主流;内转方面,部分中西部核心城市承载力已经接近上限,内转整体速度有所放缓。
美欧、日韩与墨越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分别扮演了主导者、跟随者与受益者的角色。
美欧深受制造业空心化危机的困扰,在本轮产业转移中愈发强调制造业回流。推动制造业回流是近年来美国各届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欧洲方面,2012年提出欧洲“再工业化”战略,但整体效果弱于美国,且俄乌冲突使得欧洲去工业化压力加大。2022年欧盟FDI降至-1250亿美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也在趋弱。
日本在东南亚的布局明显加快。据统计,在2020年日本的“供应链弹性计划”发布两个月后,有124家日资企业申请迁往东南亚国家,其中30个项目获得补贴。韩国方面,不少跨国公司通过在墨西哥建立生产基地事实上响应了美国的供应链重塑战略。
在发达国家“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政策影响下,以越南和墨西哥为代表的“友岸”和“近岸”新兴经济体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从FDI看,越南、墨西哥等成为全球FDI的重要流入国。
有效应对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建议
整体看,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给我国带来一定的局部性风险,得益于我国大市场、全链条、多人才和新基建等四大内生优势,尚未出现成规模的外迁和产业空心化;横向比较看,短期内“越南制造”“印度制造”“墨西哥制造”都难以迅速替代“中国制造”。但不可否认,以“果链”为代表的产业外迁案例也频频出现,成为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不可忽视的因素,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综合施策。
首先,构建推动产业有序转移的全局观,掌握好产业转移的节奏性、原则性和针对性。
一是充分认识到产业转移的整体作用是正面的、积极的,但需要与自身经济发展节奏相匹配。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既要避免过急过快外迁造成的产业空心化风险,也要避免过度干预而阻碍产业国际化布局步伐。二是按照市场为主、政策为辅的大原则推动产业有序转移。多听企业诉求,优化政府举措,减少强制干涉,对企业的去留给予一定的宽容度,对于正常的对外转移不能过多限制。三是分类施策,应对不同类型的产业转移,避免一刀切。
其次,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对冲局部性外迁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是更大力度降低制造业成本,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切实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提高政策精准性和针对性,重点聚焦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以数字化、绿色化趋势为契机,将我国部分受劳动力成本影响较大的制造环节留下来。二是借助产业升级培育本土链主型跨国公司。把握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空间布局的主导权,基于本国的优势和本国的利益来调配全球资源。三是聚焦核心零部件与关键材料等环节。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快速攻关,切实增强“全链条”竞争力。
再次,挖掘内部承接产业转移潜力,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格局。
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用蓬勃发展的中高端产业的“大市场”优势吸引更多投资,弱化外迁带来的冲击。依托自动化、智能化,开拓汽车电子、航空航天、医疗电子、人工智能等中高端市场,用内需市场的扩大抵消行业外迁的影响。二是推进开放性制度改革,继续通过加大制度性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等,营造更加稳定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投资营商环境。三是抓住下一个世界产业转移承接地尚未成熟的时间窗口,积极引导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合理有序的产业转移。
最后,扩大国际影响力,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空间布局中的主动性。
一是主动谋划相关产业的全球新定位。推进我国与发展中大国在交通、能源、数字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抓住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的战略机遇,分享其发展红利,巩固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二是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创造更加良好的经贸环境。在RCEP已经正式生效并开始积极发挥作用的良好基础上,建议加快推进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自贸协定谈判。三是借势全球化布局,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升级。继续深化与产业承接国的产业链分工合作,继续推动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向上迁移,实现产业升级和贸易替代的双重目标。
责任编辑:陈希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