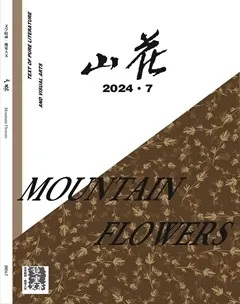捕月者的暮年
2024-07-18储劲松
故乡岳西有天下名山司空山,山中有太白书堂,前人代代相传,说是李白读书处。李白一生行迹半天下,手不释卷,绣口吐诗,所到处就是读书处也是作诗处,司空山是其避难之所,有读书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太白书堂深藏在司空山千岩万壑之中,四围松涛阵阵,位置极幽僻,附近有洗墨池、翰墨泉、奎心石、李白诗石刻、李白拂琴塑像等诗仙遗迹,有蜿蜒险阻的大唐古道,有明代中后期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罗汝芳所书“太白仙踪”摩崖石刻。山中的李白遗踪见诸典籍,绝非附会。南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记司空山和太白书堂:“中途断崖绝壑,傍临万仞,号牛背石。宗室善修者言,石如剑脊中起,侧足覆身而过,危险之甚。度此步步皆佳,上有一寺及李太白书堂。一峰玉立,有太白《瀑布诗》云:断岩如削瓜,岚光破崖绿。天河从中来,白云涨川谷。玉案赤文字,世眼不可读。摄衣凌青霄,松风拂我足。余兄子中守舒日,得此于宗室公霞。”周必大所说的《瀑布诗》即《题舒州司空山瀑布》,牛背石是司空山主峰狮子峰附近的一块巨石,形如剑脊,两边是深壑,上凿石级,古时是登顶的必经之路。
岳西在大别山腹地,从前荒陋不堪,不似今日繁华,山里人过去也见少识浅,不似今日自信。年少时就听大人说,县城西南方向有一座司空山,是中国禅宗大祖禅师慧可偕弟子僧粲卓锡之所,南北朝时期,慧可携达摩袈裟和一部四卷本《楞伽经》,由北朝南渡,来到司空山狮子峰下的仰天窝中,筑石室坐禅,终日面壁思空。曾几何时,村里的少年受电影《少林寺》和电视剧《达摩袈裟》影响至深,对少林功夫崇拜得五体投地,无论男女,一个个亦梦想当一名披斗篷挟宝剑行走江湖的侠客,以劫富济贫为己任,对与少林寺相关的司空山亦极是向往。又听乡间老先生说,司空山也是李白避难读书处,李白为司空山写了两首诗,收在《全唐诗》中。蒙昧之年,对这话半信半疑:李白那样伟大的诗人,像天上紫微星,应当栖身琼花瑶草簇拥的灵霄宝殿,至少也应当住在富庶文明的长安城里,怎么可能与皖西南边鄙、穷山沟里的岳西发生联系?但对司空山的神往之情,则因之更加深切了。
司空山离县城七十公里,其间山重水复,虽有三一八国道屈曲勾连,但在交通闭塞的当年,迢遥如在天之涯,去一趟并不容易。直到十六七岁,一个大雪初霁的日子,我才实现了朝山之愿。那个时候,侠客梦远了,文学梦悄然萌芽,朝觐司空山主要是为了寻访李白遗踪。我和几个发小踏上仰天窝左旁的石级,踩着积雪和厚冰,用三个半小时登上海拔一千二百余米的司空山极顶,然后用一个半小时下山。因为没有请向导带路,我们竟然两次错过了太白书堂,以及与诗仙相关的所有踪迹,好不遗憾。
李白写司空山的两首诗,却是记得清晰的。除了《题舒州司空山瀑布》,另一首是《避地司空原言怀》。诗云:
南风昔不竞,豪圣思经纶。
刘琨与祖逖,起舞鸡鸣晨。
虽有匡济心,终为乐祸人。
我则异于是,潜光皖水滨。
卜筑司空原,北将天柱邻。
雪霁万里月,云开九江春。
俟乎泰阶平,然后托微身。
倾家事金鼎,年貌可长新。
所愿得此道,终然保清真。
弄景奔日驭,攀星戏河津。
一随王乔去,长年玉天宾。
司空山坐落在岳西县店前、冶溪二镇交界处。从店前镇方向望过去,司空山如一尊天然大佛,背人蔼然而坐。由冶溪镇政府举头观瞻,其主峰如春笋细尖,斜斜插入半天云中,峰峦之上常年云遮雾罩,秋天久晴之日,则山气青缥可爱。登山路上,先是数千级石阶,接着是山中原隰,最后是悬崖峭壁上布满荆棘和茅草的逼仄野径以及石级,山羊、麂子、野猪、豺狼、野兔来来往往。如周必大所言,通往司空山的道途崎岖险峻,抵达山巅最后一个小时的路程,更是凶险,须双手伏地如野兽潜行,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摔得粉身碎骨。当年第一次登此山,一路上,我们诵读李白的两首司空山诗相互鼓劲,拽着树桩和草根小心攀爬。
年少不知世事艰,不识愁滋味,也不懂太白诗,只从字面上看见诗仙的豪迈放旷、傲睨不群和超然避世,却不知李白潜匿皖水之滨、卜筑司空之原,写这两首诗时,正被朝廷以附逆之罪通令缉捕,内心凄惶忧愁,远不似诗中那般逍遥自在。
李白受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案牵连,只身逃遁,避难司空山,时间为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初春。这一点由《避地司空原言怀》诗句“雪霁万里月,云开九江春”也可知。这一年大诗人五十七岁,已是人生迟暮之年。
此前,为逃避追捕,李白从永王军败之地丹阳沿水路南奔,先是逃亡到江西彭泽,后来躲进舒州司空山(唐代属舒州太湖县,民国时期划归安徽省岳西县),并在山中短暂隐居。不久,他出山继续奔逃,旋即被捕,关进了浔阳(今江西九江)监狱中。他被捕的地点不详,时间大约是至德二载(757)三月至五月之间。
因为二祖慧可,司空山成为中国禅宗发祥地,生于司空山下的赵朴初先生,将之称为中华禅宗第一山。又因为李白的两首名诗,以及萨都剌、罗汝芳、赵文楷、赵朴初等古今贤达的诗词歌赋,司空山成为了一座光芒闪耀的诗山。
诗仙不幸,罹遭大厄。
家山有幸,名存诗典。
误入永王李璘幕,最终因附逆之罪锒铛入狱,并长流夜郎,是李白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古往今来,对于李白入永王幕是被胁迫还是出于自愿,也一直聚讼不休。
李白文才天纵,仿佛天上文曲星下凡,青年时即以诗歌名扬四海,逝世后更是受百代追捧。但李白在世时,从不满足于世人仅以杰出的文学之士看待自己。他自视极高,怀抱安社稷、济苍生的崇高理想,以经纶之才自许。如其诗《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所言:“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出蜀后,他不愿走科举之路,而是遍交权贵,期望因之一朝平步青云。《上韩荆州书》:“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在诗文中,他常常自比管仲、范蠡、贾谊、张良、谢安、诸葛亮这些安邦定国的前代俊杰,深信自己可以做王者之师,也常以庄子《逍遥游》里的大鹏自喻。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身居宰辅之位,襄助君王治理天下,事成之后即拂衣而去,优游林泉,采药炼丹。《留别王司马嵩》:“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他最羡慕的人,其实是范蠡和张良。
李白六十二年的人生中,只有两次短暂的从政经历。
一次是唐玄宗天宝元年(742)秋,经玉真公主等人举荐,玄宗召李白入禁掖,为翰林待诏,所谓“代草王言,专掌秘命”,也就是掌四方表疏批答,同时应皇帝之需,随时制作应和文章。天宝三载(744)三月,因遭高力士、张垍、杨贵妃等人的谗毁和排挤,李白身不安位,主动上书恳求还山。玄宗观察其入朝以来的言行举止,也认为李白“非廊庙器”,于是赐金放还,诏书倒是多加褒美嘉奖。李白在长安待诏翰林,前后三个年头,实际上不足两年,随后挥泪出长安。
另一次是至德元载(756)岁暮,应永王李璘之召,李白入其幕为僚佐。一个多月后,李璘兵败被杀,树倒猢狲散,李白以戴罪之身仓皇出逃。
李白两次从政,结局都不美妙。前一次名义上是优诏放归,实际上是罢斥,还为布衣之身;后一次背负污名,尤其不堪。在《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诗中,李白也悲叹身世:“遭逢二明主,前后两迁逐。”观其出蜀以后行止,李白显然不像他自诩的那样满腹经纶,具备经国济世的卓越才能,甚至可以说政治识见很低,与范蠡、张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举一个例子,在永王幕中,李白认为李璘是受玄宗之命,率水师东下协助平定安禄山叛军,却不知李璘已心怀异志,有窥伺江左之心。李璘手下将领季广琛看得明白。《新唐书·列传卷七》,季广琛对诸位将领说:“与公等从王,岂欲反邪?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絓叛逆,如后世何?”众将一听如醍醐灌顶,于是割臂盟誓,纷纷离去。季广琛之外,另有江陵长史李岘、庐陵郡司马崔祐甫、鄂州刺史韦良宰,以及隐士萧颖士、孔巢父等人,深知李璘东巡无名、起心不善,都断然拒绝了李璘的征召。
李白却看不清当时的形势,以及李璘率水师东巡的真实意图。强烈的功名之心也蒙蔽了他的心智,他想趁此机会立一件大功。又兼永王接连三次派人卑辞厚礼请自己出山,李白颇为感动。《南奔书怀》:“秦赵兴天兵,茫茫九州乱。感遇明主恩,颇高祖逖言。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诗中他自言,之所以入李璘幕,是因为安史之乱中,玄宗避难入蜀,天下扰攘,自己曾受玄宗厚恩,想学东晋祖逖,协助永王廓清中原,实在没有附逆之心。
李白后来曾多次为自己入李璘幕辩解,说是受到李璘胁持逼迫。《与贾少公书》:“王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辞,扶力一行,前观进退。”大意是说,永王是玄宗第十六子,地位尊贵,又是统领数路兵马的主帅,他三次征召,限期入幕,自己无法推辞。《为宋中丞自荐表》:“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在这一文一诗里,李白更是申辩,入幕并非自愿,而是被永王“胁行、迫胁”。
北宋的苏轼和曾巩,也持胁迫说,并为李白辩护鸣冤。苏轼《李太白碑阴记》:“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辩。”曾巩《曾南丰集序》:“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但我以为,以苏轼和曾巩的政治智慧和通识大才,主张李白是被“迫胁、迫致”,应当是有意为贤者讳。
事实上,李白从庐山下山,入永王幕,并不是被胁持逼迫,而是出于自愿。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玄宗宠臣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造反,安史之乱猛烈爆发,河北诸郡和东京洛阳相继沦陷,战火迅速烧向西京长安。第二年也即至德元载(756)六月,在长安沦陷前几天,玄宗匆忙奔逃蜀郡。七月,玄宗下诏,以皇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使,统领众军收复两京;并以永王李璘、盛王李琦、丰王李珙分领诸道节度使,协助皇太子平定叛乱。玄宗没有料到的是,当月,皇太子李亨趁乱夺取了皇位,即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改元至德,尊玄宗为太上皇;并于当天派遣使者前往成都,向太上皇报告这一消息。因为动乱,加上路途遥远,肃宗的表疏未能及时送达玄宗手中。
其时,按玄宗诏命,李璘为江陵大都督,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节度使,封疆数千里,江淮租赋在江陵堆积如山。自幼生长在深宫中的他,未经世事,自以为富可敌国。他不满皇太子李亨不经父皇同意私自即皇帝位,加上他的儿子襄成王李偒有勇力,执掌兵权,劝其东下取金陵,因而萌生异志。李璘于是取用江陵租赋,招募将士数万人,随意任命官吏。肃宗看出李璘欲据有金陵、保有江表的不臣之心,诏令李璘还蜀,即玄宗避难处成都,但李璘拒不奉诏。至德元载(756)十二月,未经肃宗允许,李璘擅自率领水师东巡,自江陵沿长江往广陵而去。肃宗以高适为淮南节度使,令他与江东节度使韦陟、淮南西道节度使来瑱,通力讨伐李璘。
李璘水师东下途中,临时驻军浔阳,得知李白正隐居庐山,于是派人请他出山协助自己。这一年,距李白从长安放还、流落江湖已经十三年。这十三年中,他流寓山东,寄家室于兖州,自己飘零四方,往来燕、晋、梁、宋、吴、越这些州郡之间,没有哪一天不眼巴巴地西望长安,期盼玄宗再次召自己入朝为官,并多次低声下气地请求他人举荐、拔擢自己。其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直到仙逝前一年也未磨灭。这年岁初,李白将子女留在兖州,携妻子宗氏南奔避乱,先后寄身当涂、宣城、溧阳、越州、金陵等地。秋天,他听说安禄山部下崔乾祐已攻破潼关,玄宗避乱逃到成都,于是与宗氏从云游之地越州沿江而西,上庐山,隐居在屏风叠下。天下大乱,前程暗淡无光,他的心情是灰的。《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中夜天中望,忆君思见君。明朝拂衣去,永与海鸥群。”永王这个时候向他伸出橄榄枝,仿佛一道阳光照亮了他。征召文书到达时,他的激动心情,估计仅次于当年被玄宗召为翰林。
《周易·屯卦》,其《象辞》说:“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李白认为,当此乱世,正是自己大有作为之时。于是他欣然接受征召,来到李璘军幕之中。
由李白后来所写《与贾少公书》以及《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二可知,下山之时,他颇有得意之色,心情大好。他联想到东晋谢安高卧东山的典故:“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又联想到与谢安同时代的殷浩。此人在乱世之中隐居荒山近十年,当时朝野比之管仲、诸葛亮,所谓“起不起,以卜江左兴亡。”
妻子宗氏出身名门,是武则天朝宰相宗楚客的孙女。李白后来所作《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诗也说:“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陆离。斩鳌翼娲皇,炼石补天维。一回日月顾,三入凤凰池。”宗氏比李白有见识,反对丈夫下山入幕,观李白《别内赴征三首》诗意可知。诗中说:“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以战国时佩六国相印的苏秦自比,把宗氏比作苏秦之妻,嘲笑她轻看丈夫。宗氏无奈,倚门哭别。这也是李白自愿入幕的佐证之一。
李白投入李璘麾下,出于自愿的铁证,是他为李璘所作的《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在诗中,他一再为李璘和他的舟师大唱赞歌。第一首说:“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第三首说:“秋毫不犯三吴悦,春日遥看五色光。”第五首说:“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第八首说:“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龙骧出峡来。”第九首说:“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第十首说:“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其辞奉承太过,近乎阿谀。
李白之心,赤子之心也。他入幕的动机,是欲借李璘以立奇功,出于平定叛乱的报国热忱。他为李璘唱颂歌,并非赞同其作乱,而是没有觉察到李璘的异志,以为永王是奉父皇之命东巡,旨在勤王,“救河南,扫胡尘”,一清中原。并且,他认为肃宗和李璘只是同室操戈,缺乏皇室正统继承的顺逆观念。所以,虽是自愿,实是糊里糊涂地误入。这个政治上的糊涂人,甚至在《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第十首中赞扬李璘:“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意思是说,江陵大都督永王的府邸在云梦(江陵),这回要将金陵山(钟山)取作府中小景了。
至德二载(757)二月,李璘兵败于丹阳,中箭被擒,随后被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潜杀于旅舍之中。浩浩荡荡的江陵水师一哄而散,永王手下的幕僚和将领被朝廷通缉。李白先后逃遁至江西彭泽和舒州司空山,不久坐附逆大罪,系于浔阳监狱,被关押将近半年之久。
当年玄宗御前备受宠遇的词臣,后来流落江湖十多年无日不思建功报国的大诗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以叛逆之罪被投进监狱。
《周易·坎卦》初六爻:“习坎,入于坎窞,凶。”坎,象征险陷;习,重叠也。爻辞大意是:面临重重险陷,落入陷穴深处,有凶险。五十七岁于李白而言,是一个大坎。
正值春天,浔阳千花盛放百草连绵,牢狴之中却阴森潮湿,连青草都见不到一棵。李白痛心疾首,幽怨悲愤,日夜以头撞墙呼天而啼。他多次上书宰相崔涣、魏郎中等大臣,申诉求援。《万愤词投魏郎中》:“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诗中,他哭诉自己身陷囹圄,妻儿兄弟离散四方。末了以白玉比喻自己的清白,请求魏郎中出手营救:“如其听卑,脱我牢狴。傥辨美玉,君收白珪。”在致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江南宣慰使崔涣的求助诗《上崔相百忧章》中,李白说自己“见机苦迟,二公所咍”,意思是在灾祸发生之前,自己没有及时离开永王,被像汉代穆生和邹阳那样懂得见机而作的人耻笑。在《狱中上崔相涣》和《系寻阳上崔相涣三首》中,他请求崔涣拯救自己:“覆盆傥举,应照寒灰”,“应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能回造化笔,或冀一人生”。
在给妻子宗氏的诗《在浔阳非所寄内》中,他写道:
闻难知恸哭,行啼入府中。
多君同蔡琰,流泪请曹公。
知登吴章岭,昔与死无分。
崎岖行石道,外折入青云。
相见若悲叹,哀声那可闻。
所谓“非所”,也就是监狱。所谓“多君”,是赞美和感谢妻子,诗中用了蔡文姬归汉的典故。由诗意可知,宗氏也到处奔走,请求娘家人和其他有权势的人相助,想方设法营救丈夫。
这年秋天,李白终于出狱。他的获释,是因为两个贵人的鼎力相助,一个是宰相崔涣,另一个是御史中丞充置顿使宋若思。崔涣受命审讯李白附逆案,为之推覆洗雪,李白的冤情得以澄清。宋若思则径直将李白从狱中放出。
宋若思之父宋之悌,开元时期曾任河东、剑南节度使,是李白故交。开元二十二年(734)前后,宋之悌被贬朱鸢,途经江夏,李白当时正在那里云游,有《江夏别宋之悌》诗相赠。至德二载(757)八九月间,宋若思率兵赴洛阳平叛,途中临时驻扎浔阳,听说父亲的知交、大诗人李白被系狱中,宰相崔涣已审明无罪,于是自作主张,将李白从牢狱中放出,并聘为自己的军事参谋,掌管文书事务。获释后,李白给宋若思写了一首答谢诗《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
李白在宋若思幕中时间不长,大概不足两个月。他曾随军前往武昌,并代宋若思撰写《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为宋中丞祭九江文》《为宋中丞自荐表》等奏疏和文章。
《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是宋若思呈给肃宗的奏疏。其时,肃宗驻跸扶风。表中认为,南北分裂大局已定,又将形成南北分治的局面,因而力主肃宗迁都金陵。主张者宋若思和执笔者李白,都不理解肃宗驻行在于扶风,对于收复长安和洛阳的重要意义。由此也可以看出,李白的政治才能确实平庸,否则他必然谏止宋若思上这道不识大体的可笑奏表。
《为宋中丞自荐表》是宋若思向朝廷举荐李白的奏疏,由李白代笔。文中称:“臣所管李白,实审无辜。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霑,四海称屈。伏惟陛下大明广运,至道无偏,收其希世之英,以为清朝之宝。”不想,就是这篇荐表,又给李白惹来天大的祸事。
天下动乱之时,朝廷文书山积,应接不暇。宋若思从浔阳监狱中释放李白之后,曾向朝廷奏明此事。《为宋中丞自荐表》中有:“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覆清雪,寻经奏闻。”但肃宗和大臣忙于收复两京,没有注意到此表。举荐奏疏上达后,朝廷才得知李白已经出狱。对于肃宗皇帝来说,皇弟李璘抗旨东巡,企图据有江南,是谋反作乱,其幕僚李白为之出谋划策,罪不容赦,于是,诏命捉拿李白,意在将他诛杀。杜甫在怀念李白的诗《不见》中也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
李白闻讯,从宋若思幕中仓皇出逃,由浔阳逃到长江对岸的宿松,躲到山中,时为至德二载(757)十月。在宿松,他两次赠诗给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镐,请求张镐施以援手,并希望投到其麾下。《赠张相镐二首》第一首,前面有小序云:“时逃难,病在宿松山作。”诗中说自己:“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其事竟不就,哀哉难重陈。卧病古松滋,苍山空四邻。风云激壮志,枯槁惊常伦。”古松滋即宿松,西汉吕太后时置松滋侯国,以徐厉为松滋侯。诗中又申言自己的志向:“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李白不知道的是,这个时候,广平王李俶、副元帅郭子仪率领朔方、回纥、西域十五万将士,已经收复了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肃宗车驾已返长安。
张镐为李白求情,郭子仪也在肃宗面前为李白求情。郭子仪于李唐王朝有重构之功,《旧唐书·郭子仪传》:“十一月,广平王俶、郭子仪来自东京,上劳子仪曰: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郭子仪欠李白一个人情。唐人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记载:李白客游并州时,“识郭汾阳于行伍间,为免脱其刑责而奖重之。后汾阳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其报也。”《新唐书·李白传》也记此事。郭子仪表示,愿以所封赏的官爵赎李白的性命。他的谏言分量可想而知,肃宗自然应允。再加上其时两京已经收复,玄宗和肃宗安全返回长安,动乱眼看即将扫平,天下底定可期,朝廷亦宽宥罪人,从轻发落。《旧唐书·本纪卷十》:“十二月戊午朔,上御丹凤门,下制大赦。”《新唐书·肃宗本纪》:“戊午,大赦。”如此一来,李白捡回了一条命,从宿松返回江西,与宗氏团聚,并与朋友同游建昌、余干等地。
死罪虽免,活罪难逃,这年十二月,李白被判长流夜郎。
临行前,朝廷因“二圣”回銮,特“赐酺五日”,也就是开恩允许天下百姓宴饮,庆祝五天。李白身为罪人,不得参与,作《流夜郎闻酺不预》:“北阙圣人歌太康,南冠君子窜遐荒。汉酺闻奏钧天乐,愿得风吹到夜郎。”
夜郎本是古国,与且兰国同时存在,汉代被灭,属牂柯郡。唐朝为县名,属黔中道夜郎郡(珍州),在今天的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夜郎自大的典故即来源于此。帝禹时代,夜郎为荒服,到了唐代,仍是蛮荒之地,与浔阳有数千里之遥。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初,劫后余生的李白由浔阳启程,前往流放之地夜郎。行前作《流夜郎永华寺寄寻阳群官》:
朝别凌烟楼,贤豪满行舟。
暝投永华寺,宾散予独醉。
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
写意寄庐岳,何当来此地。
天命有所悬,安得苦愁思。
夜里投宿在永华寺,来看望他的宾客散尽,李白以酒浇愁愁更愁。与最中意的修道之所庐山渐行渐远,不知何日才能返山;与友朋也渐行渐远,不知何时才能重逢;自己已经是个五十八岁的老人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生还。诗人内心的凄苦,可想而知。
妻子宗氏和宗氏的弟弟宗璟,一路伴送李白到乌江边才回返。李白赋《双燕离》诗赠宗氏,诗中说“憔悴一身在,孀雌忆故雄。双飞难再得,伤我寸心中”,表达了对宗氏和远在兖州的儿女们的深深依恋,又作《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赠妻弟。
暮春初夏,李白走到了鄂州武昌县西塞山下的西塞驿;五月到达江夏,在这里逗留将近半年之久。盘桓此地的原因,我猜测是观望时局,期盼朝廷大赦。在江夏,他寻访旧交李邕故居修静寺,赋《题江夏修静寺》诗悼念李邕。又登黄鹤楼,望鹦鹉洲,作《望鹦鹉洲怀祢衡》诗,借曾经击鼓骂曹的汉末名士祢衡被冤杀的典故,大抒胸中愤懑。八月,又游汉阳南湖,与当地名士交往。
梦想中的赦书并未到来,他只好继续前行,秋天行至江陵,冬末进入三峡。这一路,李白作诗多首。《流夜郎赠辛判官》:“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赠易秀才》:“蹉跎君自惜,窜逐我因谁。地远虞翻老,秋深宋玉悲。”《留别龚处士》:“我去黄牛峡,遥愁白帝猿。”《赠别郑判官》:“窜逐勿复哀,惭君问寒灰。”《送郄昂谪巴中》:“予若洞庭叶,随波送逐臣。”诗意大多悲苦,有怨望之情。
《新唐书·肃宗本纪》和《资治通鉴·唐纪》记载,这年十月,因立成王李俶为皇太子,朝廷有一次大赦,“其天下见禁囚徒以下罪,一切放免。”但这次大赦,雨露之恩不及李白,可见肃宗对参与谋反作乱的李璘部下耿耿于怀。李白作《放后遇恩不沾》,诗中以西汉初年被谪放长沙担任长沙王太傅的贾谊自比:“天作云与雷,霈然德泽开。东风日本至,白雉越裳来。独弃长沙国,三年未许回。何时入宣室,更问洛阳才。”
乾元二年(759)二月末,李白乘舟从巴东行经瞿塘峡,途中登上巫山最高峰,看垂萝穹石、空谷积雪,听松风悲鸣、猿啼啾啾,傍晚下山,在客栈墙壁上题了一首《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词意沉雄,豪迈不减,但抑郁怀抱可知。诗中说:“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至此,李白在长流夜郎的途中,已经走了十五个月,沿途所受的风餐露宿之苦自不待言。
李白不知道的是,朝廷的赦书正在到来的路上。《唐大诏令集·卷八十四》之《以春令减降囚徒制》:“其天下见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其下注释:“乾元二年二月。”也就是说,李白流放夜郎,未到流放地即遇赦得释。后世有人说,李白已经到了夜郎,并说夜郎县治内,有李白故宅、旧井遗迹,在桃源洞还有李白听莺处。这些显然都是误传。遇赦后,李白有一首《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就是明证。诗中云:“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半道雪屯蒙,旷如鸟出笼。”屯与蒙,均是《周易》卦名,屯象征初生,蒙象征蒙稚,都代表着重生、新生。“旷如鸟出笼”,显言获赦之喜悦也。
几天后,李白抵达白帝城,忽然看见缤纷桃枝上有两只喜鹊在雀跃鸣啭。他站在树下,若有所思。是夜李白住在白帝城中,大醉而眠,清晨一觉醒来忽然接到赦书。李白惊喜而泣,立即返程。
春天的蜀水溶溶泄泄,山中桃瓣纷落江中,四野清明,草木滋长,得赦的人,眼中万事万物无一不美妙。自白帝城至江陵的归途,是顺水,小舟行驶如飞。抵达江陵,李白作《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尽,轻舟已过万重山。
此诗得江山之助,通篇只写舟行之速,而峡江之险已然历历如绘。辞气自然奔放,纵逸超迈,如云飞鸟逝,瞬息千里,也如诗人当时心境,晴明妩丽。李白的绝句冠古绝今,《早发白帝城》则是其绝句之杰出者。清人王士祯点评唐诗,把李白这首诗和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其三)、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推为“三唐压卷”之作。
乾元二年(759)初夏,李白回返抵达江夏,自夏天到秋天,在江夏盘桓了很久。遇赦得释,天地再新,李白复有积极用世之心,东山再起之意。
李白给江夏太守韦良宰写了一首长诗,题为《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中,他详细叙述了自己的生平经历,以及天宝十载(751)十月的幽州之行所见景象,安史之乱中皇帝奔逃百姓遭到屠戮的惨烈情形,自己入永王幕、入狱、流放、遇赦的过程。他回忆了自己与韦良宰的数次交往,并赞美韦良宰的诗作。他写此诗的目的,是请求韦良宰汲引自己:“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
在江夏期间,李白多次求人荐引,所请求的对象,上至朝官,中至郡守,下至县令。《送别得书字》:“圣朝思贾谊,应降紫泥书。”《江夏使君叔席上赠史郎中》:“希君生羽翼,一化北溟鱼。”又在赠友人诗作《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并序》中说:“今圣朝已舍季布,当征贾生。开颜洗目,一见白日,冀相视而笑于新松之山耶?”在《天马歌》中说:“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诗中仍以贾谊、大鹏、天马自喻,但与青壮年时期求人荐举时的自信自矜相比,此时的李白日暮途穷,已不复当年慷慨豪迈气概,言语多是“低颜色”之辞。
数番恳请他人提携,都没有结果,李白回首往事,悲愤难抑,瞻望将来,又倍感渺茫,于是经常痛饮,借酒发泄胸中的苦闷。《江夏赠韦南陵冰》:“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又说,“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深知此生功业已然无望,他忽转一念,自信笔下诗文可以像屈原一样流传于世。《江上吟》:“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某一天,李白在江夏遇见旧交僧人贞倩,将一生所作诗文的草稿尽数托付给他,希望贞倩能为他结集,刊布于世。《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仆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贞倩持诗人作品底稿回了汉东郡,没有下文。
一生中,李白作诗文无数,足迹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多作于酒后席上,写成后随手赠人,存有草稿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生前,他先后三次将草稿托付给三个人。第一次是天宝十三载(754),托付给好友魏万(后改名魏颢)。过了十七年,即李白逝世前一年,魏万编成《李翰林集》。可惜此集早已遗佚,仅存魏颢写的《李翰林集序》。魏颢在序言中说,安史之乱期间,他在乱离之中不慎将李白的手稿遗失,懊悔万分。上元二年(761)他因公事到山西,竟然在绛县神奇地见到残卷,惊喜之余,赶紧编排付梓。并说,只要李白还未绝笔,他将继续为其作品结集。李白第二次将草稿托付于人,即乾元二年(759),托付给贞倩,结果不了了之,不知是何原因。第三次是唐代宗宝应元年(762),临终前,李白将手稿万卷尽付当涂县令李阳冰,李阳冰于是年编成《草堂集》并作序。
李白来江夏的时候,葡萄正绿,转眼之间,梧桐树的叶子就黄了,时令到了秋天。百般穷愁无聊之时,曾任侍御史的友人裴隐自豫章石头驿寄来一封书信,约李白于当月月圆之夜同游洞庭湖,让他速行。裴隐的信于月初发出,收信地址是黄鹤楼,李白辗转接到书信,已经过了当月十五,但他相信裴隐一定在等他,于是携子女立即动身前往岳州(巴陵),与裴隐相会于洞庭。月下,他们泛舟湖中,忘世于诗酒。某夜,李白独自游湖,路经裴隐岩居之地,于是系舟湖畔,前去拜访。裴隐像是算到了李白要来,抱着一把琴从竹林深处出来迎接。当夜,裴隐弹《鹍鸡曲》助兴,两人就着月光下酒,烂醉如泥。李白作《夜泛洞庭寻裴侍御清酌》,末章云:“曲尽酒亦倾,北窗醉如泥。人生且行乐,何必组与珪。”
其时,李白族叔、刑部侍郎李晔和中书舍人贾至均贬谪在岳州,李白与他们同游洞庭,写有《巴陵赠贾舍人》《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等诗作。贾至亦有《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记此事。同是天涯沦落人,李白诗中多有宽慰李晔、贾至兼自宽之辞。他故作旷达,说“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但落寞意绪如洞庭秋色,如湖上月光,难以掩饰。
这年八月,襄州守将康楚元、张嘉延率部下兵马占据襄州城作乱,反叛朝廷。康楚元自称南楚霸王,叛军接连攻陷荆、襄、澧、朗等州郡。李白返回江陵的路途被阻塞,因此滞留沅湘之间,一直到第二年春天。他有《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两首诗记这次的荆襄之乱,后一首自注曰:“时贼逼华容县。”
秋天,李白曾赴零陵游赏。大书法家、僧人怀素家在零陵,当时怀素才二十出头,听说李白来到家乡,慕名前去拜谒。两人各怀高才,又性情相近,一见如故。李白观怀素作草书,赋《草书歌行》赠予怀素。诗中称赞少年怀素的草书天下独步,醉后下笔如闻神鬼惊、只见龙蛇走,并将他与王羲之、张芝作比,说在怀素面前,王、张不过是浪得虚名。
经过湘阴,李白作《泽畔吟序》,悼念老友崔成甫。
在零陵期间,李白作诗感叹身世漂泊,功业不就,宗党知交凋零,多成泉下之人。《秋夕书怀》:“感此潇湘客,凄其流浪情。”《门有车马客行》:
门有车马客,金鞍曜朱轮。
谓从丹霄落,乃是故乡亲。
呼儿扫中堂,坐客论悲辛。
对酒两不饮,停觞泪盈巾。
叹我万里游,飘飘三十春。
空谈霸王略,紫绶不挂身。
雄剑藏玉匣,阴符生素尘。
廓落无所合,流离湘水滨。
借问宗党间,多为泉下人。
生苦百战役,死托万鬼邻。
北风扬胡沙,埋翳周与秦。
大运且如此,苍穹宁匪仁。
恻怆竟何道,存亡任天钧。
自开元十二年(724)秋出蜀,“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浪迹江湖已经三十余年,少年壮志终成空,老大伤悲之辞令人泣下。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太白六十岁。
春天,他从洞庭返回江夏。秋天再乘舟到浔阳,与妻子宗氏团聚,寄居豫章。此间李白写有《豫章行》,追忆永王李璘事,自悼自伤。
不久,李白再度入庐山隐居,决意游仙学道,以遣余年。在给好友、殿中侍御史卢虚舟的诗《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他写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遨游太清”。此诗仙气缥缈,盛赞庐山风光奇秀,转而说寻幽不如学仙,邀约卢虚舟一道同游太清,也就是一起修道。
隐居期间,李白曾南入彭蠡湖,经松门,观石镜,探江源,缅怀谢灵运。在《过彭蠡湖》中再明学仙之志:“余将振衣去,羽化出嚣烦。”
转眼到了上元二年(761)。李唐天下其时并不太平,史朝义杀死父亲史思明即皇帝位继续造反,扬州长史刘展、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段子璋先后起兵作乱,台州人袁晁发动浙东农民起义,九月江淮之间又发生大饥荒。庐山虽高,风景虽美,朝雾晚霞、丹药方术、白拂尘和道家经籍却不能当衣当饭,李白被逼下山,流落江南金陵一带,又往来宣城、历阳二郡之间,投亲依友,靠人赈济度日。太白越到晚年,光景越惨,有多篇赠人诗作表达的主题,是希望对方周济自己。如《赠刘都使》:“而我谢明主,衔哀投夜郎。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所求竟无绪,裘马欲摧藏。主人若不顾,明发钓沧浪。”这是向刘都使借贷的诗,但下语极有斟酌。
这年秋天,李白听说史朝义贼焰复炽,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都统河南等八道行营节度李光弼出镇临淮(泗州),又欲立功报国,于是主动请缨入李光弼幕,希望“申一割之用”,但因生病半道折返。《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诗中以西汉周亚夫比李光弼,以剧孟比自己。李白的报国之心贯穿一生,历经挫折,凌云壮志始终不得伸展。每次在遭到打击之后,他的心绪会一度消沉,但要不了多久,又会满血复活,建功立业的热情再次高涨。一直到逝世前一年,六十一岁时,李白仍以抱病之躯赴李光弼军幕。所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诗仙足以当之。
可惜的是,此举实属回光返照,从此以后,太白真的一蹶不振了。
这年初冬,李白从金陵白下亭,乘小舟来到当涂,依附其族叔、当涂县令、李斯之后小篆第一人李阳冰。李阳冰《草堂集序》记此事:“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一直到宝应元年(762)春,期间李白一直在当涂养病。其在当涂所作诗歌,有一首《游谢氏山亭》。诗云:
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
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
借君西池游,聊以散我情。
扫雪松下去,扪萝石道行。
谢公池塘上,春草飒已生。
花枝拂人来,山鸟向我鸣。
田家有美酒,落日与之倾。
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
谢氏山亭应当就是谢公亭,南齐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的一座小亭。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闲居故乡山阴的陆游起复为夔州通判,自故乡入蜀,途中经过当涂,曾经游历此亭。其《入蜀记》载:“青山南小市有谢玄晖故宅基,今为汤氏所居,南望平野极目,而环宅皆流泉、奇石、青林、文篠,真佳处也。由宅后登山,路极险巇。凡三四里许,至一庵,庵前有小池曰谢公池,水味甘冷,虽盛夏不竭。绝顶又有小亭,亦名谢公亭。”玄晖,是谢朓的表字。谢朓是李白所仰慕的人。
品味《游谢氏山亭》诗意,可知其时安史之乱将彻底平定,李白在当涂养病,且有妻子和子女在身边陪伴。
宝应元年(762)三月,李白游历宣城,贫病交加之中,分外想念故乡绵州昌明县(原名昌隆,后避玄宗讳改名昌明,今四川江邮)青莲乡。这是李白最后一次出游,在皖南所作《宣城见杜鹃花》,也是其怀念乡土的唯一作品。诗云:“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乡思之情,既强烈又悲苦。出蜀之后,他再也没有回过故土,死后尸骨也埋在他乡。他又作诗悼念宣城擅酿老春酒的纪姓老翁,哀挽旧友蒋华,《哭宣城善酿纪叟》《宣城哭蒋徵君华》二首,均是伤人复自伤的言语。
接着李白游南陵,向上文所述刘都使借贷,用以偿还酒债。这个南陵在安徽南部,不是他当年应玄宗之召入朝为翰林,赋《南陵别儿童入京》,放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兖州南陵。东鲁兖州是李白中年时携子女所居之处,南陵是其住处所在的小地名,也有人说,是旁边的一座小山。李白诗《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亦可佐证其入京为翰林的南陵在兖州:“月出鲁城东,明如天上雪。鲁女惊莎鸡,鸣机应秋节。”
又游铜陵,夜里借宿在五松山荀姓老妪家中。多年世乱,民不聊生,农家生活尤其困苦,但山民朴厚,即使自家食不果腹,名闻天下的大诗人李白来了,一家之主荀老太太仍然做了一顿雕胡饭殷勤招待。雕胡即茭白的籽实,名菰米,可以食用,饥馑之年可以采来当粮食。雕胡饭不易得,古人早就认为是美馔。面对如此珍物,李白食不下咽,作《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说:“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
是年秋,李白返回当涂,仍旧依附李阳冰,病情一天天加重,自知来日无多。为报答族叔,李白为李阳冰的画像写了一首《当涂李宰君画赞》。此时,李阳冰的当涂县令即将任满,他不喜欢做官,打算挂冠而去,退隐山林。李阳冰《草堂集序》:“临当挂冠,公又疾亟。”成为族叔的负担,病笃的李白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以至精神失常。此时所作《笑歌行》和《悲歌行》,悲是悲,笑也是悲。万事付诸东流水,李白在后一首中说:“悲来乎,悲来乎。天虽长,地虽久,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且须一尽杯中酒。”诗仙平生爱酒、爱月、爱诗、爱古琴、爱宝剑、爱山水、爱功名、爱亲人、爱朋友,诗歌作品大体不离一个爱字。
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是太白绝笔《临路歌》(一作《临终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直到瞑目前一刻,李白仍自比大鹏。病榻上,他将手边所存的诗文手稿郑重交给李阳冰,拜托他代为整理结集,并请其作序。李阳冰在《草堂集序》说,自安史之乱起,八年来,李白的诗歌文章十丧其九,《草堂集》里收录的诗文,大多得之于他人。
宝应元年(762)十一月,李白卒于当涂。
《新唐书·李白传》说,代宗即位,以左拾遗的官职召李白还朝,而李白已逝。天上谪仙人李白终于回到天上,做了“玉天宾”(《避地司空原言怀》),也就是玉皇大帝的宾客。
皖南多李白故迹。
这些年,我常到皖南,无论是宣城、当涂、南陵、青阳,还是铜陵、池州、马鞍山、泾县,到处都有诗仙脚踪。皖南有福,诗仙暮年徘徊此间,山水因之生色,人文因之增辉。
三年前的春天,玉兰花开遍江淮时,我初到当涂,在谢朓、李白当年流连处,名为“青山”的青山之下,拜谒了李白墓园。穿过花木繁茂的曲径,进入园中,望到一座坟冢,见到墓碑上刻着“唐名贤李太白之墓”八个字,心中恍恍惚惚。镇静数分钟,仍然不敢相信李白的墓就在这里,离我的家乡仅一江之隔,走高速公路不过三百三十七公里,不过四个小时车程。
明知李白逝世于皖南,明知他的墓就在当涂,真的来到他的坟茔跟前,与诗仙面对面,还是如在梦游中。直到李白墓园第四十九代守护人谷常新,向我详细叙述其家族一千二百余年来世世代代精心守护李白墓园的故事,这才从迷梦中彻底醒来:哦,李太白,你原来就在这里。
也难怪恍惚。李白身上有太多的不解之谜。
他的郡望是谜,祖先是谜,父亲是谜,母亲是谜,兄弟是谜,出生地是谜,行辈是谜,“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的地点是谜,死因是谜,确切的出生和逝世年份也是谜。
关于祖先,李白在《赠张相镐》中自述,是西汉飞将军李广之后,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新唐书·李白传》也如是记载。唐朝皇帝自称是李暠后裔,所以李白认为自己与李唐皇室同宗。有人则说李白拉大旗做虎皮,其实是自抬门第的诡言,因为《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所载李暠后代,并无李白这一支。
关于他的父亲,只知道叫李客,并且是化名而非本名,具体是哪里人、做什么营生,无任何史料记载。李白现存诗文只有一篇提及父亲,即《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有人说李客是胡人,以经商为生,持此论者如陈寅恪、郭沫若。也有人说李客在西域经商积累了巨资,然后逃归蜀地,隐居绵州昌明,家中非常富有,否则李白云游扬州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万,钱从何来?但这些说法都是猜测,并无确证。有关李客的文字,只有范传正所作《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的只言片语:“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范传正的记载,出自李白之子李伯禽(小名明月奴)的手迹,必然无误。也就是说李白的父亲本名不清楚,但后改名李客,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范传正又说,李客从西域逃归绵州昌明,做了一个不问世事的高隐之士。
关于母亲,李白现存的文字中只字未提。有人说其母是胡姬,也就是以歌舞侍酒的西域女子。显然不可能,因为李白写有多首关于胡姬的诗,如《少年行三首》其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如《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如果母亲是卑微的侍酒女,他为母亲避讳,不可能写胡姬,更不会如此写胡姬。
关于李白的行辈,李白诗文中,他称为族叔、族兄、族弟、族侄的人数量众多。但古今李白研究者依照《旧唐书》和《新唐书》仔细考证,发现李白的辈分忽高忽低,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有蜀中说、中亚碎叶说、条支说、焉耆碎叶说等等,多数学人认为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即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当时属唐朝安西都护府。但清人王琦、晚清民国黄锡珪所作《李太白年谱》,认为李白出生于蜀地,即绵州昌明,依据主要是李白好友魏颢的《李翰林集序》:“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
关于李白的生年,有四种说法:神龙元年说、圣历二年说、长安元年说、神功元年说。生年不同,相应地,其行年、逝世之年也就众说纷纭。李白称为族叔的李华(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一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所写《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明言李白“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也就是说李白死时六十二岁。北宋曾巩也将李白的生年定为长安元年(701),清代王琦和现当代多数学人如詹锳、安旗、郁贤皓等,通常认同李华、曾巩的主张。本文叙事,遵从长安元年说。
凡此种种,扑朔迷离。近年读古今人所作李白年谱,诸种观点相左,叫人莫衷一是。以至在亲眼见到李白墓之前,我下意识地以为当涂的李白坟冢,也只是一个传说。
在李白墓前,春阳和玉兰花雨洒满肩头,我行跪拜之礼,心中无限感慨,并祈求诗仙分我一羽凤凰毛,助我文章之笔。
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说:“李白初葬采石,后迁青山,去旧坟九里。”采石即采石矶,又名牛渚矶,在今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的翠螺山麓。青山是山名,又称谢公山、谢家山、谢家青山,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曾筑室于此山之南。《新唐书·李白传》说,李白逝世五十六年后,即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时任宣歙观察使范传正到坟前祭拜李白,得知李白有两个孙女嫁在当地平民人家,言行颇有风范。见面后,她们向范传正哭诉道:“先祖志在青山,顷葬东麓,非本意。”范传正令当涂县令诸葛纵,遵照李白生前意愿,将其改葬到青山之下,并立碑两块。范传正作《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文中说李白“晚岁渡牛渚矶,至姑孰,悦谢家青山,有终焉之志。盘桓利居,竟卒于此。”《新唐书·李白传》:“白晚好黄老,度牛渚矶至姑孰,悦谢家青山,欲终焉。”姑孰即当涂。
青山之下的李白墓枕山面水,坐北朝南,是一个安眠的好地方。墓园占地一百亩,园中有“诗仙圣境”牌坊、眺青阁、青莲书院、太白祠、太白碑林、十咏亭诸胜迹。
李白的死因,亦有多种说法。
李阳冰《草堂集序》对此语焉不详,只说“公疾亟”。中唐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说“遂以疾终”。《旧唐书·李白传》说他是饮酒过度醉死的。晚唐皮日休说,他的死因是腐胁之疾,见其《李翰林诗》:“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所谓腐胁疾,也就是长期沉湎于酒,导致胸部溃烂。五代王定保所著《唐摭言》,则主张李白是醉中下水捉月溺死的,他的这种观点自唐宋至今流传甚广。如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台。”
综合以上诸家说法,我以为,李白有可能是晚年得了腐胁之疾,最终死于醉中捉月。
《唐摭言》说,仙逝之夜,李白穿着玄宗皇帝当年所赐的宫锦袍,畅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大醉之中望见江中月影,俯身捉月,因之而死。虽无确证,但醉中捉月,符合李白纵逸如仙的性格特征,与他生平言行也相类似。
实际上,李白就是一个捕月者,一个终生都在捕捉月亮的人。
那月亮,既是天上明月,也是诗歌之月、文章之月、功业之月,既真实美好,又虚幻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