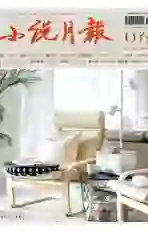未竟的河滩
2024-07-03李静睿
一
我们这种人,总是在等电话的。又等,又怕。肖运生说:“电话嘛,有点像鬼。”我问:“什么意思?”肖运生说:“来之前你都不晓得的嘛,说来就来了。”
接到电话后,我去了尼罗河畔。车被肖运生开出去了,我问他怎么办,他说:“要不等我,要不你打车嘛。”我懒得等他,也没有打车,一丁点路,我心想,不至于的。结果那小区建在山上,从一期到四期海拔逐渐上升,电话里说是四期,得绕着圈往上走差不多半小时。我出了一身汗,热也不怎么热,但四川的潮气像一条蛇,把每个人紧紧缠在里面。
五月,山桃结了硬硬的青绿色小果,一个女人站在一株桃树下等我。我远远就吃了一惊,那是个美丽的女人,长发散开,穿一条美丽的绿丝连衣裙,腰上胡乱系了个结,一根细细的金链子,往不可知的区域蔓延。我不大敢直视她,只是匆匆两眼,也看出她非常憔悴,又没有化妆,一眼即知四十岁向上,但奇了怪了,往后好几天,我都在想着她疲倦的眼神、憔悴的脸。
我定了定神才开口:“易小姐?”
她点点头,指着一楼一扇打破了的窗户说:“半夜进了人。”
我打开执法记录仪随口说:“我还要等个同事……算了,走吧,先去看看。”
一楼的三居室,带一个五十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客厅和厨房都开了门,直接通向院子。我从院子进去,四处都乱,一半是硬化瓷砖,一半种了密密花草,硬化地面上堆满纸箱和编织袋,还有两把藤椅,挨着栅栏,摆在一大蓬绣球前面。绣球无人料理,却仍然蓝而繁盛,不知道谁扔了个烟头,好端端一朵花,看着闹心,我下意识地把烟头拂下去。
烟头掉在泥上,我刚想捡起来扔了,易小姐过来,胡乱踢开几个纸箱。刚搬进来,还没收拾好,她说。角落里有一株细叶榕,初夏,树叶幽幽,和她的裙子一个绿色,那种绿阴森森的,带点鬼气。
主卧没有开屋门,但有一个转角飘窗,人是从这里进来的,一地碎玻璃碴,没有血迹,那人倒是很小心。卧室里四处都被翻过了,一地衣服。我戴上手套,拿起一件墨绿色衣服看了看,发现那是一件蕾丝内衣,又赶忙放了下去:“都少了什么?”
“一块表,一对耳环。”
“大概价值多少?”
她想了想说:“两万多块,表两万多块,耳环不值钱。”
“有什么特征?”
“没什么特征,欧米茄,蓝色的,基本款。耳环是一对小星星,褪色了,好多年前的。”
我看看卧室的床,和窗户只隔两米:“这么大动静,你就没听见?”
“我昨晚睡在客厅,收拾东西收拾累了,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
“你家别的人呢?”
她笑起来:“我家没别人。”
我有点尴尬,又看她一眼。电水壶叫起来,她泡了茶递给我,给她自己也泡了一杯。我吹着茶沫子,不是自贡人喝的茉莉花茶,而是西湖龙井。茶色青绿,我想到院子里郁郁葱葱的柚子树,又看了看她身上的绿色连衣裙。到处都绿,深深浅浅,像一个又一个的绿色旋涡。
我渐渐感到眩晕。“屋里有监控吗?”我问。
她摇摇头。
“小区有吗?”
“有的,但这边没有。”
我看了一圈,她这一排房子对着小区围墙,围墙那边是武警的打靶场,打靶场是露天的,这一排就没有装监控头。打靶场往下走是旭水河,所以这里才敢叫“尼罗河畔”,那一片是个浅滩,水也干净,虽说政府不让下水,但一到盛夏,还是有不少人在水里泡着。沿着滩的一圈水不深,可以一面泡,一面伸手去抠河底的螺蛳。嫌泡不开的就往前游,开始水浅,但再往下游有一段有个涡,每年都有人死在涡里面。大家都说,那边有河妖,每年要收一个人做祭,如果你信这个,就等今年有个人死了再下水。我小时候没住这一带,但同学里总有人说,今年的人死过咯,可以下河咯。去年那个人淹死之后,我和肖运生过来,我说,这么多年了,这个河妖也不挪个地方,也没修炼出来。肖运生不说话,铁青一张脸,看着眼前的河滩。
我又进了院子,一时不知道还要干什么,索性在藤椅上坐下来。藤椅那边就是隔壁院子,看着很久没人住了,有个野猫灵活地在两个院子之间穿梭,落落大方,这是它的地盘。我坐了一会儿,看着野猫把刚才那个烟头叼起来了,小心翼翼地藏在角落一个纸箱里,那地方大概是它的窝,远远看去不少零碎玩意儿。
我也点了一支烟,给肖运生打电话:“老板,你咋还不到?”
电话那边有鼎沸的人声,他打了个哈欠:“入室抢劫?人受伤没有?”
“盗窃,单身女人,没受伤,没有监控。”
“人没事就不着急了。你先回来,今天不想动车了。”
我有点不高兴:“我走上来的。”
他又打了一个哈欠:“你是年轻人啊。”
肖运生把电话挂了。她也出来了,拿着我的那杯茶,我有点抱歉:“同事有别的案子,要不你先去所里,做个笔录。”
她想了想,说:“等你们的人都来了吧,我再和你们一起回去,今天有点忙。”她指了指一地的玻璃碴,说:“我得收拾一下。”
“那你今晚别睡家里了。你有别的地方睡吗?”
“有,我爸妈就住丽景苑。”
我点点头,那个小区离我们刑侦大队很近。小区门口两排美食街,同事们下班总去那边喝酒,水煮克猫(牛蛙)、卤兔、葱葱烤鲫鱼、魔芋烧鸭子。肖运生下班是必定要回家吃饭的,但他隔三岔五会去一家凉菜店打包带走,那个老板是他中学同学,他们似乎不怎么熟,见面客客气气。肖运生总叫一样的东西:三两凉拌猪香嘴、两个兔脑壳,兔脑壳免辣,那是给他幺妹啃的。兔肉营养高,纯蛋白,肖运生总这么说。
老板是个真老板,生意多,并不总在,但凡他在店里,肖运生一露脸,他总要亲自接待。老板姓王,大名好像就叫王老板,因为没人叫过别的名字,他一站在凉菜店里,大家都喊“王老板”。王老板见了肖运生,永远不肯收钱,而肖运生则永远要给,两个人有时候几乎要打一架,肖运生总是赢的。在派出所这么多年了,肖运生没出过什么大事,升也升不上去,只有在这里,他好像必须赢。
后来我才听别人说,王老板也离了婚,也没孩子。我刚要油然而生一点同情了,别人说:“同情你个铲铲哟,他爸是哪个你晓得不?是我们以前的副市长!”我说:“副市长的儿子开凉菜店?”那人又说:“倒了的哟,判了十年。”“然后呢?”“人是倒了,本钱还在的嘛,人家儿子自己创的业,现在全球二十八家分店。”我说:“全球最远是好远哟?”那人说:“不晓得,反正内江有的。”我说:“然后呢?”那人说:“钱嘛,有啥子然后,然后就是人家住大别墅的嘛,想换女朋友就换女朋友,想躺着数钱就躺着数钱,要啥子有啥子的嘛。”我说:“听着和别的有钱人也差不多的嘛?”那人说:“有钱人嘛,都差不多的,烟嘛是人家只抽黄金叶的。”我说:“我老板也抽黄金叶,不是十几块钱一包?”对方看我一眼:“天叶晓得不?你去搜一下天叶好多钱。”我正在搜,那人又感慨:“听说人家连最里头的槽牙烂了,都镶了金牙。”我说:“纯金的啊?”那人说:“啊,你以为呢?”我说:“纯金的会不会有点软哟,咬得动不?”那人也疑惑:“咬得动吧,人家有钱人的金牙可能不一样哟。”
听了金牙的故事,又想到肖运生每个月的工资条,以及那张憨憨的、只有我会叫他老板的脸,我自以为理解了肖运生,理解了他为什么必须付费来这一架。他们打架的时候就像真的在打,两个人都满嘴脏话,额头上暴起青筋,为三十块钱满身大汗。王老板样子长得原本就怪,丑也说不上丑,就是让你心头不舒展,一打架更是想揍他两拳。揍是不可能揍的,我只是一直想看看人家嘴里头是不是真的有金牙,是纯金还是镀金,但王老板嘴巴始终没有张那么大。肖运生分明可以不去的,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是一次又一次去买兔脑壳,渴望遇到王老板,渴望遇到王老板然后打起来。有一次打完了,我问肖运生:“你不能换一家凉菜店啊?好几家的兔脑壳都还可以的嘛。”肖运生气喘吁吁,拎着两塑料袋凉菜,两个兔脑壳切成四块,脑花露在外面。他说:“你懂个屁。”
我该走了,却忍不住又去客厅坐了一会儿。客厅空荡荡的,绿色沙发,实木茶几,电视柜上没有电视,倒是搁着一张照片,大概是搬家翻出来的,塑封漏了气,照片上都是斑斑黄点。上头一排红字,写着“旭水中学高一(二)班歌咏比赛留影”,下面是密密匝匝的穿着校服的男生女生,男生穿不合身的灰色西服,女生穿白色衬衫,翻出大领子,配蓝色背带裙。我想从里面找到易小姐,但那几乎不可能,所有人都一模一样的红脸蛋,男生女生无一幸免,女生梳高高马尾,男生全是“郭富城”。前面有两个领唱,一起举着班级名牌,男生发型在郭富城和刘德华之间,除了个子高,别的没什么可说的,憨里憨气一张脸,他身边是一个惊人美貌的女孩,她那张红脸蛋分外红,但她整个人都幽幽的,像《聊斋志异》中的美人,误打误撞来了人间,还要参加歌咏比赛。
实在没什么理由再不走了,正午的太阳打在柚子树上,我应该打辆车,但我也像《聊斋志异》中过了夜的书生,有些恍惚,只知道慢悠悠步行往下走,直到走出一身又一身湿汗。我经过美食街,去凉菜店买了二两猪尾巴,一个小伙子给我剁尾巴。
我说:“王老板今天没来?”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王老板把生意都结咯,老板说他要结婚移民咯。”
我拎着那一点点猪尾巴,心想,日起鬼哟,这下肖运生不晓得咋子办。
啃完猪尾巴,肖运生才从外面进来,胡子拉碴一张脸,警服上滴了油汤,拎着一个盒饭。去年从警校毕业,我顺顺利利进了贡井分局刑侦大队,试用期工资三千五百块,转正后五千三百块。这种工作如今已经是好得不得了,我是意气风发进去的,一进去就遇到副中队长肖运生,然后就到了今天。
肖运生怕也有四十五六岁了,前两年离了婚,一个人带着女儿肖一诺住回了父母家。那房子在一个斜坡上面,是当年哪个机关集资建的房,过了马路就是张家花园。我去过他家,门外几株参天老树,盛夏时也没有一点光线,房子大而破,一股老人味。后头有个天井,摆了七八盆花,肖一诺拿着一把玩具铲子,在土里找蚯蚓玩。肥肥的蚯蚓从土里钻出来,我以为小姑娘会扔掉铲子哭,但她冷静地把蚯蚓捏起来给我们看,肖运生极有耐心,把那条蚯蚓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肖一诺非常高兴,给我们去冰箱里拿冰棍,我们蹲着吃冰棍,看了好一会儿,那条蚯蚓慢慢爬回土里。
肖运生这个人也没什么,无非不修边幅一点。该完成的工作他其实都定时定点完成,去年上头让抓电信诈骗,他也天天跑小区,让上当的公公婆婆们登记,一天十二个小时的工作量,也从来没听他抱怨。但奇了怪了,就这样一个人,偏偏像旭水河里的那个涡,好像能拽着身旁的人掉进里面。跟着他也就一年,我已经习惯了每天去队里先拧开保温杯,往里头扔两颗胖大海。我还习惯了跟自己说:“案子嘛,没破就没破嘛,也不可能都破的嘛。”
肖运生津津有味地吃盒饭,吃了一会儿才想起来:“笔录做完了?入室盗窃那个。”
我换了两颗胖大海:“没呢,说下午有事,等我们再上去。”
“这人倒是不慌。”
那张黯淡的脸浮在眼前:“就是,一点都不慌。”
他一筷子叉起一块回锅肉,又卷了些米饭:“入室盗窃不好破哟,要劝人家想开点。”
我想到那个女人,绿色的院子,绿色的卧室,有风的时候绿裙子紧紧裹在身上,一时有点惘然,那个女人,看着什么都能想开。队里另一个同事从外头进来:“老板,我出一趟警,旭水中学门口几个娃娃遭了抢。”
肖运生抬起头:“等我十分钟,我也去一趟。”
他急急慌慌吃饭,肖运生也是旭水中学的,他对那所学校不知道有什么感情,去年学校食堂被偷了三只走地鸡,他前前后后跑了五趟,最后把一个看着老实巴交的阿姨抓了进来。我觉得有某个地方不对,像有些东西在面前飘浮,我看他一眼,又看他一眼,终于抓住了什么:“老板,你中学什么发型?”
他感到莫名其妙,回答:“发型?郭富城吧?那时候大家不都是郭富城……不对,也有一点刘德华。”
那张胡子拉碴的脸上渐渐浮出一个高高的红脸蛋少年,我兴奋极了:“老板,原来那个女的是你高中同学。”
“哪个?”
“入室盗窃那个啊,头发好长。”我顿了顿,“那个女的有点怪,什么都是绿的。”
肖运生黢黑一张脸,忽然惨白起来:“什么名字?那个女的叫什么?”
我打开手机,翻出上午拍的身份证:“易晚星。她叫易晚星。”
过了很久很久,肖运生才说:“哦。”
二
入室盗窃案两个多月都没破,易晚星想把案子撤了。
肖运生说:“公诉案,你以为想撤就撤哟?破不了咋个办?破不了慢慢破嘛,你也不着急的嘛,要着急我比你着急的嘛,我身上还要背破案率的嘛。”
易晚星不着急,肖运生确实有一点,但不是为了破案率。他如今刮了胡子,露出一张大家都不怎么熟悉的脸,我现在才知道他的脸果真长得如此之憨。脸洗得很干净,警服也抻抻展展,衬衫扣到最上面一颗扣子,大热天,我看他每天都通红一张脸。易晚星找了个兼职,就在这附近教钢琴,有时候会来派出所坐坐,她还是那个样子,还是那条绿色连衣裙,又不化妆,只涂一点口红,更显得憔悴,但又非常美。大家都不大敢看她,她一来每个人都装作很忙,肖运生其实也不敢看,他如今从里到外都憨透了,抱着他的保温杯,满头大汗:“学钢琴贵不贵?”
易晚星抱着两本琴谱,找了把藤椅坐下来:“还可以吧,一节课一百五十块。”
“我都不晓得你会弹钢琴。”
“我妈是盐厂子弟校的音乐老师,我六年级就过了钢琴十级。”
“我都不晓得你是盐厂子弟校的。”
“后来都倒了,没有子弟校了。”
肖运生有点慌张,想把话头转回来:“明年,明年我让一诺也跟你学。”
“一诺是你女儿?”
肖运生郑重其事地拿出手机,给易晚星看一诺的照片:“明年六岁……六岁能学钢琴了吗?”
易晚星看着他:“明年再说吧,明年……明年我都不一定还在。”
肖运生不说话了,往保温杯里扔了一颗胖大海。胖大海像他,有点憨,也有点苦。
我也问过他:“你到底什么想法?”
肖运生还在装憨:“什么想法?”
“你高中没跟人家表示的啊?”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也想表示的,后头……后头出了事。”
“什么事?”
肖运生到底没告诉我什么事,也没告诉我如今他表示了没有。大部分时候他都在憨或者装憨,易晚星坐了一会儿也就走了,飘来飘去,像一朵绿色的雨云。我们七嘴八舌,骂肖运生不争气,他也不争辩,垂头丧气喝他的胖大海。我最近对胖大海有点抗拒,把肖运生送我的一玻璃瓶都扔了,我现在喝红茶,袋装茶没什么意思,也贵一些,但那个茶包让我和眼前这一切都有点距离。
肖运生终是开了窍,那天易晚星要走未走之时,他突然倒了杯茶:“能不能等我半小时?我请你吃个饭。”易晚星等了他一小时,两个人才往美食街走,风鼓动易晚星的绿裙子,肖运生神色仓皇,东张西望,像要吃什么最后的晚餐。晚餐选了克猫,我故意也去,就坐在他们旁边。肖运生憋了一脸汗,示意我快走,我偏偏还把桌子挪了挪,可以听得清楚点。
克猫现杀现剐,上菜极慢。我见他们两人沉默着剥了很久盐水花生,肖运生才开口,指指马路对面的凉菜店:“那是王宇的生意,王宇你记得吧?”
易晚星说:“记得,盈盈的男朋友。”
我在旁边插嘴:“换老板了,人家老板要结婚移民了……老板,你看看人家。”
肖运生惊了一下,像个喝茫的人突然醒过来。他有一阵没来买凉菜了,易晚星出现后他一直处在喝茫了的状态,像过于严密的生活中掉了一个螺丝钉,顾此失彼忙不过来。但他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个消息,电话响了,肖运生接完电话说:“不好意思,河里头淹死个人,我要去处理一下……你先吃,我快得很。”
我也站起来,但易晚星已经招呼老板买单:“我跟你一起去吧,我也想看看。”
肖运生说:“没得必要吧,估计就是那个涡,你也晓得,每年都死人的。”
易晚星说:“你说我晓不晓得?”
肖运生好像被噎住了,于是我们都往旭水河走。盛夏到了顶点,街上每个人都像泡在水里,有一种湿淋淋的狼狈。我们经过一株又一株细叶榕,这种树一旦长起来,简直可以一手遮天。沿路有婆婆在卖黄桷兰,易晚星买了一串,找不到地方挂,就一直吊在手上,那股香味一直缠着我们,直到河滩。
河滩上已经站满挤挤挨挨的人,今年雨水稀少,水位退得厉害,露出青色滩涂,有孩子拿着小铲子,在滩涂的缝隙挖螃蟹。我们拨开人群,法医已经到了,摇摇头说:“不晓得哪儿漂过来的,起码死了一个多月了,都泡胀了。”
肖运生说:“好久验尸?”
法医打了个哈欠:“明天嘛,明天再说。一看就是淹死的,也没得啥子好验。”
肖运生点了支烟,递到法医嘴上:“方医生,晚上加个班嘛,我抓紧写个报告。”
法医吐了个烟圈:“肖运生你咋了哟,今年想评先进了哟?”
肖运生戴上手套,蹲下去给那人翻了个身,确实什么都看不清了,但四周围观的人还是往后一退。我也往后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尸体。过去一年刑侦大队最大的案子是菜市场有个剐兔的男人,剐着剐着转手给老婆脸上来了一刀。就那个场面,我吐了两回。今天倒是还好,法医说得对,死太久了,你甚至不怎么能意识到那是尸体,像是烂成一缕一缕的衣服,裹住模模糊糊一个发胀的人形,我无端想到胖大海,又无端想到我再也不会喝胖大海。
大家对着那个人形议论纷纷:“河里头洗澡抽筋了啊?”
“不可能,你没听法医说,都死了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前还下不了水……再说了,你下河洗澡还穿牛仔裤啊?”
“自杀的吧?”
“应该是吧,不晓得咋想不开。”
“唉,没得必要嘛,五月份还是多冷的,自杀嘛跳个楼就是了,没得必要跳河嘛。”
有个老头儿很确定:“电鱼的,漏了电。”
旁边有人拎着鱼篓:“不可能,这河里头有什么鱼值得半夜来电?我给你说,我钓了二十年了,这河里头都是鲫鱼和白鲢,有条乌鱼就顶天了。”
又有人说:“河里头有水蜂子,水蜂子一斤八十多块。”
拎着鱼篓的人说:“你晓得不水蜂子为啥子叫水蜂子?”
我正想知道水蜂子为什么叫水蜂子,肖运生已经蹲下来拨拉尸体,漫不经心,像是还着急回去吃克猫:“回去对一下失踪人口……最近也没人报案啊。”
易晚星原本在我后面,她突然往前了两步,蹲下去想摸尸体的手。我拉住她:“你干什么?这不能碰。”
易晚星站起来,口红掉了色,让她更显苍白。她微微发着抖:“手表,那是我的表。”
肖运生愣了一下,才把那件烂朽了的衬衫掀开。确实,左手上是一块蓝色欧米茄,表带泡得褪了色,表已经停了,显示时间是三点二十分。不远处有孩子被螃蟹夹了手,哇哇哭起来,津津有味看尸体的人被分了不少过去,又津津有味看那孩子哭着想把螃蟹甩脱。我突然想到,今年河妖收的那个人已经进了涡,往后大家就可以放心下河。
我重新给易晚星做了个笔录,肖运生理应在场,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回所里就说自己要找人汇报,给我安排了另外一个同事。天已经黑尽了,我们都没吃饭,同事叫了几个盒饭,都是下水,腰花、猪肝、肥肠。我想到刚才泡得没有轮廓的尸体,饭盒都没有打开。易晚星倒是认认真真吃她那份猪肝,猪肝炒得太嫩,丝丝带血。我翻出之前的笔录,也不知道还能问什么,想了想才说:“要不你再说一遍五月十号那天的案发经过?”
易晚星擦了擦嘴:“我四月二十三号回的自贡,回来第三天就买了尼罗河畔那套二手房,五月三号开始搬家。十号那天我收拾到半夜两点,实在太累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早上九点醒过来,发现卧室窗户被打碎了,我放在床头的表和耳环也不见了,我报了警,等了一小时,你就来了。”
我想了想,说:“那套房子之前的业主是什么人?”
“好像是个公职人员,业主在成都,房子一直空着,就签合同和付款那两天回来了一趟,办完手续又走了。”
我回忆她卧室地面的玻璃碴,碎而干净,没有血迹。“双层玻璃现在要打碎也不容易。”
她点点头:“得有工具。”
我又看了一遍笔录:“表和耳环就那么放着?”
“就那么放着,我收拾东西顺手取下来了。”
我看看她如今耳朵上的一对耳环,也是星星,看着是纯金的:“你经常换着耳环戴?”
她笑起来:“你还没女朋友吧?你见过哪个女的就一对耳环的吗?”
我讪讪的,假装仔细看笔录:“所以小偷知道这房子现在有人住……你回自贡的事情有熟人知道吗?”
她看了看肖运生的空桌子,摇了摇头:“只有我爸妈,我连亲戚都还没来得及见。”
“你爸妈有跟哪个熟人说起过吗?”
她笑了笑:“我四十岁了,离婚,没孩子,也没工作,你觉得我爸妈会愿意跟谁说?”
我们之前都意识到易晚星大概是这么个状况,但一下被她摊开说出来,大家反而都不好意思起来,像是自己有什么把柄被人捏住。肖运生这时已经汇报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摞凉糕,他看着心神不宁,却又勉强拿出热情:“来,吃凉糕,大家都来吃凉糕。”
凉糕上浇满血红的红糖水,肖运生自己也下不了口,易晚星却还是吃得干干净净。肖运生说:“我送你回去。”
易晚星说:“我想再去河滩上看看。”
肖运生说:“没得东西看了,都收拾完了。”
易晚星说:“今天是七月半,你想得起不?”
肖运生说不出话了,他警服都没换,翻箱倒柜地找了两根蜡烛,和易晚星出了门。我整理笔录弄得有点晚,走的时候鬼使神差去河边逛了一圈。七月半,鬼乱窜,外婆说过,到了子夜时分,会看到百鬼浩浩荡荡,从奈何桥上过来,最前头两个拎着红灯笼的是鬼帝郁垒和神荼,二人率领百鬼,过了桥,过这一晚。我们这些做人的要大方一点,这一晚就把阳间让给他们,因为奈何桥过了夜才能走回头路,若是不给他们让地方,他们就是孤魂野鬼,有点造孽。
阳间还是那个阳间,沿路都是烧过的纸灰堆,被风吹得漫天飘散,大家烧过纸都回去了,街上空空荡荡,只有卖夜宵和吃夜宵的人在顶风作案。河滩黑漆漆的,起先我什么也没看见,渐渐发现有两点微光在移动,找到光之后,影子也随之出现。肖运生拿着那两支点亮的蜡烛,和易晚星走在河滩上,那条绿裙子在黑暗中显得是如此之长,像铺满了整个河滩。风呜呜咽咽,吹不动河滩,但能把裙子吹得上下翻飞,那两点光停在某个地方,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我在烛火最后熄灭之前,看见他们坐了下来,两个人都被黑影笼罩,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鬼上了河滩。
三
肖运生戒指都买好了,那具尸体还没什么进展。失踪人口对不上,也没人来收尸,寻人或者说寻尸启事就贴在美食街上,我们吃克猫和葱葱鲫鱼时总能看见。现在肖运生也总来吃克猫了,克猫有点贵,但易晚星喜欢。易晚星又买了两条绿裙子,戴着那块欧米茄,在美食街显得过于高档了,易晚星整个人都显得过于高档了。表送回去的时候,装在一个透明密封袋里,我们都以为易晚星会顺手扔了,但过了几天就出现在她手上。“还是上好的啊,”易晚星说,“我就换了根表带。”肖运生也去买了块欧米茄,易晚星那块的情侣款,抠抠搜搜一个男人,舍不得买新的,让我在网上给他买了块二手表,明明经过了验货宝,但肖运生一戴上就像假货,和易晚星的配不起来。两个人走在旭水河畔,来来往往的每个人大概都会想:这两个人咋回事的哟?根本配不起来。
不管怎么说,肖运生如今是个走了狗屎运的人,满面走狗屎运的志得意满,不晓得的还以为他升到了副科级。肖运生说:“都是虚的,我跟你说,那些都是虚的。”我问他:“那什么是实的?”肖运生说:“人啊,晓得不?只有人才是实实在在的。”我说:“哦,只有抱着女人才是实实在在的。”肖运生不说话,嘴角带笑,陷入憧憬,或者回忆。
克猫店里坐满了,我们在门口嗑着南瓜子等位。肖运生很老练地分析:“可能是内江过来的,过江龙,小偷技术有点过硬。”我说:“这也看不出来技术过硬吧,砸窗子进去的,有点技术的起码撬个锁。”肖运生被我打了脸,讪讪地不说话,易晚星在旁边打圆场:“我那个锁确实不好撬,双重防护,我后头换锁都搞了好久。”肖运生又说:“过江龙,可能是吃粉的,屋里头也不想管了。”
不管是哪儿的过江龙,尸体都得处理了。我这才知道,按照《殡葬管理条例》,这种无名尸体的火化,得让司法机关出一个火化通知。殡仪馆催了好几次,肖运生拖不下去了,总算拟了一个通知找所长签字,到了这个地步,两个案子都算一起结了。肖运生有点不甘心,他想把易晚星那对星星耳环找回来,因为易晚星说,那是她第一次穿耳洞送的耳环。火化那天殡仪馆让派出所再去个人,说还有个什么手续要办,本来应该我去的,但横街子的王婆婆报了警,说被儿媳妇虐待。我是横街子人,王婆婆是我外婆的闺密,我找了个同事替我,但最后肖运生自己去了。
我说:“签个字的事情,老板没得必要亲自跑一趟哟。”
肖运生憨憨地说:“小易让我去的,她让我给人家烧点纸。”
我说:“她被偷了还要给人烧纸?”
肖运生说:“小易这个人就是比较善良。”
我说:“谢谢老板了,回头我还你一天值班。”
肖运生说:“值班就算了,领证那天你帮我摄个像。”
我答应了,我有个摄像机,旧是旧了点,但别人领证最多拿部手机,肖运生可能觉得这样比较高档,和易晚星确定关系之后,他现在相当在乎高不高档。
王婆婆没有被虐待,儿媳妇只是说王婆婆血糖高,不能吃甜烧白,王婆婆一时气不过,就报了警。我说:“王婆婆,你还晓得怎么报警的啊?”王婆婆说:“我咋不晓得呢,110哟,你以为我憨的哟?”就这么个案子,我也莫名其妙处理了几小时,等到从横街子回来,想问问肖运生烧没烧纸,但肖运生不在,往后一个星期都不在,所长说:“狗日的请了年假。”我恍然大悟,都要领证了,请个年假准备应该的。
所长说:“准备啥子嘛准备,二婚,不兴搞仪式的。”
我说:“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不要歧视人家二婚的。”
所长说:“我要歧视也歧视你嘛,你一婚了没有吗?”
肖运生休完年假回来,瘦了一大圈,一张脸没有胡子,更显怪石嶙峋。他闷头闷脑,坐下来也不知道往保温杯扔胖大海,在那里空口猛喝白开水。我说:“老板,哪天领证?”他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快了,很快了。”我又问:“真的不搞个仪式啊?”他说:“不搞了,二婚不搞仪式。”我说:“老板,你自己看不起自己就算了,看不起易晚星要挨打的哟。”肖运生脸色惨白,像已经挨了打。
易晚星快下班时来的,拎一个琴谱包,穿一条长得不得了的绿裙子,她今天化了妆,一张脸惊人的白,嘴唇又惊人的红,连头发都卷好了,一头蓬松海浪,像要就地搞二婚仪式。肖运生见了易晚星,唯唯诺诺说:“你怎么来了?”易晚星看着非常愉快,那裙子不知是什么高档料子,一动就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等你下班啊。”她说。肖运生说:“今天事情有点多。”我在旁边插嘴:“哪里多?老板,今天我们一个接警电话都没得。”肖运生更唯唯诺诺了:“你晚上想去哪里吃?”易晚星愉快地说“今天我们不出去吃了,去我家吧,我做两个菜。”“小汪,你也来。”我想了一会儿,才明白小汪是我。肖运生狠狠看我一眼,我立刻说:“去,姐,我去,我帮你打下手。”
易晚星不需要我们打下手,她买了两斤三线肉、半只鸭子、四条鲫鱼,又去凉菜店打包了半斤猪耳朵、三两小肚子。小肚子最下酒,她说。凉菜店还是那个小伙子,手脚麻利把小肚子剖开,切成细丝。我问:“换了老板生意怎么样呀?”小伙子说:“没得区别,你不说我都搞忘了我们换了老板。”肖运生和易晚星站在后面,等小伙子用塑料袋把海椒面、花椒面包起来。凉菜店求新鲜,空调开得极低,肖运生冻得脸发青,易晚星双手抱在胸前,遮住那些因裸露而战栗的皮肤。
到了那房子,才发现重新装过了,窗户换成老钢窗,又刷了绿漆,地砖换成灰色水磨石,靠窗放了一张书桌,像二十年前的中学教室。院子倒是没怎么弄,只是收拾利落了,我和肖运生一人一把藤椅,看易晚星在前面水槽里杀鱼。她熟练地拿着一把菜刀,先用刀把把鱼敲晕,再行云流水地刮鳞剖肚,四条鲫鱼都满肚鱼子,易晚星一一掏出来冲洗干净,再塞回肚子里去。上次那只野猫还在,围着易晚星转圈圈,易晚星留下一摊鱼杂碎,野猫吃了一半,剩下一半它小心翼翼叼回那个纸箱里,纸箱里什么都有,硬币、乒乓球、没吃完的零食、扔掉的烟头。
易晚星的菜做得好极了,蒜泥白肉、子姜鸭、韭黄鲫鱼、清炒丝瓜尖,最后来了一锅酸菜豆瓣汤。菜摆在院子里,我回厨房里添了三次饭,肖运生就一直用小肚子下酒,这家里本来只有啤酒,他自己去外头小卖部买了一瓶白酒。肖运生的酒量我有数,所里聚餐他都不敢跟人划拳,我的米饭吃到第三碗,他已经确凿无疑醉了,对着易晚星哧哧笑。我理解他,要和这么个女人领证,喝不喝醉都是要哧哧笑的。易晚星也不理他,一粒一粒从汁水里拣零零星星的鱼子吃。
肖运生笑着笑着生了气:“你还跟不跟我领证?”
易晚星说:“领啊,不是讲好了元旦领证。”
肖运生说:“领你个铲铲……你故意的,你故意让我晓得的,你故意让我去火葬场的。”
易晚星说:“你晓得啥子?”
肖运生眼睛都红了:“为啥子嘛?你到底是为啥子嘛!”
易晚星说:“你说为啥子?”
肖运生的声音中有一种哀求:“二十几年了,都二十几年了,你好生生的,你就把这件事忘了吗?”
易晚星说:“我也想,你以为我不想吗,我做不到啊,答应人家的。”
肖运生低声说:“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易晚星说:“小时候,又不是上辈子。”
肖运生抱住头:“他也没杀人……老子看他一次想打他一次,但他也没杀人啊。”
易晚星说:“是不是哟?”
肖运生几乎绝望了:“不值得,你这样不值得啊,把自己搭进去了。”
易晚星笑一笑,她笑起来有种让人胆战心惊的美,她伸了个懒腰:“值得不值得,由我说了算。”
肖运生看着她:“你可以不让我晓得的,你没必要让我晓得。”
易晚星说:“光是让他死有什么意思呢,总要有人晓得,他是为什么死……对了,你最后是怎么晓得的?我还想是你太憨了,留的东西怕你看不出来。”
肖运生给自己满了一杯酒,又一口干了,这才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就是凉菜店里打包海椒面、花椒面那种,袋子非常脏,一颗金牙裹在那些灰里,闪闪发光。我无端想,这牙怕是纯金的。
四
午饭时间,我们一拥而上去食堂打饭,今天吃豆子烧鸡,去晚了只有鸡脖子和鸡皮。盈盈却坐在凳子上不动,抱住她的蓝色饭盒,木木地看着窗外。学校最近搞装修,崭新水磨石地板,老钢窗刚刷过漆,绿是绿了,但绿得让人心烦。我喊她:“杜盈盈,你打不打饭?”她愣了好一会儿,才发现我是喊她,盈盈如今说什么都战战兢兢的,像是什么都不敢确定:“不打了吧?我不饿。”
最后,是我给她打了饭,二两饭,一份豆子烧鸡,我抢到一个鸡腿。但她最多吃了五钱饭和几颗豆子,我急了,骂她:“杜盈盈,你是不是想成仙?”盈盈看着我,突然说:“你还想得起不?我小时候就想成仙。”我说:“不对啊,小时候我们都想当妖精。”她认真纠正我:“不是,我其实是想当仙女,是你要当妖精。”我想起来了,盈盈从小长得乖,大家都喊她小仙女,她披着白蚊帐说:“易晚星,你晓不晓得,我以后要当仙女?”那时候人人都看《新白娘子传奇》。我说:“盈盈,当神仙不好耍,我们当妖精要不要得?你当白蛇,我当小青,我们一起修炼,修炼一千年就能当人。”她咯咯笑起来:“那也可以,但当人有点无聊,我们要不还是一直当妖精吧。”
那时,我们都在盐厂幼儿园大班,大家都是盐厂子弟,都以为要一路子弟校读到初三,哪个晓得刚上小学,盐厂就说搞不起走了(四川方言,不景气的意思)。我们和父母一样想不明白,那么大一个厂,都以为会海枯石烂,怎么会说搞不起走就搞不起走了?一搞不起走,什么都塌得很快,厂里最后留了百分之三十的工人,食堂承包了,子弟校不办了。
我和杜盈盈就此分散,各上了各的小学和初中,到了高一,我们又在旭水中学见了面。杜盈盈修炼了十年,不管是仙女还是妖精都完全成形了,开学第一天大家就议论纷纷:“那个女的你看到没有?”“哪个?”“妈哟,长得好乖。”
我得意扬扬地说:“我幼儿园同学!我闺密!”
如今我们又是闺密了,我也算个美女,但我天天盯着她的脸看。盈盈不怎么喜欢,她用头发遮住半边脸,你不要看。我又把头发拨开,不看白不看。盈盈说:“我不喜欢我的脸,我长得太妖了。”我以为她开玩笑,说:“我们本来就是妖精啊,蛇精,你忘了啊?”她摇摇头,认认真真地说:“我长得太妖了,我看着就不像个好女人。”我吓了一跳,我去年才来月经,还没想过自己已经是个女人,我看着她说:“那我们也不能是坏女人吧,我们做了啥子坏事就是坏女人了?”盈盈说:“不用做啥子坏事,有些女人天生就坏。”我说:“不可能,妖精都能做好事,有些人比妖精还坏。”杜盈盈说:“易晚星,你太幼稚了。”
和如今的盈盈比,我确实太幼稚了。我过了好几个月才发现,杜盈盈初中就交了男朋友,而且男朋友就在我们班。王宇矮墩墩的,原本坐在第三排,他自己一定要调到最后一排,那位置我怀疑他都看不到黑板,但他看清楚盈盈是没有问题的,每一根头发丝都能看见。他们在学校里不怎么说话,每天放学,我和盈盈走到校门口,王宇总在那个电线杆下面等着,盈盈见了他,总会拉一下我的手说:“那我走了啊。”我说:“嗯,盈盈你好生点。”但我是让她好生点什么呢?在那个时候,我也并不清楚,我只是觉得,盈盈拉我手的时候特别用力,像是想和我说什么,但一直没有说出来。
我说:“王宇长得也不帅啦。”她说:“男人重要的不是帅不帅。”我说:“那什么重要呢?”她说:“重要的是实力。”我说:“王宇有啥子实力,期中考试他三科不及格,数学才考三十多分。”盈盈迟疑了很久才告诉我,王宇他爸是区长,以后可能是市长,她爸下岗了,她妈跪下来求厂长才能留在厂里头,一个月拿两百多块钱。我没听懂,说:“然后呢?他帮你爸安排工作了啊?”盈盈说:“那倒没有,我爸在广州打工。”我说:“那到底区长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盈盈又说:“现在可能还没有,以后就有了。”我说:“你还要跟他有啥子以后啊?以后你都读大学了。”盈盈说:“他说了,我去哪里读大学,他就去哪里。”我说:“你要是去了北京,他还考得起北京的大学啊?”盈盈说:“那我应该也不去了。”我说:“杜盈盈你是不是疯了?”盈盈说:“等你有了男朋友,你就懂了。”我问她:“耍朋友是不是很好耍?”盈盈有点茫然,说:“好耍啊,特别好耍,等你有了男朋友,你就懂了。”
我没有男朋友,但我也看得出来,坐在我斜后方的肖运生有点古怪,每次递作业本给我,都红着一张脸,开始我以为他是想抄我数学作业,后来才渐渐回过神来。肖运生一脸憨相,数学虽然不至于考三十几分,但也差不了好远,我一直以为他除了长得高一无是处,直到班主任为学校的歌咏比赛选主唱。校长也是有点绝,为了不耽误上课,把歌咏比赛挪在暑假,放假前要把曲目和主唱都定下来。我们班主任是从成都进修回来的女老师,满脑壳新鲜玩意儿,为了表示没有暗箱操作,大家都要一一上台现场表演,别的人我当场就忘了,大家估计也都忘了。
盈盈选了《红豆》,肖运生选了《遥远的她》。
“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夜雨中似听到她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心声有否偏差,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
按理说每个人只能唱一分钟,但大家都被这个场面镇住了,听他们把副歌部分唱了两遍。他们之后,别的人上不上场都不重要了,班主任连投票流程都没走。选拔结束后我和盈盈走到学校门口,还是那个电线杆,但王宇不在,我陪她等了五分钟,还是不在。我很高兴地说:“盈盈,我们去逛街嘛,你都没陪我逛过街。”盈盈脸色惨白,紧紧拉住我的手,大热天,她的手冰冰的,像一条蛇。“好的,我陪你去逛街。”她说。
两个人加在一起只有五十三块钱,也没什么可逛,吃了凉皮,吃了冰粉,又吃了辣得不得了的凉拌大头菜。那天白天出奇晴朗,到了傍晚,满天盛大的晚霞,两个人一次次为某朵云停下来,指给对方看。我们无处可去,却又舍不得走,反复从旭水河这边走到另一边,天已经快黑了,绚烂晚霞在一点点消散,平桥上零零星星有几个婆婆在卖菜。在剥好的苞谷米和毛狗豆中间,有一个叮叮当当的首饰摊,老板自己一边耳朵打了三个耳洞,面前摆一块纸板,上面硕大几个红字,“无痛穿耳,十块”。我说:“盈盈,我们去打耳洞好不好?我一直想打耳洞。”她吓了一跳,说:“戴耳环啊,戴耳环会不会太妖了?”我说:“妖啥子哟妖,撒切尔夫人也戴耳环,你看撒切尔夫人多严肃,你晓得不?人家是保守派。”盈盈说:“撒切尔夫人是外国人。”我说:“外国人咋了呢?”盈盈也不知道,她沉默了很久,和那天的很多时候一样,我觉得她既快乐得不知所措,又有点心不在焉。
盈盈最后也没打耳洞,我打了,那把枪对准我耳垂的时候,我紧紧抓住盈盈的手。无痛穿耳,两枪下去痛得我泪流满面,盈盈替我用酒精棉消了毒,又从老板的一盒子茶叶梗里细细挑选,想选两根最细的,插在血呲呼啦的耳洞里面。我擦干眼泪,看她低着头一丝不苟地选茶叶梗,一时觉得胸口有一股浩荡之气,像金庸小说里的场面。我说:“盈盈,我以后要报答你的。”盈盈笑起来,说:“怎么报答?”我说:“你要什么报答?”盈盈想了想说:“那以后我被人欺负了,你帮我欺负回来。”我疑神疑鬼地说:“王宇是不是对你不好?”盈盈说:“没有啊,很好的,他就是太爱我了。”我说:“那你爱不爱他呢?”盈盈说:“你怎么跟王宇一样,老问这个。”我说:“到底爱不爱嘛?”盈盈一下急了,几乎破了音,说:“爱爱爱!你要怎么才相信我?”我吓了一跳,说:“我没有不相信你啊,盈盈你怎么了?”盈盈回过神来,又恢复了平常模样。她说:“对不起,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证明爱这件事。”我说:“这件事还要证明啊?”盈盈说:“当然了,不然谁会相信呢。”我说:“还要谁相信啊?”盈盈说:“你不懂。”茶叶梗找到了,她轻轻插进耳洞。我又问:“我不懂你懂啊?那到底怎么证明呢?”盈盈语气轻松,说:“去死嘛,死了什么都能证明了嘛。”
打耳洞可以送一对耳环,送的耳环都没什么好东西,但我们选了又选,选了又选,最后是盈盈替我选了一对金色星星。我说:“有点小哟,那对大圈圈是不是好看点?”盈盈说:“这是你的名字,这对耳环能保佑你。”我说:“那我再买一对,你也被保佑一下。”盈盈说:“我都没有耳洞。”老板在旁边说:“没得关系,有耳夹款,十块钱。”那一天就这么到了尽头,我们该分开了,我们的家在旭水河的两岸,我们站在平桥的第一个墩子前。盈盈突然说:“晚星,你对我真好。”我感到莫名其妙,我哪里对她好了?今天大头菜还是她出的钱。盈盈说:“晚星,我们下次再一起逛街。”我说:“好啊,你把耳环戴上。”盈盈捏着那对星星耳夹说:“好啊,我们下次一起戴。”我说:“以后长大了,我们就可以买真正的金耳环了。”盈盈说:“好啊,以后长大了,我给你买一对真正的金耳环。”我说:“我也给你买。”
歌咏比赛那天正好是农历七月十五,班主任给每个人都画了红脸蛋,到最后所有人的脸都花了,像七月半的鬼四处乱窜,拿了第一名拍完大合影,我和盈盈往外面走,肖运生似乎想找我说什么话,顶着一张红脸蛋几次三番晃到我们前面。我不耐烦地说:“肖运生,你不要挡路。”他憨憨地说:“哦,对不起。”这么来了三次,他就远远落在后面。我和盈盈走到校门口,王宇站在电线杆下面,我才注意到那天他没参加歌咏比赛,我们的脸都绯红,他的脸黑漆漆的,像另一种鬼来了阳间。盈盈见了他,拉一下我的手说:“那我走了啊。”我说:“嗯,盈盈你好生点。”我这时候才发现,她戴了那对星星耳夹,遮在散掉的马尾后面,明明是假金耳环,但在灼灼日光下,却有和真金一模一样的光彩。
那天晚上,我和爸妈一起去河边烧纸。出门晚了,街上空空荡荡的,百鬼应该已经过桥了,只有卖夜宵和吃夜宵的人在顶风作案。风声呜咽,像卷裹着谁的哭声,月光直直往下,照亮粼粼水面,在那个旋涡的位置画了一个准确的圈。借着那点月亮,我看见水上有黑影浮动,往圆圈的中心奋力游去。
我说:“那里有个人!”
我妈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是鬼吧。”
我说:“鬼不是都从桥上过来吗?”
我妈说:“哪个晓得,可能过了桥,又想回去。”
我说:“不能从桥上回去啊?”
我妈说:“奈何桥,过了夜才能走回头路。”
我说:“一晚上都等不了啊?”
我妈说:“人家不想等了。你管人家的呢。鬼的事你都要管,我看你管得宽。”
我们烧了纸往回走,沿路都是烧过的纸灰堆,被风吹得漫天飘散,纸灰让月光显得暗淡,月光曾经指明了通往旋涡的道路,但如今水只是水,一片混沌。我无端担忧起来,我想,那个鬼该不会迷路了吧?万一她找不到那个涡,又过了夜没能上奈何桥,该怎么办?不晓得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她。我妈没有说错,我就是管得宽,我连鬼的事也想管。
原刊责编 张 菁 顾拜妮
【作者简介】李静睿,出生于四川自贡,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曾做八年法律记者,现专职写作。出版有长篇小说《慎余堂》《微小的命运》、短篇小说集《木星时刻》《北方大道》《小城:十二种人生》、随笔集《死于昨日世界》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