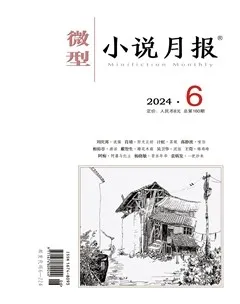苦乐年华
2024-06-25杨晓敏
杨晓敏
我家的南边,有一片不大规则的南窑塘,有三四十亩大小。不知从什么年代起,村里在此处建窑烧砖,就地挖土,逐渐掘成一大块可观的低洼地,雨水日积月累,形成全村最大的清水塘。即使在干旱的冬季,塘边水位骤降,南窑塘的西南角仍有一带深水域,凝结着一层薄薄的冰片。南窑塘名扬乡里。
南窑塘给故乡带来的欢乐,绝不仅仅限于夏季。它犹如一个聚宝盆,对于钟情于劳作的人来说,清水塘会毫不吝啬地奉献出它的宝藏。秋末冬初,落叶萧萧,在一派朔风肃杀中,荷叶残败凋零,芦花被风吹散,蒲条东歪西倒,水鸟也已迁徙。随着农闲的到来,塘边陆续多了挖藕人。
在泥塘里挖藕,本是一道讲究的工艺。懒汉永远不会精于此道。关键在于,掏了力气,能否有所收获,这也是对自己判断力和灵性的一种验证。冬季的塘边早已是一片狼藉,莲秆不见,下铁锹时往往没有目标可鉴。有时挖了半天,累得通身冒汗,依然寻觅不到一星半点的藕。泥塘里的芦根、杂草等,硬拉软扯,像搅拌在混凝土里的钢筋一样,使铁锹不能灵活自如。连换几个地方,弄得泥浆沾身,只得哀叹运气不佳,苦笑作罢。所以,明知塘有藕,不愿下泥池的大有人在。
我的五伯父则不然。他骨瘦如茎,颀长的身子略佝偻些。在塘边走动时,他喜欢把铁锹横在身后,用两只胳膊弯紧,那姿势显得很潇洒。当那双微眯的小眼睛睁开时,亮幽幽的,精气神很足。溜着溜着,待他把铁锹向下一插,莲藕似乎就聚集在箩筐大的泥坑中了。哪怕是别人挖剩的闲坑,五伯也能挖出大藕来。我常去看五伯挖藕,以为那是一种享受,高明的魔术师,也只不过有此本领,何况五伯是真功夫。他横背着铁锹在前面走,我提着小箩筐在后面晃悠悠地向塘边去,无异于师徒俩。五伯虽然不爱指点,久了,我也看出些挖藕的诀窍。五伯挖藕非常注意寻找所谓的“藕窝”,坑里只有一两挂藕,或者藕太小,费劲而划不来。他讲究站位,两脚绝不能乱晃动,否则泥浆四溢,随挖随淤,老挖不成一个完整的“坑”。锹锹下去,都要利索,不能拖泥带水,不能太零碎。见了藕最忌轻易下手动它,一则易弄断,二则手上沾泥,无法抓锹。
无论多么复杂的藕层,五伯差不多都不用手刨,而是用锹一条条剔拨出来,我曾学到一招半式,虽不算得真传,但也足够旁人羡慕了。
一年初冬,连刮几天干风,有一片凸起的塘面露底了。那时我大约十岁吧,还是有些力气的。那也算是我第一次踏入距塘边稍远的纵深处挖藕。那天我如有神助,往日的疲倦感一扫而光。我像五伯那样,审时度势般地选好角度,抖动了铁锹。这是一片过去尚未开发过的处女地,泥浆下呈沙质状,锹头无遮无拦,我在泥塘中硬铲出一条通道,惊讶地发现藕层居然会排列得那么协调完美。一挂挂赤裸裸的嫩藕被我揪出示众了。塘边逐渐增多的观众喝起彩来,我的情绪沸腾到极点。多少年来,我也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富有创意的下午。塘边的汉子们眼热,忍不住也下塘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那一大片泥塘中,谁也无法再挖到叠现的“藕窝”。直到父亲收工归来,在塘边呼喊我回家吃饭时,我才感到饥饿和疲惫。
堆成小山似的莲藕,足有六七十斤重。要知道,那时一斤萝卜才卖两分钱,像这样上好的莲藕,拉到四十里开外的新乡菜市场,一斤可卖三角钱。半天时间,我的劳动价值为二十元,比我父亲在田里辛苦一个月还挣得多!对于穷人家来说,这预算简直是个辉煌的天文数字。晚饭后,母亲细心地用针线穿透着我满手的血泡,抚摸着我稚嫩的肩膀,泪流双颊。
掌灯时分,来了几位新乡的知青,缠着父亲说,队长大叔,这藕让我们几个过节带回家吧,怎么样?每斤算一角钱,年终分红扣除。父亲的喉结滚动几下,硬生生把拒绝的话咽了回去,挥了挥手说,拿去吧,塘里还有,我再让洲儿去挖。知青走后,母亲几乎把父亲吵得无地自容,一会儿,从未对我怜悯过的父亲,竟给我掖了掖被子,用关切的语调说,累吧,明早让你妈给你煮个鸡蛋吃。这算是对我少年时期的最高奖赏。
哦,故乡的清水塘,你还记得我儿时的几丝苦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