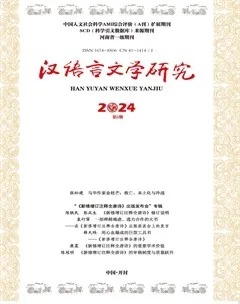“永恒轮回”与历史认知
2024-06-23姚思宇
① 参见姚思宇:《“永恒轮回”与悲剧起源——尼采艺术史观中的时间美学雏形》,《文化与诗学》2023年第2期;姚思宇:《“永恒轮回”与生命教育——尼采时间美学的思想旨归及其美育意义》,《美育学刊》2023年第4期。
② 参见[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521页。
③ 参见[德]阿尔弗雷德·冯·马丁著:《尼采与布克哈特》,黄明嘉、史敏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二版“前言”第1—2页。
④ 参见韩潮:《古典的歧途——关于〈尼采与布克哈特〉》,《同济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⑤ 参见[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版, 第9页。
摘 要: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沉思》在批判“历史学”中呈现其时间美学的生成。如同歌德重视“自然”的历史观,布克哈特的文化史研究注重直观和艺术感受力,并因其保守立场而强调对历史的持续性考察。而尼采基于“现代教养”导致人格削弱等问题,重点批判了“历史学的过量”。他提出“非历史”和“超历史”的认知方式,主张通过遗忘和封闭自身视域乃至将目光转向永恒的存在,克服“科学统治生活”对现代人的身心困扰。因而不同于布克哈特的悲观主义,尼采进一步发现了叔本华的“真诚的英雄主义”,即能够把握自身的形而上学性,在每一刻的翻转与肯定中提升生活情感。这标示着尼采“永恒轮回”时间美学观念的生成,其人文意义在于推动现代主体形成理解自我、把握现时、改造世界的能动性契机。
关键词:“永恒轮回”;历史学批判;尼采;时间美学;布克哈特
如果说,尼采以“永恒轮回”为核心的时间美学,其雏形见之于对古希腊悲剧诞生的追溯,其成熟主要体现在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的阐发①;那么,要理解这一时间观念如何生成,则应注意此间尼采对历史学的讨论和批判。众所周知,尼采借疯子之口高喊“上帝已死”,是对西方以基督教救赎论、启蒙进步论为代表的线性时间观的挑战。实际上,在此之前,反对历史进程的思想已在涌动。如德国大诗人歌德,内心偏爱古老的循环理论②;文化史学家布克哈特,继承兰克的史学思想,批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论……
尼采与布克哈特有着直接的交情。自从1869年到巴塞尔大学担任古典语文学教授,尼采和这位历史学家便有了思想交流,而直至失去理性,尼采仍与之保有通信。但后人根据他们的书信往来发现,尼采和布克哈特的关系并不对称:相比于尼采每有新作便寄送给布克哈特,并期待着布克哈特给予热情的回应,布克哈特则呈现出越来越冷淡的态度。对二者关系的关注尤其集中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30年代德语学界大多推崇尼采而贬抑布克哈特,如萨林(Edgar Salin)等认为布克哈特未能跟上尼采的思考和精神期许③;洛维特(Karl L?with)首先扭转了这一倾向,特别是1936年写出《布克哈特,在历史中间的人》及1940年代的系列评注,都是通过重估布克哈特的思想价值,强调布克哈特相比尼采更为可取的品质。④洛维特1939年完成的《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一书还意在阐明,德语思想界如果当年跟随歌德的“自然”观而不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尼采问题就不会出现。⑤在此基础上,洛维特在书中强调布克哈特作为歌德的继承人,实际是向读者提示:“从黑格尔到尼采”这一显性的思想脉络背后,还潜藏着“从歌德到布克哈特”的断裂性历史潜能。
值得注意的是,尼采1873年写作《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正是基于此前旁听布克哈特开设的“关于历史学习”系列演说(其后整理出版名为《世界历史沉思录》)的思考和对话。那么尼采的写作究竟呈现出与布克哈特怎样的思想关系?本文将重点探究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的历史认知,以从中发现尼采如何生成独特的时间美学。
一、从歌德到布克哈特:“自然”与“沉思”的背后
尼采当时参加布克哈特的历史讲座是高度投入的,他曾写信告诉朋友:“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演说中获得享受,而且,这是我在年纪稍长些时也可以做的。在他今天的演讲中,他以一种值得纪念的方式介绍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①尼采表现出了真诚学习乃至效仿的兴趣,还特别留心布克哈特对黑格尔的谈及。从《世界历史沉思录》可以看到,布克哈特当时是以其历史哲学作为对立面的引子:“这种预想的世界计划职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它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②而相对而言,布克哈特的历史观更切近歌德。
如同洛维特认为,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念从精神出发,精神的绝对性的根据在基督教里面,而歌德关于世界上发生事情的观点则是从自然出发,“自然自身就已经是理性”。③比如,当歌德遭遇法国大革命时,其对待方式是独特的。如同许多尚古主义者,法国革命的爆发对他们而言是一场不小的冲击,歌德在致F. H.雅可比的信中也承认,“法国革命即便对我来说也是一场革命,这你可以想像”④。但没有口诛笔伐,也没有唉声叹气,歌德通过研究古人让自己在图林根更好地度日,即便在重要的历史事件面前,最多也只是直观地加以叙述。因为他在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植物和骨头、石头和颜色时,常常感觉到大自然是真实的、稳定的和有规律的——相比于黑格尔仅仅把大自然看作是理念的“异在”,歌德“由它出发找到了理解人和历史的一个入口”⑤。
歌德通过“自然”理解“历史”,布克哈特也承续了歌德观察事物、考察历史的方式。阿尔伯特·所罗门(Albert Salomon)指出,布克哈特从歌德那里学到人们只能从个别的和具体的现象中得到的共同的东西,意识到每一具体的事实都有其独特的结构或构成元素,作为具体事物中的共同要素;同时又必须保持对整体的热爱,理解多样化中的一致性。⑥布克哈特对历史事件的处理还呈现出一种“创造性的同情”(creative sympathy)⑦。由于自身特有的艺术感受力和创作热情,布克哈特常常感觉到自己是“歌德家庭”的一员:他不能忍受传统编年史秩序的束缚,拒绝盛行的实证主义史学研究,而认为真正的秩序“只能作为一幅图画而被描绘出来”;他像老师兰克一样相信原始资料的根本性意义,却是因为他相信想象活动能够受到文件的不断更新的刺激和净化,以便重新实现对“历史生活的叙述”。⑧
这种对待历史的方式,布克哈特明确称之为“沉思”(Anschauung)。这个词正源自歌德的使用,包含“看见”“直觉”“图形感知”“视觉”“洞察力”等多层含义,表示从反思、沉思和对世界的积极观察中获得知识的过程。布克哈特以此区别于哲学的思考:“对我来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总是诗歌;一系列最优美的艺术作品……我的整个历史工作,正如我对旅行的热情、对风景画的狂热和对艺术的专注,源于对沉思的巨大渴望。”①对沉思的巨大渴望,概括了布克哈特只依附于具体可见的自然和历史的思想生活,坚持从美学的视野考察历史。
布克哈特同时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他把自己的人类学考察方式称作是“病理学的”,“人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忍受、进取和行动,构成一个恒定的中心”②。基于对欧洲传统遭受自法国革命以来迅速崩溃的体验、对自己眼前与欧洲传统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决裂的畏惧③,布克哈特强调对历史“持续性”的考察。他认为过去是不间断的,“历史性的人正是通过有意识地和自由地储存不间断的过去而与古代的和现代的野蛮人区别开来”;通过对历史持续性的考察能够发现,“整个人类的生存史和苦难史不过是行动的和受苦的人类的持续不断的灵魂转生”④。布克哈特的悲观主义也有着深厚的基督教血统。和尼采类似,他出生于牧师家庭,但后来自己又决定放弃神学研究乃至宗教信仰。尽管如此,“原罪(或人类的不完美性)的概念继续对他的个人信仰、他对历史的态度以及他对历史过程的理解产生强烈的残余影响”。⑤他拒绝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将提出人性本善、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观念的卢梭称为“平民”。这不仅因其贵族主义的立场,且其所认为的是卢梭“没有体会法国普通人真实的、具体的生活和痛苦”,仍然是一个“理论家,一个乌托邦主义者”⑥。
因此,当布克哈特的历史研究侧重于描绘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历史图景时,秉承“自然”的“沉思”,是有意与他那个时代最珍视的东西形成鲜明对比:现代化、理性、进步和启蒙的原则,以及自由、平等和人权等的政治理想。也有学者基于此认为,布克哈特的历史思想也是对当时政治和社会一致而彻底的文化批判,其中的政治反思不亚于尼采所说的“不合时宜的沉思”。⑦
而尼采此后写作《不合时宜的沉思》,二者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尼采用词上的明显化用,布克哈特本人也从《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这篇长文中敏锐地感受到行文中对话的张力。为此他在回信中呈现出了某种澄清的倾向:
说老实话,作为一个老师和讲师,我从来没有像有些人表现的那样,为了教历史而慷慨激昂地把它称作世界历史,而是把历史看做是一个入门课……此外,我也没有刻意培养什么有专业知识的学者和学生,我的目标是促使那些听课的人确立一种信念、萌生一种愿望:对每个个体来说,同一件以往的事情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和效果;每个人都能够并且可以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了解和理解它,并且很有可能从中看到对自身有益的因素。⑧
布克哈特坚持自己作为巴塞尔教师的身份,并有着明确的责任定位。他还把尼采的这篇论文称作“内容极其丰富的”文章,并简要地回复了两句话:“我对此原本没有说话权利,因为这部作品需要仔细地和慢慢地品赏。仅事实一项就与我们的人如此密切相关,使大家都试图立即说些什么”①。布克哈特的措辞整体上是较为客套的,而尼采的写作实际并没有直接批评布克哈特。因此要理解尼采历史认知的特殊之处,须回到文本中具体分析。
二、立足现代教养问题:尼采的“非历史”与“超历史”
从二者的行文能够发现,相比于布克哈特成熟老到的书写风格,尼采更显年轻人的激进和锋芒。他在这篇探讨历史学的文章中表达过对艺术性的历史研究的肯定,显然是对布克哈特史学的认同;但又提出“非历史”和“超历史”的认知方式,却是在一个尚处历史学热的时代闻所未闻的事件,因此布克哈特在回信中预见了“大家都试图立即说些什么”的反响。
从文章一开始,尼采就指出了动物具有令人艳羡的幸福感,原因在于动物能够遗忘,不留恋过去的东西。相比之下,人总是把此在当作“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过去时”,当作“一种不间断的曾在”“依赖自我否定和自我消耗、自我矛盾为生”②。尼采这里所说的“不间断的曾在”,仿佛是在影射布克哈特主张的历史“持续性”考察,后者认为“历史性的人”区别于野蛮人之处就在于能够在现时通过历史的延续性约束自身。就此而言,在布克哈特看来是人优于野蛮人的地方,尼采却认为是人相对于动物的短板。当布克哈特认为人可以用过去的记忆提醒现在,他可以通过讲授历史的方式使人获益时,尼采却思考了历史学过量的问题。他指出过多的历史学会使人陷入自负,但没有一味否定历史,而是认为怀念和遗忘同样是重要的,关键是要有所抉择——“唯有从当代最高的力量出发,你们才可以去解释过去:唯有在你们最高贵的品性的最强烈的紧张中,你们才将猜出,在过去的东西中什么是值得知道和值得保存的,是伟大的”③。不同于布克哈特用过去提醒当下、解释当下,尼采则力图用当下解释过去、识别过去。
文章作为《不合时宜的沉思》系列的第二篇,尼采以“不合时宜”一词统摄也就意味着批判现代性的宗旨,而其中针对的核心矛头是“现代教养”问题。尽管亲历1870—1781年普法战争的胜利、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但政治上的统一推进并不能取消尼采对德意志文化的忧心。在第一篇批评“知识庸人”施特劳斯的文章中,尼采表达了对德国人生活在“一切风格的混乱杂拌中”的担忧。④其中尼采对文化“混乱的多元”的批判,所追随的是布克哈特看重文化“整体性”的立场,也是他们基于早期浪漫派施莱格尔对现代诗艺琳琅满目、无秩序、无特点的诊断。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他继续批判了“现代教养”只是一种关于教养的知识,导致现代人“只是由于用外来的时代、风俗、艺术、哲学、宗教、知识充填并过分充填了我们自己”,成为“走路的百科全书”⑤。但他也批评浪漫派的内在性问题,因为被历史学毁坏而失去了对感觉的纯真性和直接性的信仰,以致时人只会通过抽象和算计来表现自己、乃至迷失自己。因此尼采呼吁德意志不仅要有政治上的统一,还要有民族的本性和灵魂中的更高的统一、精神和生活的统一。这构成了尼采批判历史学过量的基本立足点。
针对“历史学过量”导致的后果——人格被削弱、陷入自负、民族的本能遭到破坏、成为后来者和模仿者的信仰、导致犬儒主义情调,这些关系主体精神状况、生存状态的问题,尼采进一步批评了“历史学的教养”,也就是19世纪盛行的“历史主义”“历史感”,尤其针对实证主义史学导致“科学统治生活”的问题,尼采指出,现代人已经成为“普遍功利的工厂里工作”的零工:“分工!列队!”就是“现代的屠戮口号和牺牲口号”⑥。这种规范化、秩序化的“科学”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对人性的摧残,对生活的摧毁。当历史成为一门科学被研究时,也是这种后果的征兆。因其导致现代人“越来越失去这种诧异的感觉,对任何东西都不再有过分的惊奇,最终对一切都感到满意”①。而布克哈特当时讲授希腊文明,推崇希腊人纯粹的自由精神在城邦贵族政治、赛会竞技文化中对人性的照亮②,寄寓的也是对现实中科学主义、功利主义动机的厌倦,对培育完整的人的理想向往。
针对以上问题症候,尼采提出了“非历史”的认知方式。他认为,人要为自己的历史感规定一个度,精确地知道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塑造力,只有具有这种力,人才能够很快从过去苦痛的经历中走出来。这时的视域便是封闭的和完整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再唤起这些经历。这意味着,“非历史的人”需要摆脱智识、真理、正义乃至最优法则的束缚,产生“激烈的意愿和欲求”去迎接新的体验:“尽管有这所有的不义和所有的失误,他却挺立在不可战胜的健康和精力充沛之中,使人人看到他都高兴。”③在尼采看来,这种非历史的感受能力是更重要的且更原初的能力,是真正人性的东西诞生的基础。因此,“非历史的东西类似于一个裹在外面的大气层,生命唯有在它里面才能诞生”④。
尼采进一步阐发,如果在这种个体性的“非历史”中发现普遍性,人就把自己提升到了一种“超历史的”立场。这意味着,人因为认识到行动者灵魂中的盲目性和不义,不再去靠历史继续生活并且参与历史,也不再过分认真地对待历史学。“超历史的思想家从内部发出为自己照亮各民族和个人的一切历史,明见千里地猜出不同的形象字符的原始意义,渐渐地,甚至避免被一再蜂拥而来的文字搞得精疲力竭”⑤。尼采进而总结道,“非历史”意指的是“能够遗忘并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有限的视域里面的艺术和力量”,“超历史”则是“把目光从生成移开,转向把永恒和意义相同的品格赋予存在的东西,转向艺术和宗教的强势”⑥。二者所针对的病症即“科学”——那种只认为对物的观察是真正的观察,从中所看到的“都是生成了的、历史的东西”⑦。
因此,尼采既同布克哈特一道认识到19世纪的流行思潮、专业史学研究容易导致的人格性缺失,又进一步提出“非历史”“超历史”的认知方式,以改善现代个体的知识观念感觉、生命存在感受。而尼采此后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时,也延续了早期对现代性的反思,继续展开对 “教士们”“学者”“诗人”“预言家”等各种类型的现代人的批判。其中,他对诗人流露出一种既同情又批评的态度,行文中也有不少对《浮士德》的化用。起初查拉图斯特拉对门徒说“诗人们撒谎太多”,又说“但连查拉图斯特拉也是一个诗人”⑧。但在经过漠然、叹息、喘气之后,他说“我已经厌倦于诗人,老诗人和新诗人: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浅薄的,都是浅海”;“他们未曾充分思入深处:因此他们的感情不曾深入根底”⑨。这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尼采对歌德、布克哈特的反思批评。
三、“真诚性”与“生活感”:尼采时间美学的生成
不过,尼采即便离开巴塞尔,仍然保持着与布克哈特的书信往来,乃至在晚年仍称其为伟大的导师。海勒对此分析道:“是什么东西以这样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保留住尼采对叔本华和布克哈特的感情呢?无疑是歌德赞美叔本华身上的那种东西:知识上的诚实。也有别的东西:使他们继续活下去、保持清醒的精神活力,尽管他们有着深深的悲观主义。”①这里所谓的“诚实”和“精神活力”是在何种层面而言?尼采又是如何转化这些品质?
尼采之所以能够对诗人作出如上大胆的评论,实际正是“不合时宜的沉思”中逐渐生成的“永恒轮回”时间美学,赋予其置于“深处”的底气。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中,尼采还通过一个问题来辨识哪些是“历史的人”,哪些是“超历史的人”。他说,当被问及是否期望再次经历最近10年或者20年时,即便这两类人都说“不”,但他们所论证的方式是不同的。“历史的人”会寄希望于“下20年将更好”,因为对历史的观察使他们涌向未来,相信“存在的意义在一个过程的进展中越来越显明”②,这样的人持有的即线性进步观。相比之下,“超历史的人”之所以不期望再经历,是因为他们“并不在救赎的过程中观看”,对他们来说,“世界在每一个个别的瞬间都是完成了的,都达到了自己的终点。新的10年又能教导什么过去10年所不能教导的东西”。③也就是,“超历史的人”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视作根本同一,生命经历的每个瞬间如同圆周上的任意一点——从圆的整体形态来看并无本质差别,而它们到达圆心的距离也是一致的。这揭示的也是其其后提出的“永恒轮回”的基本特征。
尼采赞赏的“超历史的人”着眼的是圆心,即永恒的存在与意义。“过去的东西和当前的东西是同一种东西,也就是说,就一切多样性而言在类型上是相同的,作为不朽的类型的临在,是不变的价值和永恒同一的意义的一个恒定的构成。”④在随后题为《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的文章中,尼采通过展示“叔本华作为教育者真正说来应当教育的东西”,深化了相关的思考。他在其中特别批判“永恒的生成”:“由于它,人忘记了自己,忘记了个人按照一切风向散心的真正消遣,忘记了伟大的孩童即时间在我们面前并与我们一起玩的无穷无尽的童稚游戏”⑤。他认为叔本华具有的那种“真诚的英雄主义”,就在于“有一天不再当玩具”⑥,从存在出发、在永恒的东西中破解人生之谜。这里尼采对“游戏”与“玩具”的比喻,揭示了前者作为审美主体的主动性与后者作为客体被动性的差异。
尼采从叔本华身上看到的“真诚”,其主动性体现在人对自身形而上学性的把握。他同布克哈特接受其基本观念,认为人不能如同动物受欲望的驱使,盲目眷恋生活、贪求幸福。但尼采从“叔本华式的人”能够“承担起自愿受难”的精神之外,更看重的还是自我“翻转”和肯定的能力——“这种受难有助于他克制他自己的固执,并为对他自己的本质的那种完全的翻转和颠倒做好准备,而导向那种翻转和颠倒,就是生活的真正意义”⑦。正是通过翻转,“真诚的人感到自己的活动的意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从另一种更高的生活的法则出发可以解释的、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进行肯定的意义:哪怕他所做的一切都表现为对这种生活的法则的一种毁坏和砸碎”。⑧这样“叔本华式的人”,尼采认为才能远离“科学人”的冷冰冰和中立性,实现对“观察”的跃升。为此,除了延续布克哈特的观念对“卢梭的人”有最大众化作用的批评,他还引入“歌德式的人”相对照:“歌德式的人是一种保持的和受约束的力量……他有可能成为庸人。”⑨相比于这种人只是“为了高尚的柔弱,以便保存自己并对事物的多样性感到赏心悦目”;尼采称赞叔本华式的人是英雄主义的人,因为“他的力量在于遗忘自己”,“寻找非真理并且自愿委身于非幸福”①。如是,尼采在歌德—布克哈特的“沉思”之外,所看到的还是强力意志的超越性力量,不是任其“自然”的承受与保守,而是主体内在的克服、翻转、提升。
回到其历史认知,尼采最后也谈及“真诚性的每一增加都必然是对真正的教养的准备性促进”②。他以希腊文化为观照,指出古希腊也曾遭遇过五花八门的文化的危险,但是希腊人渐渐地学会了把混沌组织起来,回想自己的真正需求,在与自己做艰苦斗争之后,“成为一切后来文化民族的先行者和榜样”③。尼采强调这也是对每一个个人的比喻,显然内蕴的同样是“真诚的英雄主义”的主体性品质。为此他特别寄望于“青年”,正因他们和有教养的人相比是无知的:“仅仅确信一种在他们心中活动的、战斗的、挑剔的、分解的强势,确信一种在每一个美好的时刻都总是被提升的生活情感。”④
在此,尼采所说的“生活”(Leben)更倾向于表现“生命的力量”,不同于布克哈特的“生活”倾向于表现“生活的气息”。如吉尔汉姆(Simon Gillham)的归纳,尼采的“生命”/“生活”,既指行动或活动的能力及活动本身,也指“生命总是创造允许更复杂或更丰富的活动形式的价值,以此来提高自己”⑤。尼采出于反对历史学制造了一个“无生命的、但极为活跃的概念和语词工厂”,提出应该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倒转为“我生故我思”,因为人原初的感觉与其说是一个能思维的存在者不如说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者。⑥所以当尼采说要确信“每一个美好的时刻”都总是被提升时,进一步彰显其时间美学观念的生成。每一个时刻不一定是美好的,而主体正是要在自愿承受中把它翻转为美好,把每一刻都当成永恒去度过,不畏惧任何时刻的复返,在现实中提升生命的力量。
如果说,布克哈特也曾试图借助历史追求人的“真诚性”,即通过教学让人以自己特殊的方式理解历史并从中看到对自身有益的因素,仍然只是以历史为手段促使现代人“反身而诚”;相比之下,尼采的“真诚性”首先要求“非历史”的视域“封闭性”,认识自己的真正所需,而不是在线性进程中无限地延展,比较,欲求;尼采的“生活感”要求人“超历史”地理解自己生命的形而上学本质,创造更丰富的价值,提升存在的意义。由此,“真诚性”与“生活感”以“非历史”和“超历史”的方式昭示了尼采时间美学的生成,而这正是尼采“思入深处”的体现,也是查拉图斯特拉酝酿已久、呼之欲出的秘密。
余论
在歌德、布克哈特历史观的影响下,尼采接受了他们对自然、艺术、人性的重视和热爱;但经由历史反思生成的时间美学观念,使尼采在同样欣赏叔本华的同时,看到了布克哈特尚且看不到的“悲观主义”之外“超人”的一面——而这也标示了二人思想的根本分歧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尼采给布克哈特的最后一封信一般被布克哈特本人视为尼采陷入疯狂的表现,但实际也可以理解为尼采对布克哈特当初阅读回复其历史文的最后回应。
亲爱的教授:
最后,我宁愿成为巴塞尔的一名教授,而不愿成为上帝;但是我不敢压抑我个人的利己主义,以至于放弃创造世界……⑦
尼采从布克哈特的回信中理解他对巴塞尔教师职业的坚守,是怀揣着压抑利己主义的博爱情怀;而尼采曾经也有这样效仿的愿想,但他还是选择放弃教席而完全投入思想的创作,成为自己意志的“上帝”。尼采也从布克哈特日益的冷淡中理解,在布克哈特眼中他的选择是“利己”的甚至是疯狂的,但他最后还是想明示自己“创造世界”的理想:在语言的冲击中打破既定的思想秩序,成为未来的立法者,开启生命更丰富的可能。
就布克哈特和尼采的政治倾向而言,一般认为前者是自由主义的,立场是保守的;后者则富有革命伦理,立场更为激进。①但如前文分析,二者在历史认知和处理上,更多传递出的仍是个体主义的解决思路。布克哈特倾向于在文化史的沉思中追求私人的、审美的愉悦,并教育时人应该这样利用历史;尼采则是在“非历史”与“超历史”的阐发中,将之转换为主体意志的自我超越与更新。如海登·怀特就注意到尼采历史认知背后对共同体的消除和内在时间观的转变,指出“尼采用历史意识切断了在共同的事业中把人和其他人联系起来的最后纽带。他想像了历史本身的最终解体……尼采为了创造自主的个人,已经消除了共同体和文化的概念以及过去和未来的概念。在尼采看来,只有现在存在”。②
但这种转向个体内在的观念方法并非对社会普遍性问题的搁置。尼采和布克哈特都有意对抗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史学,因其以纯粹客观性为目标而导致对人的身心问题的隔膜与忽视,所以二人都支持把历史学当作艺术品,为的是真正进入、理解、召唤历史—现实背后的“人”,“保持本能,或者甚至唤起本能”③。布克哈特转向文化史研究,在当时还不为主流学界所认可;尼采反思历史学,亦常常不被史学界所重视,因为这挑战了他们研究的根基。而这一历史认知与批判恰恰值得文艺学领域乃至人文知识思想界所重视,因为尼采在理论解构与阐发中倾注的是对历史—现实中人的身心感受、精神状态、生命感觉的关怀,而不是为了非历史而“非历史”。
因此,尼采后来即便看到布克哈特的缺陷又始终保持对他的敬意,热衷与他交流,可以说是因为他当年在历史讲座中呈现的观念与运用,如对古希腊人和希腊文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化等“深入人心”的考察,既带动了尼采对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启蒙现代性的历史反思,也启发了尼采正视主体身心问题的人文主义视野,从而生成对历史—时间—生命新的观念认知。“那种细腻、充分展现出研究对象复杂性的历史研究,本身就具备增进我们面对世界、面对自我能力的作用;而这种展现中还具备着帮助我们反观自身、厘清自身、充实自身的要素时,它便同时成为我们改善自身、改善自身与世界关系的直接资源。具有这样品质的历史研究虽然往往和现代理论认知追求不直接相关,却是历史研究人文性的根本来源,并在这种对人的滋养中,间接地和理论创造力以及若何才能有益无害地应用理论于人的世界这样两个现代理论认知追求不可能回避的关键问题密切有关。”④这意味着,历史研究的人文意义首先在于帮助主体真正建立起面对自我与世界、处理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内在能力。也意味着,人文研究如能够将“历史—人心”作为方法,无论是文化批评还是理论生发,同样“包含着重新理解自我、诠释历史、改造世界的能动性契机”⑤。也是因为对这种能力与方法的有效自觉,尼采在随后的写作中表示,“我在发表反对‘历史病的言论时,已经学会了如何从这种病中缓慢地、费力地康复,而且,并不愿意因曾深受其苦便要在将来完全放弃历史”⑥。
① Friedrich Nietzsche,S?mtliche Brief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8 B?nden(Band 3 April 1869-Mai 1872), Herausgegeben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 Co. KG, München,p.155.
②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③ [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第287页。
④ 转引自[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第297页。
⑤ [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第303页。
⑥ 参见[美]阿尔伯特·所罗门:《雅各布·布克哈特:超越历史》,《新史学》(第4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页。
⑦ [美]埃利希·海勒:《尼采,自由精灵的导师》,杨恒达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年版,第62页。
⑧ 同上,第63—67页。
“永恒轮回”与历史认知——尼采时间美学的观念生成及其人文意义
① Jacob Burckhardt. Letter to Willibald Beyschlag, 14 June 1842, Letters, 73 (modified translalion; emphasis added).243. 转引自Richard Sigurdson. Jacob Burckhardt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Scholarly Publishing Division,2004,p.127.
②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第3页。
③ 参见[德]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9—30页。
④ 转引自[德]卡尔·洛维特:《雅各布·布克哈特》,楚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89页。
⑤ John R. Hinde,Jacob Burckhardt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0,p.115.
⑥ Jacob Burckhardt, Judgement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 Harry Zohn,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1958:243,转引自John R. Hinde,Jacob Burckhardt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ress.2000,p.115.
⑦ Richard Sigurdson. Jacob Burckhardt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Scholarly Publishing Division ,2004,p.127.
⑧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第VI页。
① [德]卡尔·洛维特:《雅各布·布克哈特》,楚人译,第41页。
② [德]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139页。
③ 同上,第193页。
④ 同上,第36页。
⑤ 同上,第168—169页。
⑥ 同上,第202页。
“永恒轮回”与历史认知——尼采时间美学的观念生成及其人文意义
① [德]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200页。
② 参见[瑞士]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194页。
③ [德]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143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147页。
⑥ 同上,第235—236页。
⑦ 同上。
⑧ [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163页。
⑨ 同上,第164—165页。
① [美]埃利希·海勒:《尼采,自由精灵的导师》,杨恒达译,第76页。
② [德]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第146页。
③ 同上,第147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287页。
⑥ 同上。
⑦ 同上,第284页。
⑧ 同上。
⑨ 同上,第283页。
“永恒轮回”与历史认知——尼采时间美学的观念生成及其人文意义
① [德]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287—288页。
② 同上,第239—240页。
③ 同上,第239页。
④ 同上,第237页。
⑤ [美]保罗·彼肖普:《尼采与古代:尼采对古典传统的反应和回答》,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
⑥ 参见[德]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234—235页。
⑦ Friedrich Nietzsche,S?mtliche Brief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8 B?nden (Band 8), Herausgegeben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 Co. KG, München,pp.577-578.
作者简介:姚思宇,南京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与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