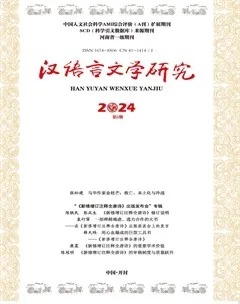左推右抱与思想认同:论陈铨的历史处境及其政治转向
2024-06-23李金凤
摘 要:陈铨在抗战时期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又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其历史处境和思想走向值得关注。作为一个既无官方也无党派背景的自由文人,在章汉夫的“檄文”发表和《野玫瑰》风波之后,陈铨的政治态度、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在国共两党的“左推右抱”中,政治立场由中立转向右倾。陈铨在抗战中后期宣扬、赞肯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理论和治国政策言论,也针对性地批评、暗讽与共产党有密切关联的左翼理论及其左翼人士。陈铨的“转向”是时代使然,现实遭遇所迫,更是符合其思想脉络的选择。时代、现实与思想等多重因素的交叉、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陈铨的本真面貌。仔细深究,陈铨的思想不曾有过“突变”,外界认为的“转向”是在特殊历史情境下其思想意识发生作用的结果,这不仅是陈铨在精神和心理上的需要,更是其思想逻辑的自然生成。陈铨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极大差异,在战时却走向了耦合,陈铨不加辨析和区分,造成误解和纠纷,也带来历史的警示。
关键词:陈铨;历史处境;政治转向;《野玫瑰》风波;民族主义
作家陈铨是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和精神个体。在瞬息万变、风云诡谲的战时环境中,陈铨经历了异于常人的生命体验,遭遇了一生中最为波澜起伏、心绪难宁的心境。过去,学界讨论更多的是《野玫瑰》风波等论争话题的事实本身和历史过程,至于左翼文化界的批判对陈铨精神世界和政治转向的影响则关注较少,也极少讨论陈铨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思想之间的关联。笔者以为,来自左翼文化界的批判、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以及陈铨的思想脉络对其情绪心态、政治选择、思想倾向都有极大影响。解决以上问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陈铨本人及其思想根源。本文即重点考察陈铨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处境与个人选择,通过细微、具体的文本材料呈现一个复杂的“个体”。
一、一则批判:章汉夫的“檄文”与陈铨的“反击”
一般认为,左翼文人对陈铨或战国策派的批判,对方似无回应,形成了不在场的单方批判。其实不然,陈铨在相关言论中有所回应。从这些只言片语中可以探究陈铨的情绪动态和思想理念。
1942年1月25日,章汉夫在其主编的中共机关刊物《群众》发表了一篇文章《“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公开指责战国策派明目张胆地追捧希特勒,歌颂法西斯主义,混淆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其本质是法西斯主义。①这是左翼文化界对战国策派最严厉的批评,从其措辞语气来看,相当于一篇战斗性极强的“檄文”,声色俱厉,打击面广。该文对《大公报·战国》前三期发表的文章都有所批评,譬如公孙震(林同济)的《知与力》、雷海宗的《战国时代的怨女旷夫》、吴宓的《改造民族精神之管见》等。其中,针对陈铨的《指环与正义》,批评篇幅最长、调门最高。章汉夫指出,不管正义、只管指环的立场和精神,“完全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侵略主义的应声虫”。②在国际局势逐渐明朗,中国已加入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营泾渭分明的情况下,章汉夫公开批判战国策派宣扬法西斯主义,无疑是致命的批判,其结论被引用、流传,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导向,给战国策派成员带来极大的压力。
自“檄文”发表后,战国策派主将陈铨对左翼人士的不满情绪在行文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就流露出来了。在此之前,陈铨在《战国策》《大公报·战国》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并不涉及中共和左翼人士的言论。陈铨言论虽有偏激之处,但他只是就自己的观点进行学理性的阐述。此文刊登之后,陈铨对左翼人士的态度发生突转。1942年1月28日,也就是在“檄文”发表后的第4天,《大公报·战国》刊登了陈铨一篇重要之文《政治理想与理想政治》。这篇文章无一字提到章汉夫及其文章,但不经意间就对此进行了“反击”与“回应”——“中国现在许多士大夫阶级的人,依然满嘴的‘国际、‘人类,听见人谈到国家民族,反而讥笑他眼光狭小,甚至横加污蔑,好像还嫌中国的民族意识太多,一定要尽量浇冷水,让它完全消灭。”①情绪的愤慨跃然纸上。陈铨等人谈“力”、论“战国”,是从民族国家立场上为“抗战建国”贡献心力。但陈铨视野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却不被左翼人士认同,遭到他们的“讥笑”“浇冷水”和“横加污蔑”。换而言之,来自左翼文人的批评之声,陈铨并非充耳不闻,不同层面和认知视角下的论争毫无意义,但一味的沉默隐忍也并非良策,他开始“发声”和“抗议”。
陈铨此文详细阐述了国民政府“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意志集中”“绝不是要求‘世界大同、‘正义和平的意志,更不是‘阶级斗争、‘个人自由的意志”②。陈铨认为,“世界大同”“正义和平”“阶级斗争”“个人自由”仅仅是虚幻的理想,并不是目前战国时代应宣传的口号,唯有“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才是战时中国“最有意义,最切合事实的口号”。左翼文化界宣传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实际影响乃减弱了民族团结的精神,增加了民族依赖的心理,甚至迟延了政治的统一,散分了军事的力量”③。这是在批评左翼文人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策略:影响了国民政府的统一,分散了抗战的军事力量,干扰了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针对国民党,陈铨希望国民政府从实际的“理想政治”出发,抛弃虚幻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强有力政府实现各方面的集权:“在目前紧迫情势下,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对于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彻底计划:训练每一个青年配作一个战士,整个的国家配作一个强有力的战斗单位。辽远的政治理想,外交官的辞令,暂时不必对民众宣传,先实行能够应付时代理想,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理想政治。”④陈铨在此显示了极强的议政意识,却也透露出对强权政治的肯定,符合国民党集权、独裁的现实需求,这自然值得左翼文化界警惕并作为批判的借口。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陈铨此文第一次对中共及左翼人士批评,恰好是在章汉夫文章发表后的第四天。目前无从得知陈铨写此文时是否看过章汉夫之文,从时间上看完全可能,这样一篇批判战国策派的重要文章,自然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到达”陈铨这边。陈铨对中共和左翼人士的态度也有显著变化,这变化不会无缘无故,极有可能与章汉夫的批判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陈铨的“英雄崇拜”观念引发了争议。战国策派内部人员沈从文、贺麟分别著文批评,“无论他们赞成或反对”,陈铨都表示“欢迎”和“感激”,不过那些“谩骂攻击的文章,或者应用一些肤浅无聊轻视侮辱的政治口号,或者因袭五四以来流行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不明时代,不顾事实,不解学理,实在没有反驳的价值”⑤。这是陈铨继《政治理想与理想政治》一文之后再次表态和回应文坛对他的批评。陈铨第一次谈论“英雄崇拜”时引起了误解和批判,他认为当时的批评都未理解其真正本意,从而再论“英雄崇拜”,“英雄就是群众的领袖,就是社会上的先知先觉,出类拔萃的天才”。①他进一步指出,意志是人类历史演进的中心,英雄的意志决定了历史的演进,从而与左翼文人提倡的“唯物史观”针锋相对。陈铨一再强调,“英雄崇拜的问题,根本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但他又解释“英雄崇拜”不仅是一个人格修养的道德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最迫切的“政治问题”。②前后矛盾,表述不清,仍旧会被人误解为提倡“领袖崇拜”“个人崇拜”,从而与国民党推崇的“领袖崇拜”价值观混为一谈,也暗合了法西斯主义的“领袖崇拜”精神。
陈铨在谈“民族文学运动”时指出:“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内部团结一致,对外求解放,而不是互相争斗,使全国四分五裂,给敌人长期侵略的机会。”③陈铨采取了主动反击的姿态,反对“骄傲别人的祖国”,反对苏联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干扰。他还特意指出一些左翼文学家缺乏民族国家意识,其理论和作品有损“抗战建国”宗旨。陈铨明显地维护国民党的思想理念,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判然不同。
学界指出,延安各界对“战国策派”文艺及其历史哲学、伦理思想、政治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1942年4月至10月。④从1942年1月起,陈铨在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方面发生了极大变动,我们也可从战国策派的核心刊物《战国策》《大公报·战国》和《民族文学》⑤觉察其中的变化轨迹。陈铨在这不同时间段编辑的三大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内容各有侧重。在《战国策》刊物上,陈铨主要介绍德国的民族性格、哲学文化,譬如,狂飙运动、叔本华哲学和尼采学说。陈铨重点介绍了尼采,从尼采的政治观、道德观、妇女观、无神论等各方面来阐述尼采的思想,总体而言偏于学理性。在《大公报·战国》副刊上,陈铨发表了八篇文章,除了《政治理想与理想政治》《再论英雄崇拜》之外,不触及党派政治或文坛文人,仅是对自身理论观念的阐述。《战国策》《大公报·战国》强调民族主义,提出“民族文学运动”,呼吁中国要向德国学习,提倡尚武精神、尼采哲学等,这都属于学术范畴和文学活动,与国民党保持遥远的距离,在必要时著文批评国民党。“抗战以来,中国的武人,在前线都有可歌可泣的功烈,中国的文官,却在后方极尽颓废贪婪的能事。”⑥这是陈铨对国民政府文官的批评。抗战中后期,他对政府的批评之声逐渐消失。陈铨在其主编的刊物《民族文学》上发表的文章与在之前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相比,具有明显差异。陈铨在此刊物上经常论述和赞同孙中山的思想言论,也不遗余力地宣传和阐述蒋中正的思想言论,支持和肯定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理论以及治国的政策言论。在支持、赞同国民党的理论学说时,也针对性地批评、暗讽与共产党有密切关联的左翼理论及其左翼文人,从而导致《民族文学》偏“右”、偏“蓝”,具有较浓的右翼色彩,这也是《民族文学》被左翼文化界批判的重要原因。⑦
事出必有因,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自由文人,陈铨在抗战中后期发生以上“突变”与他在抗战时期的经历、遭遇密切相关。这有必要重新考察他在抗战中后期的历史处境、情绪心态和思想流变。
二、左推右抱:《野玫瑰》风波引发的心理创伤与政治选择
章汉夫的“檄文”不过是一个导火线,点燃了陈铨心中的“怒火”与“不满”,真正对他造成极大伤害的是闹得沸沸扬扬的《野玫瑰》风波。确切地说,在重庆公演的话剧《野玫瑰》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风波事件,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改变了陈铨的走向和面貌。
剧本《野玫瑰》最初于1941年6月连载于重庆《文史杂志》。1941年8月3日至8日,“国民剧社”在昆明大剧院首演了此话剧,演出“极为成功”,没有任何质疑之声,“一致予以褒扬”。①这引起了中央文化部部长张道藩的注意。1942年初,《野玫瑰》剧本被他看中,他亲自组织人马公演该剧,该剧于1942年3月正式在重庆公演,取得了巨大成功。与此同时,《野玫瑰》剧本获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颁布的三等奖。紧接着,《野玫瑰》在国统区文艺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首先遭遇了左翼文化界的强烈批评与反抗。中共组织重庆戏剧界、文化界200余人由石凌鹤执笔,联名致函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要求教育部撤销对《野玫瑰》的奖励。他们认为,《野玫瑰》在曲解人生哲理,为汉奸制造理论根据,不利于抗战建国宣传政策,是有毒的“汉奸文学”。
面对左翼文化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教育部仍坚持原议,主持文化工作的官员积极扶持并在公开场合表态支持《野玫瑰》,这在无形中赋予了《野玫瑰》的官方色彩。1942年5月16日,在国民党召开的戏剧界人士茶会上,与会人士再次提出抗议,要求撤销对《野玫瑰》的奖励,并禁止上演。在场的陈立夫、张道藩、潘公展等人极力维护。陈立夫言:“审议会奖励系投票结果。给予三等奖,当然并非认为最佳者,不过聊示提倡,一二等奖,尚留以有待。”②张道藩指出:“我是学术审议会之一分子,但我不便明言我系投奖励《野玫瑰》的票或反对票。可是我又是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之常务理事,所以把戏剧界同人抗议《野玫瑰》的意见交给陈部长的也是我,不过抗议是不对的,只能批评。”③张道藩这番话说明他既参与了《野玫瑰》的投票,也知晓《野玫瑰》被抗议一事,但他仍然为陈铨辩护,“不许抗议”,“只能批评”,这是对陈铨最有力的支持。“潘主委公展最后发言,对于大家攻击《野玫瑰》,表示碍难同意。《野玫瑰》不惟不应禁演,且应提倡,倒是《屈原》剧本成问题。这时不应该鼓吹爆炸。”④潘公展甚至“面红筋胀地大声嚷叫”——“谁说《野玫瑰》是坏戏,《屈原》是好戏,谁就是白痴!”⑤潘公展极力维护《野玫瑰》声誉,显然是站在政治立场上赞同美化国民政府抗战地位的《野玫瑰》,希望借助《野玫瑰》来打击、削减郭沫若的“屈原热”,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消除《屈原》的影响。
李岚曾对《野玫瑰》论争的全过程作了完整叙述和分析,揭示其背后所蕴藏的国共两党之间复杂的政治斗争。⑥但处在论争焦点上的陈铨,未必能跳出历史的泥淖,未必能看到《野玫瑰》之争背后政治力量的博弈。他接受了来自国民党方面的“赞肯”,也遭受了左翼文化界扑面而来的整体性“批判”。各大报纸《新华日报》《新蜀报》《时事新报》《华西日报》《国民公报》等都刊载了批判《野玫瑰》的文章。例如,颜翰彤《读〈野玫瑰〉》,方纪《糖衣炮弹药——野玫瑰观后》,谷虹《有毒的〈野玫瑰〉》,孟山《野玫瑰观后感》,洪钟《评野玫瑰》,徐曼《剪灯碎语之二》,余士根《指环的贬值》……面对人生以来第一次大风暴,着实给陈铨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有资料记载,陈铨曾托人去说要看望左翼文化界领导阳翰笙,阳翰笙“连忙过去”会访老同学。⑦陈铨与阳翰笙同为1920年代初四川省立一中同学,算是多年朋友,陈铨遭到如此批判和围剿,想必是希望从老同学阳翰笙那儿得到解释或慰藉,同时也为《野玫瑰》辩解。至于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内容,目前未有资料公开。倒是阳翰笙在多年以后告知:“陈铨当时情绪有些低落,大概是挨了批判的缘故,他劝陈振作精神,继续教书写作。”①这是目前所知陈铨与左翼人士的沟通交流记载,这意味着他无法理解当时的历史情境和自身遭遇,感到迷茫无助。
陈铨作为一个自由文人,既无官方背景,也与左翼人士无任何恩怨瓜葛,仅仅因为《野玫瑰》就遭到猛烈批判,想必他无法释然。按照陈铨的学识见解和理论逻辑,《野玫瑰》并非在歌颂美化汉奸,不过是将战争、爱情与道德三种题材糅合一体,通过锄奸抗敌来批判个人主义错误,宣传民族意识。“尽管他们如何批判,我始终不承认《野玫瑰》是汉奸文学。”②理念和认知的巨大差异,导致两者之间无法正常沟通交流。左翼文化界留给陈铨的印象也就是八个字——“吹毛求疵,猛烈抨击”。但是,左翼文化界组织人马一边倒地批评甚至人身攻击,陈铨的情绪仍然受到了极大波动,埋下深重的心理阴影。
陈铨在多篇文章中有所指涉或暗示《野玫瑰》论争带给他的伤害和痛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罗梦册曾发表一篇文章《论少壮》,陈铨在其主编的《民族文学》刊物上撰文《少壮的阶级》谈论感想。陈铨对此文深有体会,产生了强烈共鸣。罗梦册认为,人生在少壮阶级是最苦痛最艰辛的阶段,在做学问或事业的道途上必然要遭遇些艰难。有时走得勇猛或迅速,难免会在路上跨过前人,顶撞旁人,踩着别人。“或者是虽根本与他人无涉,一颗彗星的出现,每会衬出他人的无颜色,也每会威胁或动摇一些过时的偶像,这样一来,几乎是无可逃免地,一个严重的打击就会随之而来。”③陈铨认为这背后“隐藏着人生的经验”,“是一段说尽人情世故的文章”。陈铨从罗梦册的言论中产生了代入感,他联想到自身被戏剧人士忌妒的生命体验,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是被攻击和打压的彗星。有知情人指出:“陈铨在剧坛上无藉藉名,在现一旦成名,多少有些气愤不过,于是以‘有毒素作为攻击陈氏的武器。”④《野玫瑰》之争确有“不便明言”的“妒忌”成分。孔刘辉认为:“深文周纳的诛心之论,还是给陈铨带来了深深的伤害,始终郁结于心,并在《嫉妒的批评》《批评与创作》等文中有所暗示和投射,日后还有感而发,写下长文讨论‘嫉妒的表现形态、产生原因和危害性。”⑤
《野玫瑰》风波确实给陈铨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创伤记忆,并对他的生存处境造成了极大困扰。陈铨亲自导演其话剧《蓝蝴蝶》,“排演时对于舞台的步位很下了一番功夫,但演员们因为对他不甚有好感,终于草草演出,不甚成功”,“陈铨的剧作虽然不少,但因为被人攻击的缘故,始终没有把他正式列入‘剧作者之列,虽然《野玫瑰》曾经得过奖,事后却给人作为攻击的资料,而今他的东西改作为《天子第一号》搬上银幕,连一块钱的版税都没有得到呢”。⑥陈铨被攻击之后,演员不配合,演出不成功,剧作家身份得不到承认,版税被克扣,困境重重,难以体面地生活。读罗梦册之文,强烈的心灵共鸣让陈铨感到遇上了知音。他深有感悟地摘抄着这一段话:“不是前边的人回头给您当头一棒,或劈面一个耳光,便是联合所有被您的光芒所威胁的人们对您作一个围攻或包剿;再不然,就是坚壁清野,与您不来往,誓死否认您这一笔帐,把您摒斥于孤独畸零的角落,或把您拌成为一个滑稽或不懂人事的征象,使人人对您不喜。这种打击,每会使一个被打者为之一蹶不振,渐渐地颓废下去;也会使每一个被打者被人遗忘,永处下尘。”⑦仔细琢磨这段话,“当头一棒”“联合”“围攻或包剿”“孤独畸零”“滑稽或不懂人事的征象”,与其说是在解说罗梦册的话语,不如说是陈铨的夫子自道、心灵独白!面对左翼文化界突如其来的批判、讽刺、挖苦,乃至误解、曲解他的文章思想,陈铨的内心遭受了暴风雨般的煎熬。这种围剿、批判严重损害了他的声誉,他在文化界陷入“孤独畸零”的境地,在事业上遭遇重大波折。有论者指出,对《野玫瑰》“批判的浓厚政治色彩,猛烈严厉程度,几乎是没有前例的”,即使“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①既然“野玫瑰”风波更多的属于政治立场上的批判,陈铨事后必然会逐渐意识到,紧跟国民党才能确保自己不被打压和遗忘,在现实中重构自身的价值和地位。
处在迷瘴中的陈铨,在创伤应激中做出了本能的反应和回应。《野玫瑰》论争过程中,来自国民党方面的保护与维护,陈铨在心理层面是动容的。我们无法断定《野玫瑰》论争对陈铨的“转向”到底有多大影响,有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正是这次《野玫瑰》论争将陈铨“拉入”了国民党阵营。通过《野玫瑰》风波事件,陈铨认识了国民党官员,建立起了事实上的联系。有资料证明,陈铨来到重庆后,的确在与国民党官员交往。“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张治中特地接近了陈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宣传部长朱家骅也在重庆宴请陈铨和西南联大的蒋梦麟、梅贻琦两位校长。”②陈铨经常在《军事与政治》杂志上发表文章,该杂志刊登了他的剧作《衣橱》《金指环》《蓝蝴蝶》以及戏剧理论文章《文学运动与民族运动》《戏剧的深浅问题》《戏剧批评与戏剧创作》等。《军事与政治》隶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张治中时任军委会政治部主任。张治中“特地接近”陈铨,本身就说明两者之间的交往与交情。和陈铨一样,留德出身的朱家骅也认同德国思想文化,他们之间有共同的学术背景。“宴请陈铨”是和西南联大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同时进行,由此可知,陈铨备受朱家骅尊重和重视。
陈铨在1950年代初“肃反运动”的交代材料中坦言:“当我握笔写《野玫瑰》这个剧本的时候,在中国政治上我认识的人很少,国民党的大头,如朱家骅,张道藩,潘公展,陈立夫,张治中,戴笠,我一个也不认识,我认识他们在1942年到重庆之后,由于《野玫瑰》的关系才认识的。”③这份材料说明,陈铨来重庆之前与国民党官员未有联络。可以推断,陈铨在为《战国策》与《大公报·战国》组稿写文章时,也不认识这几位官员。但是《野玫瑰》事件改变了这一距离,将他们的关系拉近了。《野玫瑰》风波事件相当于一个桥梁,联系起了陈铨与国民党,也类似于一个挡箭牌,阻碍了陈铨与中共之间的联系。
话剧《野玫瑰》的成功给陈铨带来了巨大声誉,使陈铨由一个默然无声的大学教员迅速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著名的文化人士,他的人生从此走向了新的道路。1942年8、9月,陈铨来到重庆,经好友向理润介绍到中国电影制片厂任“编导委员”。紧接着是中国青年剧团编导、重庆正中书局总编辑、重庆青年书店总编辑。1943年1月正式担任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中国青年剧团隶属于国民党,正中书局是由陈立夫创立并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的党营出版机构。中央政治学校是中国国民党训政时期培育国家政治人才的主要基地,当年地位类似今日的“中共中央党校”。陈铨积极参与了国民党官办的文化机构,也配合了国民党官办的文艺刊物《文艺先锋》和《文化先锋》。1942年9月,张道藩在《文化先锋》创刊号上炮制出代表官方文艺政策的文章《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由梁实秋的质疑与批评引发了不大不小的论战,陈铨站在张道藩这边,著文《柏拉图的文艺政策》给予声援。他认为,国民党现在实行文艺政策是世界的潮流趋势,无可厚非。当今时代是由个人主义转向了柏拉图的集团主义,“文艺方面,是否需要文艺政策,这完全要看民族生存的大前提之下,是否需要,假如需要,是没有多少讨论的余地的”。④这段话看似客观、无所偏颇,但考虑到“民族生存的大前提”,陈铨已然揭晓:抗战时代需要文艺政策。一些事实证明,来到重庆的陈铨与张道藩、李辰冬等人多有交往。陈铨事后承认:“在重庆时,张道藩命他办《文艺先锋》及《文化先锋》,他常来请我写文章。他又奉命来拉我入党,我没有答应。”①目前尚未有充分证据证明陈铨是否参与了《文艺先锋》和《文化先锋》的编辑工作,但力所能及地在此刊物上发文章,陈铨照办了。陈铨没有“答应”入党,抵制住了李辰冬、蒋复璁等人的游说,可能是出于各方考量,但这并不代表他与国民党就是泾渭分明,相反,陈铨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复杂而微妙。
事实上,正是《野玫瑰》风波事件,将陈铨与国民党之间联系起来,也将他与中共疏离开来。左翼文化界不接受陈铨,集体抨击他,给他扣上“宣扬法西斯主义”“汉奸文人”的帽子,视之为中共的敌人、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防御心理,这反而将陈铨抛向了国民党阵营。自陈铨由昆明来到重庆之后,他就与国民政府采取合作的态度,明显支持和宣扬国民政府的政策、文化理念。当陈铨有机会担任青年书店总编辑,有能力创办《民族文学》刊物时,他结合自身的思想理论,既坚持倡导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民族文学运动”,又赞同宣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理论。陈铨在《民族文学》刊物上不断替国民党宣传,对中共态度不友好,这就使刊物具有较强的右翼特征,进一步刺激了左翼文化界的批判。洪钟《“战国”派文艺的改装》专门针对《民族文学》的言论挑刺,他认为陈铨的文学理论,仍然建立在法西斯的哲学基础上,指责“陈铨所见的民族运动跟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民族运动是毫无共通之点的。如果硬把法西斯的侵略民族主义强加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头上,其存心如何我们颇不便忖度了”。②这里蕴含着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洪钟意识到陈铨在将自行倡导的“民族文学运动”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结合起来。阅读《民族文学》刊物会发现,陈铨的确是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自身的民族主义理论、文化改建等方面的指南针。二、陈铨的民族主义理论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颇有相似之处,但洪钟否认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其最终目标是将陈铨与法西斯主义画上等号,“陈铨=法西斯”,破坏其名声,诋毁“民族文学运动”。三、如果陈铨的“民族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一样,那么这就说明陈铨与国民党在合作,文人依附现任政府,洪钟不便明言,“其存心如何我们颇不便忖度了”。还是中共机关刊物《解放日报》编者说得明白:“在大后方严密的书报杂志检查法网之下,这种公开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刊物,却可以自由自在地向出版界放毒,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家里岂不是怪事!”③《解放日报》编辑直接认为《民族文学》是在宣传法西斯主义(事实并非如此),并谴责国民党纵容、包庇陈铨。
不管陈铨是走向法西斯还是走向国民党,抑或是停留在“中间地带”,左翼人士皆双向出击、嘲讽批判,陈铨已被中共树立为统一战线之外的“敌人”。皖南事变之后,左翼文化界屡遭国民党当局压制,陈铨的言行举止无疑令左翼知识分子不喜,并在无意中助力于国民党文化统制的需要。作为左翼知识分子转移文化斗争的目标,也作为中共执行文化斗争策略的手段——统战是需要的,树立对手和反面也是需要的,两者共存于中共文化斗争政策之中,陈铨不幸成为其中的典型人物,被批判也就不可避免。陈铨无力抵抗“非左即右”的历史大趋势,深处政治旋涡中的他无可奈何,可悲地成了国共斗争的牺牲品。
三、理念契合:现实政治与民族主义思想的激发
必须指出,《野玫瑰》风波事件绝不是陈铨偏向国民党的最终原因,它只是一个关键节点,没有它可能不会有后续的事情发生,但仅有《野玫瑰》风波事件却并不会改变陈铨的精神状态和政治面貌。陈铨的变化与选择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不全是国共两党的“左推右抱”,也不仅是时代和现实的因素,而是深层次的思想认同,其政治转向存在自然的内在逻辑关系。
首先,陈铨的民族主义理论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有相似、契合之处。国民党名义上公开继承弘扬的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两者之间从形式上看没有多大区别。民族主义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中占据最重要地位,这也是国民政府理论宣传中最核心的理论支点。陈铨接受和宣传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在肯定和宣扬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孙中山在民国20年代就意识到,帝国主义宣扬的世界主义并不适合受屈辱的中华民族,应认清中国现实,提倡民族主义才能改变目前中国的命运,它是拯救中华民族的重要武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①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概括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动向,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既先进又完整的思想体系。对于孙中山的思想理念,陈铨深以为然。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的民族浩劫,如何激发民众投身于抗日救亡大潮中,形塑浓厚的民族意识,这是具有民族情怀的陈铨重点思考的问题。陈铨一方面接受了从西方传来的尤其是德国思想资源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重视意志、情感、浪漫、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宣扬尼采的意志哲学,将之作为激发民族情绪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陈铨又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政府的抗战建国纲领中获得了另一种理论资源。陈铨民族主义的理论渊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我们对比孙中山、陈铨的民族主义言论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一关联。
在思考中华民族如何走出困境、摆脱屈辱地位时,孙中山和陈铨都借助了民族主义这一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武器,意识到民族主义远比世界主义、国际主义更适合当时中国国情,是中国切实需要的主义。陈铨借助民族主义及其民族文学,试图在中国兴起一场“民族文学运动”,开创“第二度新文化运动”。抗战时期,陈铨创作才能大爆发,创作了众多剧本,如《黄鹤楼》(1939年)、《野玫瑰》(1941年)、《金指环》(1943年)、《无情女》(1943年)、《蓝蝴蝶》(1943年)以及独幕剧《婚后》《自卫》《衣橱》等。其核心主题就是锄奸抗敌,宣传民族意识,批判个人主义错误,宣扬民族主义。陈铨万万想不到,一片苦心、十分热忱,换来的却是左翼文化界的冷嘲热讽、污蔑抵制,攻击自己为希特勒之流,战国策派就是在宣传法西斯主义,这对陈铨而言是当头棒喝、严重打击。这促使他在现实的政治选择上更加倾向于虽不乏腐败却也英勇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理论、抗战建国纲领深得陈铨的认同和赞赏,这就有了思想的基础和行动的可能。
仔细辨析,陈铨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思想是有分歧、差异的,陈铨的民族主义思想本质上是文化民族主义,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思想是政治民族主义。但在抗战背景下,在激发民族情绪、培养民族意识等方面,两者却走向了高度的认同。有学者指出:“此时的陈铨,已经完全摆脱了个人主义,成为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而且确实是比较倾向于政府权力层面的民族主义者,强调民众顺从政府和领袖的领导,共同抗击外敌的入侵,实现民族的复兴。这样的倾向,理所当然会受到喜欢批评政府的自由主义者和提倡启蒙大众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猛烈抨击。”②笔者以为,这个判断是可靠的,陈铨在1942年以后的确是倾向于政府权力层面的民族主义者,但他并非一开始就倾向于国民政府,而是在现实碰撞之后思想发生变化的结果。时局和时代是外因,《野玫瑰》风波是十分重要的现实因素,思想的认同、理念的契合才是陈铨政治转向和行为转变的核心要素。
留德时期,陈铨亲眼看到德国民族的性格与思想对德国走向世界强国发挥了重要作用。陈铨认为,德国人的民族意识、天才学说和英雄崇拜是其性格与思想的结晶,也是欧洲思想的另一派,在德国思想体系中根深叶茂。在德国的三年零四个月,对陈铨思想面貌的形成影响深远,并对抗战时期陈铨的政治选择和思想变化奠定了基础。随着抗战的爆发,陈铨逐渐从个人主义走向民族主义。在抗战前期,德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对国内知识分子而言,的确有了一个重新思考中国何去何从的新维度、新视野。中德关系的历史也已经证明,德国对中国的崛起确实具有诸多借鉴的资源。在陈铨看来,德国的军事技术、民族精神、思想文化等都值得中国学习和效仿。1933—1938年,国民政府恰与德国政府关系密切,中德在军事和经济上亲密合作,蒋介石聘请了德国顾问团为军事参谋。在思想文化领域,国民党旗下的蓝衣社曾宣传法西斯主义是救国的主义。抗战初期,德国的军事参谋仍在为中国抗战服务。尔后随着两国矛盾的加深,德国政府承认汪伪政权,中德才断交。这说明,陈铨倾向于国民政府是具有现实依据和思想基础的。
国难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的是国民党掌权的国民政府,这个政府是担当抗日救亡重任的政府,也是政权统一和政局稳定的象征。在民族危难之际,知识分子更需要一个统一、稳定的政府来面对国际战争,早日摆脱国家的危亡状况,走上民族独立自主的道路。战时知识分子,大体上倾向于国民政府。教授学者们纷纷走出书斋学堂,或投笔从戎,或投身政坛,或议军议政,采用各种方式为国家民族贡献心力。参政议政,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秉持书生论政、文章报国的传统文人精神,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陈铨的政治倾向、思想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陈铨的转变是时代使然,现实遭遇所迫,更是符合他思想脉络的选择。战国策派曾被郭沫若列为“蓝色”,被左翼文人认为“为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政治提供理论依据”①,虽言过其实,但并非空穴来风。学界在平反、重读陈铨的同时,有必要重新探究陈铨与国民党、共产党的真实关系,进一步思考战时语境下中国文人与当权政府、政治派别、个人际遇的多重关联。
四、结语:文化符号的典型个体
陈铨是因意识形态斗争而改写历史命运的典型文人,也是在抗战中后期自由知识分子认同国民党理论的代表人物,这是具有文化符号的典型个体。由于左翼文化界的批判、排挤,他们出于政治文化斗争的需要,将陈铨排除于中共统一战线之外,并逐渐将其树立为右翼文人。国民党出于文化统制的需要,巧妙地接住了左翼“推送”过来的“烫手山芋”,借势于陈铨的“名气”和“思想”为其服务。不管是左翼的大力打击,还是被现实政治利用,陈铨的转向和右翼化倾向归根结底在于深层次的主观思想意识。多重因素的交叉、碰撞、融合才最终形成了陈铨的本真状态。考察陈铨的一生及其重要节点,不曾有过“突变”,外界和后人认为的“转向”,其实是在特殊历史情境下其思想意识发生作用的结果,这不仅是精神和心理的需要,更是思想逻辑的自然生成。
多年留德求学经历、长期信仰民族主义思想、更具有传统文人的民族情怀,在特殊的战时环境中,陈铨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思想走向了耦合,但在本质上这两种民族主义是有区别的。陈铨无意去辨析,将两者混为一谈,尚未厘清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区别,这导致他始终无法在民族主义思想层面上与国民党做出恰当的区分与界限。自然,在政治权力与个体命运的纠缠中,一个小人物在“势大于人”的历史局势中,其处境十分尴尬,原本是符合其思想脉络的选择在特殊环境中被误解、被扭曲。陈铨一生推崇的“强力意志”恰似自身命运的反讽,终究难逃“浪漫悲剧”。陈铨的右翼化情有可原、理有所依,也值得重新审视。在历史洪流中,个人是渺小、无力的,尽可能地对统治集团保持高度的警醒,避免在短暂的“个人利益”、切近的“政治环境”以及可能的“思想契合”中,充当或被利用成集权统治的传声筒。以后人之眼观之,这对深处历史旋涡中的陈铨来说确实过于苛刻了。历史并未远去,这是陈铨留给后人的思考命题,也是今人知史明鉴的一面镜子。
① 陈铨:《政治理想与理想政治》,重庆《大公报·战国》1942年1月28日第4版。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陈铨:《再论英雄崇拜》,重庆《大公报·战国》1942年4月21日第4版。
左推右抱与思想认同:论陈铨的历史处境及其政治转向
① 陈铨:《再论英雄崇拜》,重庆《大公报·战国》1942年4月21日第4版。
② 同上。
③ 陈铨:《民族文学运动》,《民族文学》1943年第1期。
④ 秦林芳:《论延安各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1期。
⑤ 笔者认为《民族文学》是战国策派的后期刊物,参看笔者论文:《“战国策派”研究的历史现场与基本史实》,《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1期。
⑥ 陈铨:《论英雄崇拜》,昆明《战国策》1940年第4期。
⑦ 详情可参看笔者论文:《“大政治”与“大文学”——陈铨主编的〈民族文学〉》,《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3期。
① 孔刘辉:《陈铨戏剧活动考——从清华学校到西南联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3期。
② 《“戏剧界茶会”速写》,《时事新报》1942年5月20日第4版。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陈白尘:《对人世的告别》,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62页。
⑥ 李岚:《〈野玫瑰〉论争试探》,《中山大学学报论丛(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⑦ 阳翰笙:《阳翰笙日记》,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左推右抱与思想认同:论陈铨的历史处境及其政治转向
① 徐志福:《阳翰笙与陈铨》,《走近阳翰笙》,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67—268页。
② 陈雄岳:《与家兄陈铨相处的回忆》,1980年代手稿。转引自孔刘辉:《陈铨戏剧活动考——从清华学校到西南联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3期。
③ 陈铨:《少壮的阶级》(论坛),《民族文学》1943年第2期。
④ 欢:《〈野玫瑰〉作者陈铨》,《星期电影》1947年2月1日第6版。
⑤ 孔刘辉:《陈铨戏剧活动考——从清华学校到西南联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3期。
⑥ 欢:《〈野玫瑰〉作者陈铨》,《星期电影》1947年2月1日第6版。
⑦ 陈铨:《少壮的阶级》(论坛),《民族文学》1943年第2期。
① 马良春、张大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7页。
② 季进、曾一果:《陈铨:异邦的借镜》,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③ 《陈铨档案》,南京,南京大学档案馆。
④ 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编:《文艺论战》,重庆: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225页。
左推右抱与思想认同:论陈铨的历史处境及其政治转向
① “他”,即李辰冬。《陈铨档案》,南京,南京大学档案馆。
② 洪钟:《“战国”派文艺的改装》,《群众》1944年第9卷第22、23合刊。
③ 《解放日报》编者:《“民族文学”与法西斯谬论》,《解放日报》1944年8月8日第4版。
① 黄彦编注:《三民主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重印,第9页。
② 季进、曾一果:《陈铨:异邦的借镜》,第86页。
左推右抱与思想认同:论陈铨的历史处境及其政治转向
① 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作者简介:李金凤,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