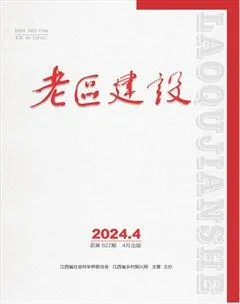红色资源地方性呈现的方向与路径
2024-06-21郑硕夫
摘 要:在红色资源开发中突出地方性,建立其与地方其他资源的关系,是将红色资源转化为地方发展资源的关键所在。以四川广元为例,发现寻找红色资源与交通、生态和历史等其他资源优势的内在契合点,是呈现红色资源地方性应当遵循的方向。以多方协力调动民众参与红色资源开发为基础,通过生活化场景凝聚集体情感、差异化开发直面市场需求、具象化载体凝练可感符号的路径,红色资源的地方性在建构红色主题的过程中变得更为鲜活。主动承接和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在区域文化整体性中凸显红色资源的地方特色,为开发红色资源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红色资源;地方性;契合点;主题性;广元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7544(2024)04-0081-09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红色资源的重要性,指出“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1]。从广义上看,红色资源主要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具有资源属性的物质和精神形态。[2]近年来,全国红色旅游蓬勃发展,接待人数从2004年的1.4亿人次增长到2019年的14.1亿人次[3],各地开发红色资源的热情也随之高涨。然而,许多地方未能实现红色资源之间、红色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之间的有效整合,降低了红色资源的便利性与吸引力[4]。这折射出当前红色资源开发未能很好结合地方特色。而地方性是增强红色资源可见度的关键要素,成为民众建构红色资源空间认同的附着点。[5]找准开发利用红色资源的自身定位,有助于红色资源匹配地方产业发展与社会市场需求。[6]
可以看出,地方性的顺利呈现,关乎红色资源同地方其他资源联动开发的效果,亦能拓展红色资源的转型思路。当前研究虽较为重视结合地方案例探讨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但大多停留在宏观现状、问题和对策层面,未能很好结合案例深度阐释红色资源地方性以何种方式存在,又通过何种途径呈现出来。鉴于此,本文希望借助个案研究,对红色资源开发中如何呈现地方特色进行阐释,从而为革命老区因地制宜开发红色资源、助力当地发展提供参考。
二、文献简述与案例引介
唐文跃认为,地方性是某地自然与文化附着于地域环境之上的独特性,能赋予地方资源更强的外部感知。[7]虽然红色资源共同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华民族奋斗的精神谱系,但其产生背景和表现形式同样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唯有借助当地其他资源,方能更好地予以开发和呈现。
对此,有学者分别从避免同质、缩短距离、打破分割、突出特色[8],构建基于“资源—产品—市场—产业”互动共生的开发系统[9],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10]等方面提出结合地方特色开发红色资源的原则。这种结合,需要面向民众生活诉求,将红色资源同其他地方特色资源进行多样化组合。[11]具体来看,可通过构建地方红色资源矩阵、赓续地方红色文化血脉、强化地方相关政策供给、实现地方行动主体协同等措施予以完善。[12]而游客与本地居民基于多感官参与的“身体在场”,同样对红色资源的地方性呈现至关重要。[13]此外,红色资源的本地化开发离不开产权清晰的法治保障,明晰红色资源与旅游发展“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的法律界限。[14]
然而,既有研究大多将红色资源同地方其他资源的联动开发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由此提出呈现红色资源地方性的诸多策略,却较为忽视红色资源究竟能与哪些地方资源相结合,以及这种结合的程度与效果。另外,研究者过多关注红色资源如何借助地方性呈现实现对民众的教化,却未曾深入思考民众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能动作用,从而难以触及红色资源本土化开发的内在动力。因此,本文首先试图探究红色资源地方性呈现的基本原则,以厘清红色资源与地方其他资源实现关联开发的可行方向;再以此为基础,审视红色资源如何围绕当地民众的主体参与,在不断建构主题的过程中呈现地方性,从而丰富学界对红色资源本土化开发模式与转型路径的理论探讨。
本文选取四川广元为研究点,首先在于广元红色资源具有时间跨度长、空间分布广、类型丰富的特点。具体来看,当地红色资源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时期,涉及“川陕苏区”“三线建设”“抗震救灾”“脱贫攻坚”四大主题,涵盖战斗战役遗址、石刻标语、革命文物、纪念场馆、红色歌谣故事等多种类型,且广泛分布于市内各区县,其中录入全省历史红色遗址遗迹名录库的红色资源高达741处。[15]虽然广元近年来从政策规划到实践探索中,逐渐重视结合当地禀赋开发红色资源。但总体而言,当前广元红色资源开发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未能很好凝练出体现地域特色的红色文化符号,红色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效应还不明显。因此,以广元这个红色资源丰富、地域特色鲜明,但整体开发不甚完善、充满较多开发潜力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基于地方优势和他者经验,对红色资源地方性呈现的方向和路径进行探索性思考。
三、寻找契合:红色资源地方性呈现的应有方向
红色资源与地方其他资源的联动开发并非自然而然之事,二者究竟能否结合,以及从哪些方面结合,关系到双方联动开发的效果。换言之,寻找红色资源与地方其他资源的内在契合点,应该成为红色资源地方性呈现的重要原则。近年来,广元获得国家森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康养十强市等荣誉称号,显示出较强的区位、自然和历史文化优势。随着文旅业的发展,当地民众逐渐熟知和认同这些优势。因此,我们首先应结合地方优势,厘清广元红色资源联动地方其他资源呈现地方性的应有方向。
(一)红色事件与交通枢纽
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16]。可以看出,川陕苏区为红军的战略转移和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天然屏障。作为川陕苏区核心城市之一,广元历史上不仅是陆上出川入川的重要通道,而且是嘉陵江上游的水运枢纽。这一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成就了许多重要的红色事件,有助于我们针对性地挖掘和打造当地红色资源。例如,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在广元苍溪塔子山渡口取得强渡嘉陵江的胜利,开启了与党中央会师的长征之路。在这场胜利中,组建于广元旺苍王庙街戏楼的我军历史上第一支正规水兵部队——红四方面军水兵连发挥了关键作用。若我们将“强渡嘉陵江”“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首个水兵部队”等红色符号进行系统整合,则可让红色资源借助广元水运枢纽这一区位特色变得更为具象可感。
如今,兰渝铁路、西成高铁的通车和广元港的通航,为广元提供了“北向出川、南向出海、东向入江、西向入欧”的通道优势,使其在2022年成功入选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名单。因此,我们在结合广元区位优势开发红色资源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广元本身,还应站在服务国家区域战略的高度,与川陕革命根据地其他地区一道,在共同诠释“川陕苏区精神”时代表达的过程中进一步明确定位、彰显特色。
(二)红色遗迹与生态本底
自然环境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形成和资源开发有着广泛影响。有研究者认为,对自然环境的感知是红色旅游的重要部分。红色旅游地不仅以红色文化为特色,而且大多以自然环境为底衬。[17]广元的红色遗迹,往往和当地多山地、环境佳的自然生态本底相得益彰。
为了壮大根据地群众基础,红军曾利用广元所在的大巴山区多坚硬岩石的特点,组织刻字队(又称钻花队)镌刻了近2000幅向当地百姓宣传党政方针的石刻标语。[18]2003年,广元充分借助多山地势,在城区南山腰兴建了“红军文化园”,集中展示从民间搜集而来的红军石刻碑文,在方便群众感受红军精神的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广元红色资源自然禀赋的理解。
在“三线建设”时期,广元多山的地形特点恰好符合“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建设方针,不仅为当地留下了宝贵的人才和工业基础,也造就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为顺应当下不断兴起的“工业旅游”“怀旧旅游”热潮提供了良好平台。
红色资源与山区农文旅产业的融合,亦能为我们寻找红色资源与自然底色的契合点提供广阔思路。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后,广元人民在灾后重建中感恩奋进,充分利用山地优势,大力发展茶叶种植、红心猕猴桃栽培、乡村旅游等产业,实现了对红色资源的时代传承和活化利用,不断赋予其新的精神内涵。 此外,广元依托地形、气候和水文,形成了良好的生态优势,成为四川首个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市。其绿色低碳的生态本底,高度契合红色文化传递的艰苦朴素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现代人追求健康生活品质的游憩理念。《广元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便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成渝地区高品质生态康养“后花园”、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的发展目标[19],为我们从广元生态优势入手,呈现红色资源地方性提供了政策指引。2022年11月通车的苍溪县黄猫垭镇高台村红色美丽村庄道路,作为四川省首条红色乡村示范路,则通过红色主题串联起沿线村庄的生态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红与绿”有机融合的有益尝试。[20]
(三)红色精神与厚重历史
广元古称利州,有着以三国文化、蜀道文化等为代表丰富历史文化资源。虽然它们与红色文化类型不同,但均可借助特色主题旅游线路串联起来,既有助于增强旅游的教育属性和价值引领,又能强化红色资源的历史厚度与体验属性。
在广元,昭化古城革命遗址群、红军攻克剑门关战斗遗址等红色资源,不仅与当地三国文化存在空间上的密切联系,而且与三国文化有着相通的精神内核。如红四方面军和蜀汉军队都是从外地来到广元,但均不畏强敌,善于利用当地风俗开展工作,重视同当地民众的血肉联系等。这为我们多维度阐释红色资源的地方特色与丰富内涵提供了参考。
作为古蜀道金牛蜀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剑阁县翠云廊有迄今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人工栽植驿道古柏群。2023年7月2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翠云廊时指出,“这片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之所以能够延续得这么久、保护得这么好,得益于明代开始颁布实行‘官民相禁剪伐‘交树交印等制度,一直沿袭至今、相习成风,更得益于当地百姓世代共同守护。”[21]不难看出,以翠云廊为代表的蜀道文化资源,与红色文化一样蕴含着廉洁自律、造福地方、服务人民的文化基因,同样可以赋予广元红色资源更为鲜明的历史主题。如今,翠云廊已成为重要的廉洁教育基地,对开发宣传广元红色资源起到明显推动作用,不断丰富着红色文化的承载方式和精神内涵。
四、建构主题:红色资源地方性呈现的可行路径
找到红色资源与地方其他资源的契合点,为红色资源呈现地方性提供了明确方向。然而,想要延此方向将地方性变得更为鲜活具体,我们还需思考如何将契合了红色资源与非红色资源的地方性凝练为可感可触的主题元素。建构主题,正日益成为许多地方增加旅游资源地方特色的重要着眼点。[23]
由于红色资源承载着几代人对当地自然文化资源的生活化理解和实践,故而只有依靠民众集体智慧,才能凝结成唤醒当地民众记忆和情感的红色主题。为此,我们可结合广元“剑门蜀道、女皇故里、红色热土、康养胜地”的城市名片,在调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通过回嵌生活情境、开发差异产品、凝练可感符号的方式,让红色资源的地方性借助特色鲜明的主题予以呈现。
(一)多方协力调动民众参与
诚然,红色资源的严肃性、庄重性和教育性,使得政府在开发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红色资源并非孤立静止、远离民众的产物,而是为当地人共同创造、口口相传。如许多红色歌谣,便来源于广为流传的民间俗语。若忽视人这一核心要素,我们便容易简单复制别处经验,所建构的红色主题难以获得民众认同。
当前,广元在红色资源开发中,同样存在民众低度参与的问题。从当地人言语中,笔者了解到政府在打造红色景区时未曾充分听取他们意见,并不重视搜集整理民间红色文化与红色记忆,所展演的红色节目显得较为单一,没能将当地文化元素很好融入其中。即使民众想要参与打造当地红色文化,却因缺乏便利平台渐渐消退了热情。
要想畅通民众参与红色资源开发的方式,地方文化工作者的支撑必不可少。他们能深入民众生活情境,激发他们不断形成挖掘红色资源价值的行动自觉。例如,“知客”这一活跃在广元农村的乡贤,常利用自身“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和良好的乡土语言表达能力,为老百姓深入浅出地讲述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深受民众喜爱。近年来,广元通过党建引领“知客协会”的组建,不断提升知客个人素养,将他们的文化才能有效地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24]在红色资源开发中,知客同样可以扮演组织者、协调者和宣传者的角色,用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调动他们的参与热情。
另外,号召相关企业加大开发红色资源开发的力度,将其转化为促进当地文化产业、生态产业发展的地方资源,不仅可以带动当地民众就业,而且能为他们参与建构红色主题搭建良好平台。延安红色景区便与企业联手,通过商业和文艺手段,结合当地居民生活现状、职业诉求和个人发展,不断建构极具个性化和多元化的红色记忆。[25]近年来,广元苍溪县黄猫垭镇高台村为了挖掘“黄猫垭歼灭战”所在地这一文化符号,依托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瞄准红色景区祭拜用花、接待讲解这一市场空白,发动群众种植菊花、组建讲解队,让红色资源开发在富民兴业中获得了来自当地民众的大力支持。
(二)回嵌生活凝聚集体情感
传统上,我们过多关注红色资源承载的宏大叙事,却较为忽视它与当地民众生活细节的紧密联系,从而难以勾起民众对红色资源的情感共鸣。许多以戏剧、美术、节庆等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红色资源,则通过凝结当地人生活化的集体情感展现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26]这启示我们重视来自民间的非物质红色资源,善用非物质手段表达民众对红色精神的本土化理解,从而让红色资源更具平民色彩和生活气息。如湖南汝城沙洲村围绕“半条被子”这一带有生活画面的故事宣传军民鱼水情深。旺苍“中国红军城”所处社区,通过兴建妇女生活馆,积极组织女性来此学习书画、茶艺、刺绣等非物质文化技艺,不仅很好延续了红军重视妇女工作的传统,而且借助红色文化不断提升民众的闲暇质量。
另外,建构体验式红色主题场景,同样有助于民众集体情感赋能红色资源的地方性呈现。自《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以来,尤其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广元大力营造多个红色主题场景。2009年建成开放的“红星公园”,位于九华岩战役遗址处,但它并未将目光局限战役本身,而是以红军塔为中心,用名人题词碑刻、红军敬礼雕塑等红色景观串联起红军主题纪念区、抗震救灾纪念区、教育励志休闲区和红星广场四大区域,方便人们在登山、跳广场舞等日常休闲活动中深刻领悟红军精神的时代和地域内涵。近年来,政府又在红星公园新修了茅草屋、土城墙、登山绿道等设施,为民众情景式体验红色文化提供了更多平台。
也应看到,相比于许多红色资源开发成熟的地方,广元还缺乏对红色主题餐馆、红色文创产品、红色地方美食、红色文化街区等消费场景和业态的打造,导致红色主题场景难以满足民众多样化的休闲游览需要。在调研中,我们注意到红星公园虽离广元市区不远,但公园周边餐馆、商店、指引标识等配套设施不仅数量缺乏,而且未能从整体上烘托红色主题。如此一来,许多外地游客很难专程来此或长时间在此感受广元红色文化魅力,红星公园的主题性场景亦难以突破时空限制而广为传播,发挥红色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反哺作用。
(三)直面市场实现差异开发
红色消费场景的缺乏,折射出广元红色资源开发片面依靠政府投入,缺乏市场导向的弊端。而直面市场需要的前提,离不开我们对不同市场主体的差异化认知。受年龄、职业、爱好和地域影响,不同群体对同样的红色资源往往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因此,当前许多地方才会将红色资源开发与亲子、研学、康养、团建、民俗旅游有机融合,扩大红色旅游的受众群体。
遗憾的是,直面市场的差异化开发在广元还比较欠缺。例如,南山红军文化园虽然汇集了大量标语碑刻,但长期缺乏形式新颖的宣传。若非单位组织的主题活动,游客很少自发来此。即使到此游览,他们仅能被动欣赏标语碑刻,难以听到讲解员的深度讲解,“吃、喝、购、学”等全方位需要更是匮乏。虽然红军文化园周边有几个农家乐,但文化园工作人员告诉笔者,由于它们定价过高,经营内容与红色主题相去甚远,往往难以满足游客的游览需求。
基于红色景区自身定位细分游客类型,满足其在红色旅游中的多维需求,是实现红色资源差异化开发的前提。例如,我们可在摩天岭战斗遗址、红军攻克剑门关战斗遗址等靠近风景名胜区的红色资源开发中,针对老年人等群体的康养需要,重点以当地绿色美食、清新空气为宣传点,打造一批精品民宿小院,将红军文化、三线建设文化等红色资源与老年人的怀旧情怀相联结;对于中国红军城、红军文化园、昭化古城革命遗址群、木门会议旧址等集中展示红军文化的博物馆似景点,则可多开发面向青少年群体的红色研学活动,邀请英雄人物、专家学者、地方贤达开展讲座,并在研学活动中融入当地非遗体验;而对于红坪苏维埃旧址、黄猫垭战斗遗址等地处乡村的红色景点,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带动村民在特色产业中融入当地红色文化,既有助于提升乡村旅游的教育价值,又能增加红色资源的附加值,建构更具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的红色主题。
(四)群策群力凝练可感符号
人是符号的动物。红色资源只有借助“符号化”的高度凝练,才能更好为民众所感悟和认同。[27]而这些凝练的符号,可以通过民俗歌谣、文创产品、标志景观等具体可感的方式予以呈现。在城市街区路灯、大桥、雕塑等造型设计中融入体现当地红色文化的符号,构建城市红色文化网络[28],便有助于我们从细微处增加民众共建红色主题符号的热情和机会。
虽然“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川陕苏区后期首府”“抗震救灾与感恩奋进”等词汇集中概括了广元红色资源的地方性主题,但它们大多停留在特定景区或官方文字宣传中,并未较好融入城市景观营造和市民活动组织当中,缺乏生动形象的符号化表达,自然难以调动民众参与开发红色资源的热情。
活用当地民众对家乡山水和文化的形象化、生活化理解,我们可以获得地方红色资源向可感符号转化的灵感。在南充仪陇朱德故里景区,笔者发现当地人将三块浑然一体,形似党徽的石头命名为“锤镰石”;根据琳琅山形似五角星的特点设计修建了五星迷宫。这些做法让当地特色景观与“伟人故里”红色主题符号有机融合。从当地人对这些具象符号绘声绘色、充满自豪的讲述中,笔者发现这种结合并非文旅单位为了开发旅游资源临时起意为之,而是源自当地百姓多年以来对朱德精神的质朴理解和对家园山水的深沉热爱。
朱德故里景区借用山水景致对红色资源的符号化表达,启示同为川陕革命老区的广元,充分利用当地人对家乡自然景观代代相传的“拟人化”理解,建构体现民间智慧的红色资源主题符号。其实,早在革命年代,民众便将当地多山地势特征融入红色歌谣创作当中。一首“木门寺,背靠山,徐总(指徐向前元帅)站在山门前。山头彩云飞,四面红旗展。徐总笑,干人(指穷人)欢,哈哈阵阵打上天”①的歌谣,便通过“山”“红旗”“徐总”“干人”等符号,为我们传递了木门会议后红军实力壮大的生动画面。如今,我们依然可以将广元的秀美山水打造为红色文化的有形载体,增强民众参与共建红色符号的积极性。例如,对于苍溪黄猫垭战斗遗址及周边区域的红色资源开发,我们便可围绕当地形如黄猫的两块巨石做文章,充分发动民众挖掘或建构各种主题符号,从而为这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经典战役增添更多可感元素。
另外,红色美食、文创、民宿产品亦能成为凸显地方红色资源主题的符号载体。近年来,朱德故里景区以“慢宿、慢食、慢行、慢游”理念为指导,通过“景区带村、景村一体”模式让当地百姓参与红色主题符号凝练。对于广元而言,我们亦可借助当地重视发展生态、康养旅游的契机,将红色资源所蕴含的绿色、质朴精神特质融入养生、低碳美食或环保民宿当中,在丰富红色精神时代价值的同时,赋予绿色产品更多红色基因。
五、结论和启示
综上所述,在红色资源开发中突出地方性,建立其与地方其他资源的关系,是将红色资源转化为地方发展资源的关键所在。从广元开发红色资源的实践中,我们发现,红色资源要想更好地呈现地方特色,实现与地方其他资源的联动开发,首先可从区位条件、自然禀赋、历史底蕴等方面,寻找两者在外在表现和内在精神上的契合点,从而明确双方相互结合以展现红色资源地方性的应有方向。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借助多方力量调动民众参与开发红色资源的热情,通过营造生活化场景、开发差异化产品、凝练具象化符号,建构体现红色资源地方性的鲜明主题。总之,地方性虽蕴含于红色资源当中,但它的凸显并非自然而然之事,而需通过民众广泛参与的开发实践,将红色资源同地方其他资源的内在契合点外化为易感知、可消费、广覆盖的场景与符号,方能成为带动地方发展的文化力量。
近年来,广元在开发红色资源中,逐渐体现出对资源地方性的重视与营造,这对于许多革命老区开发红色资源同样具有借鉴价值,也有助于我们避免片面依靠政府投入,忽视多主体参与和社会需求的弊端。然而,广元的红色资源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川陕苏区这片红色热土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主动承接和融入区域发展战略,才能进一步找准自身地方特色与优势。因此,如何将红色资源的地方性呈现更好地置于区域发展的背景之下,实现区域内部、区域之间文化资源的整体性和互补式开发,则成为后续研究可以深入思考的方向。
注释:
①这首歌谣的歌词来源为笔者于2023年8月2日拍摄于广元旺苍“中国红军城”景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J].求是,2021,(19).
[2]许若溪.红色资源的基本要素与时代价值[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10).
[3]王金伟.中国红色旅游发展报告(202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4]朱虹,宋丹丹.红色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J].旅游学刊,2023,(1).
[5]徐玲英,童兵.媒介化视域下红色资源的创新传播[J].当代传播,2022,(2).
[6]黄建红.“红三角”内源式发展: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衡山案例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23,(3).
[7]唐文跃.地方性与旅游开发的相互影响及其意义[J].旅游学刊,2013,(4).
[8]刘定禹,饶志华.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四维视阈[J].学术交流,2013,(8).
[9]黄细嘉,宋丽娟.红色旅游资源构成要素与开发因素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
[10]姜铭铎,赵云.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开发策略——以长征沿线为例[J].社会科学家,2022,(5).
[11]宋昌耀,厉新建,张琪.红色旅游的高质量发展[J].旅游学刊,2021,(6).
[12]卜昊昊,刘芮.地方感视域下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恋地呈现与在地化策略[J].档案与建设,2023,(9).
[13]张欣.旅游人类学视域下体验式红色旅游研究——基于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红色教学旅游基地的田野调查[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
[14]李淼磊,周刚志.红色资源旅游开发的内涵、问题及法治化路径[J].北京社会科学,2023,(3).
[15]中共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 广元市地方志编撰中心编.广元市红色资源概况[Z].内部资料.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闫昕,晏雄,解长雯,等.红色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链式生成机理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3,(3).
[18]李后强.弘扬长征精神振兴革命老区——以广元为例[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2).
[19]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关于印发《广元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2022-01-11)[2023-12-14].https://swglj.cngy.gov.cn/New/show/906538a8-fbd5-475d-be32-9c0365ba5228.html.
[20]裴文超.四川省首条红色乡村示范路,正式通车![EB/OL].(2022-11-14)[2024-01-30].https://www.nrra.gov.cn/art/2022/11/14/art_5145_197580.html.
[21]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7-30(01).
[22]陈胜.川陕苏区红色精神的传承与弘扬[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20,(3).
[23]段明明,罗丹.全域旅游背景下地方主题式旅游区发展策略探讨[J].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报,2019,(4).
[24]王翠.任务型乡贤:乡村精英再造的有益探索——基于四川省广元市“知客”队伍参与乡村治理的调研[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2,(4).
[25]白凯,康晓媛,王博林.延安城市居民红色记忆的建构路径与代际差异[J].自然资源学报,2021,(7).
[26]王伟,土登生根.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红色+”模式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2,(4).
[27]白海霞.红色旅游地文化氛围生产与旅游者价值观内化关系研究[J].大理大学学报,2022,(9).
[28]张铮,刘钰潭.记忆的弥散:延安纪念场馆中红色文化的空间生成[J].南京社会科学,2023,(7).
Direction and Path of Localized Presentation of Red Resources
—— Taking Guangyuan, Sichuan as an Example
Zheng Shuofu
Abstract: Highlighting localiz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d resources and establishing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local resources is the key to transforming red resources into local development resources. Taking Guangyuan, Sichuan as an example, it is found that finding the internal integrating point between red resources and other resource advantages such as transportation, ecology, and history is the direction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for localized presentation of red resources. Based on the coordinated efforts of multiple parties to mobilize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d resources, the localization of red resources becomes more vivid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red themes by condensing collective emotions through real-life scenes, facing market demands through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and condensing tangible symbols through concrete carriers.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undertake and integrate into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highlighting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d resources in the integrity of the regional culture,will provide new ideas for us to develop red resources.
Key words: Red resources; Localization; Integrating point; Theme; Guangyuan
责任编辑:李佳佳
基金项目: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红色文旅研究中心项目“广元红色资源的主题性开发研究”(HSWL23Y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喀斯特多民族地区社会时间耦合机制研究”(23YJC850003);四川旅游学院“博士训练营”科研专项(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项目“乡村休闲文化变迁调查及优化策略研究”(2023SCTUBSSD02)。
作者简介:郑硕夫,四川旅游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