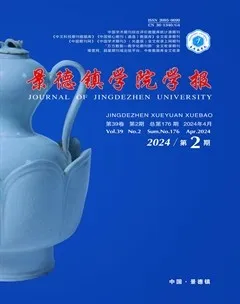从《曹雪芹》看编导主体意识在当代中国古典舞剧实践中的呈现
2024-06-20孙晓芳
※ 投稿时间:2023-11-21
作者简介:孙晓芳(1980-),女,辽宁沈阳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舞蹈编导教学研究。
摘 要:在舞蹈艺术实践过程中,编导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尤其是编导的主体意识在其中起着基础和支配的作用,是编导行动力、决策力和指导力形成的关键因素。中国古典舞剧《曹雪芹》的成功问世,与编导主体意识的融入密不可分,从此剧中编导主体意识的呈现看,主要体现五个方面,即结构布局意识、史料还原意识、文化传承意识、舞台设计意识和文化自信意识。正是由于该剧编导具有以上五个方面的主体意识,使《曹雪芹》成为一部具有内涵深度、情感温度、艺术高度的当代优秀中国古典舞剧作品。
关键词:古典舞剧;《曹雪芹》;编导主体意识;呈现
中图分类号:J7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699(2024)02-0075-07
由北京市海淀区委宣传部出品,中关村国际舞蹈中心、亚洲大美青年艺术团(北京)有限公司创演的古典舞剧《曹雪芹》于2020年9月16日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以来,因其独特的艺术架构、个性化的表现方式、写意化的舞台设计受到了业内人士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并在2022年9月21日成功入围第十三届中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舞剧终评作品名单。此剧的问世,一方面展示了当代我国在舞蹈创作、表演、教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新时代我国古典舞艺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的新成就。此剧之所以能够获得观众的认可和良好的口碑,并且获得艺术和票房的双成果,与参加舞剧策划、编导、演员、舞美、宣传等全体人员的努力密不可分。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由刘震、何夕、程宇、崔睿等组成的核心编导团队,在洞察我国古典舞剧艺术创演历史和现状、把握舞剧创作艺术规律的基础上,以团结协作的精神集思广益,为舞剧谋篇布局,在群策群力中集中体现出编导主体意识所发挥的效力。特别是在首演之后,编导团队本着“出作品、出精品”的原则再次精准打磨,同时也从不同角度呈现出了编导主体意识在中国古典舞剧艺术实践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多线交叉—编导结构布局意识的呈现
对于“曹雪芹”这个名字,几乎所有人都可能联想到他那部名垂文学史的鸿篇巨制《红楼梦》,但是在此剧作的叙事结构上,并没有将目光聚焦于《红楼梦》以及小说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具体形象上。而是从“曹雪芹”这一现实的人物形象出发,力求展现他从“钟鸣鼎食到举家食粥”的人生遭遇,将更多的笔墨着色于曹雪芹的日常生活、情感历程和文学追求,通过舞蹈和戏剧的融合,再现和还原曹雪芹的本真形象。舞剧的戏剧叙事性决定了它的结构布局性特点,即在人、事、物的相互关联和时间、空间的变化与交错中组织结构、构筑层次、形成布局,从而塑造人物形象、阐述事件过程,并借助一定的空间呈现舞剧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首先能够肯定的是,历史上发生于曹雪芹家族中的事件是真实的,曹雪芹曾祖父曹玺、祖父曹寅所拥有的高官厚禄以及包括曾祖母在内与宫廷的特殊关系、康熙皇帝南巡驻足曹家、在雍正六年由于亏空案被抄家等事件,都有史实资料可查。正是由于从“座上客”到“阶下囚”身份的转变,为舞剧结构布局的形成提供了可大笔书写的条件。编导并没有按照曹雪芹人生经历的顺序娓娓道来,而是采用多线交叉的方式将其不平凡且戏剧性的人生经历进行构筑和编织,并以故事叠加的方式还原了曹雪芹的本真形象,让人们暂时避开《红楼梦》的刻板印象和记忆定势,从历史与真实、叙事与抒情的视角去理解、思考曹雪芹这一形象。
舞剧整体上采用了标题化的结构方式,由“一序四幕”构成,分别是[序·百年怀想][第一幕·知交京华][第二幕·空老牵挂][第三幕·如梦大观][第四幕·只立千古],从这五个部分前后的关联看,共呈现出四条线索。
舞剧第一条线是时间线,舞剧并非按照时间的序列从曹雪芹的幼儿时期叙事,而是在[序]中,由妻子芳卿寻曹雪芹进入情节,在“夜深忽梦少年事”的虚幻气象中映照出离世的曹雪芹。这种采用倒叙的手法拉开序幕,给舞剧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也预示着接下来情节的发展将给人带来一种陌生感、期待感,为引人入胜氛围的营造进行了很好的铺垫。
舞剧第二条线为空间线,此剧在编导处理上的一大特色就是空间位置的变化,在时进时出中将叙事情节串联得无比紧密。如第一幕“知交京华”,叙述的是曹雪芹搬迁到北京后的生活,而在第三幕、第四幕中则叙述少年时期曹雪芹在金陵老家时发生的故事。这种空间位置的转移和变化均是通过梦境来呈现,以此表现出曹雪芹对年少时期美好光景和事物的回想,这与第一幕中曹雪芹穷困潦倒的京城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更加地凸显出戏剧性效果。
舞剧的第三条线是人物线,存在于多角度构思、多维度叙事、多人物塑造中。如在中、老年曹雪芹、芳卿两位主角形象的塑造上,在舞台上又通过少年曹雪芹和芳卿形象的设置,烘托和渲染回忆往事的情景;在第一幕中曹雪芹与京城三教九流人员之间发生的各种故事;在第三幕中与官吏、表哥之间的交往等,通过曹雪芹与不同人物之间的交往,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曹雪芹的人生经历。舞剧的“回归线”为情感线,即在多线交错以及各种情节的发展中,最终回归到了舞剧的核心要义“情”上,为了能够更为立体化地表现出曹雪芹之情,编导们从“爱情”和“人文情怀”这两个角度出发,通过“一序四幕”的故事叠加,在起伏跌宕、张弛有度的情节叙事中展现出来。
在爱情的表达上,着重围绕曹雪芹和芳卿的故事而展开,在舞剧中,芳卿是曹雪芹的表妹,青梅竹马的少小生活奠定了他们后来相知相爱的基础,芳卿也是伴随曹雪芹著作《红楼梦》走向生命终点的女人,因此编导在芳卿角色上着色较为浓重,除了第三幕外,在剧作其他部分中均有芳卿角色的出现,其目的就通过爱情还原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曹雪芹。其次,在“人文情怀”的表现上,主要出现在第一幕中,通过曹雪芹与京城恶少之间的相斗与相交、曹雪芹与西山平民百姓之间的相扶与相助,生动地塑造出了一位具有真性情和人文关怀的曹雪芹形象。
二、叙事情节—编导史料还原意识的呈现
对于舞剧编导而言,在创作关于历史人物的剧作时,其难点在于如何能够在剧作中表现出人物的真实性,尤其是在叙事情节的组织和表现上,只有贴近史实真相,才能激发起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认同感。从历史上关于人物、事件的记录看,在正史之中,多为王、侯、将、相的“传记”,而对其他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的记载,多散见于各种笔记、稗史、集录、话本等“非正史文本”中,因此缺乏一定的可信度。曹雪芹作为“非正史人物”,在正史中难觅其生平事迹,只能从“非正史文本”中寻找有价值的资料。其次,自曹雪芹完成《红楼梦》以来,随着小说的不断传播,二百多年来受到海内外读者广泛地追捧,随之而形成了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派,史称“红学”或“曹学”,与曹雪芹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这些都为编导们提供了可参考的资料。
舞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并非以史实记录见长,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艺术化塑造时,一般会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应尽可能地在现有史实资料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以此贴近真实;第二个是在一定范围内容的允许下进行艺术化处理,也就是要报以“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态度去丰富和完善舞剧的叙事情节。《曹雪芹》的编导团队从以上两个原则出发,在追求资料可信度的前提下紧扣发生在曹雪芹身上的细节,实现了叙事情节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从资料的挖掘看,在叙事情节的构思上,编导团队并非凭空臆想杜撰情节,而是求助于红学、曹学研究团体,其中,北京曹雪芹学会给予了编导团队极大地的支持,获取了丰富的史实资料,以此充实了舞剧的叙事内容,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编导团队的细心之处,也体现出了附着在编导身上尊重历史、对舞剧艺术高度负责的主体意识感。在樊志宾《曹雪芹西山足迹考》[1]、张云《对曹雪芹与北京西山的思考》[2]、胡鹏《曹雪芹在西山遗迹寻踪》[3]三篇文章中均研究并记录了曹雪芹在西山生活和著书的事迹,其中关于曹雪芹帮助西山人民从事手工劳动以养家的事迹最为津津乐道。为了能够帮助病残、鳏寡老人谋求生计,曹雪芹编著了《废艺斋集稿》一书,此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了有关金石篆刻、风筝之作、手工编织、布料印染、食物烹饪、园林设计等方面的内容,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清代手工产业笔记。在剧作的第一幕中,编导将上述史料用于曹雪芹与西山人们交往的叙事情节中,成为表现曹雪芹身负人文情怀的亮点之处。
在舞剧中,芳卿无疑是不折不扣的女主角,编导将芳卿角色定格为曹雪芹的妻子是有史实依据的,在吴恩裕《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著和遗物》[4]、于杞《曹雪芹书箱与春柳堂藏书》[5]、林同华《20世纪的“红学”:解读、反思与展望(下)》[6]三篇文章中,均提到晚年曹雪芹和续妻的故事。关于“芳卿”的真实身份,综合现阶段专家、学者的研究,曹雪芹在雍正五年(1727年)受两江总督尹继善之请赴江南做幕僚时,于秦淮一带寻得的当年在江宁织造府中的一位丫鬟,在朋友的撮合下与这位女子结为连理,后曹雪芹借《西厢记》中“花前邂逅见芳卿 ”一句为新娘命名。在现有史料中还记载到,曹雪芹在编著《废艺斋集稿》一书时,芳卿也有参与,并且在他们新婚时的书箱中,曹雪芹还为芳卿题写了五行的数目。正是由于编导抓到了史料中所记载的这些内容,将其改编成舞剧的情节,为塑造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曹雪芹形象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为了能够将叙事情节熔铸于“情”这一条“回归线”上,舞剧编导在挖掘史料素材中所体现出的锲而不舍、追求史实真相的精神,正是编导主体意识在其中所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舞剧《曹雪芹》在叙事情节方面之所以能够牵动观众的心,正因为编导抓住了塑造人物形象的魂,这种魂并不是编导天马行空似的信手挥成,而是在背后付出了艰辛的资料搜集劳动。通过对史料的挖掘、整理和运用,一则能够探寻出可进行叙事的内容,尤其是从只言片语的史料记载中发现了叙事的细节(在文艺创作中,人物形象与灵魂最为直接的表现就蕴含在看似不起眼的日常细节之中);另则从舞剧的核心要义“情”出发,通过对史料的挖掘,增强了舞剧情感的强度、加大抒情的力度、开掘出情感表现的深度。在叙事情节贴近史实真相的同时,编导又以恰到好处而不过分地艺术想象,将历史视野中的曹雪芹拉回到了现实生活中,让观众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只有通过《红楼梦》才能够认识和理解的人物。就这一方面看,编导史料还原意识在舞剧创作中“功不可没”。
三、风格表现—编导文化传承意识的呈现
舞剧作为一种舶来艺术,在我国出现还不到百年的时间,在我国舞蹈界,公认的中国第一部舞剧为舞蹈艺术家吴晓邦于1939年创作的《罂粟花》。近九十年来,数代中国舞蹈艺术家以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扎实的舞蹈基本功底为资本、以刻苦学习的精神为引领,实现了西方舞剧中国化的历史性嬗变。就民族化古典舞剧的编导而言,一方面要通过对民族文化元素的运用彰显其风格,另一方面则要结合中、外古典舞的表现技巧丰富其艺术表现力。因此,如何能够使《曹雪芹》这部舞剧既体现出民族化风格,又能够综合运用古今中外古典舞在表演实践方面的成就,成为编导在创作实践过程中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如果在风格表示上过于现代,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古典舞的意义与内涵;如果在舞剧表现方面过度的“洋化”,则必然与中国故事、中国题材并不相称,上述方面成为编导文化传承意识形成及其发挥的重要因素。
从《曹雪芹》的风格表现看,主要采用了“一体多翼”的方式,所谓“一体”,指的是舞剧的舞蹈特质,为了能够呈现出叙事的中国化,编导采用了中国古典舞的表现手法,如在第三幕中由女子群舞表现的“梦回江宁”,以充满水乡气息的古典舞步配合旗袍、纸扇等服装和道具,尽显灵动、曼妙的江南风格。除了在表现上极尽中国古典舞表现元素之外,还融合了中国民族民间舞、现代舞的元素,如在第一幕中,曹雪芹与京城恶少的“对打场面”,就运用了满蒙民族摔跤时的肢体和步伐技巧,同时又糅入了现代舞的表现语汇;在第三幕中的男子群舞,为了能够衬托青年曹雪芹志气高昂、血气方刚的性格特点,在表现技巧和风格上则借鉴了胶东秧歌的元素。
其次,在舞蹈形式方面,也体现出了中国古典舞所追求的气韵生动的审美特征,舞剧中独舞、双人舞、女子群舞、男子群舞的综合运用,于宏阔浩瀚的气势和细腻委婉的表达中完善了舞剧层次化和生动传神的艺术表现。如在第二幕中的镜中双人舞和第四幕中的月影双人舞,前后呼应,共同叙写曹雪芹与芳卿之间难舍难分、永不相离的爱情故事;由女子和男子分别承担的群舞,不仅在舞台艺术表现上夺人眼球,同时在与曹雪芹、芳卿双人舞的互动中,以流畅的气韵呈现和深厚的情感表达升华出了舞剧的主题。由此能够看出,舞剧在舞蹈表现方法的运用上,在保持古典气息和风格的前提下,有意识地借鉴和融入了其他舞蹈形式的表现元素,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即为了能够多角度的呈现叙事情节、立体化的塑造人物形象、沉浸式的展现人物心路历程,从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的角度对当代中国古典舞的文化归属与文化身份进行了强有力界定和诠释。
所谓“多翼”,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上,并以具体的叙事情节展现出来。如在第一幕中,由于抄家罚没,曹雪芹被迫迁到京城西山黄叶村,与以往衣食无忧的生活和众星捧月的身份相比,此时曹雪芹已身陷囹圄,衣食住行完全依靠自己,在身体和精神上呈现出疲倦困乏的状态。而当他坐在书桌前著书时,仿佛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力量,其奋笔疾书的状态像换了一个人,在表现这一状态时,编导通过对中国书法元素的融入,将草书艺术中的起笔、呼应、变化、转折、收笔、回锋等动作衍化为舞蹈语言,以此而表现和传达出人物的精气神。
在音乐的运用上,编导也有意识地融入了民族音乐的元素。首先,这部舞剧在音乐风格方面完全是中国化的,如对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主题曲《枉凝眉》(王立平作曲)旋律元素的运用,让观众与电视剧音乐和影像形成了共鸣;其次,就舞剧的音乐背景看,历来都是由西方管弦乐队、现代电声乐队进行烘托,此剧在保留传统配器手法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色,体现出了浓郁的民族音乐风格,如在第一幕曹雪芹与京城恶少的“较量”中,在乐队配器上加入了中国鼓、板鼓、笛子的音色,配合着源自民间打击乐的节奏和京韵大鼓中的旋律元素,既从情节方面渲染了气氛,又表现出较强的地域风格特点,以此而说明了情节发生的地点。
四、艺术品质—编剧舞台设计意识的呈现
与《丝路花雨》《奔月》《人生若只如初见》等大型的中国风格舞剧相比,《曹雪芹》在道具、舞美设计等方面虽犹不及,但是编导别出心裁的简约化设计与布局却能够驾驭舞台整体,钩沉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遐想和回忆,尤其是在与剧作抒情写意式主题的契合上几近完美。正如舞剧的总编导刘震所言“达到一人一书的境界”,因此简约化、真实化、抒情化、写意化的道具和舞美成为此剧舞台品质构筑的关键因素,也深刻地体现出了编剧艺术设计意识的重要作用。
首先,从舞台道具的运用看,在中国风格的舞剧中十分强调“典型道具”的运用,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表现符号贯穿于全剧,起到传递信息、引领剧情、表达情感的作用,这种情况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传统戏曲中善于运用信物的习惯有着很大的关联。在《曹雪芹》中,编导也关注到了这一特点,尤其是对“燕型风筝”道具的运用,成为该剧在表演中的一个光点,通过对剧作的叙事情节和情感表达的观察可以看出,燕型风筝的喻义十分深刻,并具有明喻和暗喻的特征。在明喻方面,燕型风筝意味着曹雪芹和芳卿之间的爱情。在我国古代的文论中,“双飞燕”是一个典型的爱情意象,如三国曹丕《清河》诗“愿为晨风鸟,双飞翔北林”;唐代李白《双燕离》诗“双燕复双燕,双飞令人羡”。在史料记载中,芳卿辅助曹雪芹著述《废艺斋集稿》时,其中包含《南鹞北鸢考工志》一篇,为专门讲述制作风筝的文章。因此燕型风筝道具在剧中的运用,既与史料记载呼应,又形象化地比喻两人之间的爱情。除了明喻两人的爱情外,燕型风筝还明喻曹雪芹的人文情怀。曹雪芹寓居西山黄叶村期间,曾教会村民如何制作风筝谋求生计,因此风筝道具的运用也代表着在曹雪芹身上所体现出的人间大爱。在暗喻方面,燕型风筝分别在剧中各幕中出现,突破了空间的限制,以此来暗喻曹雪芹对家乡的思念。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燕子除了具有爱情的喻意外,还具有“信使”“传书”的含义,如南朝江淹《效李陵从军》诗“袖中有短书,愿寄双飞燕”;清代顾炎武《寄刘处士大夫》诗“聊裁一幅书,去托双飞燕”,均表达了以燕为使传书送信的意思。所以,以燕型风筝贯穿全剧,并在金陵、京城南北两地空间的变化中隐含、诠释曹雪芹思念家乡的心结。
其次,在舞台服饰设计方面,编导并没有将关注的焦点放置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而是通过衣服表意推动情节的发展。舞剧的第三幕主要是表现清朝官场的黑暗,特别是表现出了官场中官员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巨型清朝官服的运用,当带有图文的印章于舞台上方垂落之时,数名官员各持官服一角,互相争夺,刻画出官员们争权夺利的丑恶面目。当印章落在舞台上的瞬间,曹雪芹的表哥—平郡王福彭也被压在了巨大的官服下面,以此而象征封建专制下的皇权势不可挡,实际上也生动地再现了曹家被抄家的场景。由此可以看出,编导在设计曹家被抄家以及曹雪芹入仕这两个情节时,只是运用了印章道具和一个巨大的官服,采用这种简约化、符号化的舞台设计手段,能够鲜明地呈现出舞剧的写意性特征。
最后,在“一人一书”的主旨的呈现上,编导不是通过《红楼梦》去塑造曹雪芹,或者通过曹雪芹的人生经历去表现《红楼梦》的创作过程,而是淡化《红楼梦》的角色和地位,因为在编导的艺术设计意识中,正是有了曹雪芹才有了《红楼梦》,坚持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也是“一人一书”主题的由来。在舞剧第四幕中,经过对曹雪芹形象的深度塑造和展示完他的心路历程之后,“红楼梦”三个字在多媒体影像的投放中缓缓而出,达到了“一人一书”的表现效果。此时的“红楼梦”并非指的是小说文本,而是以此来总结曹雪芹的如真如幻、如梦如醒、如实如虚、如真如假的一生,对应着《红楼梦》中的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成为剧中的“点睛之笔”。
五、团队协作—编导文化自信意识的呈现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12月14日所作的《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7]报告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中去。”同时,又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古典舞剧《曹雪芹》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应合了新时代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体现出了舞剧编导在艺术实践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文化自信力。一部舞剧的成功创演,并非一人之力所能够完成,而要凝聚团队力量,才能够创作出精品。
“曹雪芹”作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形象,《红楼梦》作为一部妇孺皆知的文学作品,在以往的电视剧、电影、话剧、音乐、绘画、戏曲等各种艺术体裁中均有所呈现,为了能够与其它艺术体裁在表现形式、手法和内容上有所区别,舞剧《曹雪芹》编导团队从区别于他者的角度进行切入,以创意化的编导意识、创新性的编导思维赋予了舞剧别样的艺术品质和审美追求。这种“旧题新作”的创演模式对当代中国舞剧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强劲的引领性作用,也充分地体现出了编导文化自信意识在当代舞剧艺术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文化自信意识是形成编导团队协作的主要动因。该剧集中了我国当代舞蹈艺术中颇具影响力的编导专家队伍。该剧的总导演兼编剧刘震为我国著名舞蹈家、中国古典舞编导和表演方面的代表人物,在《曹雪芹》创作之前,已经成功编导了《楚水巴山》《人生若只如初见》等作品。正是由于刘震在创作多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古典舞剧并获得成功的基础上,成为他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再次打造一部优秀古典舞作品的动机。由他带领的《曹雪芹》编导团队可以说是我国当代古典舞剧创作方面的强大阵容,尤其是“一人一书”舞剧主题的提出,成为该剧编导团队着力实践的“指南针”和“目标点”。这一主题看似“简约”,却凝聚了曹雪芹这位文化巨人一生的故事,承载了《红楼梦》这一中国古典文学巨著的精髓,非有高度文化自信者力所能及。
其次,该剧编导们的文化自信意识体现在对素材的挖掘、提炼和运用上。很多关于“曹雪芹”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基本上都是从小说《红楼梦》中获取创作元素,而此剧则不然,在很大程度上有意避开《红楼梦》元素,这就避免出现生搬硬套、高度模仿和移植的情况。舞剧编导为了能够尽最大可能地呈现出作品的原创性价值,决定执行“向史料问根的方针”,一方面能够发现和探索新的创作素材,另一方面则是能够运用贴近史实的资料去还原真实的曹雪芹。因此,要完成上述工作,既需要团队的协作,又需要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做到尊重文化现实,又能够生成文化意义,如在剧中书箱、风筝等道具的运用,就源于史料中的记载,具有现实性特点,当将这些道具运用在舞台上时,其代表的并不是具体的道具本身含义,它不仅具有抒情写意的内涵,而且具有了更为艺术性的文化意义。
最后,在团队协作下,该剧编导们的文化自信意识还体现在非遗文化的传播方面。虽然中国古典舞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个舞种,但究其历史看,却是中国古代舞蹈在当代的延续,自身就有着先天的文化和艺术“基因”。在文化自信意识下,一个民族要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和亲和力,具体到中国古典舞的创作方面,就是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元素,在作品中呈现出传统文化元素的价值,并能够起到传播、传承、推广和发展的作用。在曹雪芹移居北京西山黄叶村后(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他的很多事迹、传说被流传下来,在2011年“曹雪芹传说”作为北京市民间文学的代表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受保护对象。对于中国古典舞编导而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为有效的措施就是传承和发展。即按照文化自信的要求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文化价值在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中得以传播,正是基于新时代如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与发展,不仅成为该剧编导们艺术实践的动力,同时也显现出团队协作精神下编导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舞剧《曹雪芹》的问世,让人们认识到了一位充满人文情怀、内含社会大爱的曹雪芹形象,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转化,实现了“以文培元、以文化人、以文铸魂”的意义。
六、结语
在舞蹈艺术实践过程中,编导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尤其是编导的主体意识在其中发挥着基础和支配的作用,是编导行动力、决策力和指导力形成的关键因素。无可争辩,正是由于编导们在剧作结构布局、叙事情节、风格表现、舞台品质等方面的精雕细琢,使《曹雪芹》成为一部具有内涵深度、情感温度、艺术高度的当代优秀中国古典舞剧作品。不难发现,舞剧《曹雪芹》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由其承载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得益于编导主体意识在实践中的呈现和运用。此剧的成功问世也象征性地说明了在新时代中国古典舞剧的创作上,应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编导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也说明了在编导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应从主体意识培养的角度入手,才能够激发编导人才的创造力和创新力。
参考文献:
[1]樊志宾.曹雪芹西山足迹考[J].红楼梦学刊,2006(05):166-184.
[2]张云.对“曹雪芹与北京西山”的思考[J].曹雪芹研究,2015(05):131-136.
[3]胡鹏.“曹雪芹在西山”遗迹寻踪[J].曹雪芹研究,2018(08):184-186.
[4]吴恩裕.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著和遗物[J].红楼梦学刊,1979(04):275-311.
[5]于杞.曹雪芹书箱与春柳堂藏书[J].高校图书馆工作,1986(04):47-48.
[6]林同华.20世纪的“红学”:解读、反思与展望(下)[J].学术月刊,2001(04):34-44.
[7]周乐,何燕利.一场生命的书写:从古典舞剧《曹雪芹》的创作谈起[J].舞蹈,2022(05):97-100.
[8]关冠.以《杜甫》为例浅析古典舞剧的融合发展[J].戏剧文学,2021(03):97-100.
[9]于平.关于当代中国新十大古典舞剧的述评(下)[J].当代舞蹈艺术研究,2018(06):44-51.
责任编辑:邓晔
Presentation of the Principal-being Awareness on the Choreographer in the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Drama: A View Gained from Cao Xueqin
SUN Xiaofang
(Shenya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Shenyang 110000,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ractice of dance art, the role of choreographer is obviously extremely important. Particularly, the principal-being awareness of choreographers can be counted as the motive power for the design of the dance art, as it is essential to decision making, guidance offering and performance of choreographers. The success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drama Cao Xueqin is largely due to the integration in it of the principal-being awareness of the choreographer, which is presented in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scene arrangement, history reproduc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It is just the principal-being awareness of the choreographer shown in the five aspects mentioned above that made Cao Xueqin an excellent contemporary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drama profound in connotation, affection and artistic quality.
Keywords: Cao Xueqin; classical dance drama; the principal-being awareness in the choreographer; pres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