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文学中人物形象分析
2024-06-16李淑君
李淑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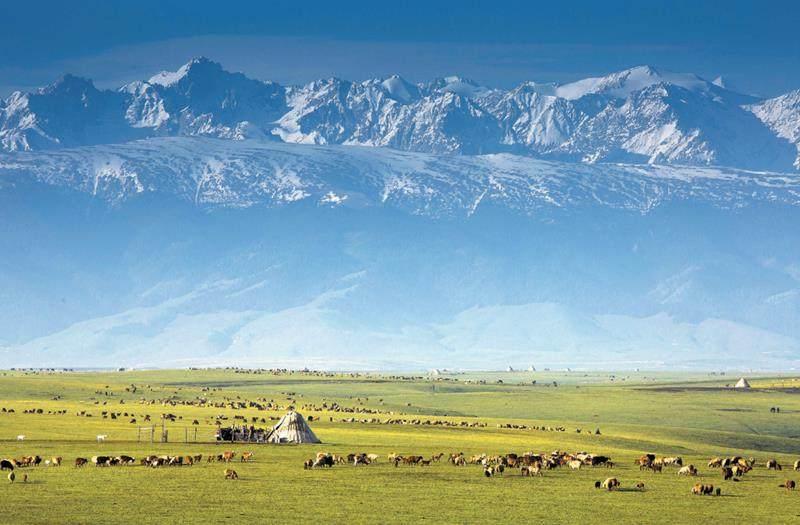
摘 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是不可被忘却的,他们秉持“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创造了兵团奇迹。本文以兵团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了刘月季、梅小二、“北京渣滓”群像,运用文本细读法对人物形象进行解读,深入发掘兵团精神。
关键词:兵团文学;人物形象;个案研究
一、善良的戈壁母亲——刘月季
刘月季的一生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作者笔墨精练,仅用两三页就将她的数十年讲述完毕。刘月季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父母包办婚姻,日常就是照顾家庭和管理家政。后面的日子里,她与丈夫孕育了长子钟槐。丈夫参军临行前,面对妻子决堤的眼泪和凄凉的微笑,一时不忍,给她又留下了一个孩子——次子钟杨,哺育这两个孩子是她奉献一生的开端。
十二年很快过去,收到丈夫来信的刘月季到新疆寻夫。来到一片广阔天地的她意识到,女性不仅可以是妻子和母亲,更可以是为祖国做贡献的兵团建设者。女性意识与自我意识同步觉醒,这一精神的蜕变意义重大。文中没有直接提到她的工作如何升迁,但她却实实在在为兵团做了巨大贡献,先是为开荒造田的部队烧水,待到师里派出先遣队建设新城,又为那几十个人的吃饭喝水忙碌着,有时还要帮着洗洗衣服,新城初建,牵挂儿子的她回到原先的团里,被安排担任机关食堂的司务长。自此刘月季的工作岗位就没有再被提及,一直到最后一章中提道:“早就过了退休的年龄,是郭文云坚持让她继续干机关司务长的工作的。”一个农村妇女,到最后竟能做到机关司务长的层级,可见刘月季是一个多么优秀的女性,兵团给了她发挥自己才干的机会,她也用自己数十年的无悔奉献为兵团事业添砖加瓦。
刘月季鲜少用言语标榜自己,但文章中几句话也透露出她积极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例如“啥事情要么不干,要干就得让自己看得过去,也要让别人满意”“母亲说她所做的只是她认为该做的事。母亲说外祖父告诉她,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活在这世上得留下个好名声,要不就白在这世上走这么一趟了”。她将这些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母亲尤其同情那些遭遇了不幸的弱者”,这句话是对她朴素又正义的三观最好的概括:孩子等小辈在她的眼里是“弱者”,她收养钟柳、爱护钟槐钟杨、照顾钟桃,哪怕是没有亲缘关系的孟少凡,她也心疼他父母早亡,对他多有照顾。孟少凡后因犯下错误连累钟柳,可当他一封电报打到刘月季手上时,她仍不辞辛劳立刻赶去外地将他从越来越偏的“歪路”上拉了回来;丈夫后娶的妻子孟苇婷在她的眼里是“弱者”,她给即将临盆的孟苇婷擦拭身体,心疼孟苇婷在戈壁滩上修大渠,带病重的孟苇婷去乌鲁木齐看医生,在孟苇婷最后的日子里替她守护她的家。凡此种种,都表现出她仁慈的天性和宽厚的心胸。
总而言之,刘月季作为“戈壁母亲”“兵团母亲”当得起敬佩与赞扬,她既普通平凡,又伟大崇高,她质朴高尚、艰苦奋斗的一生从个体层面体现了兵团人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的人生追求与崇高理想。
二、困境中成长的进取文学家——梅小二
梅小二是《天堂河》的女主人公,整篇小说从她的视角出发,围绕着她的生长环境和成长经历描绘出一幅人物众多的生活长卷。
梅小二既孤独又缺爱,她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刚出生时就因为金发褐眼而差点被抛弃荒野,父母唯一对她稍好的时刻,却是给她穿新衣服、替她梳洗,为了把她送给别人当养女。父母虽然还是心软将她接回家,但在整个童年时光中,她依然是家中地位最低的那个。在天堂河农场的邻里之间,她也没有要好的玩伴,为了交到朋友,她不惜通过折辱自己的方式来获取她所认为的友谊。比如刘大满从前看不起她,带着别人欺负她,但当她开始发育后,刘大满带着不良的念头跟她跳大绳,她也欣然同意。除了非正常方式,她有时也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吸引小伙伴,这是她文学天赋的初步体现。尽管有着不幸的童年经历,但她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将其作为日后写作的丰富素材,体现了她在挫折中强烈的进取精神。
王伶对女主人公梅小二的心理描写从来不吝笔墨,通过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展示出了一个想象力丰富、感情丰沛、性格敏感的天生文艺分子的形象,也为她后来作品获奖、成为作家埋下了伏笔。例如第六章,她观察沙土地上的生灵,“做野兔免不了被人吃,做土鸟会困在沙漠里,做蚂蚁会累死在异乡……我是嫉妒土牛们过得比我自在,不会有谁注意它们,它们也不会遭谁伤害。能躲到深深的地底下,多好啊”,这些已初步展现了一个作家所必需的观察体悟细微生活现象的能力;又如听美女蛇拉小提琴时,“我一听就想睡觉,但并不真的睡着,只觉得像浸在了温水里那么温暖。闭上眼睛,还能够看到很多好吃的东西……”,充分说明梅小二有音乐上的天赋,文学与音乐有相通相近之处,也为她后来成为作家埋下了伏笔;在决定动手写小说时,她说干就干,她当时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如果我不及时写出来的话,万一哪天我死了,谁来写呢?……即使多么苦涩的回忆,一经写出来,都是好看的故事”,爆发的倾诉欲和对文字的热爱也是作家的必备要素。
三、困境中依然坚强不屈的“北京渣滓”群像
全文中的“北京渣滓”群体,都应该以负面形象出现,可王伶偏偏撷取了他们人性中善的一面,这是《天堂河》高于其他兵团小说的原因。丁罗锅、美女蛇、莫斯科这三个是具有代表性的“北京渣滓”,尽管当时处于困境,但他们身上照样存在着兵团精神和人性光辉。
在教育事业上,“北京渣滓”都体现了无私奉献的兵团精神。丁罗锅、美女蛇、莫斯科都担任过老师,都表现出了对文明、对知识的敬重。在天堂河农场开展教育启蒙是艰难的,但他们都尽心尽力教育着孩子们。新老师每次上任时,都会从形象开始端正庄重起来。莫斯科“头发是梳过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那副断了腿的黑边眼镜粘上了雪白的胶布,还穿了一件从没穿过的蓝中山装”。丁罗锅“从前总是在他的驼背上搭块脏乎乎的破毛巾,用来擦汗,现在毛巾没有了,背上的小山干干净净,一览无余”。美女蛇“穿着一件红格子外套,黑色长裤,身材苗条……英气勃发”。对穿着打扮的重视能明显体现出他们对“老师”身份的自豪。
(一)父爱如山的“丁罗锅”(丁木)
“丁罗锅”原名丁木,他是全文中最能体现父爱的人物。小油菜花并非他的亲生孩子,但“丁罗锅”对她的爱超过了爱自己的生命,小油菜花先天不足,他“到处为她找奶吃……上班下班都背在身边,仅有的一点工资几乎全花在了给孩子看病上”。小油菜花即使落下了小儿麻痹的后遗症,不仅肢体残疾还略带痴傻,但他依旧对她很好,给她梳辫子,教她读诗,给她做风筝,学生们送来吃的他都为她攒了一口袋,让缺爱的梅小二羡慕不已。
当富户胡倒要收养小油菜花时,丁罗锅不舍小油菜花使人几欲落泪,“他颤颤巍巍从女儿的头抚摸到她的脸,一只手最后落到她的残腿上”。但这并不是他悲剧的结束,他因犯了错误而被排挤,在绝望中,他选择了自杀。
(二)一心奉献的“美女蛇”(白冰冰)
“美女蛇”有着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虽然她平时都低调地用帽子或头巾去遮掩它们。她最心痛的事情是无法与亲生女儿刘二满相认,只能以一个普通老师的身份去关注她。她一生最痛快的日子就是当老师,她是天堂河农场最当之无愧、最认真负责的老师。
她决不允许孩子因为大人之间的恩怨而不学习,宁可被骂也不断去家访。她有着科学的教育方法,还关心孩子的卫生健康,要求他们保持干净。她不单单像一个老师,更像孩子们的亲人。白冰冰一心一意为了学生,尤其在最基础也最关键的粮食问题上,她向家长们保证孩子只要上学就有饭吃,办法就是将自己和莫斯科的口粮都省下来给学生。“这天中午我们吃的是稠玉米粥,白冰冰竟然在喝着能照得见人影的洗锅水!”
她的死亡是为了救人,梅小二与她非亲非故也并非是她最得意的学生,但当危险来临时,她依然毫不犹豫将梅小二救起,而自己却葬身于冰冷的河水中。
(三)顽强不屈的“莫斯科”(林清)
“莫斯科”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物,他长相帅气、多才多艺,但他最为珍贵和令读者动容的是他的善良与坚韧。
梅小二在孤狼看守的玉米地里偷玉米,被孤狼发现,孤狼本要狠狠教训梅小二,因为梅小二的父亲梅老贵曾折辱他,但莫斯科拦住了孤狼:“我说放了她,就放了她!不许你再在小孩子身上报复!不许!”他极少用这种强烈的语气说话,但他说出来的话分量极重,使孤狼退却了。“莫斯科”尽管也受过梅老贵的毒打,但他比孤狼更理性,并不将仇恨转移。
他从来都是为集体着想,为了这一群同伴,他总是不顾一切争取正当权利。在断水断粮的时候,他带头抢粮库;在“北京渣滓”因守堤而牺牲后,他不断上访,为死者争取正名,最终让“北京渣滓”在天堂河农场的待遇有了提升。
四、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韩天航、王伶作为兵团作家,其作品便是他们对兵团文学、对国家文艺发展做出的贡献。韩天航笔下的刘月季是兵团精神的集大成者,她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在兵团工作数十年,在工作和生活中无私奉献,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中也坚持奋斗、开拓进取,是当代人的榜样;王伶笔下的梅小二,尽管遭遇了许多挫折,不被家人重视、感情曲折等,但她的心里一直有一颗文学的种子,受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所影响,她利用自己的经历去写作;至于“北京渣滓”群像,他们的身份在当时并不被认可,但依旧以自己的方式为兵团做出了巨大贡献,“丁罗锅”悉心抚养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美女蛇”尽心尽力教导学生,体现了兵团精神中的无私奉献,“莫斯科”在逆境中依然顽强不屈,体现了兵团精神中的开拓进取。总而言之,这几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韩天航、王伶对兵团精神的文学表达,对兵团文学的发展、兵团精神的发扬起到了促进作用。
(喀什大学人文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喀什大学人文学院2022年研究生创新课题《兵团文学中人物形象分析——以韩天航、王伶作品为例》研究成果(项目编号:RM202208)。
参考文献
[1] 韩天航.母亲和我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 王伶.天堂河[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
[3] 姜萌萌.韩天航小说创作思想研究[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2020.
[4] 雅森.韩天航小说创作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20.
[5] 邹赞.“摆渡者”的吟唱:韩天航小说对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历史记忆的文化书写[J].社会科学家,2021(4):14-19.
[6] 张书群.兵团精神的文化认同:以韩天航小说《母亲与我们》为个案[J].昌吉学院学报,2011(2):38-41.
[7] 陈云,易国才.成长小说视角下的《天堂河》[J].语文建设,2014(30):4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