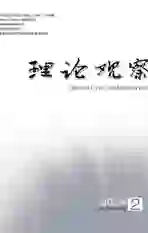具身认知视角下文学语言特性反思与重构
2024-06-13刘帅
刘帅
摘 要:传统的“形象论”视阈下对文学语言特性的界定,只关注到文学语言进入公共场域后的特点,而忽视了文学语言发出的生理机制以及文学语言从私人语域跨越到公共语域的过程。身体叙事学主要考察了内文本身体与叙事之间的关系,但却忽视了文本外身体对叙事的重要作用。在两个残缺的理论体系中我们需要反思与重构,重新恢复身体、语言与叙事的天然联系。基于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借文本外身体来重探文学语言特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借文学语言来揭示文本外身体在叙事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在对文本外身体与文学语言关系的考察中,我们窥见文学语言的特性在于具身与构象。
关键词:具身;文学语言;身体叙事学;赛博格
中图分类号:I0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2 — 0102 — 06
文学语言特性的反思,是文艺理论的一个经典议题。对文学语言特性的反思经历了从语言论视阈向形象论视阈的转变,但随着“后理论”时代的到来, 单纯“形象论”视域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弊病,如何在“后理论”时代重塑经典文论命题是我们当下面临的重要任务。身体叙事学以其独特的理论关怀和学术建树为我们反思和重构文学语言特性提供了新视角。
一、辨正:文学语言与身体叙事学及其关系
(一)概念探微:“文学语言”与“身体叙事学”
对“文学语言”的概念界定,重点在于“文学”一词的认定,具体有两条路径:其一是将“文学”视为文学性,其二是将“文学”视为具体文学作品。文学语言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语言是指规范化的全民语言,它在口语的基础上加工而成,也泛指各种文学书籍中所运用的书面语言;狭义的文学语言则专指文学作品中的语言。[1]我们在此反思的文学语言不仅是狭义的文学语言,更是广义上的文学语言。对文学语言特性的反思经历了从语言论视角向形象论视角的转变 。首先 20 世纪初的语言论转向直接催生了对文学语言的关注,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理论家都相继对文学语言特性做了探索,雅各布森认为文学语言的本质在于能指与所指的不稳定性;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学语言的特征是拒绝简化,以达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瑞查兹认为文学语言是“内指” 的。进而在语言论研究基础上,以童庆炳、赵炎秋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基点,对文学语言特性作出了进一步反思与修正。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对语言与物质的关系做过探讨,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 简言之,即语言。[2]作为意识物质性外壳的语言从出场伊始就同时与“精神”和“物质”保有密切联系:一方面语言是精神的具象化存在,另一方面语言又是物质生活的产物。由此,当代中国学者从形象论角度出发,对文学语言特性进行了修正,他们提出文学语言特性在于构象性这一基本论断。所谓“构象性”即文学语言构建形象的能力,这一观点恢复了文学语言与生活的联系,突出了语言论视角中被遮蔽的语言与生活的互动性关系。赵炎秋在《形象诗学》中从“文学语言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主体,总要表现出一定的生活内容”[3](p167)、“文学语言表现的总是感性具体的生活”[3](p169)、“文学语言总是运用各种手段,调动自己塑造形象的潜能, 以满足表现具体生活的感性形态的需”[3](p171)三个角度论述了文学语言特性在于其构象性,并且对语言如何构象作了充分的论述。自此“文学语言特性在于构象性”这一论断基本成为形象论视域下文学语言特性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一观点在传统理论语境之中具有强大生命活力和深远理论意义。但随着后理论时代的到来,也出现了理论与文学实践断裂的情况,显露出一系列的弊病。
身体叙事学即以身体为视点的叙事学研究。作为一种具有全球性视野的叙事学形态,其理论构设横跨中西方语境。西方语境中身体叙事学的出场始于对经典叙事学与身体美事的双重反思,一方面以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核心的经典叙事学因对历史社会文化观照不足,进入21世纪后其发展已经显得疲软;另一方面“尽管身体在文学和文化批评中产生了兴奋,但它对叙事学几乎没有任何影响”[4](p02)。基于此美国学者丹尼尔·潘戴以身体为视点对经典叙事学进行了重构。在《叙事身体:建构身体叙事学》一书中,他将身体与叙事都置放于历史化进程中,还原历史语境中身体与叙事的交织性关系,进而激活身体的叙事活力。立足于此,他指出身体叙事学主要有两条研究路径:其一是观照“身体是如何被建构为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4](p03),其二是探寻“身体是如何影响我们思维方式和叙事分析”[4](p03)。而当代汉语学界对身体叙事学的探索,则可以溯于2008年许德金、王莲香发表的《身体、身份与叙事——身体叙事学刍议》一文。首先他们对西方语境中身体叙事学建构作出了反思,他们指出“潘戴所做的工作在叙事学界具有某种开拓的意义”[5],但其理论内部因对“身体”定义模糊而导致其理论效力不足。进而他们建构了当代中国身体叙事学的研究框架:其一在于“身体”概念的定义,他们认为有两层身体即“文本外身体”与“内文本身体”,“文本外身体”是指文本创作者和接受者的真实身体;“内文本身体”则是指作为文本形象存在的想象性身体。其二在于通过“身份”这个中介将“身体”与“叙事”放置到更为广阔的社会语境中,“从文化诗学的角度探讨身体与身份在叙述中的作用”[6],凭此建构中国式的身体叙事学。
(二)致思理径:文学语言与身体叙事学的互渗
那么我们为何要将身体叙事学引入到文学语言特性反思之中呢?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第一是身体叙事学理论亟待构建与丰富。现阶段的身体叙事理论大都集中在内文本场域,主要揭示内文本中的身体形象是如何推动叙事,而缺少文本外身体的观照,即需要恢复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的身体在叙事理论中的地位。而文学语言正是文本外身体与叙事文本的交互中心,由此对文学语言特性的反思可以补写文本外身体在叙事场域的理论缺位;第二是文学语言特性研究亟待发起新一轮自反性重构。自提出“文学语言的特性在于其构象性”后,学界少有对这种观点的反思,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对话关系被切断。引入全新的身体叙事理论或许可以重新恢复起这种理论的对话关系,推动文学语言特性研究向纵深化方向发展;第三则是以赛博文学为代表的新型文本实践需要召唤新型文艺理论。所谓“赛博格”强调的是一种人机融合,唐娜·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指出:“赛博格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生活于界限模糊的自然界和工艺界”[7]。赛博格反映在文学领域,一是作为内文本身体的赛博格,即文本中存在的以“人机交互”为特征的身体形象;二是作为文本外身体的赛博格,即以智能机器为主体的文本创造者与接受者,如微软公司所制造智能作家“小冰”。赛博格在文学场域中的兴起对文本叙事方式也产生了影响,凯瑟琳·海勒指出在赛博格对文本的介入中,叙事也被迫裂变——“文本分裂成主干和枝节,主干包括主要的叙述,枝节主要是由插图和线条构成的假肢性的延申”[8]。综上而述,赛博格文学的出场重新定义了“身体”,也重新定义了“叙事”,因此作为“身体”与“叙事”交互中心的文学语言也应该作出进一步的探索,以呼应新型的文本实践。
二、反思:文本外身体与文学语言的关系
许德金、王莲香在《身体、身份与叙事——身体叙事学》对“身体”进行了界定,据此将“身体”分为文本外的身体即真实作者和读者的身体,以及内文本的身体即文学形象的身体。从理论发展史看来,身体叙事学的研究主要围绕内文本身体进行建构,而对文本外的身体讨论不足。但文本外身体既是语言的发出者,又是语言的接受者,基于此笔者对文本外身体与文学语言的关系进行了反思。
(一)文本外身体生理向度与文学语言的出场
一方面,文本外身体的生理属性是文学语言出场的前提条件。文学语言的出场,即文学语言从创作者身体发出的过程,大致包括物象刺激、思想形成与语言发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文本外的身体是直接的感受器。这一阶段,创作者依靠生理器官对外部世界(即自然与社会)和内部世界(即自我意识)进行观照,以得到物象,进而给予大脑刺激。这一阶段直接决定了语言的特性。文学语言的出场要求这一阶段身体对外物的感知必须是具身的,所谓具身是从属于认知科学的概念,这一概念至少包括两重内涵:“其一,认知依赖于经验,而经验来自拥有不同感觉运动能力的身体;其二,个体的感觉运动能力与一个更广泛的生物学、心理学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9],其本质在于打破认知过程中的身心二分,强调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构成作用。具身性认知才有足够的动力催生文学语言而离身性认知催生的则是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第二阶段,文本外的身体是直接的储存器和处理器。在这一阶段,创作者依据第一阶段所形成的认知类型(具身认知或离身认知)来进行编码处理,形成思想。如果第一阶段产生的是具身认知,那么在这一阶段,创作者的身体会更大程度介入到思想形成过程之中,使思想带有创作者的主观意图。而如果第一阶段产生的是离身认知, 那么在这一阶段,创作者的身体不会参与到思想的构建之中,所谓的“思想”更多的则是一种社会意识或者信息编码,而少有创作者的主观意图。第三阶段,创作者的身体是直接的传达器。著名心理学家 A.P.鲁利雅曾绘制过思想到语言过程线路,这个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超始于某种动机和总意向,(2)经过内部言语阶段(3)形成深层句法结构,(4)拓展以表层句法结构为基础的外部言语。”[10]在这个阶段,身体承担的是传达器的作用,身体需要将内部言语外化为外部言语,完成语言出场的任务。
(二)文本外身体社会向度与文学语言的入场
另一方面,文本外身体的社会属性是文学语言入场的先在条件。文学语言在实现出场之后,面临的又一问题则是文学语言的入场,即文学语言如何从私人语域跨越到公共语域?根据拉康镜像理论,人类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是以身体认同为前提的,即认识到身体是自我的且与外界分离的,那身体的社会属性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我们从私人语域进入公共语域。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在《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中对身体作了分类,即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医学身体。笔者认为在这五种身体形态中,政治身体与文学语言入场关系尤为明显,政治身体直接决定了文学语言能不能进入公共场域。王一川先生在《近五十年文学语言研究札记》中提出“近五十年中国当代文学语言呈现四种演化状态:大众群言(1949—1977)、精英独白(1978—1984)、奇语喧嚣(1985—1995)和多语混成(1996 至今)”[11],由此观之文学语言的入场,实际上与我们的政治身体密不可分。近五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语言呈现的四种演化状态实际上与我们四种政治身体有关:1949 年—197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现代中国人政治身体的成型,在这一刚刚成型的政治身体的影响之下,我们的文学语言面临的任务便是以通俗化的方式来重建民族记忆,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语言更多地体现人民的意愿,呈现出大众化的特点,如《小二黑结婚》中乡土性的语言风格。1978—1984 年,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语言面临的任务是反思与解放, 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语言呈现出浓厚的精英反思意识以及自由意识,如以北岛、江河为代表的朦胧诗人的语言风格;1985——1995 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赋予政治身体以消费的属性,这一时期的政治身体被嵌入了消费文化的元素,在这一身体的影响之下,文学语言呈现出奇异性的特点,变得多元与丰富,如先锋小说、寻根小说中的语言使用;而自 1996 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我们的政治身体越来越开放和多元,据此也影响到文学语言,在这一身体影响下,文学语言也变得更加多元开放,比如网络文学中的语言以及赛博格文学中的语言。此外,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消费身体、医学身体都会给予文学语言入场以影响,在此因篇幅问题,就不多做论述。
综上而言,文学语言与文本外身体呈现出两层关系:一方面,身体的生理属性赋予文学语言出场的生理基础;另一方面,身体的社会属性也会影响到文学语言能不能进入到公共话语空间,以实现语言的价值。基于此,在文学语言与文本外身体的紧密缠绕中,我们又如何来推进文学语言特性重构?
三、重构:具身与构象
对文学语言特性的考查,经历了从语言论视阈到形象论视阈的转变。赵炎秋在《形象诗学》中提出了“文学语言的特性,就在于它的构象性”[3](p167)的观点,同时围绕文学语言何以具有构象性,语言如何参与构象做了详细的论述。这一观点突破了语言论的狭窄视角,恢复了语言与生活的联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这一观点没有涉及到文学语言与文本外身体关系的考察,忽视了文学语言的出场,而仅仅关注文学语言的入场。
构象性是文学语言的特性,这一论断有以下弊病。第一,只从文学语言出场这一端考虑,而忽视了文学语言入场这一端。构象性是指文学语言能够构成某种形象。但是这一特点仅仅是从文学语言的作用来进行界定,是文学语言已经具有“文学性”之后的反思,而对于文学语言产生之前的过程没有反思,即没有考虑到文学语言到底是如何被创造。我们认为文学语言的生成,既要考虑到文学语言入场之后的效用,同时也要考虑到文学语言出场之前的过程,唯有从这两端入手,才能进行全面的界定。第二,构象性不仅仅只是文学语言的特性,凭此无法区别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科学语言的准确边界,但是即使在理想形态之下,构象性也不是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的区别。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同样具有构象性,构象性是语言的基本特性之一。如果语言不能构建形象,就无法传递意蕴,进而也无法承担交际或表达的任务。这两大问题的存在,推动我们对文学语言特性反思进一步深化, 在此我们将基于“具身认知”这一新型原理,在认知科学与文学的交叉视野中,重新思考文学语言特性这一重要问题。
“具身认知”是20世纪80年代认知科学中所出现的一种新型研究取向,意在强调身体在认知活动的重要作用,以突破传统身心二元论的桎梏。1945年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出版《身体现象学》一书,在其间他自觉避开了笛卡尔所制造的身心二元论陷阱,将身体视为知觉的主体,主张感知活动中身体与心灵的互通,这一观点还原了认知过程中的身体维度,反驳了传统视阈中认知离身性的看法。进而立足于这一概念,我们可以探赜到文学语言特性反思的新方向,即在身心统一论中重新还原文学语言的生成过程,进而探寻其具体特性。在这一考察方向中,我们发现文学语言的特性在于具身与构象。
从具身到构象的过程,是文学语言从出场到入场的过程。文学语言的生成, 实际涉及到两个加工端,一个是出场前作者的加工,另一个是入场后读者的加工。具身是对前一个加工端的界定,而构象则是对后一加工端的界定。下面我们对文学语言的生成过程做一描述:首先物象给予作者以生理刺激,形成具身认知;其次在具身认知的指导下,身心界限被打破;进而在身心合一的基础上,作者的主观意识外化为生理动作,形成文学语言;最后文学语言进入公共场域,发挥构象能力,形成形象,完成语言目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运作过程也存在一些问题。按照问题的属性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大类:实践论问题与本体论问题,实践论维度的探讨主要观照文学语言的生成机制,本体论的讨论主要观照文学语言的本体属性,凭此在实践与理论两个维度共同揭示文学语言的生成与本质。
(一)文学语言的实践论思考
1.文学语言的生成是否一定需要物象刺激?
物象刺激是引发作者生理体验的前提,这里所谈到的“物象”可以是实在的物象,也可以是储存在作者大脑中的虚拟物象。没有物象的刺激,一方面作者没有形成语言的材料,另一方面作者也无法进入发出语言的状态。陆机《文赋》中就曾对物象与文学语言生成的关系进行探讨,“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11],物象刺激构成了文学语言生成的必要条件。
2.具身认知是否决定文学语言的生成就一定是即时性的?
我们认为具身认知与文学语言的生成不一定是即时性的,在实际的文学语言发出过程中有两种情况:一是具身认知与文学语言同步出场,即在具身认知萌发的瞬间,作者的心理状态直接外化为规范化口语或者书面语言;二是具身认知与文学语言出场的延误,即在具身认知萌发之后,作者可能会出于某些考虑而延误文学语言出场,这种延误与作者的主观审美、创作动机以及社会的文化环境相关,作者可能会在认知形成之后对语言进行二次加工,造成文学语言出场的延误。但需要说明的是文学语言的延误出场并不代表文学语言具身过程的无效,作者对这一语言的再次加工始终都是需要围绕具身认知进行,具身认知是文学语言出场的必要环境。
(二)文学语言的本体论思考
1.文学语言是否具有具身性?
我们认为文学语言与具身性并不是一种所有关系,二者构成了双重因果关系:一方面在文学语言出场之前,必须经由具身认知唤起,才能催生文学语言诞生;另一方面则是在文学语言入场之后,由于文学语言具有构象能力,其构成的意象又能够唤起语言接受者的新一轮具身性认知。立足于此,我们没有以“具身性”和“构象性”来表述文学语言的特性,而是用“具身” 与“构象”两个过程来定义文学语言的特点。
以“具身”和“构象”两个过程来定义文学语言的特性,一方面能够区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另一方面又没有否定在现实语境中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的相互滑动。
2.立足于“具身到构象”这一过程,我们如何区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
需要表明的是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在实际语言运用过程中并没有明确边界,因此我们谈论三者的区别是基于这三种语言在出场之前和入场之后所呈现出的不同分野:
首先,我们谈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差异:第一,在出场之前,文学语言更靠近身体;而日常语言与身体的距离更远。在具身认知指导之下,文学语言离身体的距离更近,有两种表现:一是文学语言在表现形态上会融入更多创作主体的身心感受;二是文学语言在语言性质上会表现更多创作主体的身心状态。以劝酒场景为例,《赤壁赋》中苏子劝客饮酒的表达是“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12],可以见出《赤壁赋》中的劝酒辞更多地观照到创作主体的生理体验,将苏轼的眼部视觉体验与心理感受融合在一起,一方面以一叶扁舟写眼部视觉,另一方面以举樽相属写心理活动,这种身心融合的表达方式也使得文本语言更能透彻地表达出苏轼的旷达之感。而日常语言由于认知的离身,往往与身体距离更远,如“您喝酒吗”则是创作主体直接以心灵控制身体,在身心二分的情况下,对他者的简单询问,而少观照创作主体自身的生理体验与状态;第二,在出场之前,文学语言更为纯粹,而日常语言则是多维复合的。文学语言因更靠近创作主体的身体,所以能够保留更多创作者身体的原始印记,维持语言本真状态;而日常语言因为远离身体,故少有创作者身体痕迹,显示出更加复杂的情况。仍以上面邀请喝酒的语境作说明:“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13]同样是保留了创作者眼部视觉与心理感知的文学语言,而“您喝酒吗?”这一日常用语体现出社会礼制的介入,发言者在发言之前总要考虑到发言的场合、语言接受的对象等因素,使语言呈现出更加复杂的面貌。第三,在入场之后,文学语言更具多义性,日常语言的意义则较为单一。由于在出场前文学语言始终保有一种纯粹性,所以进入到公共场域之后,文学语言像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拥有了更大的阐释空间,进而形成了文学语言的多义性。而日常语言由于在出场之前,就受到了语境、语言接受对象等因素的多重限制,在入场之后它的阐释空间反而被限制与压缩,进而能够实现准确的语义表达。第四,在入场之后,文学语言更具有构象性,而日常语言的构象能力较弱。由于文学语言更多地表现了身体多维器官的感知,其语言状态相较于日常语言则更为形象。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文学语言所构成的“象”比日常语言更为形象; 二是文学语言所构成的“象”的意义比日常语言更深远。比如在一个下雪的天气, 日常语言的表达可能是“好大的雪啊”,而文学语言的表达则是“未若柳絮因风起”[14],这两句话相比,一方面日常语言是单纯静态的抒发,我们只能看到大雪的形象,而文学语言则是以柳絮作比,马上浮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白雪纷飞的动态形象;另一方面在意象之外,文学语言的表达使我们看到了发言者的想象使白雪穿越了季节,化作纷飞的柳絮,体现出发言者独特的意趣,而日常语言在这一点上,显然是不及文学语言的。
其二,我们来谈文学语言和科学语言的分野。第一在出场之前,文学语言是身心合一,而科学语言是身心二分的。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关于具身与离身的区别表现在语言与身体的距离,而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关于具身与离身的区别则是表现在身心关系上。文学语言在入场之前身心是合一的,而科学语言则是主体的心理直接控制了主体的身体呈现。科学语言是以表达真理为目的,在入场之前在发言者头脑中的不是具体物象,而是抽象概念,这个抽象概念无法引发发言者的具身性认知,因此身心也无法融合。比如对“灵感”一词的定义,科学语言是“文艺、科技活动中瞬间产生的富有创造性的突发思维状态”,而文学语言则是“众里寻他千百度,慕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15]。第二在入场之后,文学语言构建形象,科学语言阐明概念。由于入场之前,身心关系的不同,二者出场后的语言效用也不同。文学语言始终以构建形象,营造审美氛围为目的,而科学语言则是以还原现象,表达真理为目的。我们仍以对“灵感”的发言为例,文学语言侧重描述的是灵感产生的过程以及心灵体验,而科学语言则是对“灵感是什么”进行了界定。
四、结语
文学语言被两个身体共享,具身是面对语言发出者身体的特性界定,构象是面对语言接受者身体的特性界定。单单只从一端界定文学语言特性,是无法形成理论内部的自证循环。从具身到构象既是文学语言从出场到入场所需要完成的任务,也是文学语言与其它语言的特性差异。但在现实生活中,本来就不存在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科学语言的明确区别。日常语言、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之间是不断滑动的,这种语言的滑动实际上也是我们认知的滑动即从离身到具身的滑动。
从具身到构象,基本还原了文学语言出场与入场两个环节,恢复了文学语言与身体联系。但是新一轮人机融合思潮下所产生的赛博格文学以及机器人文学,可能会重新定义文学语言的特性,如此种种都会将文学语言的特性研究推向深化。但无论是赛博格文学还是机器人文学下的文学语言都始终是一种身体语言,只不过是从单一身体走向了多维身体,从现实身体走向了虚拟身体。具身与构象仍会是文学语言从出场到入场所必不可缺的质素。
〔参 考 文 献〕
[1]赵炎秋.文学原理[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6.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1.
[3] 赵炎秋.形象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67,169,171,167.
[4]PUNDAY D.Narrative Bodies:Toward a Corpreal Narratology[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02,03,03.
[5]许德金,王莲香.身体、身份与叙事——身体叙事学刍议[J].江西社会科学,2008(04):28-34.
[6]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314-315.
[7]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66.
[8]汤拥华.重构具身性:后人类叙事的形式与伦理[J].文艺争鸣,2021(08):56-63.
[9]卫志强.当代跨学科语言学[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105.
[10]王一川.近五十年文学语言研究札记[J].文学评论,1999(04):16-26.
[11]陆机.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
[12]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6.
[13]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C]//白居易.问刘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6:1358.
[14]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9.
[15]辛弃疾.稼轩词编年笺注[M].邓广铭,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0.
〔责任编辑:杨 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