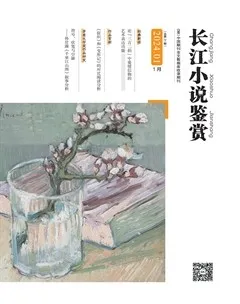《卢太学诗酒傲王侯》“醒世”意味探析
2024-06-01王伊菲
王伊菲
[摘 要]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十九《卢太学诗酒傲王侯》是根据明嘉靖年间浚县名士卢楠冤狱案改写而成,通过对冤狱起因的改写,弱化了历史上卢楠狂傲的性格;通过对冤狱平反过程的改写,将卢楠因文名远播而得到文人相救的真实历史,改为由正直官员主持平反。改写的故事仍具有警醒世人勿以诞傲取祸的意蕴,但冯梦龙通过突出“县令自古可破家”的叙事,表现了权力的森然可怖,以及缺乏功名和家世背景的士人的弱势地位。对于冯梦龙这样的既无家世背景也无功名的弱势者来,这样的艺术处理也表露了作者自怜与自警的心理。
[关键词] 《卢太学诗酒傲王侯》 卢楠 冯梦龙 晚明文士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01-0032-04
《醒世恒言》卷二十九《卢太学诗酒傲王侯》是冯梦龙“三言”中为数不多的根据明代时事改编的小说。小说以嘉靖年间的诗人、名士卢楠为主人公,主体情节围绕卢楠为当地县令诬陷入狱十余年的冤情展开,虽以“诗酒傲王侯”名篇,通篇并未呈现诗人、名士诗酒自娱笑傲王侯的惬意,反而展现出卢楠因细故得罪县令而几乎家破人亡的惨剧。篇末更明确点出小说用意所在:“莫学卢公以傲取祸。”“三言”整体上具有通俗性质,编刊者也一再强调小说“导愚适俗”。具体到《卢太学诗酒傲王侯》,本文在与卢楠冤狱“本事”的对照中考察它的叙写方式,也将在“凡事还须学谦谨”的训诫之外,发掘小说包含着冯梦龙的自伤自警以及对晚明士人群体行为方式的隐忧。
一、历史上的卢楠之狱
发生于嘉靖时期的卢楠冤狱事件传播甚广。卢楠(1507—1560),字少楩,一字次木,河南大名府浚县人。据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三《卢楠传》记载,卢楠“先世业农,获则什一而息之,故以赀雄于乡,父为入赀太学上舍”,这表明卢楠并非出身于簪缨世家、书香门第。卢楠曾在国子监(太学)读书,即小说标题称卢楠为“卢太学”的原因。卢楠长于诗文,才高气广,但并不擅长时文八股,因此在国子监时,“数应乡试,罢免归”,此后仍然“试辄不利”,没有取得功名,于是以诗人、名士自居。由此可知,卢楠心里交织着失意与自负两种强烈的情绪,《卢楠传》说他“为人跅斥,不治生产,时时从倡家游。大饮,饮醉则弄酒骂其座客”。放浪不羁、使酒骂座,这是典型的名士做派,也可能就是他日后蒙受冤狱的源头。
至于卢楠遭遇冤狱始末,各种文献材料或简略,或零散,笔者据当代学者傅瑛《卢楠年谱》作一完整梳理。冤狱始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卢楠时年三十四岁。是年六月,卢楠家佣工张杲身死,张杲之母状告卢楠毒打张杲至死。卢楠称六月二十一日,张杲偷场麦被发现,被责打后逃遁,次日,天大雨,张杲被倒塌的墙压死。时任浚县县令蒋宗鲁不采信卢楠之说,刑讯逼供,卢楠屈打成招,被判处死刑,收押入狱。此后由巡按御史樊某主持会审,一度将案情认定为“以家长殴雇工人至死”,依据明代法律,卢楠罪不至死,改判为劳役、罚粮等轻刑,嘉靖二十年正月结案,卢楠暂时还家。二月,其父被强盗逼死,财物被抢光,六十天后,卢楠之母因伤心太甚去世。四月,按察司重审此案,卢楠再次入狱,至六月定案,卢楠被判死刑,再度收押于浚县监狱。本年内其二子相继夭折。在监狱中,卢楠不断致书有关官员以及自己结识的朋友,希望他们帮助自己平反。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蒋宗鲁离任,此后魏希相、石茂华先后继任浚县县令,均未予平反。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卢楠故交谢榛为营救卢楠,携卢楠诗文入京,结识任职于刑部的李攀龙、王世贞,李、王也积极参与营救卢楠的活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平湖进士陆光祖任浚县县令,改判卢楠服三年劳役。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陆光祖联合滑县县令张佳胤再审卢楠案,以其冤情上报。冬,卢楠平反出狱,距案发入狱已有十二年之久[1]。
卢楠案件相关审理记录并未保存下来,案件的真实情形已很难得到完整地还原,称这一案件为“冤狱”,实际上只是依据卢楠的自陈以及同情卢楠者的记述。在基于卢楠一系立场的卢楠案叙事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案件的起因:卢楠曾因细故得罪县令蒋宗鲁,因此被蒋宗鲁借故嫁祸诬陷。王世贞《卢楠传》中记述:“令尝从客语楠:吾旦过若饮。楠归,与翁媪益市牛酒,夜共张至旦。而会令有它事,日昃不食。楠愧且望之,斗酒自劳,醉,则已卧。报令至,楠故徐徐出坐,久之楠称醉不能具宾主。令恚去,曰:吾乃为伧人子辱,愧见其邑长者。亡何,……役夫夜压于墙陨。事闻令。令色动曰:唶累,是复能倨见我耶?匿役夫所由死状,当楠抵坐。”而参与为卢楠诉冤的謝榛在《四溟诗话》卷三更提及“卢生楠以诗获罪蒋令”,即卢楠自负诗才,曾讥刺蒋宗鲁诗作。由此可见,卢楠并不仅是在酒醉失礼这一件事上得罪蒋宗鲁。蒋宗鲁为人睚眦必报,有公报私仇之嫌。
此案更值得重视的是文人联合为卢楠辩冤脱罪的过程。从蒋宗鲁的仕途履历来看,他能力颇为突出,为官时有建树,人品、政声也不恶,清人田雯在《滇记》“名宦”中,列举“明之以理学文章气节著者”,列入了蒋宗鲁之名。以任职浚县而论,蒋宗鲁任满后即升为户部主事,也表明其治绩突出。平心而论,即使不存在个人恩怨,以蒋宗鲁的立场,认为卢楠是蠹虫毫不奇怪。蒋宗鲁重判卢楠或许是出于报复,但卢楠本身有嫌疑,而蒋宗鲁的判决却显得是惩治地方豪强,使部分同情卢楠、想为卢楠翻案的人也心存顾虑。卢楠脱罪靠的是他在文坛上的声气,他的故友谢榛也起到关键性作用,《明史·文苑三·谢榛传》中说,谢榛“入京师,脱卢楠于狱”,又在卢楠传中说,“平湖陆光祖迁得浚令,因榛言平反其狱”。但谢榛本人并不具有这样的影响力,他的作用主要在于将卢楠的诗文携入京师,将事件的影响扩散到一个更高层的圈子,特别是结识王世贞、李攀龙后,借助于二人的地位与声望,影响了陆光祖等人。据雍正《畿辅通志》卷六十七《名宦》载,王世贞说他“出卢楠于缧绁,……尤为旷举”,证明王世贞在平反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总之,在历史上,文士的互通声气、彼此倚助,形成卢楠杀人案确系冤狱的舆论,从而影响到司法。
卢楠的生平具有传奇性,待死狱中十数年,因为诗文被人所赏,得到文坛名家的支持而翻案,其冤情昭雪出狱,又被传为文坛佳话,谢榛携卢楠诗文入京,结识李攀龙、王世贞,这是明代重要文学团体“后七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谢、李、王怜才惜士,营救卢楠,增加了案件的关注度和传播力。可以这样说,卢楠的名士身份以及由此牵涉到的明代文坛名家,为案件带来了传奇性与传播力,使之进入冯梦龙的视野。
二、《卢太学诗酒傲王侯》中卢楠之狱的叙述
冯梦龙编写《卢太学诗酒傲王侯》时,距卢楠案已七十余年。七十余年间,李攀龙、王世贞在文坛地位稳固,他们对卢楠案的陈述成为世间广泛接受的“真相”。冯梦龙曾在《古今谭概·矜嫚部》中叙及卢楠冤狱,即采取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中《卢楠传》中的观点与叙述,這篇小说同样如此。此外,冯梦龙对卢楠的作品也相当熟悉,比如小说所引“卫河东岸浮丘高”七律一首,“逸翮奋霄汉”五律一首,二首俱见于卢楠《蠛蠓集》。需要注意的是,卢楠《蠛蠓集》卷五有诗《丁未梦中游王西轩园作》,诗题后自注:“是岁十一月二十日,狱吏谭遵令狱卒蔡贤笞楠数百,谋以土壤压杀之,官觉之免。”谭遵、蔡贤二人也被写入小说。这些都表明冯梦龙清楚历史上真实的卢楠其人以及案件过程。在这一前提下,小说所叙之卢楠、所叙之案情与史实的显著差异,就必然有其艺术上的考量。
《卢太学诗酒傲王侯》采取了案中有案的叙事框架。卢楠冤狱作为主线,中间穿插卢楠所涉的人命案作为案中案。案中案将历史上的张杲艺术化为钮成,钮成被卢才殴打后病发而死,而卢才作为真凶也被卢楠之狱的昭雪者陆光祖拿获。与历史上张杲死因成疑相比,小说的处理无疑更清楚地说明卢楠之案确系冤狱。在主线即卢楠冤狱的叙事上,真实事件中的县令蒋宗鲁艺术化为汪岑,卢楠与县令结怨的原因也有了重要的改写。在小说中,卢楠与知县的冲突集中于赏花饮酒。小说开头即交代卢楠家有园林,种植了名花,故事的展开是知县歆羡饮酒赏花之乐,数次约定到卢楠家饮酒赏花,都因故失约,情节的反复延宕,除了增加小说的趣味之外,显然也有改造历史上的卢楠之意。小说这些情节意味着,卢楠固然有任气使酒的性格,但在与县令的交往上,已经表现出了相当的隐忍。得罪县令发生于最后的赏菊花失约上:卢楠因县令屡次“卑词尽敬”要来家中赏花,因此动了“俯交”之念,主动邀请县令来赏花,知县过时而未到,卢楠心中郁闷,自己先饮酒大醉。等知县来时,已沉醉不起,而知县却感到受到极大的侮辱。《卢楠传》记载,知县来时,卢楠“故徐徐出坐,久之楠称醉不能具宾主”,有意羞辱知县,小说里则是卢楠的确“不能具宾主”。显然,相较真实的历史,小说有意弱化了卢楠使酒任气的性格,从而强化卢楠遭遇的“冤”。同时,知县反复失约而卢楠尚且隐忍,卢楠一旦因醉酒不能接待知县就蒙受冤狱,这种对比突出了没有功名的书生、名士在权力面前的弱势地位。
小说中卢楠获释过程的叙述对史实的改编更为显著。历史上,卢楠被释是由卢楠文名动员起来的文人网络与蒋宗鲁及其支持者角力的结果,过程一波三折。小说的叙述则趋于简洁,卢楠以为“我卢楠相知满天下,身列缙绅者也不少”,向相识之人求救,但汪知县却借此制造新的障碍,宣扬“卢楠恃富横行乡党,结交势要,打死平人,抗送问官,营谋关节,希图脱罪。把情节做得十分厉害,无非要张皇其事,使人不敢救援”,历史上传为美谈的文人同气连枝、闻声相救也就被排除在叙述之外,美谈中的重要角色谢榛、李攀龙、王世贞等在小说中都没有留下姓名。小说中,为卢楠平反的功劳完全归于陆光祖,而陆光祖之所以一到任就关注卢楠案件的真相,恰恰是因为他上任之前,早已升居高位的汪岑要求他不得为卢楠翻案。陆光祖反感权力对于法律的干涉,经过自己的察访,找到杀死钮成的真凶,获得案件的真相,才为卢楠平反。
“酒癖诗狂傲骨兼,高人每得俗人嫌。劝人休蹈卢公辙,凡事还须学谨谦。”《卢太学诗酒傲王侯》中,卢楠并没有张扬到主动招惹县令,但仍有着名士的傲骨与酒癖诗狂,最终导致身陷冤狱,累及家人,荡尽家产。卢楠相知满天下,都无助于他昭雪冤狱。这样的人物设计和情节安排,突出了“从来县令可破家”的现实,排除历史上文人闻声相助的佳话,进一步消解了对名士生活的浪漫想象。
三、冯梦龙的改写与晚明士人的趋向
人们对于过去历史的书写,常常是因为它能够引起对现实的思考,并与现实生活产生联系。冯梦龙对于嘉靖时期名士卢楠故事的重新书写,也与他本人对现实的感受有关。
所谓名士,与规规焉以礼法自饬的士人不同,他们或轻世肆志而成为“高士”,或举止狂放而为“狂士”“畸人”……冯梦龙对于名士并不陌生,他生活的苏州就是名士的大本营。弘治正德间的唐寅、祝允明、张灵等,都是大名士,《明史·文苑传二》说:“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荡不羁为世所瞩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嘉靖、隆庆以至万历年间,明代社会的名士、山人不断增加。甚至冯梦龙本人也是一位名士,在同侪间有“畸人”之称。《卢太学诗酒傲王侯》把卢楠当作读书人、小名士的前车之鉴,但他其实对卢楠的真实生活与心理状态有深切的了解,小说对卢楠的描述带有他本人自伤、自警的意味。
真实的卢楠家有田产,但出身低微,他本人又“文福不齐”,“锦绣般文章,偏生不中试官之意”,未能取得功名。卢楠出身低微,未获功名,这些情况与冯梦龙极为相似。至于小说称卢楠“世代簪簪,家资巨富,日常供奉,拟于王侯”“与他往来的,俱是名公巨卿”,这是反讽的写法,反映了卢楠陶醉于名士身份时的自我感觉。卢楠假如真有这样的社会背景,就不会遭受冤狱,而小说后文的叙述也验证他确系缺乏背景、易于拿捏的小人物。因此,冯梦龙在卢楠故事中蕴含的不平之气,实际上也来自他本人的生活体验。
冯梦龙同样没有出身背景、没有获得功名,他还没有卢楠那样的财产,在权力面前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因此,同为名士,他的选择与卢楠也不同。卢楠可以绝意仕进、纵情诗酒,成为高士、狂士型的名士。冯梦龙则不然,他固然是名士,但也无非是出入青楼,这样的举止在晚明社会并不鲜见。这些举动其实与世无忤,不致引起社会的关注与具体官员的反感,其处世态度也不至像狂士那样易于引起纠纷。同时,他也没有像卢楠那样做一个不事生产、不务科举的高士。他参与戏曲、小说创作刊刻,并非借此立异,而是带有借以谋生的意味。尽管科举的失败消磨了他的雄心,但他一直没有放弃科举仕进的梦想。在早前出版的《警世通言》里,《钝秀才一朝交泰》《老门生三世报恩》两篇由冯梦龙所撰的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绝望中的幻想。在“三言”最后一部《醒世恒言》里,《卢太学诗酒傲王侯》一篇中,作者通过对卢楠不幸遭遇的书写,表达了自伤之情,也通过对卢楠的反思,流露出自警之意。
由于出身阅历的不同,卢楠与冯梦龙同为名士而实际行为方式也不同。在冯梦龙写作《卢太学诗酒傲王侯》之时,士人群体中一种新型的名士团体迅速发展起来,其中心发源地仍在苏州,1624年冬成立的应社是这种新型名士团体的代表,其特点是高度卷入现实的政治生活。相较之下,卢楠一类的名士是“狂士”而兼具“高士”的特点,看重的是“雅”“俗”之分,以摆脱社会、忘情政治为高,他们的狂也往往表现为举止随意,鄙视所谓的俗人俗吏。应社所代表的是“狂士”而不是“高士”,他们关注(个人的或国家的)现实的利益与政治的得失,看重的是“正”“邪”之分,敢于越过正常的政治运行规则,以言论和行动攻击他们认为不良的官员与政策。应社甫一成立,即广通声气,其联络地域之广、与官场联系之紧密,已然失去了传统文社以文会友、互相砥砺的原意,而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
冯梦龙对应社之类社团的政治性活动并不热心,迄今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他曾参加过应社、复社[2]。依《卢太学诗酒傲王侯》中所表达的思想,冯梦龙应当对士人参与这种政治的强力对冲,以刀锋争食的方式获取科场的便利,有着强烈的担忧。尽管《卢太学诗酒傲王侯》的确可能有“醒世”的作用——提醒士人收斂自己的行为,但这种预警在当时似乎并无必要,晚明的政府已经无从约束和反击这种行为。晚明这种士风,要到清初的“哭庙案”等大案之后才得以扭转。
参考文献
[1] 傅瑛.卢楠年谱[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2] 王凌.也考冯梦龙的“社”籍[J].汕头大学学报,1988(Z1).
[3] 卢楠.蠛蠓集[M]//文渊阁藏《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M]//文渊阁藏《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 冯梦龙.醒世恒言[M].北京:中华书局,2019.
[6]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7] 熊象阶.浚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8] 沈阿玲. 卢柟及其《蠛蠓集》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1.
[9] 李洵.说“卢柟之狱”[J].史学集刊,1994(3).
(责任编辑 罗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