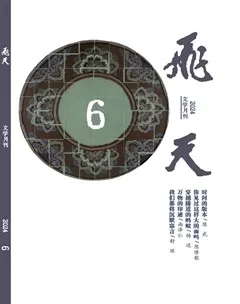野狐和小黑狗
2024-05-31敏奇才
敏奇才
奶奶在世时常讲一些动物与人之间亲近友善的故事;也讲一些动物与动物之间亲近友爱的故事。
奶奶讲的故事里的那些动物主要是一些野生的。它们都和人一样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尤其是讲到一只野狐住在我家堆放杂物的窑洞里,喂养大了一窝狗崽的故事,让人感动不已。其实,有时候人还做不到那一点,但一只野狐却恰恰做到了。
小时候听到这样的故事时,常常感动得流泪不止。听完后问奶奶那些让人喜爱让人感动的野狐去了哪儿时,奶奶却沉睡在了她的梦乡里,让人浮想联翩。翌日便和听了故事的人一道到那深山或是山崖下面的窑洞里去寻觅,或是在那山林里去偶遇。
她讲得最多的是一个狐母的故事,常常讲常常让人感动,我怀疑奶奶讲的这个故事跟我家那条看家护院的狗故事是一样的,但当我后来向奶奶求证这个问题的很多细节时,奶奶早已离开我们沉睡在了地下,把思谋的无限空间留给了无限遐想的我们。
狐母生养
奶奶说,狐母是在一個夜深人静的春夜里生养的,我家的那条母狗也是在一个春夜里生养的。
奶奶说那窝野狐就出生在我家屋后那段白土陡崖下西头的窑洞里。恰巧,那段白土陡崖下的东头拴着我家那条母狗,崖畔下掏着狗洞。母狗是怀了狗崽的,随时有可能在狗洞里下崽。可怎么就有野狐在此下崽呢。确实令人想不通也想不明白。
但奶奶说,野狐就是在那里下崽的。
屋子后墙上装着一个很小的偏门,只能容一个人进出,出了偏门,走过一段菜地间留出来的小路,就到了崖下。崖上长着稠密的白刺,白刺丛里盘住着几窝红雀。在春天的早上,红雀放开嗓子像唱歌一样清凌凌地唱着“西湖水镜”,把人从清晨的睡梦中叫醒。崖头的白刺丛里也住了几窝铃铛雀,公雀一天到晚清脆地唱着歌儿,母雀静静地趴在窝里孕育着小铃铛,见了人不惊也不飞,像只死雀,有时候吹过一阵猛烈的大风,雀窝随着刺枝摇晃,它像荡在摇篮里,更不惊不飞。就这白刺上的红雀也曾有人打过它们的主意,一只叫声优美的红雀能卖好几千元呢。所以在崖畔下用粗铁丝扯了一条长长的浪绳,拴着我家的那条母狗,以此来惊吓打那几窝红雀主意的闲人。
在那陡崖下西头,奶奶还掏了一个能躬身进入的窑洞,是堆放杂物的,距离狗窝不是太远。
在那个空荡荡的窑洞里,奶奶堆放着一些不太需要的东西,用勚后卸掉的圆头铧片,磨成新月样的弯镰,吃土吃成弯月似的铁锨,刨土刨成秃刃的镢头,像弹弓杈样的枯杈,饱经沧桑布满裂纹的榔头,裂了筋骨的担子,秃骨爪样无梢叶的扫帚和用烂的背篼之类的农具,她舍不得将这些东西扔掉或是烧火,放在那里完全是为了一种久远的念想。
其实那些废物放在那里是很挡路的。
但这些东西毕竟是她用顺手了的,过段时间,她都要过去看一眼。从那些旧物上思谋过往的日子,思谋酸甜苦辣。
一天早上她过去看的时候,发现窑洞里那个破旧的烂背篼跑到了窑洞外面。奶奶很是奇怪,难道背篼长了腿会跑路。奶奶决定过去看个究竟。
奶奶穿过菜地到崖畔西头一把提起了那个破旧的背篼,见只狗样的东西跑了出来,火红的尾巴长长地扫在地上,忽地窜出了菜园子,像道火光翻过园子墙一闪就不见了踪影。
奶奶发现扣背篼的地方,有堆零零碎碎的毛发,像狗毛又不像狗毛。
几只红雀叫得很欢,声音清脆而空灵地在崖畔上荡漾,听着让人身心愉悦,心情舒畅。
奶奶看着堆在地上的毛发就想是谁家的狗可能要在我家的崖畔下下崽。可奶奶一想不对,谁家的母狗下崽,除非是野狗,要不然它是不会跑到别人家去下崽的。
奶奶决定在第二天清晨过去再看个究竟。
第二天清晨,奶奶背着背篼到屋后去抱烧水做早饭的干草。突然记起了昨天看到的那条拖着长尾巴的狗的事。当时奶奶就想,昨天的时候,那地方扣着背篼呢,那今儿个没有扣背篼看它到哪儿叨毛盘窝呢。奶奶找了一圈,发现那长着红毛的长尾巴狗竟然跑到那个堆杂物的窑洞里盘了窝。一夜之间,那长尾巴狗不知是从哪儿叼来的毛发,竟然粗糙地在窑洞的墙角盘了一个窝,周围用尾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像扫帚扫了似的。
奶奶远远地看了一会儿,就不敢靠前了。她知道动物都是有灵性的,也是和人类有距离的,如果有人动了它的窝或是动了它的崽,留下了人的气息,它们就会弃窝或丢下幼崽另觅新窝而去。这是一个残酷的选择,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抉择。
有天清晨,奶奶又去抱烧火的柴草时,那只狗样的东西像团火球窜出了窑洞,依然拖着长长的大尾巴。奶奶终于看清是一只野狐,灵巧地跃过墙头,像阵风火红火红地刮过了崖畔,钻进不远处的树林里不见了踪影。
野狐在崖畔下窑洞里盘了窝是准备下崽呢。那些年社会上还没有禁绝枪械,猎人们时常早出晚归,背一杆老土炮或钢砂枪,追兔撵鸡,猎狐打狼,用野生珍贵的皮肉来换取生活的必需品。在村庄附近没有野鸡、野兔之类野生活动的踪迹,更没有野狐野狼之类的大个头野生的活动轨迹。野生都被猎人追撵到了无人烟的林子里去了。其实,就是没有人追撵,它们也会逃之夭夭,因为农人要耕作,就养了牛马驴骡;因为要攒粪,所以家家都养有一群羊。每家一头牛或一匹马或一头驴子,每天放过来踏过去,山上的野草都来不及长,就被牛羊等家畜挨着地皮吃光了。不像现在,牛羊不养了,山上的草长成了林,就连无人住的人家的门洞里都长了草,草根都长到了坚硬的路基下面,有种吃透路基的架势。
草木一茂盛,那些远行的野生又都回到了昔日的故土,胆大的野生还进门窜户在无人的空地上筑巢盘窝,与人和谐共处了。草木长起来的同时,国家也全面禁绝了枪械,断了人类谋取野生皮肉的念头。
奶奶见到的这只野狐是在村庄的植被恢复之后才进入村庄的。也许在庄外的崖畔下下崽哺育后代对野狐来说有着无法预料的危险。昼夜乱窜的野狼野狗会时刻惦念它的幼崽,让它无法安心养育后代。所以它选择了我家崖畔下现有的窑洞,而且不远处还有那条凶恶的母狗在看家护院,其他野生是不敢来的。野狐也许正是看中了这点。
奶奶不敢打扰野狐,不敢前去查看,只是远远地看了几眼就抱着柴草回到了灶房。
其实,那只野狐是一只雌狐,瞅准了我家窑洞的安全而产崽的。
不几日,奶奶再去抱柴草时,听到了窑洞里狐崽儿嗷嗷待哺的叫声。
奶奶老远看了一眼,一窝七只狐崽挤在一起,眯着眼像我家那年春头上生下的几只狗崽一样,麻乎乎的,听见人的动静就互相拥挤着叫了起来。看来是饿了,母狐一定是外出觅食去了。这时候的母狐一定是最辛苦的了,它得昼夜不停地出外觅食,将有限的能量转化为充盈的奶水喂给嗷嗷待哺的崽儿。
我家那条拴着扯了条浪绳的母狗也是腆着肚子,撕扯着身上的毛铺在了窝里,丢在墙角的那件破烂得不成样子的皮褂子被它拖回了窝,它也准备下崽了。
一天清晨,奶奶去崖畔下的洋芋窑里掏洋芋时,发现扯着浪绳的母狗静静地卧在窝里,长长的浪绳上没有了铁环的摩擦声。奶奶心想,这狗儿也有安静的时候。见奶奶走近时它龇牙咧嘴地好像有些许的不情愿。
奶奶看见了它空瘪的肚子,于是笑着说,我家的狗儿坐月子了。奶奶转身走进灶房,给坐月子的母狗端了一大碗热食。见奶奶端来了热气腾腾的热食,母狗才收起了它龇牙咧嘴的样子。
奶奶趁空瞅了一眼,五只小狗肉唧唧地挤堆在一起,也都眯着眼。母狗边吃边回转身看它的狗崽,满眼的惬意,像生了孩子的年轻媳妇们充盈着满满的幸福感。
狗崽狐母
在狗崽还没有睁眼观望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知是谁家不堪老鼠的袭扰放了老鼠药,吃了老鼠药的老鼠越过了我家的院墙和场墙,慌不择路跑到了崖畔下,被母狗逮住了好几只。母狗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逮一只吃一只,连续吃了三四只,吃了被老鼠药闹糊涂的老鼠后母狗终于把自己也闹糊涂闹傻了,最后寸肠俱断,死于非命。
母狗死时,鼓着眼盯着窝里的狗崽叫声凄绝惨厉。绝望至极地在狗窝里用前爪刨了个大坑,最后口吐白沫,蜷着死在了那些狗崽面前。
母狗死后,嗷嗷待哺的五只小狗崽就成了没娘娃,饿得东倒西歪,蜷缩着挤在一起叽叽地叫着。还没有睁眼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也没有正眼瞧过它们的狗母,却和它们的狗母阴阳两隔,成了断了狗奶的几只孤狗。它们的叫声弱弱地穿行在崖畔下的园子里,让人怜悯,也让人心疼。
奶奶试着用喂婴儿的奶瓶装了羊奶去喂几只嗷嗷待哺的狗崽。可它们却簇拥着不吃羊奶,让奶瓶中滴下来的羊奶任意洒淌,也不咽一口。
奶奶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央人把它们抱养走。可谁会抱养一只连奶都不会吃的狗崽呢?没有人会操那个心。很多人连自己的儿女喂奶都嫌麻烦呢,谁还有那个耐心去喂养一只既没有睁眼也不会吃奶的狗崽呢。
奶奶在村里转了一圈,没有人答应领养。奶奶在村里人前人后讨了个没趣。
要是那些狗崽再不吃奶,不是饿死也得冻死。
奶奶搬了条凳子坐在崖畔上,看着冷冷的狗窝陷入了沉思。她自从嫁到这个家里以后,还没有让一只羊啊鸡啊饿死过冻死过。那些在腊月里下了羊羔的母羊,在开春的二月里吃了刚冒出地皮的草芽子,一时拿捏不住淌了几天黑屎,突然卧倒在地上站不起身。可它的羊羔还在吃奶当中,奶奶就当羊羔的妈妈,嘴对嘴喂羊奶,也喂嚼碎炒熟的大豆,硬是把一只只看着活不过来的羊羔子救活了。
可现在这几只狗崽不吃羊奶,面食更不吃,他还真没有办法喂活这几只狗崽了。
那只野狐不時地翻过院墙跑进来,给它的那几只狐儿狐女喂狐奶。喂奶时几只狐儿狐女兴奋地叫着、争着,争先恐后地吮吸狐母的狐奶。
那几只狗崽的叫声越来越弱,越来越小。
奶奶看着可怜,拿了张羊皮铺在了那几只狗崽的身下。她想,它们已经饿着再甭叫它们冻着。听天由命去吧。奶奶说着离开了狗窝。
那天晚上,奶奶没有好好地睡着,一直处在半睡眠状态之中。
天刚亮,地上还麻乎乎的。奶奶赶紧到崖畔下的狗窝里瞅那几只狗崽。
狗窝里的狗崽全不见了。羊皮干干净净地放在狗窝里。奶奶在狗窝周围查看了一圈,还是不见那几只狗崽。它们自己爬出了狗窝还是被什么东西吃掉了?它们自个爬出狗窝的话,肯定是爬不远的。要是被什么东西吃了,那会留下痕迹的。可现在没有任何痕迹表明它们被什么东西吃掉了。
奶奶站在狗窝边百思不得其解。
窑洞里野狐崽儿的叫声吸引了奶奶的目光。决定过去瞅一眼窑洞里麻乎乎的狐崽。奶奶刚要迈步,只见下了七只狐崽的野狐,飞烟样地钻出了窑洞,迅疾地跨过园子墙消失在了田野里。
奶奶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看到窑洞里的狐崽竟然多出了几只,乱乱的挤在一起,互相挤压着。
这就奇怪了,原来的七只狐崽竟然成了十二只。奶奶再一细瞧,原是狗窝里的那五只狗崽却跑到了狐窝里。那些肉唧唧的东西,才睁开眼,还没有见到这个世界的美好,狗母死后又饿了一天,它们连挪一下的劲都没有,怎么就爬到了野狐窝里呢。肯定是被野狐叼到自己窝里的。
奶奶悄悄看个究竟。
野狼是家狗的老舅,所以把小狼崽放进狗窝吃狗奶时,狗会照看得一丝不苟。也有人见过野狼养大过土狗的事。但就是没有人见过野狐会养狗崽,这绝对是一个奇闻。
那只火红的野狐翻墙出去的时日久了,不知它丢下狐崽干什么去了。
吃过早饭,奶奶来到白土陡崖东面原来狗窝那儿,背了个背草的大背篼,倒扣着把自己悄然藏在了里面,坐在她给狗崽铺过的那张羊皮上,从背篼的竹缝里看窑洞里的狐崽。
外面的太阳从背篼的竹缝里驳斑地透进来,轻抚着奶奶的身心。
奶奶目不转睛地看着窑洞门口,她想那野狐到底是怎样喂养狗崽的。
奶奶知道,野狐是杂食动物,它饿急了啥都吃。不是太饿的时候,它会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掏只田鼠,叼只野鸡,追只兔子,偷只家鸡。偷家鸡得冒一定的生命危险,要是被鸡主知道了,会在它经过的路上装几个夹子,放几条绊绳,有时也会故意丢一片鸡肉或一根鸡腿,上面抹上老鼠药,想方设法药死它。说是野狐贼精,但在人类面前,它们都不是对手,难以逃脱人类的捕灭。不过这只野狐却从来没有叼过奶奶养的任何一只鸡。秋冬季节,肥肥胖胖的鸡们在后园子里漫步散心。在万物生长的春季里,几只母鸡领着各自孵化的小鸡,在后园子里的空地上捉虫刨食啄嫩草芽吃,也没见小鸡少过。假如小鸡少了,那一定是旋在虚空里的老鹰趁小鸡躲藏不及而叼走了。一窝小鸡要长大,让老鹰叼走几只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奶奶坐在大背篼里面,窥探着外面的世界,窥探着狐母和它的狐儿狐女们,还有那几只嗷嗷待哺的狗崽。
后园子那堵墙的豁垭处一道红光一闪,那只野狐弓着腰嗖嗖几步就窜到窑洞里,挨个嗅了嗅它的狐儿狐女和那几只狗崽,随后躺倒在地上,用嘴拢用爪子刨,把狐儿狐女和狗崽都收拢在了它的身下,然后静静地喜看它们吃奶。这时候的野狐像喂养了无数个儿女的女人,用它长长的尾巴轻扫着身下的狐儿狐女和狗崽,闭了眼,沉浸在幸福当中。在这个世界上,作为母亲最幸福的事也莫过如此。
奶奶看得浑身发热,阵阵激动,一行清泪哗地流在了胸前。伟大的母爱,就是这个样子的。人是这样的,动物也是这样的。而且眼前的这只野狐比我们人类还要伟大,它竟然喂养了五只也许与它的家族终生为敌的狗崽。
奶奶后来常给我们讲,并要求我们在今后一定要善待一切有气之物。她说一切有气之物都是有灵性的。
奶奶一颗紧悬的心总算放下了。
自从野狐在后园子里安了家,生养了狐儿狐女,一并喂养了狗崽后,奶奶就不让我们到后园子里去玩了。其实,那时候我们是不知道野狐在后园子里安了家并生养了狐儿狐女的事。
当那些狐儿狐女和狗崽快要喂养大了的时候,奶奶留下了一只黑狗崽,把其余的四只送了人。这回,奶奶抱着已睁开了眼睛,还能吃面食的狗崽送人时,再也没有人推辞说不要了。因为狗儿已经能在地上自由地跑着自己吃食了,不需要特别的照顾。用奶奶的话说是好养了。奶奶把这些狗崽送人的目的是让那些狐儿狐女快点长大,再不然,七只小野狐加上五只狗崽,野狐的奶水已供不应求了。野狐要有足够的奶水,那它就得不断地进食,它进不了食的时候很有可能要做偷鸡摸狗的事。这是奶奶最担心的事。野狐一旦做出了这些坏事,就会有人跟踪它的行踪,用人的智慧给它下绊子,置它于死地。
一些吃剩的鸡腿、羊肋、干馍馍、剩饭,奶奶悄悄地端来倒在了原来的狗食槽里。在野狐出去觅食,小野狐和小狗崽饥饿的时候,小狗崽竟领着小野狐走到狗食槽里吃奶奶留给它们的吃食。
在小儿们爬墙的豁垭处,奶奶砍了一捆酸刺罩住,不让那些闲得无聊的小儿们翻墙到我家后园子里来。只留了野狐进出的那处豁垭。那处豁垭已被野狐的皮毛刷得亮亮光光的,像我们时常翻越的那堵学校墙一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有人时常翻越那里。
狗弟狐兄
那一窝小野狐和一只狗崽在奶奶和狐母的照看喂养下,长得很快。白天,天晴的时候,它们就在后园子里追逐、戏耍。
奶奶说,小野狐和狗崽出窝玩耍了几天后,狐母不是早上叼来了一只野鸡就是下午叼来了一只田鼠,扔在园子的空地上或是窑洞口,让小野狐和小狗崽撕咬着吃。小野狐和小狗崽也不顾鼠毛和鸡毛,用力撕咬,吞咽,填着肚子。
奶奶还说,小野狐和小狗自己能吃食,说明狐母要给它们断奶了。狐母一断奶,小野狐就得离开窑洞。这里只不过是它们临时的生养之地,它们的生存之地在远方的大山里。
那只小黑狗也得留下来,它跟着野狐将是一只异类,它的命运是终生和人生活在一起,生活在這个不大的后园子里,继续狗母的事业,看家护院,终老一生。
奶奶悄悄把它抱到前院里,用条小绳子拴了起来。被绳子拴着的小狗不耐烦地叫了几天,叫得让人有点难过。夜晚,后园子里传来了阵阵像婴儿般哭叫的声音,那是狐母的叫声,它在寻觅,它在找寻,它在叫回小狗。可它哪里知道小狗从此将与它们天各一方,也许再也无缘相见了。
春天完了。
后园子里的蔬菜也慢慢地起身了,绿汪汪地罩住了裸露的地皮。
小黑狗已习惯了被小绳拴着,吃了睡,睡了吃,安安静静地在那片小天地里成长。
后园子窑洞里的小野狐长得像模像样,把草垛下躲了多日的几窝小老鼠被它们嗅着一个不剩地刨挖了出来,吃掉了。
奶奶后来念叨着对我们说,要是狗早就分窝了,但野狐还在我家的窑洞里住着,没有分家的意思。弄得我家把窑洞跟前那片地空了很久。母亲说要种几垄葱过冬时吃,奶奶不让种,说让它空着;父亲说起种些绿头萝卜,秋后腌萝卜干,奶奶还是不让点。那片空地就长了些杂草,一直荒着,荒到夏天的时候。奶奶说可以在那片空地上种些东西了。父亲和母亲笑着说,荒着去,明年再种。今年再赶不上时候了,只能种些白菜,可白菜种得够多的了。
奶奶笑了笑,算是默认了。
其实,奶奶一连好几天都没有见到狐母和那些小野狐了。原来,它们分窝走了。小野狐一分窝,狐母有可能要孕育新的生命了。
后园子里一下子显得空荡荡的,没有奶奶的牵挂了。
奶奶只好把小黑狗牵了过来,拴在了拴它母亲的那个拴狗桩上。小黑狗被牵到后园子里来的时候,那个兴奋,那个愉悦,无以言表。
小黑狗被拴在拴狗桩上,直直地望着窑洞,像在召唤着与它一起喝狐奶长大的那些狐哥狐姐。可它们却一去不复返,在大自然的深处寻找它们的幸福去了。
小黑狗就这样望着、成长着。寂寞了的时候,它会似狗似狐狂躁地叫上几声,把它那奇怪的叫声在黑夜里传出很远很远。远山里,偶尔也有野狐像婴儿哭叫似的呼应着。听到野狐的呼应,小黑狗就兴奋地围着拴狗桩转来转去,想挣脱那根拴它的细绳。
日子一晃就到了秋天,万物成熟了。
庄稼地里的庄稼沉醉在秋天的喜悦里。这时候,奶奶突然生病住进了医院。拴在后园子里的小黑狗一直由奶奶操心,别人也就忘记还有那么一只狗在后园子里被拴着。拴着的狗没有人记着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一天两顿狗食那是按时要给的,可奶奶一住院,谁也没有记起后园子里被拴着的小黑狗。
奶奶在医院里的时候,还对家里说起过被拴在后园子里她的狗。可家里人一边忙着操心奶奶,一边忙着收割庄稼,竟然把在后园子里拴着的小黑狗给忘了,忘得一干二净。
等到奶奶住了七天医院出院后,经提醒,一家人才记起了被拴在后园子里的小黑狗。
父亲和母亲赶紧到后园子里去看。他们当初的想法是,小黑狗肯定被饿死了,得赶紧过去解开埋掉,要不然奶奶知道后要大骂几天的。可当过去看的时候,小黑狗活得好好的,没有太挨饿。只见狗窝附近散落着一些野鸡和嘎拉鸡的毛。父亲和母亲就奇怪小黑狗被拴着怎么还就抓住野鸡和嘎拉鸡吃了呢。他们想肯定是哪里的野狗给小黑狗叼来的野鸡和嘎拉鸡。
他们决定看个究竟。
深夜里小黑狗发出了似狗似狐的叫声,远山里传来了野狐的回应。
小黑狗的叫声越来越激越,远山里野狐的回应也越来越近。
父亲拿了手电筒,站在后院的小门洞那儿,看着后园子里的动静。时候不大,只见一只狗样的野生嘴里叼着东西翻过后园子墙,把东西抛给了小黑狗。父亲拿手电筒一照,那个狗样的东西拖着长尾巴嗖地一下跃过墙头,一晃就不见了。这时父亲才看清楚是一只野狐叼著一只嘎拉鸡喂小黑狗呢。
父亲就很奇怪地回屋向奶奶说起了野狐叼着野鸡和嘎拉鸡喂小黑狗的事。
奶奶听了嘿嘿地笑个不停。“我家后园子的窑洞里就住着一窝野狐呢。是这窝野狐的狐母喂养大了那窝死了狗母的小狗。它们是一窝吃着狐奶长大的奶亲。”
父亲笑着对奶奶说道:“怪不得您不叫我们在后园子窑洞前面种菜,原来是这种情况。您说那里有窝野狐住着不就得了。”
“我一说,你们这个过去瞧一眼那个过去摸一把,不就惊着野狐了。野狐本来就是小胆子野生,是惊不得的。再说人的气味也会让野狐弃窝远走的。”奶奶眯了眼笑着说。
奶奶慢慢挪下炕,拄了一根棍子,说她得看看她的小黑狗儿去。看饿瘦了没有。
一家人跟着奶奶往后园子里走去。
后园子里黑得摸不着东西,小黑狗卧在黑洞洞的狗窝里,一对狗眼明晃晃的像两颗天上的星星。
奶奶蹲下身,摸了摸激动着跳跃的小黑狗,压低声音说:“是谁喂你的?是你的狐母还是狐兄狐姐?”
“现在有人操心你了,你就多吃点东西。再不要被饿着。”奶奶抚着小黑狗的头,像对一个吃奶的婴儿说着话儿。
激动的小黑狗突然安静了,远山里传来了野狐的叫声,忽远忽近。
小黑狗的狐兄狐姐惦念着它们的狗弟。
奶奶躺在炕上,闭上眼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个世界上人类不但有血亲也有奶亲,动物也有血亲和奶亲。我原来不相信动物之间有奶亲,但我现在相信了,也亲眼见证了。”
但谁能说清楚野狐和狗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恐怕没有人能说清楚。
只有我奶奶是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