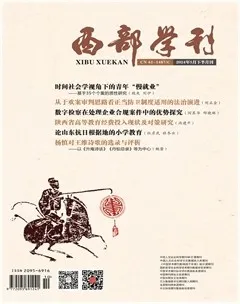抗战时期中共在浙江的青年动员研究
2024-05-23范人杰
范人杰
摘要:根据外部环境演变和自身政策的迁移,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浙江青年动员可以分为抗战初期的蓬勃开展、相持阶段的波澜起伏和反攻阶段的再掀高潮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动员内容和主要形式各有侧重,有的聚焦于政治动员,有的则以军事动员为重点,还有的关注文化动员,并表现出了公开性和保密性紧密结合、广泛性和特殊性高度统一,以及团结性和斗争性无缝衔接等特点。这些特征鲜明的动员策略成为抗战时期中共成功领导浙江青年动员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浙江
中图分类号:K265;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4)10-0114-06
On the CPCs Youth Mobilization in Zhejiang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Fan Renjie
(Party School of Anji County Committee of CPC, Huzhou 313300)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ts own policies, the youth mobilization in Zhejiang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namely,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war, the ups and downs in the phase of confrontation, and the climax in the phase of counterattack. The content and main forms of mobilization in each stage have different focuses, some focuses on political mobilization, some focuses on military mobilization and others on cultural mobilization, showing a close combination of openness and confidentiality, a higher degree of unity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and a seamless transition between solidarity and struggle. These distinctive mobilization strategies became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of the CPCs success in leading youth mobilization in Zhejiang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Keyword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youth; mobilization; Zhejiang
浙江作為抗日战争史和专门史研究的重镇,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浙江省内各类动员研究可谓硕果累累。然而,略有缺憾的是以往学界对浙江省内的动员研究大多按照组织、军事、宣传等传统类别进行分类研究,或者止步于对群众动员的研究边界,对各类具体人群的动员研究较少涉猎。为了弥补这些细微缺憾,本文尝试转换视角,打破学界对浙江动员工作研究传统范式的“桎梏”,聚焦青年这一群体,并将青年动员的形式、特征及成效纳入历史原貌中开展研究,借以促进抗战时期浙江省内动员研究版图的逐步完整。
一、学术史梳理
改革开放后,在“眼界下沉”的学术感召下,中共领导的基层动员工作引发了学界极大兴趣,研究热潮兴起。本文通过对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浙江动员工作学术史进行梳理回顾,并将相关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以下两类。
(一)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浙江青年动员工作史料唤醒
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于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浙江青年动员工作研究主要以史料唤醒为主,侧重于史料发掘的综合性和资料性,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1)将浙江革命青年运动单列成专辑,重点介绍了徐玮等26位浙江青年志士的革命事迹[1]1。杭州大学历史系、浙江省档案馆(1985)对相关历史文献、报刊资料、回忆录及图表进行梳理和集成,真实还原了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招生的历史面貌,指出其办学宗旨是使有志青年真能为国家民族服务,增强抗战力量[2]。以上资料的开发不仅使文献档案、口述史料等学术矿产免于沉睡,对于鼓舞浙江青年不断矢志奋斗也具有正面意义。陈秀萍等(1990)将浙江青年运动历史与现实国情相关联,强调浙江青年要为改革出谋划策、要振兴中华,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必须了解历史[3]7。通过史料的持续梳理,抗战时期浙江青年的活跃态势也逐渐呈现。浙江青运史研究室(1992)认为,中共浙江省委青年部给各级青年部青委会的指示信对于全省各地青年运动的开展具有思想引领的作用[4]427。楼子方(1995)立足于全省各界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时代背景,重点介绍了中共领导的浙江各青年爱国团体的活跃态势,指出浙南地区“青年运动超过东南各省”[5]65。
新世纪后,学界对浙江青年动员工作的史料研究更加注重体系和规范性。2001年,《浙江省青年運动史资料丛书》出版,《浙江青年运动与青年工作编年纪事》与《共青团浙江组织史资料》囊括其中,《浙江省青年运动史资料丛书》编纂委员会(2001)客观系统地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浙江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的发展轨迹,为浙江青年运动的可持续研究提供了科学而详实的文献资料[6]。《浙江青年运动志》编纂委员会(2011)同时关注中共、国民党地方政权及汪伪政权三方在抗战时期浙江青年运动中的具体方位,并明确指出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抗日政策的变化是浙江青年救亡组织解散的直接原因[7]344。尽管上述研究成果的视角和侧重有所区别,但均为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浙江动员工作专题研究进一步展开作了史料铺陈。
(二)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浙江动员工作专题研究
学界对于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浙江动员工作存在不同认知,研究旨趣主要集中于群众动员和宣传动员两个方面,也成为其专题研究得以顺利开展的突破点。
在群众动员方面,王新菊(2014)着重聚焦媒体在群众动员中的张力,指出《浙江潮》是知识分子就当时社会问题发表看法的一个重要场所,对推动广大民众认清社会现实有着巨大的帮助作用[8]。蔡禹龙、肖如平(2015)将目光下移,利用龙泉市图书馆馆藏的大量保民大会资料对抗战时期龙泉县的保民大会进行考察,指出新县制推行后,保民大会已成为宣传和动员广大乡村民众支持抗战的利器[9]。萧宸轩(2021)指出,为实现更深层次的民众动员,中共在和地主的反复博弈中突破了早先“二五减租”“二五减租”:1939年,中共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正式公布《减租减息办法》:“地主之土地收入,不论租佃半种,一律照原额减收百分之二十五”。的困境,满足了民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从而达到了动员效果[10]。抗战时期中共对少数民族民众动员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一些成果,张根福、王晓帆(2022)在畲族动员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指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族地区的民众动员充分结合了畲族的民族特性[11]。向豪(2022)将研究的时间轴框定为1938年至1940年,指出这个时间段内浙江党组织重视利用统一战线为群众动员工作营造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12]。
在宣传动员方面,张印举(2020)在研究中发现《浙江妇女》的妇女宣传动员一方面有着比较明显的“苏联情结”,另一方面也肯定了这种动员方式促进了妇女抗战意识的觉醒,宣传了中共的革命观和妇女观,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13]。逄淑美(2021)从经济、政治、文化和人员四个维度对浙西抗战报刊的抗战动员展开剖析,并点出《民族日报》《浙西导报》是浙西地区抗战社会动员和文化传播的典型代表[14]。彭文文(2021)指出,中共坚持在沦陷区、国统区、游击根据地创办红色报刊,并将其视作开展斗争的重要策略,这点是其他地区的报刊所不多见的[15]。
除此之外,王才有(2018)将民间会社嵌入中共领导的革命动员中,认为中共党团组织嵌入模式之由“会”入“社”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革命逐渐工农化的缩影[16]。两年后,王才有(2020)通过管窥中共浙江暴动的演进,指出军事动员和日常斗争的交织递进构成了此后中共革命发展的新常态[17]。在王才有的指导下,闫家威(2022)认为,中共在浙东抗战中所体现出的社会动员要素恰恰是中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权力下探的延续[18]。
综合已有研究,可以得出“动员工作”是有组织、有目的、声势较大的群体性活动,涉及复杂的网络系统,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斗争等方面。当前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浙江动员工作研究已从20世纪的宏观把握细化到专题捕捉,并已初步探索与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互联互通。然而,美中不足的是针对专门群体的研究相对缺乏,而这种缺乏也正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发挥空间。
二、中共领导浙江青年动员的阶段演进
(一)抗战初期的蓬勃开展
从1937年日军入侵浙江到武汉失守是浙江青年动员工作蓬勃发展的时期。日军侵袭浙江后,其暴行激起了浙江民众的义愤填膺,包括青年在内的各阶层纷纷涌入抗日大潮。在此背景下,中共临时省委及后来的浙江省委正确分析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政治情况[1]109,从多方面主动开展统战工作,稳定住了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促使下,广大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许多青年志愿参军上前线抗击日军,各界青年组成的抗日救亡团体,如抗日救亡义勇军、抗日青年救国团、青年救亡室等如雨后春笋般在全省各地涌现。与此同时,上海、南京、无锡及杭州等沦陷区的学校也在向浙江后方地区迁移,一时间云集浙江的青年学生、青年工人与本地青年一起积极开展各类救亡活动,在之江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抗日热潮。
(二)相持阶段的波澜起伏
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到1944年日军“扫荡”四明山区是第二个阶段,处于抗日斗争的相持时期。在这个时期,浙江青年动员工作呈波澜起伏之势。以日军对国民党“打拉并用”政策的实施为饵,国民党顽固派对于中共领导下的青年动员工作已从前期的消极配合转变为百般阻挠。例如,国民党第三战区“军风纪巡察团”在浙南勒令解散一切抗日救亡团体,许多革命青年被暗杀、逮捕。顽固派在政治上推行所谓的“以共制共”,强迫、引诱青年中的动摇分子自首或发表脱离中共的声明。直到1942年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被国民党杀害于永康,此时浙江的反共高潮达到顶峰。大批爱国青年损于国民党顽固派之手,革命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公开的和半公开的进步青年组织均很难开展活动。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共浙江省党组织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756的方针,及时调整工作方法,以各种合法的、群众习惯的形式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保存了青年骨干力量,延续了浙江青年运动的血脉。
(三)反攻阶段的再掀高潮
从1944年3月四明山区反“扫荡”斗争到抗战胜利是中共领导浙江青年动员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广大青年在中共领导下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不懈努力。同时,浙江的青年动员工作也再度掀起高潮。在外线,广大浙江青年在浙东区党委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反“扫荡”、反“蚕食”、武装保卫秋收的英勇斗争中。仅在1944年7月至9月,浙东青年就协助当地游击队毙伤、俘虏日伪军781名,夺回被抢粮食数十万斤。在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中,中共宣传动员的效应也同样明显,广大浙西青年积极参加民工队伍,在长达百余里的粮食运输线上昼夜兼程为新四军运送粮草,并在新四军征兵时踊跃报名参军。在内线,根据地青年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全力加入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中,“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必须于两三年内完全学会这一门”[20]。广大青年不仅是“减租减息”中的先锋骨干,在大生产运动中担当生力军,并成为文化教育战线上的活跃分子。根据地青年能有如此“多才多艺”的表现,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中共开发青年能量的正向功效。
三、中共领导浙江青年动员的形式再现
(一)政治动员
中共在浙江青年中的政治动员早期主要表现在成立各类青年抗日团体,抗战后期主要是发动进步青年参与民主政治建设。1936年11月,中共中央就提出了“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当作自己为民主共和国斗争的最中心任务”[21]。并且在经历日军咄咄逼人的入侵后,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深刻地认识到,要想坚持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领导和开发最广泛的青年救亡运动是当务之急。因此,1937年秋中共临时省委就开始有意识地将广大青年统一到有组织、有行动的团体中去,与一切青年成立联合的统一的组织。在中共的关怀和指导下,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舟山青年抗日宣传队、诸暨抗日救国会等全省各地的青年抗日组织纷纷成立,并积极利用自身的合法身份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战后期,随着浙东和浙西两大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定型,中共出于巩固根据地的考虑,重视将当地青年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带头人,积极发动和吸收当地进步青年进入根据地各级政权和社会团体。如浙东区党委于1945年5月成立的浙东青年联合会筹备会,就在根据地建设中发挥出了应有的活力,成为中共立足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得力帮手[7]350。
(二)軍事动员
在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挤压下,如何保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韧性成为迫切问题。中共选择的应对之道是领导根据地群众开展军事动员。其中,有效发动青年参军参战是中共在浙江领导军事动员的最主要手段。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到军队里去——这是在今天挽救民族危亡的最有效的方法。建立生力军,充实我们的旧队伍,责任都在我们青年朋友的肩上。”[22]来源于中共的主动吸收,大批青年加入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如新四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以浙西为例,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军的不断紧逼,中共在天目山区站稳脚跟的当务之急就是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因此,在各级党政军机构的宣传和感召下,浙西抗日根据地的广大青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场面在天目山区不断涌现。在1945年8月的参军运动中,仅长兴县就有1 600多名青年加入新四军[5]333。“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歌谣在浙西大地广为流传。而且,这些青年在抗战胜利随着新四军北撤后转战大江南北,成为日后中共“南下干部”的重要骨干。
(三)文化动员
武汉失守后,在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关于“将青年运动开展到军队、工厂、矿山、学校、铁路、码头、轮船、城市、农村等各青年救亡团体去”[4]405的指引下,如何提高青年活泼性,使青年干部消除死板的沉闷现象成为各级党组织的新任务。基于此,全省各级党组织正确灵活地运用策略,主要通过文艺宣传和青年教育两种动员方式来提升青年参与抗日救亡工作的活跃度。鼓舞性的文艺宣传工作普遍从文化上、艺术上、口头上展开,如浙南地区出版《生线》《救国导报》等10余种综合性的刊物用于理论宣传,同时组织歌舞队、剧团、木刻社、漫画社、墙画队布置抗日环境,满街满巷甚至乡村偏僻角里,均弥漫着抗敌的呼声[4]412,在文艺宣传上获得了很大的成果。文艺宣传的广泛铺开需要知识青年的支撑,同时,作为同顽固派斗争的一种软性策略,在周恩来同志“在学校里学习、到前线学习、到军营学习、到群众中学习”[7]346的指示下,全省各级党组织不断调整文化动员的表现形式,把青年教育和抗日宣传结合起来,利用读书会、工农夜校、短期小学、青年学社、工人巡回施教队等形式提高其学习兴趣与文化水平。如此动员行为不仅激发了各界青年的抗战情绪,而且使浙江大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愈加生机勃勃。
四、中共领导浙江青年动员的策略特点
(一)公开性和保密性的紧密结合
抗战时期的浙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主次地位的不断交替是中共领导青年动员侧重于公开活动或走向隐蔽的主要考量。抗战初期,日军在军事上给予了国民党浙江当局巨大压力,其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国民党省政府在闽浙边临时省委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后,于1937年7月27日主动致信中共临时省委,要求重开和谈[3]107。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也存在着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和复兴社“复兴社”:即中华民族复兴社,也称“蓝衣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加紧镇压抗日民主运动,以黄埔系骨干分子为主,于1932年4月借“复兴民族”之名,在国民党内成立的带有特务性质的派系组织。由蒋介石任社长。1938年4月,复兴社宣布解散,并入公开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特务处则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CC系“CC系”:即中央俱乐部(The Central Club)又称CC系,是一个政治派系,实力主要分布在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门,尤其是组织部、中统、地方各级党部和教育系统(尤其是大学)。间等矛盾。外部环境的“改善”使得中共在抗战初期能够正确地利用这种矛盾,采取合法的手续争取到各种青年抗日团体的公开活动,如扩大宣传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发动青年上前线、响应国民党当局号召,以及发动保卫大浙江运动等,这些公开活动既扩大了中共在青年中的影响,也在某一阶段内取得了国民党当局的同情和信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并不是直接从公开活动就地迈入隐蔽战线,为了避免重蹈大革命失败的覆辙,其在合法领导青年运动时也时刻保持着政治清醒,并非毫无保留地公开活动。1939年5月下发的《中共浙江省委组织对今后任务的决定》中曾明确要求:“各级干部(连省特委也在内)必须各有一种职业掩护,如店员、学徒、买办、经理、先生、新闻记者、机关支援、各救亡团体的职员及队员、小教、律师、教授、做工、耕田、读书等职业。”[23]并且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时服从于中共中央的指示,选择了隐蔽精干,以秘密的小规模的活动代替原来的公开的大规模的活动,如浙南党组织的地方工作人员及武工队都改为晚上活动,主要的群众工作如开小型宣传会、座谈会、调查会以及登门拜访等都在夜间进行[24]。如此,在隐蔽中等待再次公开活动的战略机会。
(二)广泛性和特殊性的高度统一
为了避免过分刺激浙江的国民党各级地方政府,尽管中共强调不以公开面貌来领导和发动青年走上政治舞台,但是无论从地域性还是群体性着眼,中共领导的青年动员已经在浙江全省铺开,工作涉及范围广泛而卓有成效。从地域上讲,从浙西到浙东再到浙南,中共为加强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普遍建立起了特委、中心县委、市委的青年部或青年工作委员会,由青年同志专门负责,同时,青年工作部门加强了对各地青年动员的运作指导。在具体工作上也有很好的多方面的表现,在动员青年上前线、宣传教育、推动群众工作及青年统一战线方面有很多值得称赞的优良工作经验。这种经验的取得并非偶然,它是建立在中共在浙江青年工作上一盘棋的指导思想以及广大青年群体的努力基础之上的。
不仅仅关注青年动员的广泛性,中共对青年群体的领导也体现在对特殊群体的个别关照上,如青年学生、台湾同胞等。1939年春,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从重庆来到东南抗日前哨视察工作。而青年学生作为人民抗日力量的生力军和先锋队,正是周恩来东南之行的关注重点。是年3月24日,其专程参加浙西第一临时中学的开学典礼,寄予青年学生深厚期望,强调要不断地把新青年的血液渗进去,使广大人民共同向政治进攻的前途迈进,共同担负起政治进攻的责任來[25]。周恩来还看望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歌咏队和台湾义勇队,希望他们在不同岗位上,通过各自工作唤醒青年,为抗战最后胜利做出贡献。
(三)团结性和斗争性的无缝衔接
浙江作为国民党的“龙兴之地”,蒋介石对此地的重视程度远超他省,再加上江浙财团是国民党的重要经济依靠,浙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均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相对而言,中共在浙江开展青年动员的难度大大增加,这也决定了中共在浙江的一切合法的政治活动绕不开国民党当局,必须积极主动地去团结国民党才有可能实现目标。而出身桂系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再次主政浙江,表现出的政治立场和倾向使得中共相信有争取其团结抗日的可能性,而黄本人也确实接受了中共的部分抗战主张,相对开明。他治下的国民党官办各抗日团体均有进步青年参与其中。由中共地下党员、爱国青年协助其共同起草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在抗战初期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虽然不可否认的是黄绍竑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巩固自己地位和实力的考虑,但其顺应抗日洪流的举动不仅稳定了浙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为中共领导青年动员创造了契机。
尽管中共在团结黄绍竑的过程中表达出了极大的诚意,但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依然固执己见,惧怕统一战线,以致采取事实上与日伪势力沆瀣一气压制青年运动,解散青年救亡团体。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面对日伪顽的同流合污,在思想上对“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9]745的认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景阳冈的老虎终究是要吃人的,你同它斗,它要吃人;你不同它斗,它还是要吃人”[26]。因此,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宁波的进步青年向群众大量散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发表的谈话和革命文件。平阳、瑞安、青田等地的青年在中共的号召下纷纷参加地方武装组织,进行自卫斗争。尤其在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中,浙西的爱国青年积极协助新四军运送粮草,提供情报,全力反击顽固派的猖狂进攻,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结束语
日军入侵浙江后,中共逐渐意识到青年是抗战中一股新的力量,如何发展与组织全浙青年参加抗战工作和参与军事活动,是一个现实的重要问题。据此,中共开始有意识地加强对青年群体的发动和领导,浙江青年运动也在其领导下得以普遍开展,并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各式各样的青年组织与青年救亡活动,普遍于各个地区的每个角落,从敌人炮火直接威胁下的沿江沿海以至最偏僻的穷乡僻壤[4]428。无论是政治参与、军事斗争或是宣传教育方面,浙江青年均表现出了与年纪相符的朝气和活力。中共以其独特的策略和方法准确抓住了浙江青年动员的脉搏,其领导下的浙江青年动员也因此成为浙江抗日战争史的一个有机部分彪炳史册。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五(浙江革命青年运动专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2]杭州大学历史系,浙江省档案馆.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347.
[3]浙江省团校《浙江青年运动史》编写组.浙江青年运动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4]浙江青运史选编编委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青运史资料选编[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
[5]楼子芳.浙江抗日战争史[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
[6]浙江青运史资料丛书编纂委员会.浙江青年运动与青年工作编年纪事[M].北京:中华书局,2001:96-115.
[7]《浙江省青年运动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青年运动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
[8]王新菊.《浙江潮》对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的分析[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
[9]蔡禹龙,肖如平.自治与动员:抗战时期的保民大会——以浙江省龙泉县为例[J].民国档案,2015(3):70-75.
[10]萧宸轩.中共在浙东的民众动员研究(1941-1945)[D].杭州:浙江大学,2021.
[11]张根福,王晓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浙西南畲族的民众动员[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42-51.
[12]向豪.浙江地区党的群众动员工作研究(1938—1940)[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13]张印举.《浙江妇女》与抗战时期中共的妇女宣传动员[J].新乡学院学报,2020(5):56-62.
[14]逄淑美.浙西抗战报刊的抗战动员研究:以《民族日报》《浙西导报》为例[J].图书馆杂志,2021(7):132-136,150.
[15]彭文文.全面抗战时期浙江红色报刊的抗战动员研究[D].杭州:浙江理工大学,2021.
[16]王才友.由“社”入“会”:浙江中共组织嵌入与革命动员的演进(1925—1934)[J].中共党史研究,2018(11):47-65.
[17]王才友.从军事动员到日常斗争:中共浙江暴动的演进(1927—1928)[J].中共党史研究,2020(5):79-94.
[18]闫家威.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分散游击与社会动员[D].杭州:杭州师范大学,2022.
[1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24.
[21]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運动文件选编[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441.
[22]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89.
[23]浙江省档案馆.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战时期(上)[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88.
[24]龙跃.坚持浙南十四年[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145.
[25]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周恩来抗日前哨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45.
[2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