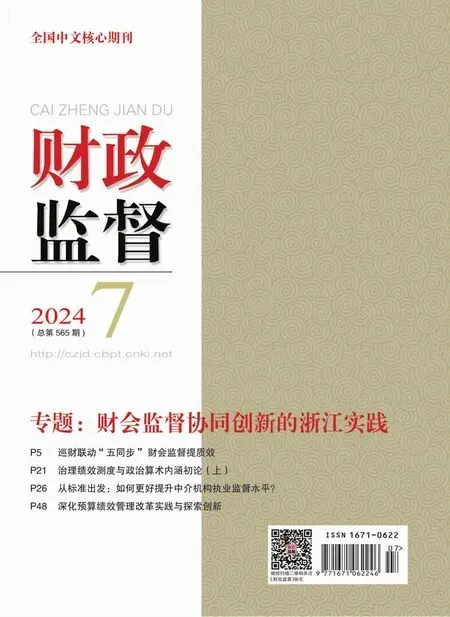治理绩效测度与政治算术内涵初论(上)
——兼与邱东教授商榷
2024-05-22宋丙涛潘美薇
●宋丙涛 潘美薇 张 庭
近代以来,由于欧美在科学技术帮助下对全世界的征服既展示了现代武器的军事威力,也凸显了数据管理的效率优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数据或数字化表达视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要件之一,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明确把数目字管理的采用与否视为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黄仁宇,1997)。 但在国家治理绩效的研究中,数字却从来都没有成为文明的判断标准。 当然,随着用数字来记录人类行为的方法与途径的不断增加,数据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日益凸显,未来的人们或许会把数据的使用当作一种文明升级换代的标志(Lazer,D.等,2021)。 但迄今为止,不仅在有关国家治理的讨论中,文字记载体现的对公平的追求以及道德内涵的重要性还是要远远超过数字与图画的记录方式体现的对效率的追求;而且数据应用技术发展本身遭遇的ChatGPT 困局也表明,仅仅以科学和理性作为治理工具的“现代文明逻辑”似乎遇到了致命的困境。①
一、 经济统计的治理测度历史背景
确实, 作为治理的技术基础,数据管理与经济统计几乎是与文明的探索同时出现的。 例如,《山海经》就记载了约40 个邦国、550 座山、300条水道、100 多位历史人物、400 多个神怪畏兽构成的图腾。 该书按照空间把这些临近族群的经济资源与族群结构一一记录下来,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第一个经济统计数据库(张岩,1999,2004)。 类似地,西方文明的起源同样伴随着相关治理数据的记载。比如,犹太宗教文献曾详细记载了早期祭祀过程中的贡品数量与种类,提供了神权政府治理的成本数量②。 而在英国崛起的过程中,治理数据收集与记录同样是其近代文明诞生的前提。 甚至可以说,正是税收基础数据库的构建奠定了英国工业革命坚实的治理基础——英格兰早在威廉征服之后就进行了全国治理资源的普查工作,其成果《土地调查清册》因其对现代英国的形成以及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被载入史册。
1940 年代,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要,原本服务于国家内部治理的数据搜集整理日益转向了旨在提高对外战争能力的国民收入核算。 同时,作为“政治算术”的治理测度也逐渐变成了作为“市场计算”的经济统计。 尽管有许多学者注意到这一转变的缺陷,也一直在竭力呼吁治理决策者应该予以重视 (贝淡宁和莫映川,2014;宋丙涛和潘美薇,2019),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这些呼吁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邱东教授是近年来少数几位试图从政治的高度对经济测度的治理本质与目标重新进行思考的国内学者之一。 在《基石还是累卵——经济统计学之于实证研究》一书中,邱东教授(2021)强调,统计工作是有关国计的国势学, 经济测度就是“政治”算术。 因此,邱东教授主张把统计数据的使用放在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进行宏观分析,而不要在现有的新古典范式中就事论事地进行微观争论。他呼吁计量经济学家不要在不了解数据来源与背景的情况下随意构建数学模型、得出经济结论、提供政策建议。
很显然,以邱东教授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已经围绕着经济测度应该有的政治自觉与需求导向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也为中国经济统计与治理绩效测度研究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但本文认为,这些学者提到的许多关键问题仍然没有在研究中得到充分阐述。本文尝试在这些学者的基础上,冒昧地就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作一延伸性分析,特别是试图强调政治决策与科学实证、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的主次关系,以求教于广大同仁。
二、经济测度的治理取向与政治内涵
(一)东西方治理模式的差异
与大多数经济学家把统计当作一种研究技术不同,邱东教授在研究中反复强调,统计是国家治理的学问,是一种国势学研究, 而不仅仅是经济研究的计量工具。 他强调,正是出于国家治理和国际竞争的需要,“国势学” 在近代欧洲应运而生,配第的《政治算术》正是定量的国势学,斯密的《国富论》则是定性的国势学。
不过,作为治理理论的国势学,其结论往往是不同的治理模式,并且不同的治理模式反映了不同的价值取向。 在东方,秦汉之后的国家治理基本上是儒法结合的模式,而希腊罗马以来的欧美则始终坚持法家式的治理模式。东方的儒法治理模式,以儒家理念为价值取向,以法家制度为治理工具,追求公共经济利益空间共享的天下一体治理目标。尽管并不完全排斥法家倡导的“富强”以及“法术势”等功利性观念,却只是作为实现儒家追求的“天下为公”之社会的辅助手段。与之相比,在欧美的法家治理模式中,法家的功利性观念不仅被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更是作为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③
在中国传统的国学或“国势学”中,治理目的是实现环宇之内万事万物之和谐。 由于认识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即“人”是“弘道”不可或缺的中介。儒家不仅赋予了“人”远高于其他事物的社会地位——人为万物之灵,而且秉持着“以人为本”的原则。此外,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价值取向的治理模式是“公天下”的模式,“公”指代的是全体社会成员之利益, 尤其是包含了弱势群体的“大公”利益。 这一治理模式由于以社会和谐与利益共享为目标(宋丙涛和潘美薇,2019), 深刻体现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 实际上,正是得益于儒法治理模式的践行④, 传统中国才能延续两千多年而不坠,并成为世界诸古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 从未中断的文明。
反观西方, 大多数的文明理念没有被传承下来, 而流传下来的希腊罗马文明却充满着利益竞争的战争气氛, 并导致了一千多年的“黑暗的中世纪”的文明断裂。 今天西方的治理或政治逻辑正是来自于古希腊的竞争思想, 主要是指为了城邦公民的利益进行斗争的技巧, 包括政治阴谋与辩论术在内⑤。 正是以此为基础,布坎南建立了公共选择学派, 并成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主流与“政治算术”的理论基础。因此,无论是在古代的希腊罗马, 还是在今天的西欧北美,对于那些精于利益算计的“政治”精算师来说, 对于那些把公职人员的自私视为理所当然的公共选择理论来说, 儒家的君子公心逻辑是无法想象的。其实,色诺芬早就知道, 只有牺牲雅典的利益才能解决希腊人的合作问题 (N.G.L. 哈蒙德,2016)。 但既要牺牲雅典的利益,也要牺牲雅典决策者个人的利益, 这样的政策与思想是希腊文明的创建者——雅典人没法接受的。于是,昙花一现的色诺芬的合作治理思想就逐渐被汹涌而来的亚氏理性逻辑与罗马竞争精神淹没了。
(二)治理模式与测度指标的内在联系
当然, 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的治理模式, 用以衡量治理绩效的测度体系也不尽相同。以儒家价值观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其测度体系贯彻着“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大公”中的所有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需求满足、且是长远利益的满足为衡量标准。以法家价值观为主导的治理模式, 其测度体系则体现着“功利主义”的原则,以“小公”利益的满足、 且往往是眼前利益的满足为衡量标准。
因此, 中国早期的政治算术就是德性实现程度的评价, 中国早期的治理绩效测度就是社会和谐水平的评价。比如,儒家指出的以“庶、富、教、均平”为核心的评价体系。 这套测度指标显然考虑了人类的全方位需求,人口繁盛是人的生命需求,富裕程度是人的物质需求, 教化水平是人的精神需求,均平则是人的社会秩序需求。对于儒家思想主导下的治理体系而言, 所谓的测度指标要服务于什么目标、 要测度什么是需要首先讨论的。 这是一个治理模式的选择,也是一个政治是否正确的判断。
然而, 西方的法家治理模式下的测度指标维护的是本国人的利益, 且是本国少数人的利益, 甚至只是本国中少数掌握着社会资源的强者的利益。因此,与战争能力以及经济总量等有关的竞争性指标会成为他们重要的关注点。
确实,在西方政治家的商战模型里,财富源于抢劫与商业,治理“基于商业繁荣和资本富足”,而道义的维持与利益的共享却根本不在他们的思考范围之内⑥。正是这些错误的治理理论, 奠定了二战后美国人构建的以战争能力为核心的、 以商业交易为基础的经济统计指标的基础。
事实上, 在西方, 从古希腊到大不列颠,再到美利坚合众国,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宪政革命, 其治理模式的本质都是战争与商业利益的结合。于是,所谓的“政治”算术其实都是小集团经济利益的算计,只是在商战的背景下披上了“政治”算术的外衣而已。甚至可以说,一部剑桥学派哈蒙德的《希腊史》几乎就是一部商战算术史:哪个城邦拥有多少收入,可以购买几艘战舰,可以装备多少重装步兵,最后落脚到“打一仗是否划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配第用国民收入帮英国的国王算战争账, 库茨涅兹用GNP 帮美国总统估算战争能力,就是西方用经济测度来代替“政治”算术进行外部扩张实力比较与排序的延续。
由此可知, 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实际上应该叫做国家经济核算。 而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是以生产者个体的收入为观察值,然后进行加总得出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总值。 正因如此,才有了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指出的人均GDP 不能反映差异与结构的社会正义质问。 但从西方“政治”算术的历史渊源来看,这些核算指标本来是评估国家战争能力的,本来就是某“政治”集团参与商战的利益算计,而不是全体居民的社会福利指数,因此政治学家对结构性的指责在原来的语境下其实是一种苛求。
(三)现有经济统计研究的“价值”缺陷
显然,东西方治理模式由不同的价值观主导,相应地构建了不同的测度指标体系。 而究竟是站在“小公”利益的立场,关注法家式的竞争性指标(如战争能力),还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聚焦儒家式的以人为本的指标(如秩序稳定),实际上是一个研究对象的选择问题。
以邱东教授为代表的国民核算体系研究者,尽管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但他们仍选择了近代欧洲的国势学研究作为起点。 这表明他们试图在法家的治理模式中讨论治理绩效测度问题。 特别是,对产业结构的讨论、 对贸易逆差的计算的关心,都表明了他们的思考确实是法家模式的延续,而不是儒家模式的重构。
例如,尽管邱东教授反复提到GDP 被称为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毋庸置疑,如果没有价值观的判断,如果没有政治算术中的“正确治理”的内涵正义性考量,GDP 确实可以和原子弹一起并列为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经济测度或许就是政治算术。 然而,邱东教授(2021:序)一再强调了这个“正确治理”的政治是不能被忽视的,并指出,“为了数学处理方便而将政治因素剔除,是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陷。 ”因此,邱东教授虽然关注到了统计背后的政治意义,却没有深究“政治”作为“正确治理”的特殊含义,因而对现代经济学的“价值中性”缺乏警惕性。
或许正是因为没有首先讨论测度对象,邱东教授往往把经济统计、治理绩效测度与政治算术混淆在一起。尽管邱东教授在引证荷兰的Mugge 教授和美国的戴蒙德教授等人的论述中,曾反复关注了经济测度的政治意义,但对萨科齐与OECD改进方案的福利测度指标可能会出现的“去政治化”“去政府化“倾向,以及国家治理内涵中的社会正义价值没有给予关注。以至于,在讨论经济统计研究的核心问题时,难免会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贸易顺差等竞争实力的争端上。
确实,当邱东教授(2021:112)把德国教授赫尔曼·康今的“国势学”课程作为世界经济统计学的出发点时, 他正确地指出,“论学不能不数典,更不能数典忘祖。 ”但讨论“国势学”仅仅从赫尔曼·康今与威廉·配第出发,却忽视了在我们的祖先中,管仲、商鞅、韩非子等都对“国势学”有着重要的贡献,甚至其贡献与学术价值都远远超过了康今与配第的研究。
(四)治理绩效测度的价值内涵
事实上, 从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看,测度理论的基础是分类学,而分类的目的是人的需要。 由于法家的目标是战争的胜利, 以此为据的测度体系就是战争能力的评估,二战后期出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是这个治理目标的准确反映。 但儒家思想更为关注人群的和谐相处,因此,我们认为,以人为本的儒家思想才是现代文明的思想渊源,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为核心的人本思想才是全球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当然,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表现为价格的价值指标其实也是一种需要分类的方式。因此,学者(邱东,2021)对西方谚语“不能将苹果与橘子加在一起”的借鉴,就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 因为, 对人类的需要而言,根本不存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在中国古代的治理理论中, 不仅金木水火土可以相生相克, 而且还因为他们与人的需要密切相关而被放在一起进行测度比较。于是针对“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的测度难题,中国古人早就提出了“一寸光阴一寸金”与“才高八斗”的替代变量测度比较办法。因此,对于“不同物量各异,其实不可直接测度和比较”的难题,只要从人的需要出发,就能找到比较与测度的切入点。
或许,正是因为没有注意到,统计的正确性要求,今天的部分经济学家仍在把“小公”内部的个人福利作为自己的目标,而不关心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的构建。事实上,在命运共同体内部, 不同人的公共产品需求是互不相同且互相竞争的。比如,所谓的“希腊民主政治”,其实就是拥有“公民”身份的局部人对自己利益的特殊保护机制。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一个所谓的“机会均等原则”,很可能就是在所谓的“公平”原则掩护下去追求个人私利的强势集团的政治诉求。
相反, 周孔之道的治理原则就是公心精英的君子逻辑。 而文明的演化历史又告诉我们, 只有这样的以人为本的文明才能演化,只有这样的治理才是正确的治理。如果我们的治理绩效测度是为了人类文明的延续而构建知识和数据, 如果我们的政治算术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特别是要包含弱势群体的幸福)而参与治理,和谐共处与以人为本的原则就是国家治理的第一原则,也是绩效测度的第一原则。 ■
注释:
①任剑涛教授(2023)在谈到ChatGPT 带来的危机时指出,“在ChatGPT4 发布之前,人类担忧程度相对较低;其发布以后,人类的担忧陡然增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担忧, 是因为以西方的知识体系为主导的人类知识主要依赖于科学与理性, 但相对于同样理性又不会犯错的机器人, 人的理性就没有了优势。
②“公元前515 年3 月,祭司们兴高采烈地为第二圣殿奉献了一百头小公牛、 两百只成年公羊、四百只羊羔和十二只山羊(以赎十二个部落的罪)做祭品。 ”(西蒙·蒙蒂菲奥里,2015:59)
③需要指出的是, 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在中国表现为农战体制(主要是大秦帝国),在西方则表现为商战模式(早期的希腊罗马与近代的荷兰英国),二者的区别在于战争依赖的财源不同。
④一方面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超越小群体的狭隘利益,以广博的胸怀接纳异族、异国的民众;另一方面则善于使用“立竿见影”的法家治理理念作为辅助手段。
⑤相反, 孔子认为,“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
⑥汉密尔顿等(1980:15)写道,“事实如此,不管这是人性的多大耻辱, 一般国家每当预料到战争有利可图时, 总是要制造战争的。”笔者认为,这只是欧洲人、雅典、罗马、英国、美国的人性观,东方的儒家有不同思想,儒家要改造人性,带来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