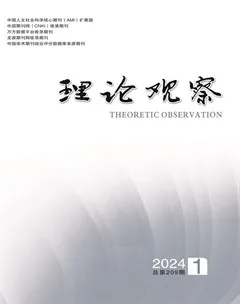两汉至两宋:“精舍”之源流考辨
2024-05-17朱晨鹭
朱晨鹭
摘 要:“精舍”本是《管子》中所提及的安定内心的一种修行方式。到了汉代,“精舍”成为了儒生自立的书斋,供其著书立说、讲习儒经。在不断地发展和演化中,形成了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代表具有佛教性质的精舍和唐宋时期的世俗化精舍,之后这一概念逐渐定型。通过对两汉至两宋这一历史时期内“精舍”一词在文献中所表现出的概念与涵义进行释义、考证,考察其从两汉至两宋在中国社会中释义的变化,辨析不同历史时期内其性质、概念的差异探究,从而反映两汉至两宋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
关键词:精舍;儒学;佛教;世俗
中图分类号:K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1 — 0080 — 05
“精舍”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一书中,《管子》云:“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敬除其舍,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1]卷16管子所阐述的,是一种心灵的修行方式。一個人内心安定,便能达到耳聪目明、四肢坚固的效果,此人的身体便可成为留住“精”的地方。《管子》一书受道家思想影响极重,所谓“精”,就是指精气,道家认为“精”乃生命之本源。精气通达便可产生生命,继而产生思想与知识。可见,精舍在最早呈现出的,是一种内心修行后达到的饱满状态。“斋者,其书院精舍之别名乎。”[2]卷17《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中,将精舍归为“斋”,而“斋,谓夫闲居平心以养思虑若于此。”[3]卷8因此,斋是用来修养身心,以达到“洁”的场所。“斋”与“精舍”所表达的意思属同一层面。这一概念在两汉时期得到实化,成为儒生讲经说法、研习经典的场所,被赋予了强烈的儒学意味。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文化模式的转变,精舍一词又呈现出不同的涵义,到宋代基本定型。关于精舍之释义 ,学术界已有相关讨论,但多从书院与精舍的对比角度着手。①本文主要基于两汉至两宋这一时间段,广泛收集资料,分析不同文献、不同语境中,精舍概念的演变,考证其源,辨析其流,总结精舍在不同历史时期内所表现出的特征,以期反映其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两汉:“精舍”的儒学化时期
两汉“精舍”这一概念被实化,使其真正地成了修身养性、研习经义的场所。东汉人王阜,“少好经学,年十一,辞父母,欲出精庐。”[4]卷13,512这里的精庐,当指王阜家中之书房,专供其读书修养;郑玄曾求学扶风马季长,季长自恃为后戚,为人傲慢,郑玄不得见,只好住在其居所旁,“自起精庐”。[5]卷上
《华阳国志》中也提到西汉时期的文翁在蜀地担任郡守期间,为诱导教化、改进野蛮民风,“立文学精舍讲堂”。[6]卷3承宫为西汉时人,因为少孤,替人牧豕,“乡里徐子盛明《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其庐下,见诸生讲诵,好之,因忘其猪而听经。猪主怪其不还,行求索。见而欲笞之。门下生共禁,乃止,因留精舍门下。”[4]卷14,541—542徐子盛的精舍,是他用来给乡里讲授经学的场所,带有明显的私学色彩;《后汉书·姜肱传》中提到这样一则故事:姜肱与弟弟一起渡江去拜谒郡守,在途中遇到强盗,兄弟二人争相赴死,感动了强盗。最后只取了他们的衣物,并未要他们性命。之后郡守询问起来,姜肱只是托以它辞,不供出强盗。最后“盗闻而感悔,后乃就精庐,求见征君。”[7]卷53,1749 史料中所言“精庐”当是其修学研经之所;《风俗通义》中记载了陈国人张汉直跟随廷叔坚研读《左传》,有一鬼魂侵扰其家人,家人前往南阳寻找他,“去精舍数里,遇汉直与诸生十余人相随”[8],此处的精舍,也应该是廷叔坚汇集门人、讲经修读之所;此外,东汉桓帝时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这些文献
中所提到的精舍,就是带有讲经、授课的私人讲
堂。[7]卷67,2190
精舍亦称“精庐”。东汉光武中年之后,国家太平,经学渐起,时风日盛。“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7]卷79,2588承担弘扬一家之说的作用。
两汉时期,修建精舍的最初目的并不在于讲学,而是儒士文人为了潜心读书、修身养性而筑建的私人活动场所,而其教育的职能,则是伴随着这些精舍在地方上影响力的扩大而逐渐形成的。
二、魏晋南北朝:“精舍”的佛教化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精舍一词被赋予较强的“佛教”特征。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于魏晋得到了迅速发展。由于颇受统治者支持,魏晋时期的佛教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在此文化背景下,精舍的概念也不再单纯地停留在儒学阶段,进而被饰以浓厚的释家色彩。
译经是魏晋佛教传播的主要方式。《华严经》《楞严经》《阿弥陀经》等佛家经典,均在这一时期被译出并广泛传播。精舍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被运用到佛家语境中。法祖帛远曾在“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9]卷15,559《出三藏记集》中在记载慧远法师时,曾说“远创造精舍,洞尽山美……营筑龛室。”[9]卷15,566—567并与“息心清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于精舍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9]卷15,567这一时期,精舍与寺庙概念基本等同,在文献中也常出现并用的情况。如刘宋时期的建康枳园寺,东晋车骑将军王邵敬佩当时得道高僧智严,想让他搬迁到京城,因智严不喜喧闹,于是“于东郊之际,更起精舍,即枳园寺也。”[10]卷3,99同样情况的还有新亭寺,东晋孝武帝在高僧竺法义圆寂后,“买新亭岗位亩,起塔三级,义弟子昙爽于墓所立寺,因名新亭精舍。”[10]卷4,172《水经注》载,清水之上,有比丘释僧训所立精舍,“寺有十余僧,给养难周,多出下平,有志者居之。寺左右杂树疎颁。”[11]卷9,225这里的寺便指代精舍。天竺僧伽罗多,元嘉十年在钟阜之阳造立精舍,即“宋熙寺”。[10]卷3,129类似于这样“精舍”与“寺”通用的例子在魏晋南北朝文献中不胜枚举。《释名》对“寺”有如下解释:“寺,嗣也。治事者嗣续于其内也。”[12]卷5说明在当时汉地的佛教精舍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与管理职能。而精舍与寺释义的互通,则是这一时期译经的结果。
汉地“佛寺”一词来源,应是佛国的“伽蓝”。在早期的佛经中,“精舍”与“伽蓝”二词存在细微差别。伽蓝之梵语为samgharama,意为僧众共住之园。法显也释伽蓝为“众僧住止处”[13]3,居住、研经为其主要功能;而精舍之梵语为vihara,毗诃罗,意为僧坊,一般指有佛像或者佛骨陈列处,供奉、祭拜是其主要功用。早期的佛教徒在修行过程中,常常居无定所,只临时搭建住处亦遮蔽风雨,后人便在其遗迹或尸骨之上建立精舍。佛经中频繁出现的“衹桓精舍”[14]卷10,又叫祇苑,是佛教最早的精舍之一。《佛国记》中对祇洹精舍有一段较为完整的记载:
精舍东向开门,门户两厢有二石柱,左柱上作轮形,右柱上作牛形。池流清净,林木尚茂,众华异色,蔚然可观,即所谓祇洹精舍是也。佛上忉利天为母说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见佛,即刻牛头栴檀作佛像,置佛坐处。佛后还,入精舍,像即避出迎佛。佛言:“还坐,吾般泥洹后,可为四部众作法式。”像即还坐。此像最是众像之始,后人所法者也。[13]3
可知,由于波斯匿王想要见佛,专门营造佛像以示寄托,故而有此精舍。再如醯罗城中的“佛顶骨精舍”,国王担心精舍中佛骨被人抢夺,令国中八位豪姓之人,每人持一印,每出佛骨,需要八人同时开启精舍迎取;[13]5无忧王之弟在王宫之侧建佛牙精舍,“以众宝庄严,上建表柱,以钵昙摩罗伽大宝置之刹端”,旁又有一精舍,“中有金像”[15]卷4,89;也有为法器而专立的精舍,如那竭国中的佛锡杖精舍。[13]5更多的则是如祇洹精舍这样的供养佛像的处所。一些规模较大的精舍一般“至斋日,则开门户”[13]20,而普通精舍则专供民众供养祭拜,门口“朝朝互有卖华香人,凡欲供养者,种种买焉。”王国之间也常常互相出资供养精舍。[13]5可见,佛教早期精舍的特征,首先其建造的原因大多是有佛或早期高僧活动的痕迹,其次便是其中有可供奉之物。后来,国王或商人往往会出资修建精舍赐给僧侣居住,如波斯匿王之妾曾为比丘尼作精舍[14]卷22,也有一些虔诚的信奉者自建精舍,请佛陀或僧侣居住讲经,于是精舍与伽蓝的功能便逐渐合二为一了。法显对中天竺国的一段记载,大致可以看出“佛国精舍”的基本形态。
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众僧住止房舍、床褥、饮食、衣服都无缺乏,处处皆尔。众僧常以功德为业,及诵经坐禅。[13]5
且精舍中的比丘、比丘尼、沙弥、昙师、律师都有各自要朝奉的尊者。这些精舍受到国家的支持、民众的信奉,有固定的僧侣和土地。无忧王曾奔那伐弹那国城西建跋姞婆伽蓝,“台阁壮峻,僧徒七百人”,傍一精舍,“中有观自在菩萨像,至诚祈请,无愿不遂。”[15]卷4,81—82还有建那补罗国王宫城中之大伽蓝,“僧徒三百余人,并博赡文才。其精舍中有一切义成太子宝冠,高减二尺,盛以宝函,每到斋日,出置高台,其至诚观礼者,多感异光”,城侧另有一精舍,“中有刻檀慈氏菩萨像,高十余尺,亦数有光瑞”。[15]卷4,90引正王为龙树菩萨在黑蜂山建伽蓝,在诸精舍中各铸金像。[16]卷6这里的精舍与伽蓝明显是包含关系,精舍在此期已作为伽蓝的一部分,不再是专供圣物的独立场所。伽蓝与精舍皆有僧侣居住的意思,但二者的差异在于,精舍在发展的早期更强调独立性,往往是高僧自行修行或生活之地;而伽蓝最早则是僧团聚集之地,经过不断地发展壮大,逐渐成了包含佛像、僧舍、经堂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单位,即寺庙的形态,而其中供奉佛像的精舍便是其主体。
故在译经过程中,vihara一词被中原高僧译为“精舍”,主要是源于其特性与汉文中的“精庐”有异曲同工之妙,皆强调了最初修行状态的独立性。而后逐渐成为寺庙的代称,则是因为在佛国,伽蓝与精舍的形态在逐渐发展中已融为一体。
除此之外,魏晋时期亦有少量的道士精舍。树木丰茂、危崖飞泉之侧,“多结道士精庐焉”。[11]卷32,753寿春县故城北,有一“陆道士解南精庐”,“临侧川溪,大不为广,小足闲居,亦胜境也。”[11]卷32,750枝江县东南有“道士范侪精庐”[11]卷34,795;孙吴有道士琅琊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17]卷46,1110陶弘景记录了南朝宋初,长沙景王在茅山建道士精舍之事,梁天监十三年该精舍改名为朱阳馆[18]卷下,50;陶弘景弟子張子良,其姨母“十岁便出家随师学道”,“立精舍”。[19]卷3,91魏晋时期亦是道教发展成型的重要阶段,故道士立精舍修道也是普遍行为,只是数量、规模上无法与佛教精舍相提并论。
由此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以来形成的以儒家讲学为特点的精舍,基本已进入了佛教的语境,成为以研习佛典、供养佛教神祇、供佛教徒修行的宗教场所。在这一时期,由于精舍较强的佛教意味,精舍一词的儒学功能似乎在佛学的热潮下被掩盖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是精舍的概念及功能变得更为全面、多元的表现,也是唐宋时期精舍释义“世俗化”[20]的基础。
三、唐宋:“精舍”的世俗化时期
自魏晋以来形成精舍的佛教面貌对唐宋两代影响至深,唐代甚至还出现了“御史台精舍”。[21]卷139唐代御史台中设有台狱,狱内设有精舍,供犯人忏悔。北宋的文献史料中也常将精舍与佛寺混用。与此同时,唐宋时期的社会文化给予了精舍新的内涵。
(一)祭祀、宗教性质的精舍
上文提到,佛教精舍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其中有可供奉之物,也就是其祭祀功能。唐宋时期,带有祭祀、宗教性质的精舍便是由这一观念发展而来。
多数情况下,唐人语境中所谓“精舍”,便是寺院之意,这是魏晋时期精舍“佛教化”的延续。白居易、韦应物、李白等都在大量的诗歌中,提到精舍,韦应物是一位佛教信徒,他的诗歌经常以佛寺、
精舍入题。如《始除尚书郎别善福精舍》[22]卷5,231、《春月观省属城始憩东西林精舍》[22]卷8,382、《游开元精舍》[22]卷9,454等。白居易有诗:“我爱此山头,及此三登历。紫霞旧精舍,寥落空泉石。朝市日喧隘,云林长悄寂。犹存住寺僧,肯有归山客。”[23]卷8这里的精舍显然是指山中小寺;《唐阙史》中也称青龙寺为“青龙精舍”。[24]卷下除讲学、修心外,精舍也可供旅人借宿。《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贞元初年游子木师古夜投古精舍的故事,“主人僧乃送一陋室内安止。”[25]卷472温庭筠有诗名曰《宿辉公精舍》,记录夜宿山中禅房的景象[26]卷8; 诗人贾岛曾寓居“延寿里精舍”。[27]卷1
与此同时,唐宋时期的道家精舍也在不断发展,并逐渐推广成为习惯。如茅山西侧之祠宇宫,为唐天宝年间修,专“立精舍度道士焚修”[28]卷45;南宋时期,西湖之畔的葛岭之上,有一道教精舍,用以纪念“葛仙故迹”[29]卷10;《册府元龟》载,句容人许迈,少好学道,在余杭悬霤山上立精舍修炼。[30]卷809
除此之外,在唐宋两代,一些公祠、生祠也被称为精舍。《舆地纪胜》记载王明因对豫章民众有恩德,民众“图其像于上精庐以祠之”[31]卷26;宣和年间,刘忠显公由于护国有功,朝廷便在其立功业之地
立“圆通精舍”为其祠,绘像于其中,供邦中人共奉祀[32]卷32;宋末遗民谢翱终身不仕,避世于浙东,卒后其徒吴贵“买田月泉精舍”[33]卷6作为其供祀之地。
(二)文人、隐士精舍
除带有祭祀、宗教性质的精舍外,唐宋时期的文人、隐士都致力于自建精舍,作为其读书、隐居之地。尤其到了宋代,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许多学者逐渐在佛教思潮的笼罩下解脱出来,纷纷在文章中为“精舍”正名。“若其精舍以府寺名之,亦非天竺之本名。盖始出于汉,有司梓匠之后遂同乎府寺而得名焉。”[34]卷16“今有儒家字为佛家所窃用,而后人反以为出于佛者,如‘寺‘精舍之类,不一。”[35]卷126《韵语阳秋》也曾指明精舍之本义,“晋孝武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沙门居之,故今人皆以佛寺为精舍。殊不知精舍乃儒者教授生徒之处。”[36]卷13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之上,唐宋时人纷纷自立精舍,作为书斋。王旦之孙王巩,在山林僻静处“立精舍,日夜著文”[37]卷53;南宋学者欧阳守道为自己隐居之地命名“寻乐精舍”[38]卷26,724,旨在找到孔颜乐处的愉悦与平静;陈傅良也为自己构建读书精舍,写诗称“森森万木一精庐,黄卷青灯自卷舒”[39]卷7;南宋大臣朱权于颜公山上筑精庐观,“手编诸家易说凡百余万言”。[40]卷11一些文人精舍产生了教育职能,精舍主人常建书堂,聚生徒。一些乡绅于郊外创置精舍,教授附近子弟读书。如欧阳守道笔下的“学礼精舍”。[38]卷25,710其中的一部分在后期逐渐发展成了书院,这是宋代较为特殊的现象。但这样的精舍并不等同于书院。张惠芬指出,较之书院,精舍一般不具备书院式的讲堂、藏书、祠宇,且在行政管理系统上与朝廷及州府不相干,具有较强的个人性、私立性。[41]
(三)山居、别业
除宗教、学术外,唐宋时期的精舍兼具休
闲功能。李德裕曾为自己所居之精舍撰《二芳丛
赋》[42]卷2,523,他的精舍便是建造在山林之中的一处小宅;另有《牡丹赋》道:“今京师精舍甲第,犹有天宝中牡丹在。”[42]卷9,693此“精舍”则有精美府邸之义。到宋代这样的现象更为普遍,北宋人韩子苍在郊外弃官养疾之地叫做“同德精舍”[43]卷9;林端仲于其居前筑精舍,身患疾病时,便前往单独居住,斋戒清洁,修身养性[44]卷38;南宋人壶山居士长年辟居于山林宅斋中,其斋名为“簾庐精舍”[45]卷357;另有寿康精舍、光严精舍、松泉精舍等都为唐宋时人在郊外或山林之中创置的别居,专供其修养、休憩。
唐宋文献中甚至出现了“守坟精舍”[46]卷3,7128、“墓道精舍”[46]卷3,7131,大多是时人在双亲守孝期间临时搭建的住所。可见,该时期精舍的涵义已日趋日常,每种功能之间的界限也不再那么明显。这是符合唐宋时期世俗社会发展的特征的。内藤湖南提出,唐宋之际,中国文化的转向呈世俗化、平民化趋势。[47]世俗化意味着文化的多元特征,唐宋時期精舍一词在宗教、学术、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四、结语
“精舍”一词,究其根源,是指一种隔绝外物、平心静气的修行状态,原本只是一种抽象的精神概念。两汉时期,伴随着儒学的兴起,精舍的概念被实化,成为儒生研习经典、著书立说的场所。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佛教的兴盛,精舍进入到佛家语境中,成为僧侣共居、钻研佛法、供奉神祇的宗教场所,常常与“佛寺”“寺院”等词混用。汉地精舍与早期的佛国精舍在形态上有些许的不同。佛国精舍一般指供奉佛骨、佛像或佛迹的场所,具有较强的祭祀功能,后随着功能的不断加强、规模的不断扩大,逐渐成了集祭祀、研经、居住为一体的僧伽蓝的形态。魏晋时期的高僧在译经过程中,将这样形态的场所译为精舍。唐宋时期,精舍一词基本已经包含了前代形成的所有概念,一方面,其祭祀、宗教性不断发展,不但兼容了佛道二教,连一些生祠、公祠也被称为精舍;另一方面,其儒学性亦得到了充分发挥,逐渐形成了文人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的书堂,并在此基础上慢慢形成了书院。与此同时,唐宋时期的精舍还包括时人修建的山居别业、守孝时临时搭建的住所等。可以说,精舍一词的概念在唐宋时期形成了多元化、世俗化的特征。
从两汉至两宋,精舍一词概念的演变和发展,大致表明了这一历史时期内的文化走向。两汉是中国历史上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是儒家撰写经典、学术争鸣的开端,精舍的概念在这一文化推动下,注入了浓厚的儒学元素;魏晋南北朝是政治、文化的大分裂时期,随着儒学体系的式微,知识阶层及普通民众开始寻求一种更为开放、柔性的社会文化,佛教便在这样的环境下迅速发展,广为流行,这是促进精舍一词佛教性质的根本原因;唐宋两代是文化多元发展的重要时期。从宗教角度来看,唐宋两代包容的社会氛围为释、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学术角度来看,唐代中后期的古文运动以及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运动直接推动了中国历史上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即宋代理学的兴起;从生活角度来看,宋代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以及新兴的市民阶层,更是促进社会朝世俗化、生活化方向发展。在这样的文化感染下,精舍一词亦展现出了世俗化、生活化的多种面相。
〔参 考 文 献〕
[1]房玄龄,注,刘晓艺,校点.管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28.
[2]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
[3]祝穆.古今事文类聚[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25.
[4]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常璩.华阳国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33.
[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409.
[9]释僧祐.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0]释慧晈.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1]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刘熙.释名疏证补[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3]释法显,撰.佛国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4]四分律[Z].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15]慧立,彦棕,著,孙毓堂,谢芳,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6]释玄应,释慧琳.一切经音义[Z].狮古白莲社刻本.
[17]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10.
[18]陶弘景,撰.华阳陶隐居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50.
[19]陶弘景,撰.周氏冥通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91.
[20]李弘祺.精舍与书院[J].汉学研究,1992(02):316.
[21]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2211.
[22]韋应物,撰,孙望,校笺.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3]白居易,著,岳喻衡,点校.白居易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112.
[24]高彦修,撰,阳羡生,校点:唐阙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348.
[25]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6]温庭筠,撰,刘学锴,校注.温庭筠集全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687.
[27]贾岛,著,黄鹏,笺注.贾岛诗集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2:24.
[28]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M].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2068.
[29]潜说友,修纂.咸淳临安志[M].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3447.
[30]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9415.
[31]王象之,撰.舆地纪胜[M].北京:中华书局,1992:1175.
[32]史浩,撰,俞信芳,点校.史浩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59.
[33]谢翱,撰.晞发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9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53.
[34]晁说之.嵩山文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34:446—447.
[3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3026.
[36]葛立方.韵语阳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3.
[37]周必大,撰.文忠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561.
[38]欧阳守道,撰.巽斋文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
[39]陈傅良.止斋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551.
[40]程珌.洺水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382.
[41]张惠芬.论宋代的精舍与书院[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01):34.
[42]李德裕,撰,傅璇宗,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18.
[43]赵与时,著,齐治平,校点.宾退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20.
[44]黄榦.勉斋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450.
[45]佚名.壶山四六[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357.
[46]张淏,纂修.宝庆会稽续志[M].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47]内藤湖南.东洋文化史: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M].林晓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包 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