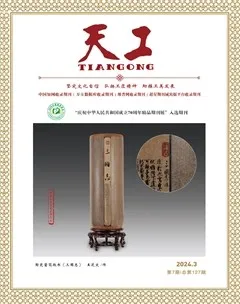庞薰琹工艺美术思想的形成
2024-05-17陈驰
[摘 要]庞薰琹是我国早期工艺美术教育家、中国现代美术的先驱。抗战时期庞薰琹在贵州地区的艺术探索对其工艺美术教育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抗战时期,他开始重新审视民族传统艺术,深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和实践,发掘民族民间艺术的资源,认识到民族民间艺术丰厚的思想内涵和创造精神,改变了他对民族艺术的理解,形成了以人民的喜爱和需要为宗旨的民族民间艺术思想。
[关键词]抗战时期;庞薰琹;美育思想;民族艺术
[中图分类号]J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556(2024)7-0094-03
本文文献著录格式:陈驰.庞薰琹工艺美术思想的形成:以1939—1940年贵州地区考察为核心[J].天工,2024(7):94-96.
抗战时期,学术界掀起了探索“民族形式”的思潮,艺术家从各自的角度回答如何基于传统建构现代美术的问题。庞薰琹深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探索,场域的变化给他带来了心态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在逐步了解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的过程中,他从积极探索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作风逐渐转为关注人民的生活需要。这段考察对他后来从中国传统艺术出发探索中国现代艺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我们分析中国传统艺术的当代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视域转变:关注民族传统艺术
在民族救亡的时代语境下,庞薰琹留法归国后,从艺术的自我表现意识转变为关注社会生活、关注民族传统艺术。在20世纪30年代留法时期,庞薰琹在法国遇到一位权威的艺术批评家谈论到中国有着优秀的艺术传统,鼓励庞薰琹回国学习中国传统艺术。[1]这件事为庞薰琹探索民族传统艺术奠定了基础。他归国后便开始关注“民族性”与“装饰性”的问题,随后建立了一个颇有朝气的中国现代美术社团——决澜社。决澜社首次画展后,他提道:“我回国的主要目的是想研究我国的艺术传统,回国后只是看了一些书,根本还不了解什么是我国的艺术传统。”[2]
1938年,与庞薰琹同在北平艺专的王曼硕等一大批同事和学生前往延安,庞薰琹和20世纪初的大多数艺术家一样受到抗日救亡思潮的影响,自觉关注起中国文化存废问题,他意识到艺术不仅是表现自我,还应与时代背景、民族兴亡结合起来。庞薰琹对民族传统艺术的广泛研究是在抗战大后方的昆明时期。他在昆明时期接触了大批文化艺术学者。在西南联大时期,文学家沈从文先生曾将他收集到的土家族挑花布摆满一屋子邀请庞薰琹去看。沈从文先生和庞薰琹相交甚好,他此时正出任西南联大教授,极力鼓励庞薰琹研究中国传统艺术。[3]同时庞薰琹得到陈梦家、闻一多、杨振声等专家学者资助,借阅大量中国古代文化书籍。铜器以及相关的书,使庞薰琹产生浓厚兴趣,并边读书边收集、描绘纹样。他认识到祖国的文化遗产如此丰富,开阔了民族艺术的研究视野,他以装饰性的眼光去探寻祖国的民族文化艺术。他说道:“祖国的文化如此丰富,越来越感到只会画几笔画,那就太狭窄了。作为一个中国美术家来说,认识祖国的文化遗产,确实是必要的。”[4]
庞薰琹经梁思成、梁思永兄弟介绍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9年9月,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派遣,庞薰琹与民族学者芮逸夫深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贵阳、安顺、龙里、贵定四县的苗族村寨六十余处,收集标本,并选择服饰纹样制成图片。[5]抗战以前,贵州受到外界影响较小,而贵州的少数民族由于多居住在山区,仍保持着原始的民风民俗。20世纪30年代,普通大众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认知较少。但庞薰琹说自己本身就对少数民族艺术传统感兴趣,于是决定先深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6]这三个月的探索对他后来的美育实践与美育思想的确立具有深远的影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纯净的人文自然具有润泽人心的功能。特别是对于庞薰琹来说,刚经历上海时期的紧张局势、生活处境的窘迫,到了抗战大后方的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场域的转变给庞薰琹带来心灵上的抚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艺术为他打开了新视野,贵州苗族服饰纹样高超的艺术性和多元性,使他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有了新的认识。
二、观念转变:关注人民的喜爱和需要
庞薰琹通过“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来解释其艺术理念,他指出“宗”就是人民的爱好和需要,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以及文化和艺术传统。时代、社会是不断变化的,在这千变万化中有本质的规律,即人民的喜爱和需要。
在考察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前,庞薰琹请教了梁思成先生,他一再叮嘱:要尊重各民族文化,搞好民族间的关系,不能为把资料弄到自己手里,采取骗、偷、抢种种手段,而不顾对方的风俗习惯。[7]在逐渐深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过程中,他们始终秉持这条原则。对于少数民族艺术传统,避免采取猎奇的眼光,逐步发掘少数民族单纯、善良的内在美。“当地土著居民的歌舞和淳朴的性格、健壮的体格、欢快自立的精神,极大地吸引了庞薰琹。他在贵州山区做过几个月的旅行。在此期间,他与苗族人民关系融洽,颇有情谊。”[8]考察期间,在安顺时有一位苗族朋友为他们领路,从一个寨子送到另一个寨子,确保了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少数民族单纯、善良的品质提升了庞薰琹对真善美的认知,促进了他对民族传统艺术的多元性认识。“极大多数中国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是淳厚的,在生活上始终保持着朴实勤劳的习惯。他们所喜爱的东西,正符合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他们喜欢朴实、淳厚的表现形式。这种朴实淳厚的表现形式,正是民族美术中的优良传统,他们不单有这种喜爱,而且在民间艺术上就充分表现了这种思想感情与表达形式。”[9]他们淳朴、坚韧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些优良传统恰恰是构成民族形式的精神基础,经过长期积淀,运用于民族艺术创作中,且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基于对实际生活的细致观察,随着生活的发展而发展。
庞薰琹以装饰性的眼光看待少数民族艺术,深刻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少数民族艺术来源于他们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朴实勤劳的品质。贵州的苗族仍然保留着原始的生活习俗,包括对自然最原始的一种崇拜,具体表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中,赋予其象征性的意义,蕴含着民族的個性、创造性,反映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等。“每个苗族妇女,从七八岁起就要学挑花。绣啊,绣啊!一绣多年,绣了头巾绣花边,绣了护背、胸带再绣绑腿,费工费线,还要在劳动之余绣。为省灯油,有时要在月下绣。”[10]绣衣不仅仅是她们一针一线亲力亲为,更是寄托她们情感的珍贵之物。“反映在工艺装饰中的动物形象,是蕴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表现着一定的哲理意念的艺术形象……动物题材的装饰,画的是动物形象,表达的是人的思想感情。人的思想意识是随时代的发展而演变的。我国几千年来的动物图案都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各地区和各民族的民间装饰艺术也各有自己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11]庞薰琹关注到里面的精神内涵,领略到中华民族的个性。这种强烈的个性便是民族形式的精神基础,这种精神使得少数民族一直延续至今。
少数民族艺术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基于对实际生活的细致观察而形成的。每个时代的少数民族艺术呈现出不同特征。“一九三九年,我在贵州安顺苗族地区过春节,正月初一到初三三天,每天总有几十个姑娘,坐在寨子外山坡太阳下绣花边,这些花边我几乎都看过,风格是苗族的传统,但是所绣花纹没有相同的,人人都在创新……在她们的作品中,传统与创新结合得很好,这样结合是出于自然的结合,它来之于生活,直接又为生活服务。”[12]少数民族的生活劳动在庞薰琹的眼里构成了一幅多彩的生活画卷,在他的记录下,苗族人民尚美的一种心态,她们的手工绣花,对新花样的追求,这些都表现了她们代代传承的民族美学和民族艺术传统。“这些山里姑娘,没有什么绘画基础,更没有受过什么专业技术的训练,百分之九十以上没有出过那个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姑娘没有上过学……因为她们尊重自己的劳动,爱惜这些布,这些线,因为都来之不易。这种群众中潜在的艺术智慧,对我触动很大。从那时起,我逐渐摆脱个人名利的追求,我决心要想尽办法为群众多做一点有用的工作。”[13]她们熟悉自己的生活,就地取材,创作出自己喜爱的东西,这也是她们一直传承几千年而屹立不倒的优良传统。
民族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自然。少数民族人民把自己对自然的想象、对生活的期盼融入艺术创作中,形成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精神基础,支撑他们一直走到今天。
在抗日救亡背景下,艺术界对民族形式的探索有不同的观点和做法,而庞薰琹在深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过程中不断感受、不断理解,发现少数民族独特的个性,这种个性是民族美术中的优良传统,是民族形式的精神基础。生活中的美育是终身的美育。庞薰琹在观察与体验中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审美经验,对探讨抗战时期的中国美术具有重要意义。
三、思想转变:民族传统艺术的精神创获与启示
经过三个月的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后,庞薰琹开始反思现实,反思新美术。只有立足于传统,才能赢得国际地位。他关注到民族艺术的深层内涵,民族美术的优良传统正是人民大众思想感情的隐性表达,通过生活用品等实体的方式表达出来,进一步影响和改造他们的生活。“文化是劳动积累,我们不能设想没有稳实的基础,而能在平地里起高楼,文化也是如此,抹煞传统,而想凭空创造新文化是不可能的,文化的传统必须继承发扬,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在好的基础上再求好,逐步做到尽善尽美,这样文化才能上升,才能发展。”[14]
关注人民大众的需要,并以人民大众的喜爱作为宗旨。晚年时期,庞薰琹在一次装饰绘画班的讲话中提到包豪斯的时代早已过去。他意识到决澜社时期的艺术没有密切结合群众,缺乏对民族生活的关注。庞薰琹在1944年对决澜社时期的回忆中谈道:“就因为‘决澜的旧宗旨已不适宜暴风雨的前夕。‘决澜解散了,‘决澜的社员分散到各地去踏进各种生活。希求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民族,以备建设一个新的民族。”[15]这里的“旧宗旨”我们可以结合当时的中国,他们这样一批欧洲艺术的追随者并不能被当时的群众理解和认识,甚至是脱离了当时的客观现实。由此可以看出,他在深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以后深刻认知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以及人民群众的智慧。
启发人民的思想,发扬爱国精神。“在老庄思想中,装饰艺术的境界最终归于一种‘道的存在,也就是说装饰的作用不只是体现在物质生活方面,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超越现实功利和物质累赘之外的精神自由是老庄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16]从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精神出发探索与现代艺术的联系,探寻人与社会自然的发展,他主张:“工艺美术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满足人民物质生活方面的需要,同时也为人民精神生活提供支持,培养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艺美术设计人才。”[17]工艺美术工作者在原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群众喜爱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与发扬原有的传统,教育群众,启发群众。我国几千年来受到封建统治的压迫,后来又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他要以人民大众所接受的,来自民间的工艺美术所带有的朴实的风格,来肃清消极影响,发扬群众的爱国精神。同时他认为要把中国传统艺术和西方艺术的长处结合,找出一条新路来。
貴州的考察对庞薰琹的影响极大,对民族精神、文化和艺术传统的发现和挖掘贯穿着他之后的艺术道路。亲眼见过和亲自经历过战争的残酷,见过无数的劳苦大众,不管是抗战前线还是抗战大后方,庞薰琹及他们这一代人怀着热忱的爱国之心,满怀热情地为人民幸福而奋斗。这也是贯穿他一生的思想。
参考文献:
[1][2][3][4][6][13]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96,135,161,162,181,192-193.
[5]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集刊12[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4.
[7][10]庞薰琹.薰琹随笔[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91:63,69.
[8]庞薰琹美术馆,常熟市庞薰琹研究会.艺术赤子的求索:庞薰琹研究文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5.
[9]庞薰琹.图案问题的研究[M].上海:大东书局,1953:25-26.
[11][12][14]庞薰琹.庞薰琹工艺美术文集[M].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6:108,101,80.
[15]周爱民.庞薰琹文集[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8:26.
[16]周爱民.庞薰琹艺术与艺术教育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19.
[17]庞薰琹.论艺术 设计 美育:庞薰琹文选[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412.